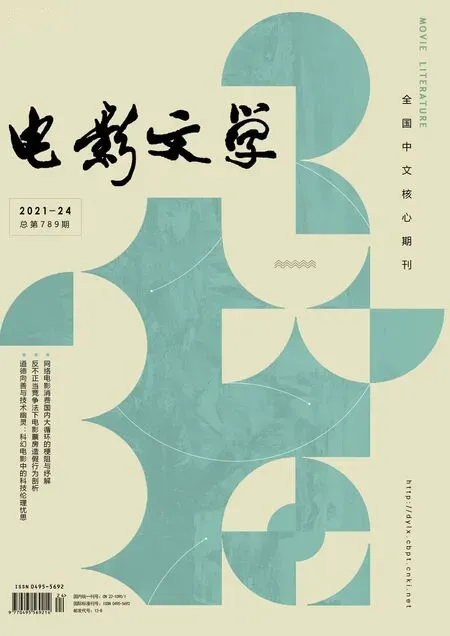西北边疆题材剧中的“怀旧乌托邦”意象
王 月
(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存在坐标上的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割裂的,两者在审美中达到完全的同一。时间艺术也展开了审美空间。”面对现代化的文化焦虑要找到释放的出口,其中一条路是指向空间,而另一条路则指向时间。社会发展太快,身体及理性被裹挟向前,但心灵却不一定跟得上城市化与技术化的速度,人就不免会向往自己曾经熟悉、适应和舒适的精神地带与想象时空。新世纪以来,以《戈壁母亲》(2007)、《在那遥远的地方》(2009)、《大牧歌》(2018)等为代表的主流西北边疆题材电视剧借助话语主体的话语实践,在边疆想象的构成中夹杂了对于旧时“好时光”的追忆,青春叙事与红色编码的心灵史被反复开启,“好时光”也催生了“好地方”的诞生——集体主义与个人生命的“黄金时代”恰与张开双臂亟待开拓的边疆热土作为某种乌托邦的时间与空间的两种维度达到同一。怀旧的集体文化心理因边疆想象而被“撩拨”和抚慰。
在时间上,剧作多定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之间,且“文革”前多为叙事重点时段,呈现了带着红色印记、理想豪情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厚重的年代感形成了该类剧作的怀旧调子。从经济角度来看,边疆仿佛代表着某种现代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起点,苦地、险境、绝域的景观不容忽视,它代表着现代性上的欠发达状态;但从心理层面来看,剧中则从空间到时间塑造了一个归宿与家园的形象,尤其是普遍的“过去”的时间定位和对过往诗意化、美化处理及深情追忆代表了创作者和多重文化场域共同的话语选择。这种选择是一种共谋,或说是不同话语不谋而合的相遇,不同话语主体和文化场域“怀”的是不同的“旧”,“怀旧”却同时满足了国家话语、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表达和价值需求,在具有强烈时间特征的空间上形成了话语的交织。
一、国家话语——以“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承载主流意识形态
剧作“身份”是决定其话语特征的重要因素,主流媒体作为阿尔都塞所说的生产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的重要载体。“火红年代”的“红色”故事因历史叙事的厚重感、英雄的艺术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本雅明)及其深入人心的前经验与前文本具有非凡的优势。
不论是解放军的剿匪卫国、来自天南海北的军垦战士的拓荒事业、雪山之巅的边防卫士感人至深的壮举,还是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号召的有志之士在农业、牧业、医疗、石油、核工业、艺术事业中的伟大贡献,其核心内容都在于:展现国家艰苦卓绝的成立和发展历程及教化人心的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崇高品质。历史往往是永久的可再生资源,在主流话语中,它的重要价值在于以真实的时间触感和时间的演进性来形成民众共同的国家记忆,从而佐证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写作过程……必定具有达成意识形态,甚至原型政治的功用。”相对于时间上的点状叙事来说,横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和包含千锤百炼历程的叙事使得政党、政权更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国家机器自然会将时代性的故事——这一重要的符号资本和文化遗产“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在电视剧已经成为红色文化的主要传播阵地之时,主流话语在电视剧中的“怀旧”是一种必然。
政治性的动机要实现于电视剧中,少不了艺术化的处理和感性的建构。多部剧作所呈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及“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曾经“悲哀的人民”由于经历了长久苦难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时代,所以有着难以抑制的捍卫和建设新生政权的激情,弥漫着一种时代性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具有恒久力量。“火红年代”的精神力量与边疆独具特色的“广阔天地”一经结合,再加上其充满潜力的处女地特征,让边疆大地成为一片巨大的共产主义热土,洋溢着掩盖不住的浪漫主义气息。这是一种与反思现代性、担忧现代文明会消解人文精神的解构和批判性质的浪漫主义不同的浪漫主义,它更多的是为阶段性的政治斗争服务、表现为“英雄主义”、泛“梦想的实现”“献身精神”等要素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主流价值观增加了感性的因素和审美的向度,从而在精神层面对民众产生有效的“询唤”效果。
二、精英话语——缅怀“精神”占据文化主导的时代
成立和建设新中国时期,万象更新,把“小我”奉献于这样的时代,是精英知识分子曾经为之澎湃之理想和义无反顾之事业。“理想”“精神”“情怀”“信仰”曾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关键词,且不管是官方还是大众都曾对这些价值极其尊重与推崇,曾是引领时代思潮的主要价值观。“那个年代”四个字,包含了家国情怀、侠肝义胆、奋不顾身和对具备远见卓识的创世英雄的想象,是一个在记忆中被诗意化的时代,被勾勒为“精神的黄金时代”,是“实用主义、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大获全胜之前”的让人深情回首的“理想”时代。
从人物上直观地看,从新世纪20年来的西北边疆题材电视剧中,知识分子的人物地位、性质及数量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去”的人物成为精英文化对自己的想象性构建。如果说在《西圣地》(2006)中知识分子还是衬托农民出身、军人和工人身份的主人公杨大水的次要人物,《戈壁母亲》(2007)中知识分子程技术员是一直被压制的悲剧性角色的话,那么到了10年后的《马兰谣》(2016),从浙大和哈军工毕业的林俊德等人就已经成了剧中的灵魂人物,《大牧歌》(2018)中上海大学畜牧专业毕业的林凡清也是全剧的核心。不仅如此,主要人物的形象、行为和语言等方式往往也投射出知识分子的情趣与风格,再如《沙海老兵》(2018)中进疆先锋队——英雄团团长在传统军人形象基础上多了一层儒士风采——会作诗,并出人意料地在迎接女兵的联欢会上娴熟地拉起了手风琴。知识分子角色的数量变多,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多精通音乐、文学,爱好阅读,语言文雅。
丹纳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黄书泉教授认为,“中国20世纪的精英文化产生、形成于近代启蒙主义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几经蹉跎,到改革开放标志的新时期重新形成自己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政治和经济双重挤压下,一方面从整体上走向社会边缘,另一方面产生分化——这一切使得精英文化已不再是曾经那样的社会精神思想的中心”。而随着科学技术与文化建设在市场经济和国家治理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国家话语、经济话语和社会话语逐渐提高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这也成为边疆题材电视剧(以及传统文化类、科普类等节目)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表述微妙变化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一。而且,在国家主流文化的保护下,这些剧都坚守了较为高雅、深刻、持稳的文化质地,没有在商业化引诱下如同一些所谓的“新红色经典”一样将人物“痞化、野化、俗化”,坚持了知识分子的审美和文化底线。
再往深处看这些剧的叙事层面。创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使命”,于是电视剧中的新疆故事选取了解放边疆的剿匪故事、支援边疆的知青故事、守卫边疆的边防故事、建设边疆的火热事业,这些题材显然都是在主流话语框架之中的。而在这样的命题框架中,精英话语也在“红色经典”的编码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允许的范畴内表达着自身的思考、情趣、集体情怀与价值观,剧中深嵌的母题包含个人价值的追寻、爱情亲情的浪漫与温暖、出发与归家的抉择、家国责任、自由与人性的坚守……这些体现了精英知识分子一向强调的“人的主体意识、自我价值,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深刻反思性、独特的审美旨趣和对终极价值等的探索在多部剧中有所体现,这就意味着精英话语在进行自我的文化表达。
相对于“当代剧”,“老故事”里有许多值得精英话语发掘的叙事资源和动人的情怀。电视剧所建构的美好的往日时光里包含着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寄托,它试图弥补物质时代与大众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文本”这一语境中知识分子淡出主导地位的失落感。其修辞策略是“火红年代+广阔天地”下的“理想”与“情怀”,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使得这种“理想”与“情怀”显出不一样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
儒家认为,君子的人生追求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也很好地总结出历代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社会理想、政治理想及至审美理想。剧中人物身处往日时光,却表达着当下精英文化的精神诉求。个人理想上:人格道德上追求完善,如栗峰一样义薄云天;人性解放,自由潇洒,如草原民族般策马驰骋;能力修养精益求精,挑战极限,实现极致的个人价值,如林俊德一样追求科学真理。社会理想上:爱情自然发生,忠诚如一,人与人不分民族,不分彼此,幼幼老老,相互守望,如入大同。政治理想上:保家卫国,建功立业,对民族兴亡、人民疾苦责无旁贷,信念如磐石般不可动摇,就如同来到帕米尔高原的援疆医生吴天云、放弃都市生活的上海知青林凡青……这样的时代和地方,还意味着审美理想的达成,自由广阔,人心纯粹,如世外桃源,指向“梦幻式向往”。复归这样的旧时光,即假想式地满足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的统一,回归知识分子极为珍视的精神、诗意与情怀。
反观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电视剧,如家族伦理剧、情感纠葛剧、青春偶像剧、商战剧、刑侦悬疑剧……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身影寥寥可数且不常成为主角。而在边疆题材电视剧中的知识分子角色,具有“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特征,朝气蓬勃,信念坚定,既有国家胸怀,又有人性情怀,这样的“笔墨”是在缅怀尊崇“精神”与“情怀”的年代,也是精英文化群体主体意识的寻回与强化。
三、民间话语——青春的生命记忆与年代感的视觉消费
对于国家话语,革命年代及昔日激情是论证政权合法性、凝聚人心、提升感召力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精英话语,以“情怀”之名为“缺钙”的时代提供思想力量,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抗。这两层话语都试图使特定历史与价值观重新“附魅”和神圣化,从而发挥出文化权力。而对于民间话语,早已盛行着浓郁的怀旧风,但它并不像前两者那样严肃,也并不试图寻找某些整体性的终极价值,其以“回忆”之名做一次精神还乡,或是实用地消费着旧时光,“怀旧”对于不同的大众群体有着不同意味和价值。
对于中老年观众,“逝去的岁月”巩固其“存在感”,在怀旧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军营生活、支援边疆的知青生活、热火朝天的集体大生产、物质匮乏但信念笃定、精神充实的岁月;老朋友、老物件、老样子、老故事;“那个年代”的“诗歌、行走、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这些表意符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曾经的生活方式和独特气质,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构成了被特定时代话语编码的“心灵史”,是不可磨灭的情结,就像汪政所说的,这类故事的生产与接受“是一部分人青春记忆的证明,犹如各地的知青饭店一样,一个人不能容忍自己的生命曾经是空白或被否定”。
电视剧的声光与叙事艺术将旧时光浪漫化、诗意化和陌生化了。如诺瓦利斯所说:“把普遍的东西赋予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这就是浪漫化。”特定的年代、旷野、边疆生活能唤醒群体的特定回忆,美化的、诗意化的怀旧仪式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电视剧对曾经的青春的描绘并不像老照片那般斑驳、晦暗,主调也更不是平凡、琐碎、悲哀与凝重,而是五彩斑斓、风华正茂的“正青春”,是一代人曾经的活力、强盛、意气风发与英姿飒爽,是儿女子孙们未曾见过的发着光的生命阶段,是引吭高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怀旧书写影响着中老年群体的社会定位与自我调适,使这一群体在大众媒体平台上提升了“存在感”。
“曾经”并不只有青春记忆,也包含对小时候、母亲、乡土、家园的怀旧。剧中的女性书写如《戈壁母亲》中的刘月季等提供了一种温柔、宽厚、包容的母体想象,激发“那些美好幸福的记忆瞬间以及值得肯定的生活细节”。而令人心神宁适的自然大地,也往往意指着精神回归的空间。
同时,在经济话语对社会整体发挥出越来越强的控制力量的时代,行为标准日趋统一与功利,中下层民众的失落感与失衡感推动民间话语“顺着国家话语对红色经典的推动”,召唤曾经的红色年代,“在一个渐趋多元、中心离散的时代,深情追忆权威、信念”。而剧作中火热的共产主义氛围为“体会着当下的失落,怀念迷失的美好”的群体提供了一个“旧梦重温”和对比当下的形象指向,旧时光、青春年代、母体、共产主义氛围等元素共同形成了一个“黄金时代”的象征空间。
对于年轻人,“别样青春”构成“复古”时尚。电视剧里有父辈甚至祖辈的“别样青春”:神圣的权威、执着与纯洁、浪漫与奇遇、励志与成功……也有童年时代的模糊记忆和对旧时代的间接的朦胧认知,这些转化为一种对陌生时空的好奇和消费,构成一种“复古”时尚。
对消费而言,影像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它能否建构出美好想象才重要。对于新生代年轻人来说,新的时代语境使其更倾向于个性化的文化,而上代人精彩的“别样青春”确实不同于今日之生活,剧作放大了其传奇性和浪漫性,对年轻人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下,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加速了民众向内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国家独特的历史进程和其中的审美与文化对年轻人产生了一定的号召力。“励志故事”、青春记忆、历史符号、边疆特有的空间震撼感,都成为对年青一代的吸引力。影像细节也可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物化消费(时尚用语为“国潮”)的引子,军装、军包、军用水壶;搪瓷缸、解放鞋、花脸盆;知青主题的餐馆、酒店、博物馆;边疆旅游体验……时间在这里既可以空间化,也可以物化、消费化。
主流价值借时代叙事与新疆影像“重返当代青年情感世界与生活中心”,精英借此影响其审美取向、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而年轻人也因为这样的叙事、符号包括相应的“消费”弥合与父辈之间的裂隙,形成代际观念与经验的交叉。
综上所述,特定时代情绪的设定,固化了西北边疆在观众心中的时间属性与年代倾向,其成为具有年代色彩的怀旧“乌托邦”的想象物。然而文化艺术层面的符码建构已然在某种程度上“现实化”与“合理化”,多元话语的投射形成了“景观”与现实的偏离。对边疆文化的“附魅”和现实的“祛魅”之间,时间的遥远化、陌生化处理与现实的真实性之间形成了某种话语的张力。未来对于边疆呈现的时间维度选择上,需要更多地反思、修正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