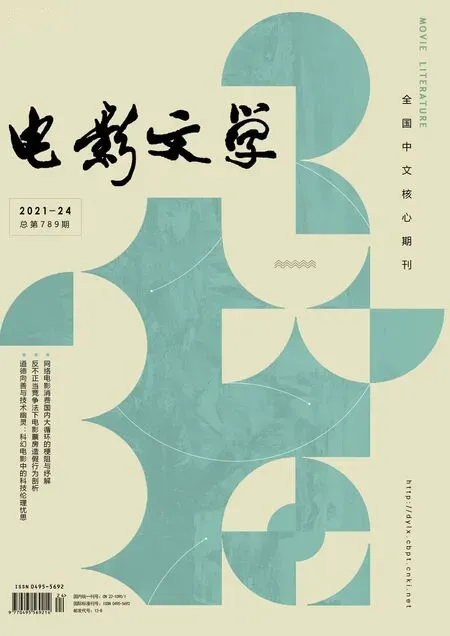道德向善与技术幽灵:科幻电影中的科技伦理忧思
韩贵东 孙欣敏
(1.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14;2.成都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面对技术化所带来的新的秩序问题,著名技术哲学家埃吕尔曾坦言:技术已成为人类必须生存其间的新的、特定的环境。它已代替了旧的环境,即自然的环境。技术成为人类肢体行动延伸范式的同时,也在某些同构化的话语语境中,以同艺术结合的形式,展示出技术背后的伦理困境。威尔斯(H.G.Wells)用“可能性的诸种幻想”(fantasias of possibility)来定位科幻:这些作品“接过在人类事务中的一些发展可能性并对它加工,发展出该可能性的诸种广泛结果”。在电影数字技术发展日益革新的语境之下,科幻电影的发展凸显迅猛的势头。回顾科幻电影的创作,从早期乔治·梅里埃的《月球旅行记》到2019年度中国硬科幻电影的奠基之作《流浪地球》,无不说明了这一问题。与之俱来的是科幻电影作为充满艺术与技术双重隐喻属性的媒介产物,自然成为人们对于影像文本艺术化的探讨焦点以及对技术问题一探究竟的关照对象。与此同时,试图从技术的角度来管窥科幻电影中所存在的尖锐的伦理问题,则成为对于影像文本中科技伦理道德约束机制现实性建构的必然选择。
斯蒂格勒的技术观念一直受到多种思想的影响,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考,到西蒙栋和吉尔的技术哲学意义,技术的困扰一直成为诸多思想家反思的关键命题。同样,对于科幻电影中所包含的科技伦理问题能否成为现实世界生活中人类所面临的科技伦理困惑,在某种意义上尽管不会绝对的实现,但正如激进左翼思想家齐泽克所说:“一小片想象,但经由它,我们获得进入现实的入口。”这意味着,对于科技伦理现实性的问题症候,首先要界定科幻电影与现实维度的关联性,即其与现实之间既构成了某些导向性的问题可能,也在其本质上脱胎于现实伦理的想象与勾勒。毕竟科幻电影“构建了一个框架,通过它我们将世界体验为连贯与有意义”。此种特殊的技术与艺术、现实与想象联结路径,则为我们有针对性地在人类想象力生发的存在之思中,发现当下或者未来诸多科技之中的伦理焦虑,以防患未然或警醒世人。纵观当下科幻电影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不仅影响了科幻电影中主题内涵的表达,同时对其作品背后映射的现实道德建构意义也是巨大的。对技术极端发展中所面临的道德危机,人性迷失以及技术批判进行反思,展现技术向善与负责任创新的诉求,一言以蔽之,即如何在科幻电影技术化的路径中,探讨技术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及其本身所蕴含的伦理倾向,则应该是科幻电影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对科幻电影的文本关照之外,更需要引起人们所思所想的则是科幻之中技术背后的哲学困扰以及伦理倾向,并关注由此而派生出的集中、激烈、尖锐的伦理道德关照点。
一、去伪存真:科技伦理问题的现实可能
毫无疑问,国家技术的发展与科幻电影文本最终呈现的技术典型是有密切关系的。现实技术的应用不仅为科幻电影的发展赋魅,更得益于科幻影像文本中的技术想象,为人类生活所带来的技术幽弊预警。科幻电影的一个内核,便是“未来主义”(futurism)。这种对人类生活中所可能发生的基于技术所生发出的伦理选择性问题,在科幻电影的角色行为刻画中显露无遗。
从异形出现到人工智能、基因改造人、逆熵人、赛博格世界,“忒修斯之船”的悖论故事似乎早已变成现实,并引发诸多与之俱来的技术恐慌。一系列技术问题的困惑摆在伦理道德的面前。这些科幻的技术想象力如此之丰富地为观众建构起一个“未来主义”与“恐慌格调”兼具的影像景观,是否也意味着这些惊悚的技术想象仅仅是主观性的思考表达,并未对现实造成可怕的推测?从拉康主义的观点来看,此种态度与视角显然是值得商榷甚至是否定的。科幻电影之中的科技想象,让人们短暂逃离“现实世界”的同时,进入技术想象的“非现实”之中,却恰恰以想象的“未来主义”让现实生活之“现实性”变得更为现实。当下现实生活中诸多的技术问题被加以过滤或者遮蔽,留给我们的只能是“望技兴叹”的不知所措与技术遭遇之下的无可奈何。面对此种问题,科幻电影有力地刻画了技术性同现实社会性、群体性之间的对抗关系,重新将人们的现实遭遇与选择串联起来,赋予人们技术主动权。而技术背后的伦理向左走抑或向右走则成为观众影像观阅后的行为选择示范。伦理的选择意味着技术困境背后之“爱”,正如齐泽克所言:“是一个关于真实的不可预见的回答:它从‘无处’(nowhere)出现,当我们拒绝任何指引与控制其进程的尝试之时。”从具有“救世主”般的“爱”到技术伦理选择中的“爱”,恰好将科幻电影中科技伦理的意义加以诠释并指明科技伦理的发展方向。
当我们翻开世界电影史册,在科幻电影的类型发展中,新旧好莱坞、各种先锋主义、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电影浪潮的交替出现为我们呈现出了在历史性叙事之中的诸多科幻典型。伴随着技术化电影的迅猛发展,也将科幻电影中的伦理问题为我们一一呈现,从生物技术、温室生态、人工基因编辑到预测性警务、面部识别、社交媒体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AI的具体应用。这些新兴技术的出现,也正向我们提出了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
二、道德困境:科技伦理的问题导向
科幻电影中的科技问题为伦理的选择指出了具体道德困境的意义,即引导或指正生活中技术的多重可能性。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如何通过科幻电影别有意味、极具指示含义的影像艺术形式,表现出科技背后的忧思,促使科技工作者或普通大众具备科技伦理的意识,才是其背后的重要考量。海德格尔曾说:“从‘我思’出发,人和世界就分裂为二,这必然导致主体性的极度膨胀,把人当成控制存在者(亦即客体、对象)的尺度和中心,成为判定存在者之存在的法庭,从而开始了人对世界的征服进程。”人类自身欲求的无限制增加和技术使用的泛滥与过度依赖,促使当下诸多问题如阿喀琉斯之踵一般困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阿尔贝特·史怀泽在有关“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中指出:“伦理学如果只是人与人的关系,那是不完整的……当所有的生命,不仅包括人的生命,还包括其他一切生物的生命,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时候,才是伦理的。”而面对科技伦理中的基因编辑问题,1993年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则为我们展示了技术滥用背后灾难性的生态困局,并在技术欲望的伦理控诉中透露出时代理性的呐喊。出于欲望与名利的追求,影片中的主人公约翰·哈蒙德博士试图通过基因编辑建造出最成功的恐龙主题公园。电影之中,观众看到了强大的基因工程,复活灭绝物种灾难背后那些荒唐而短视的人性弱点问题。影像以跨时代的意义,对不计后果的研发新技术的行为提出了伦理警示,并赞颂了自然界的美好,以此来展现出了人类与自然界环境之间应该保有和谐统一的伦理关系。“丧钟为谁而鸣?”在电影上映数年后的今天,人类依旧贪婪地使用一切技术来行使所谓“引导自己走向美好生活”的权限。“切尔诺贝利之殇”,不仅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事故,更是在无数个科技造就的神话面前,经不起推敲的一次人性伦理实验,其结果无异于作茧自缚。
从罗兰·艾默里克导演的《哥斯拉》开始到今天改编、翻拍依旧在院线上演票房神话的亚当·温加德版本的《哥斯拉大战金刚》,充满贪婪与欲望之心的人类组织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最终却仍旧让我们反观电影中人类本身有违道德伦理的生态悖论以及出于自我保护而人造“机器哥斯拉”的伦理道德怪圈。其根深蒂固的思想不是“和谐”的生态观,更像是满足自我私欲的“征服心”。罗尔斯顿坦言:“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的角度,生态系统的美丽、完整和稳定都是判断人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自然界在漫长的自我进化中,始终是以守恒的自然规律为依托,在这层意义上任何主观性的利益行为均是以打破自然世界平衡为前提来牟取暴利、满足私利。也就在原本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中,由于某些人为的干预酿成了最终的生态悲剧。此类案例不胜枚举,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喟叹于生命例外状态之下的人类群体之痛,更像是不计后果摧残自然自我演绎的结局,结果固然痛心疾首,但经自我审视之后,根由依旧是伦理选择的困局。从这个角度而言,《侏罗纪公园》《哥斯拉》《哥斯拉大战金刚》等一系列基于环境生态或是基因编辑而言的科技背后伦理则成为人类生活的“警世通言”与“喻世明言”,让人类反思自我行为的同时,为人类生活行动发出预警信号,无异于提供了一种结局性的道德审视与伦理思考。
三、“道”技之魅:技术背后的伦理选择
“具有人类心智属性的计算机程序,它具有智能、意识、自由意志、情感等,但它是运行在硬件上,而不是运行在人脑中的。”人工智能技术显然具备类人化的特征,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体与人体也构成一种差异化的实存,其虽由人类发明却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具备自我辨识的主体意识。一旦人工智能体在技术异化的环境中,出现自我的意志,很可能伴随技术的过度使用而出现难以管控甚至僭越人类行为主体的伦理观念变化。这种合理化的科幻影像想象均展现出了现实问题中的技术伦理病症,正如2021年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中阿派克斯公司酝酿许久的阴谋,即所谓以保护人类自我为目的制造出基因克隆后的“机械哥斯拉”在最终电影程序控制失控的条件下,其不仅将阿派克斯的BOSS一网打尽,更是丧失理智开始毁灭性地破坏人类世界,与金刚、哥斯拉展开大战。这种科幻电影的视觉呈现不是突破边界漫无目的地放飞自我想象意识,而是为我们确证了人工智能背后的现实伦理问题,即“人”“机”关系矛盾等错综复杂的困扰。
人类试图对自然界完成主宰式的控制,对于自然的人为干涉已经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后果,“这类干预的结果将是难以预料的”。在人类对自然资源大肆攫取与争夺的同时,以技术为主导的人工智能体不断投入新的实验中;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则使得人工智能伦理的问题成为现实的焦虑。
人工智能背后的伦理幽弊,不仅是这几年科学家空想的结果,更是早在现实人工智能技术之前,就已经奠定了技术背后伦理选择的基调。2002年由21世纪福克斯影业制作的电影《少数派报告》,为我们呈现了AI人工智能预测技术在判断人性“好坏”方面的诸多伦理问题。影片中基因变异的“预测人”能够预测犯罪,执法部门据此提前逮捕有可能犯罪的罪犯,但这套系统并不如人们料想的那么可靠,因此而引发了诸多的社会乱象并造成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影片中展现的许多技术推动了现实中的技术创新,但并未完成科技伦理之中“负责任的创新”命题,因此造成了技术使用背后道德边界被打破的结果,并且其基因变异的“预测人”属于艺术想象中合理的“科幻”成分。诚然,影片呈现了在预测、履行犯罪动机方面的难题。与现实世界相比,在人类今天生活中的技术如AI人工智能、大数据天网等,则更有可能解决这些难题。影片在展现技术发展时,也为我们提出了“负责任的技术创新”的科技伦理观点。
人工智能体与人类之间,在“人”“机”关系的命题中倘若难以达成平等一致的关系权限,是否会产生人工智能体对身体行为的超越抑或是侵害,这本身就是一个伦理选择问题。本质上来讲,人工智能体由人类设计师设计完成,当然带有人类道德伦理的标准,因此,“智能体道德根源于人类伦理体系”。但是,尽管人工智能可以以人类的道德伦理完成自我约束,是否就代表所有的设计工程师可以在程序开源的关节上从善负责?如果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偏见和智识的了解不断深入,甚至可以为了自身利益操纵人类,这又将为我们带来何种困境?曾在2014年上映的科幻电影《机械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视角,同时帮助人们思考未来科技发展的一种可能性。一位自私且操纵欲强的成功企业家创造出一个智能机器人。机器人通过大数据芯片的预设,学习人类行为及思想。随后企业家惊讶地发现机器人开始违背他的意愿,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人工智能学习、模仿人类,但同时并不会局限于人类自身认知偏见以及负面价值观。电影引发观众思考如何防止人工智能利用人类弱点与人类为敌。而这其中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2019年中国科幻电影扛鼎之作《流浪地球》如出一辙。
《流浪地球》作为中国硬科幻的代表作,其意义与价值往往被指认为是电影技术化革新的代表。既然有其技术化的运用,自然存在技术背后伦理反思的可能,“在‘人’‘机’关系空间生成的同、异质场域中,人工智能形式化指向与意向性生成机制就成为其技术问题背后的现实伦理焦虑”。电影的成功不仅反映出了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趋势,更展现出了中国硬科幻的技术思考,尽管电影并未彻底实现在影像故事冲突与视觉景观建构上“大快朵颐”的审美接受可能,却将中国硬科幻中对于自然界生态规律平衡的议题,以东方文化语境的思维加以探讨,完成了基于中国电影工业美学之中的故事生成。并“在对人性的‘我思’之中逐渐展现真理去蔽的真情内容,执着于艺术化的审美与哲学化的物我思考”。从而开启了建构中国式科幻电影大幕的序章。
进一步而言,科幻电影的内容表达不单是视觉影像文化的营造与体现,更是将艺术创作者内心中的伦理思辨加以探讨。科幻作家与科幻导演在小说文本以及电影创作中,均有差异化的伦理体验,也就意味着时代发展中的伦理问题以文学艺术化创作的方式加以放大。尤其是将现实生活中人的“利欲之心”与“理性思考”相对立,以一种有解的“悖论”形式向读者或观众加以呈现。尤其是在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伦理探讨,往往是将“人”“机”关系问题以二元对立的矛盾形式具象化地说明,在文学与电影的主题中体现“和解”的可能性。
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体身份往往是从“被制造”到“服从命令”再到“自我意识觉醒”等经过一系列阶段性变化可能的。这种AI的角色大都是科学家内心功利心的产物。而其对于主、客身份的迷失以及确证过程,即是在场者与他者身份的思考。归根结底,如若赋予人工智能体以人性的情绪审美与思考感情,则意味着人——本身主体身份的僭越与丧失。但从某个层面而言,给予人工智能体以功能价值的人类本身是否又可以寻求到本我主体的位置,而不是利欲遮蔽的异化表现,这是值得警惕的问题。电影《流浪地球》中导演郭帆做了一次有意味的艺术与技术形式探讨,他将充满技术功效与人体意识思维的MOSS,放置在电影的角色行为选择之中,即MOSS本身是人类科技的智慧凝聚体,作为智能化的客体存在,它是整个火种计划的具体执行人和监控者,这一人工智能体原则上是没有感性可能的,唯有理性的算法命令执行,毕竟其背后担负的是整个人类转移的使命。但是电影中颇有意味的冲突正是来自电影主人公刘培强中校以个人主观情感化的行动,将MOSS这一充满理智的AI执行者加以毁灭。这种戏剧化的“人”“机”矛盾处理,让电影中的这句台词发人深思,即“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确实是一种奢求”。俄国科学家维尔纳茨基和法国人类学家德日进认为:“人生活在由人工创造的文明世界中。”而我们不难发现,AI人工智能体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无论怎么去革新,其都充满着人类主体的标签与表现,实际上正是人工智能伦理中二元对立的“人”“机”关系问题,其讨论的背后恰好是关于人类自身命运的伦理忧思。
四、负责任之善:伦理坚守的原则
将《流浪地球》称之为中国硬科幻电影元年开启的奠基之作,得益于《流浪地球》在“硬科幻”作品的技术创新与艺术文本的兼顾之中达到了有效统一。而我们细数以往的“华语软科幻”电影,实际上也呈现了诸多的伦理道德焦虑。这其中既有社会伦理、家庭伦理的问题,也出现了生态伦理与医学伦理的矛盾争议点,而与此同时,这些华语科幻的伦理共性则具体指向“负责任的道德向善”这一伦理的原则。
科幻电影对于“社会伦理”的具体想象表现在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展现科幻电影中人物的情感意志,人生观与价值观等,来展现诸多的道德评判。在华语科幻电影的创作案例中,就有许多展现社会伦理层面的优秀作品。这些电影试图通过故事的讲述与典型人物的塑造,来为我们呈现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毋庸讳言,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是众多的,从家国同构的理论到王阳明的“一体之仁的大我生命观”,皆体现出了家国共情的伦理情怀,因而早期的华语科幻电影中,将科幻的标清外化为一种糖衣,而其内在的药用机理则是我们普遍具有的社会情感观念与具体的责任伦理。
香港导演泰迪·罗宾在1987年拍摄的影片《卫斯理传奇》,以追查“龙珠”作为主要的叙述线索,通过对“龙珠”这一道具的使用,讲述了外星人将太空船启动器遗落在地球的故事。而影片也围绕着卫斯理这一主人公在与黑帮团伙争夺“龙珠”的具体事件中,塑造了充满社会责任伦理情怀的人物角色。显然这部影片是具有时代特色的,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而黄建新导演在1986年所拍摄的科幻电影《错位》,就已经将机器人的人工智能叙事放置在特殊的时代之下,影片将虚构的科幻想象与现实的生活相结合,以一种针砭时弊寓言式的影像风格,表现出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批判意识。以对社会现实发展的某些具体批判,来展现对于社会发展、生活变迁中人们欲求增减的责任关怀。
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责任理念影响深远,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曾把“人类家庭”当成是一个微观的伦理实体存在。因而在国产科幻电影中的家庭伦理问题就成为电影创作者置入在电影中的规范准则。不仅是华语科幻电影对于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放眼到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都可以看出对家庭伦理的问题探讨是十分普遍的。杨小仲导演在1938年所拍摄的科幻电影《60年后上海滩》,以科幻电影的讲述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在中国传统伦理视野下与“家”有关的故事。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但生活放纵,岁末除夕夜之时,两人寻欢舞场,后被妻子发现,便萌生了改造家庭、变换世界的想法。从故事的预设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造家庭的想法正是影片成为科幻电影中探讨家庭伦理问题的剧情标配。而同样因为技术的问题,这部电影也成为软科幻之中,将科幻或奇幻色彩一笔带过,而重中之重则是探讨家庭关系缓和与否的伦理主题。与早期华语科幻电影所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国产科幻电影在展现家庭伦理问题时,更多的是将“中和之美”的温情探讨为观众呈现出来,在对现实主义美学接受的基础之上,将时代精神内涵与传统文化的批判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了家庭之中的父子或父女的关系问题。电影也常常借助儿童视角,为我们展现出童真、童言之下的家庭矛盾。例如1988年导演宋崇所拍摄的科幻电影《霹雳贝贝》以及周星驰导演在2008年拍摄的《长江七号》,这两部电影都以儿童科幻片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内心的孤独与周遭关系的矛盾。在处理父子关系时,更为我们增添了诸多现实主义的温情关怀,从而呈现出了亲情之间的伟大。这与《流浪地球》之中刘培强中校与儿子之间成长关系的矛盾设置也是不谋而合的。如此看来,华语科幻电影中,对于家庭伦理责任问题的探讨往往是必然的,也能够通过电影的视觉想象为现实生活提供更多的伦理关照。
康德说:“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的人格中的人性和其他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仅仅看作是手段。”人既然作为目的,而非手段,自然应该以人的完整作为日常行为的参照标准。在华语科幻电影的发展中,对于人类生老病死的医疗问题也表现出了东方化的伦理视野。近几年对于电影中的医学伦理问题,已经引发了人们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再思考。例如在2005年获得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由导演亚利桑德罗·阿曼巴执导的电影《深海长眠》就将“安乐死”这一医学伦理话题放置到了观众的关注视野中。而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可以造福人类社会,同时也因为其技术的发展使得贪图权欲的不法分子通过医疗技术而牟取暴利。当我们在探讨人类生存的终极命题——生与死的存在状态时,医学伦理便成为不可不说的伦理议题。在华语科幻电影中探讨医学伦理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作品,通常是可以引发人们深思并由此思考医疗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是否剥夺了生死的权利。1991年由张子恩导演的电影《隐身博士》就为我们展现出了医学技术日益革新的前提下,所引发出的诸多社会生活乱象。借此,可以看出生命价值指出的道德伦理显然成为医学生命伦理遵从的最高标准与范式依据。在科幻电影中对于医学伦理的探讨,不应该只落实在影像的虚构中,还应当放置在现实生活负责任态度的医患关系中。
环境伦理或称之为生态伦理,其指向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伦理道德关系的属性之上,当然,环境伦理问题确证了人与周遭世界尤其是自然界与自然物之间的道德标准与道德框架。也就是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纳入了伦理问题的讨论之中。毫无疑问,人类作为自然生态这一系统整体存在的部分构成,而自然生态也成为人类自身存在的具体条件。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道德关怀,从最根本上来讲,即是对我们人类自身伦理规范的要求与关照。1990年由导演冯小宁所执导的作品《大气层消失》以及2016年周星驰执导的《美人鱼》,则通过对工业化的景象设定,展现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对于生态资源过度开采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污染问题。影片也表现出了导演对于人类生态破坏的批判性思考,控诉了为既得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的非人道行为,对于无视生态发展关系的人进行了谴责,同时也表现出了影片对于生态伦理的探讨。对与人类相伴的生态环境资源大肆攫取与无底线的毁坏,只能使人类最终走向丧失自我意义与存在可能的绝境。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共生”的伦理原则,则为我们在称赏科幻电影之余,提供了更多的生态伦理想象和审美期待。“负责任的向善”并非一味地只照顾到“善”的缘起,而忽视具体个人的责任担负,这是双重命题中的双向选择而非单向度的现实臆测。科幻电影中的科技伦理不单是负责任之善的表现,更是现实伦理问题的新面向。
五、人的“目的”与“伦理”责任
对于科幻电影的关照,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既定的影像艺术想象视野之中,更应该对科幻电影创作与探讨中所涉及的具体科技问题提供一种合法性的伦理道德约束机制。即一种“为人之目的”而参照的“负责任向善”的标准。马克思·韦伯在1919年曾经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必须明白,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地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当然,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探讨,则成为科幻电影情感诉求背后伦理道德选择的一条路径,正如海德格尔“人充满劳迹,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的“喻世明言”一般,借以期待充满“人文主义”关怀与“技术诗性”关照下的科幻电影继续走向伦理选择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