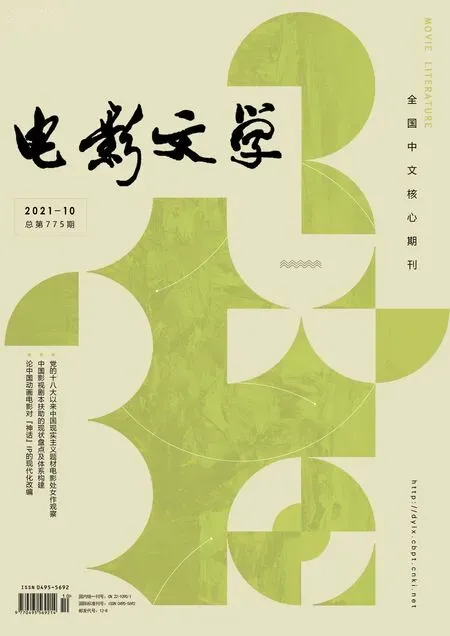数字技术时代影片《一秒钟》的文本意味
(1.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3.安徽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影片《一秒钟》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张艺谋献给电影的情书”,“情书”这一极具私人性质的情感告白方式被张艺谋用来向电影示爱,这既是为影片进行商业宣传的噱头,又似乎在向观众暗示,这是一部属于他的私人电影。正是缘于对电影执着又狂热的爱恋,他不甘心胶片时代的悄然退场,他要坚持以电影的形式与之告别。毋庸置疑,电影是最适合发挥张艺谋才华的艺术载体,正是电影让他名利双收,享誉国内外。当然,张艺谋也让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了国际影坛。相互馈赠与相互成就的张艺谋与电影之间俨然成为彼此生命里最完美的相遇。
影片《一秒钟》作为张艺谋向胶片时代的致敬和告别之作,故事内容简单平实,主要人物少,人物关系也不复杂,场景设置集中,加上张艺谋名曰“返璞归真”的影像风格,使得这部电影在当下凭借数字技术不断建构多元视听奇观的影像世界中显得相当突兀、不合时宜。英国文学理论家克莱夫·贝尔认为,“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也是独特的性质,就是传达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有通过简化手段,艺术家才能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没有简化,艺术不可能存在。”基于此,我们将探讨影片在看似极简的艺术形式表述策略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文本意味。
一、数字技术时代:影片的“出场”意味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数字技术,经过短短几十年的革新与发展,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娱乐等社会活动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随着5G时代的到来,其高速率、低时延和广连接的特征,使得VR、AR等数字技术进一步升级,这引发了传统电影从创作模式到制作、传播与接受流程整体的深度变革。电影由胶片时代记录和再现现实转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使得“想象创造想象”“电影创造电影”成为未来电影发展的新模态;电影创作者身份由专业转向业余,影片中技术叙事日渐常态化,影像流的超时空生成及迅捷传播,消解了电影的仪式感和神秘性,数字化编程技术使得人人参与、融入和改写影像,成为一种现实、一种游戏,电影与非电影的边界模糊;日益多样化的新媒体平台去除了往日电影院神圣的光环,观众不仅可以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屏幕上看电影,而且可以任意手控影片播放进度,随时参与互动评论,观众主体性意识与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网络短视频的大量涌现,深得大多数年轻观众的青睐,传统电影观众群体发生分流。伴随屏幕的分化和裂变、内容的芜杂与文体的解放,视觉文化中电影主流地位渐趋瓦解,这些都促使电影理论界、业界人士再度反思“电影是什么”“电影将会成为什么”这些事关电影本体论的命题,由此也引发电影艺术地位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电影已死”“电影之死”等各类有关电影终结论的宣言以及“后电影”“互动电影”“反电影”等各种新概念在新世纪以来频现不止,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电影之死》一书的扉页上写着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一句话:“大创造者亦即大毁灭者。”这意味着人们对数字技术的迷恋,杀死了胶片。而胶片,一直是迷影人虔诚膜拜的电影物质载体。因此,马丁·斯科西斯在给该书作序时,认为“保持原汁原味的电影体验和留住电影的手工艺感,数字技术并不足以取代胶片库,不过要使电影每一幅画面恢复最初的光彩,数字技术肯定是大可借助的”。他呼吁人们采取实际行动来保护和修复胶片电影。正是基于同样的“胶片情结”,影片《一秒钟》成为张艺谋“心心念念很多年一直想讲述的故事”,“我永远也忘不了小时候看电影时的情景,那种难言的兴奋和快乐就像一场梦”。因此,“胶片”和“看电影”成为整部影片的主体情节建构。
二、“胶片”和“看电影”:影片的主体情节建构及其意味
影片不仅赋予“胶片”普通的道具功能,和“松花江牌5501型固定式放映机”“汽车”“摩托车”“疙瘩棉袄、棉裤”等一起还原、再现了那个时代面貌,而且担当着重要的故事角色和情节叙事功能。“胶片”既是三位主要人物相识、相互缠斗的主要缘起,也是推动故事情节进展的重要“抓手”。影片基本上围绕着“偷胶片”→“夺胶片” →“毁坏胶片” →“抢救胶片” →“放映胶片” →“馈赠胶片” →“遗失胶片”线索展开。其中,村民抢救胶片属于重头戏。影片用相当长篇幅浓墨重彩地呈现村民抢救胶片的过程,范电影作为这场施救工程的主持者和领导者,极尽发号施令之威信。他指挥村民回家取床单、洗脸盆、筷子、蒲扇等工具,然后用床单传送,用筷子捋平,用蒸馏水擦拭,再用蒲扇轻摇徐风吹干。这段影像过程既用大量细节来凸显修复和保护胶片的专业性,又极具仪式感、浪漫化和奇观化。“胶片”在张艺谋电影中似乎重新“复活”了。生命鲜活的胶片电影能够给予身处物质、精神双重匮乏年代里的观众带来多少企盼和娱乐享受?张艺谋接连编排了“放电影”和“看电影”两场重头戏。在他的记忆中,儿时放电影、看电影的场景始终让他魂牵梦绕。特别是电影正式放映前,放映员开始对光时,那是全场观众沸腾、欢乐的高光时刻。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追逐着那束光进行个人化的狂欢活动。正如张艺谋所言,人们等着电影放映的心情甚至比看电影时还要高兴。即便是人们看了很多遍的电影《英雄儿女》,每当影片主旋律响起时,大家还会不由自主地一起激情澎湃地颂唱……观众看电影时几近迷狂的陶醉神情简直令我们震撼。
然而,对于影片的三位主要人物而言,电影于他们的意义似乎不在于娱乐——劳改犯张九声舍命追逐胶片的动机在于想看《22号新闻简报》上一秒钟的女儿影像,假小子刘闺女拼命抢夺胶片的目的在于给弟弟做灯罩,放映员范电影费尽心思指挥村民抢救胶片实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和特权。虽然他们对电影本身似乎没有表达出太多热爱的情感,但电影于他们却属一种精神寄托或言生存之根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片《一秒钟》围绕着“胶片”展开故事不但建构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电影之间不同寻常的情感关系,而且用张艺谋一向娴熟驾驭大场面、擅长建置群体主义美学场景的影像奇观向我们呈现了电影在那个时代的多重意义与特殊地位。在张艺谋看来,“电影能吸引观众的还是写人,关于人的故事、人的命运。就在人上下功夫,而技巧和技法只是配合这点”。“我觉得电影其实就是抓情感”;“情感是最重要的,无论哪个历史阶段,无论故事是什么样的,人物的情感是最打动人的。我们今天的技术可以说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一个作品、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故事传递出来的情感,这是我们永远要看的。”基于此,我们发现,影片《一秒钟》某种程度上正是张艺谋针对数字技术时代电影的发展现状、困境及未来趋势做出的个人创作反思和探索。他用近乎四十年的电影创作实践告诉我们,电影还是要将镜头对准人和人的情感,这是讲好故事的关键。这种带有电影本体论探索色彩的创作实践,使得《一秒钟》具有一种自觉的电影“自体反思”意味。
三、作为媒介与艺术的电影:影片的“自体反思”意味
“所谓‘自体反思’,指的是电影史上那些具有媒介自省意味的影片。”这类影片都是关于电影的电影,有论者又称之为“元电影”(Meta-cinema),“元”即是“自体反思”之意。“元电影将电影自身作为对象,标示了一个内指性的、本体意识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射的电影世界,包含着对电影艺术自身形式和构成规则的审视;包括所有以电影为内容、在电影中关涉电影的电影,在文本中直接引用、借鉴、指涉另外的电影文本或者反射电影自身制作过程的电影。”影片《一秒钟》作为一部典型的元电影,着重从两个层面对电影进行了“自体反思”。
一是作为媒介的电影,主要反思它的存储、放映与观影机制。作为电影的存储物质载体,胶片虽然在张艺谋电影中获得了生命般的存在质感,但影片在具体的故事情节展开过程中体现了它容易损伤、褪色、卷曲、不易保存等脆弱的特点,较之数字电影,胶片电影无论存储、运输还是放映起来都非常消耗人力物力。因此,历经百年之久的胶片时代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但电影会伴随我们一生,电影会以新的技术形式存在,它始终会存在。”由此,我们发现,基于特定技术形态存在的电影媒介自身有着客观发展的生命史,这与现存的电影历史形态完全不同。对于我们熟知的电影历史,澳洲电影档案保护专家乌塞给予了激烈的批判:“电影没有被当作一种历史客体对待……从来没有一种编史方法能够让电影充分地自我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张艺谋以其敏锐的艺术家眼光引导我们怎么“看”电影历史,如何去应对数字技术时代不绝于耳的有关“电影之死”的言论是颇具现实意味的。
二是作为艺术的电影,主要反思电影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影片不乏浪漫化地塑造了那个时代群体观影的仪式感,充分表现了电影在胶片时代的意义与地位。它不仅担当着娱乐、政治教化的功能,甚至还是人的生存之道和精神支柱;通过讲述一个关涉父女亲情的故事,彰显出胶片电影的美学特质即是“忠实地记录与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片《一秒钟》不仅意味着电影是一门让“时间”变得可见的艺术,也是一门让“爱”变得可见的艺术。影片中最令观众动容的一个镜头——《22号新闻简报》播放完一遍后,范电影对着正背朝自己观看电影的张九声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怎么样?看到女儿了吧?”张九声猛一转身,我们看到了一张泪流满面的脸。这里,爱,虽于无声处,我们却清晰可见。值得体味的是,为了让父女之爱的清晰度更高,影片通过直接引用电影《英雄儿女》中“父女相认”的经典情节,对既属观众又是片中人物的情感进行再度强化塑形。“父女相认”的催泪场景不仅令硬核执法者即农场的保安热泪盈眶,而且直击捆绑在一起的张九声和刘闺女的情感软肋。他们的眼泪意味是多重的,他们既为影片情节所感动,更为自身未完成的“父女相认”仪式而悲痛。尤其于张九声而言,劳改犯的身份不但间接导致女儿的意外死亡,而且即便女儿有幸还活着,她会愿意与这个父亲相认吗?(张艺谋电影《归来》中的父亲本可以归来,却因亲生女儿的告发而终将无法归来。在那个政治立场与利益可以凌驾于个人血缘伦理情感之上的时代,张九声的情感焦虑与缺失是鲜明可见的。影片通过“文中之文”的互文形式不仅让人物情感表现极具张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过去和现在的联系,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迁,父女亲情恒存。
互文作为一种文本记忆自身的方式,使得每一个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其他文本的痕迹,但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对话而非简单地相互复制与模仿。法国文论家蒂费纳·萨莫瓦约指出:“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地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基于父女关系的建构和情感体认,《英雄儿女》和《一秒钟》之间构成了互文性关系,但旧文本父女情感走向是饱满和丰盈,新文本父女情感则趋向缺失和虚无。这种逆反式互文手法无疑将影片《一秒钟》中父女之爱的情感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最大强化。
电影史上,通过讲述有关爱的故事对电影进行“自体反思”的经典影片,还有美国的电影《雨中曲》(1952)和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1988)。不同于影片《一秒钟》展现父亲对女儿的亲情之爱,这两部影片着力表现的是男女之爱,他们不仅深爱电影,而且电影也是他们彼此相爱的“触媒”。对于电影与爱之间的关联,法国早期的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认为,“对于电影来说,热爱人是至关重要的。……电影是名副其实的爱的艺术”。当代的阿兰·巴迪欧更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爱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指出“在爱与电影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密关系。……电影的运动来自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人类之爱永恒,作为表现爱的电影艺术也会生命之树常青。
由此可见,影片《一秒钟》通过电影作为媒介和艺术两个层面对电影自身进行了深度反思。技术是电影作为媒介生存的物质载体,人类新旧技术形态的发展与嬗变必然带来电影物理生命的兴衰过程。尤其是每一次新科技革命,必然带来电影在视听效果方面的跃升。不断制造影像奇观,让人们逃避现实世界,这似乎正是电影的娱乐本性。但娱乐不是电影的全部,正如电影学者贾磊磊所言:“在创作理念上,如果仅仅把电影作为一种‘视觉的盛宴’来营造而忽略对其精神品格的建构,那将是电影精神的退化”;“电影最终还是反映人、表现人的,数字技术只有在丰富和强化表现人的情感世界时才是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影片《一秒钟》从电影作为艺术层面的反思,强调电影关注人与人的情感对当下数字时代的电影发展现状是深具批判价值与启示意味的。
张艺谋拍电影,一直在官方审查、自我表达与打动观众三者之间倾力权衡。出身农民的他深具务实的精神特质,认为影片通过官方审查是实现自我表达的前提和基础,而让观众心动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和精神动力。在考量如何打动观众的问题上,他觉得让影片“好看”是关键和前提。也许,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学界批判他近乎四十年的电影创作存在“形式创新有余而叙事不足”缺陷的主要缘由。但倘若以此观照影片《一秒钟》的形式表述策略问题,情形似乎有所改变。
该片在内容上仍然没有脱离叙事不足的窠臼,特别是对于人物情感的起伏变化缺乏必要的烘托和铺垫,但是在形式上也没有一味地标新立异。影片既没有高饱和度的色调,又弃用了烘托情感氛围的音乐,视听效果上可以说简化到了极致。这对正凭借数字技术不断强化电影的奇观性本质、不断探索未来电影创作新的可能性的数字电影而言,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反讽意味。数字电影依凭数字技术不断“再生产”和“再建构”现实,确切地说,数字技术在终结胶片电影的同时,也基本终结了现实。尤其是以数字特效为支撑的数字电影不断强化着观众的视听感官欲望,人的情感和理性智慧却被严重弱化。史可扬教授指出:“数字技术所制造的‘数字影像奇观’不是电影的艺术本性,……它永远不可能代替形式中的‘意味’。”基于此,张艺谋以个人的青春记忆与怀旧情绪作为影片《一秒钟》的主要视觉表征和重要精神向度,对电影进行自体反思颇具现实启示意味。影片在看似极简的形式表述策略背后包蕴着较为丰富的文本意味。应该说,这既体现了张艺谋作为专业电影人的敏锐度,又再次表征了他的电影艺术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