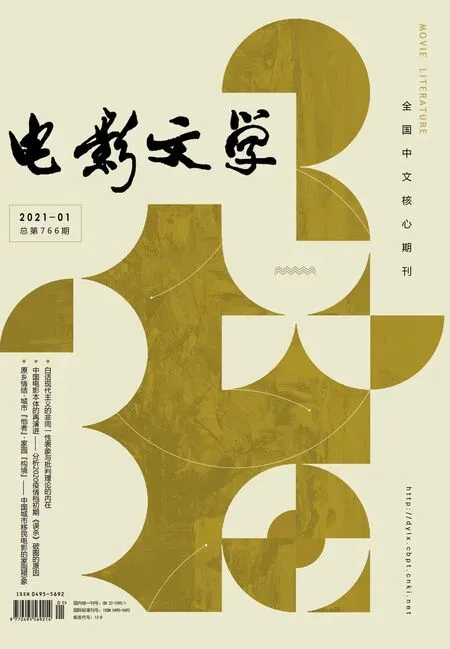费穆《小城之春》创作上的现代性指向研究述评
杜娟娟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一、民国电影的现代性品质
相对中国电影史上其他时期电影而言,民国电影可以说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首先,就发展过程来说,它是中国电影的开端;其次,在历史文化意义上它又处在这样一个分界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技术与观念、理性与未分化——的撕裂状态。它的呈现状态必然是既传统又现代,既具有西方的理性精神,又保有东方的文化氤氲;既是科学的、技术的,又是文化的、艺术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也就是早期民国电影创作时期,电影创作对传统戏曲、戏剧以及文明戏的依赖性很大,有很重的模仿、延伸痕迹。这一点,无论从题材的选择、表演上动作与对白的程式化还是舞台布景的“戏剧性”上都可以看出。选择费穆的《小城之春》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其一,《小城之春》创作所处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是民国电影发展的成熟时期,电影创作上已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与初期电影创作大不相同;其二,在视觉造型与艺术本体性的探索上,《小城之春》呈现出独有的既现代又本土,既“扩张”又含蓄的品质。基于此,本文选择这一论题来进行拓展研究。
本文将研究主题集中在“现代性”上。“现代性”不同于“现代”,也不同于“现代化”。 要了解“现代性”,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现代”。现代不是一种时间概念,不是古代的延伸,而是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生存样式和品质”。这种“生存样式和品质”体现在社会和思想结构的方方面面,并最终锐化为“现代性”这一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品质。国内对现代性论述最为中肯的是学者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刘小枫将现代性的品质特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政治上的民主法权国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法权上的世俗—人本自然法,知识学上的意识历史化原则,精神上(艺术、哲学、道德、宗教)的非理性个体化。”这种品质规定涉及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法律、认知以及精神领域,不一而足。艺术上的“现代性”标示为“非理性的个体化”,也就是感性,它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按照韦伯世界“凡俗化”的说法,可将现代性概括为两个层面:社会生活层面(或世界)的合理化;个体心性层面(或世界)的审美性。综合刘小枫与韦伯的观点,此处,我们首先需要对艺术上的现代性这一点进行细致分析。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性首先是指社会各领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即社会各领域要以理性为自身立法,从领域内部而非援引其他领域的标准来规定自身。以艺术领域为例,格林伯格很早就在《走向更新的拉奥孔》中论述了艺术的门类规定性问题,认为绘画的平面性与雕塑的三维性是现代“艺术不可还原的本质”。艺术具有自己不可还原的本质,电影作为第七艺术要确立自身就要回到自己媒介不可还原的规定性上。其次,现代性又指个体心性层面的审美性,这是指艺术领域内部。审美性就是感性,它的基本诉求之一便是:“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最后,既然说是民国时期的电影,那么,这一时期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特质便具有不同的品质质态,而这些均体现在拍摄手法的运用与创造上。
电影作为19世纪末的新兴艺术,没有古老的历史传统,不像绘画、雕塑、诗歌、音乐那样对文学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且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另外,电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必然带来电影视听媒介的进一步独立与凸显(如电影镜头的表现力、电影的韵律感等)。这些都是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确立自身的方向。既然是有关民国电影的“现代性指向呈现”,论述上加了“民国”,也就包含了“传统的”和“本土的”含义项。而这样一种含义项,在《小城之春》中体现为“时间感”。电影本就是一个时空综合体,但是,这里的“时间感”并非电影播放的物理时间,也不是影片中故事情节发展延续的时间(事实时间),也非观众的心理时间,而是“内时间”。关于“内时间”的研究,从现象学到后现象学一直是西方思想家们探讨的重点,从胡塞尔、梅洛·庞蒂,到海德格尔、伯格森等都有涉及。其中就“内时间”这一问题进行专著研究的是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这本书的引论当中,胡塞尔简要地阐述了什么是内时间,以及这种内时间在我们看一个物时是怎样展开的。他说,内时间“不是世界时间的实存,不是一个事物延续的实存,如此等,而是显现的时间、显现的延续本身”。也就是说,内时间它不是现实存在的物理时间,即连接我们生活事物、生存事件并使之成为一个合理的统一体的客观时间,而是“显现的时间”和“显现的延续本身”。“显现”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去蔽”,是“存在本身”。所以说,内时间是一个“存在着的时间”,“不是经验世界的时间,而是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通俗点说,就是在意识层面,当“我的”意识与生活世界相互敞开,无物无我,彼此不分,水乳交融之时,便是“显现”,也即“去蔽”“无蔽状态”。那么,内时间究竟如何展开内呢?回答:通过“体验”。其次,胡塞尔指出,“内时间”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心理时间。因此可以了解,“内时间”为人自身存在的体验时间。实际上,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文化门类都是在讲“内时间”。比如诗文、书画、戏曲、书评、园林构造理论等,庄子讲“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目无全牛”“物我两忘”,刘勰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些都是在讲“内时间”。具体到电影,便是观影者在观影过程中与影片中的人物、场景、故事情节相互融合,内化成一种独特的体验性状态。正如费穆在《略谈“空气”》中所言,他认为他做导演的一条法则便是“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因此,本文将“内时间”设定为民国电影的现代性品质。
关于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根据所查资料,无论是专著还是期刊论文,评论文章并不在少数。从阅读的文章来看,大多数文章都看到了《小城之春》在内容思想与展现形式上的独特之处,比如随处可见的“诗性品格”“东方美学”“东方风情”“民族化风格”等显著的字眼。但种种用词的出现总给人一种大而无当、笼统涵盖的感觉,仿佛只要将《小城之春》置于其下,种种用语的含义便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其次,从搜集的与“民国电影的现代性”或“《小城之春》的现代品质”等关键词有关的文献资料来看,它们所说的“现代性”或现代品质与本文所言有所出入且较为混杂,并常常从这一“混杂”出发来论述《小城之春》创作上的现代内涵。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现状,在展开论述之时,我们有必要厘清什么是艺术上的现代性,《小城之春》的现代性品质又呈现为何这些问题。
二、艺术上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民国电影是指1905—1949年这一时期的国内电影创作,费穆的影片《小城之春》创作于战后的1948年。费穆导演的电影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两个时期。30年代的创作有《城市之夜》《人生》《香雪海》《狼山喋血记》《镀金的城》《孔夫子》,编导《春闺梦断》,赴抗日前线拍摄纪实性抗战宣传片《北战场精忠记》,并与奥地利电影艺术家弗莱克夫妇合拍《世界女儿》。40年代的创作有《小城之春》和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生死恨》。
电影属于舶来品,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第一次放映法国影片,这一行为标志着电影在中国的引入与诞生。此外,无论是有声片还是彩色片的出现,这些电影发展历史性节点,国外技术的引进与创新对于民国电影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摄影、录音(由蜡盘录音到光学录音)、染印(由三条分色底片到染印转移法,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生死恨》就是用多层彩色胶卷拍摄的)等技法的革新。电影本就是技术发展的产物,中国电影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存在着无法割舍的关系,而作为技术的产物,它必然是“现代”的,无论其媒介如何发展。
另一方面,民国电影又具有它自身的“本土特色”。从现象上来说,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影片《定军山》是一部戏曲片或舞台纪录片;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也穿插着《穆柯寨》等四个京剧片段;而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生死恨》则是由京剧大师梅兰芳演绎,是一部京剧艺术片。从创作上看,电影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影戏”,其一是因为它与西方电影技术的关系,它以当时西方最新的电影技术为艺术手段。还有较为重要的两点是:第一,与传统戏曲(或戏剧)的关系。民国电影以传统戏曲作为创作的根本,对传统的故事情节、影片结构、银幕表现乃至空间造型等都有所借鉴;第二,从名称“活动影像”“动的影像”来看,民国电影与中国传统皮影戏也有着至深的关系。“中国皮影艺术是集民间绘画、雕刻与戏曲故事、唱腔、音乐、表演等巧妙结合而成为一体的独特民间艺术品种……是一种戏剧、美术综合艺术形式。”此外,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叙事方式、诗歌的意象性、绘画的写意感与空间造型以及传统园林建筑对电影场景空间在构图上的启发等,这些因素都对民国电影本土化有着一定的作用。
关于“现代性”的通常解释,这里引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两书中的相关论述。书中关于“现代性”的解说是:“现代性”就是理性,也即合理化与合法化。人以理性为自身立法,社会上的各个领域、专业、门类同样要为自身立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那么,该如何理解艺术上的“现代性”?波德莱尔指出:现代的艺术作品处于现实性和永恒性这两条轴线的交会点上:“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对此,哈贝马斯的解释是:“正是由于作品不断地浸入现实性之中,它才能永远意义十足,并冲破常规,满足不停歇的对美的瞬间要求。而在瞬间中,永恒性和现实性暂时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说,瞬间即永恒,在艺术的这样一种瞬间直感中蕴含着永恒性。刘小枫对艺术上“现代性”的论述是“精神上(艺术、哲学、道德、宗教)的非理性个体化”,也就是所谓的感性,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在艺术上凸显为视觉现代性,具体到电影上则表现为视听综合体的锐化体验,即对于视觉和听觉乃至两者综合作用下的媒介性的强化与突出。
如同民国时期的海派绘画,又如当时的月份牌绘画,两者在现代性的探索上都有所成就。前者在学习西方立体透视、对景写生等专业技法的基础上融合传统写意、碑学书法等技巧,形成雅俗共赏的视觉效果。后者在传统工笔画的基础上,结合民间擦碳像和西洋水彩法,再加上晕染皴擦,形成类似西洋画的明暗、立体效果。至于民国时期的电影,它的现代性指向亦有类似呈现。
首先,作为技术的产物,民国电影已经慢慢取得了声画的独立与统一。声画的独立与统一,就是媒介的独立与统一,即媒介凸显。这是基础,是技术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它们才能够确立电影的构架,也就是电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这与技术的进步,包括摄影术的发明、录音系统的完善、染印法的创造密不可分。再细分下来,还要涉及“声画蒙太奇、电影音乐、音响处理”,“摄影造型的探索,涉及运动摄影、光影调子、实景拍摄等,还有纪录片手法的应用”等。
其次,既然是说民国时期电影的现代性指向研究,那么就必然要涵盖一种本土性在里边。如前所述,民国电影与中国传统的戏曲、绘画、诗文、园林建筑以及近代的文明戏都有所关联。例如,对传统戏曲程式化(或简练化)的动作与对白,以及“场景设置的集中性”“场面调度的生动性”“构图的舞台化”等特点的借鉴与运用;再如,对传统诗文所独具的意境美、意象性,“境生象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审美理念的转化与呈现;又如,传统绘画所独有的“留白”、气氛感、人物与景物的安排布置方式的借鉴,而这些对电影的空间布景有相当大的影响。无论是戏曲、诗文还是绘画,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民国电影,特别是费穆电影《小城之春》所特有的诗意、流动性和体验感。在此,我们将《小城之春》现代性指向所呈现的特质称为“内时间”。这是一种内心体验的时间,但这样一种“时间”恰恰是要通过此前的一系列因素的创造性运用、转化与配合才可能达成。那么,在费穆《小城之春》中,这种达成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三、费穆《小城之春》创作上的现代性呈现
如前所述,费穆《小城之春》创作上的现代性指向呈现是与中国传统的诗文、绘画、戏曲以及文明戏的美学特征密不可分的,这是其本土性的一面。我们将其本土性的这面表述为“内时间”,现将这一特质进行细化阐述。
关于影片《小城之春》,在其上映之初(1948年)便有敏锐的评论者看到它的独特之处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诸如:“《小城之春》的作者用东方色彩的笔致——冲淡的笔致来描写一则美丽的东方人的故事。”“导演的笔淡淡描画,像一幅淡墨的山水小品……”“冲淡”“山水小品”等字眼奠定了《小城之春》这部影片的品质基调。观看过费穆这部作品的观者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总体印象:该片故事情节单纯,没有复杂的矛盾冲突,人物也只有精练的五个,“不注重情节的渲染,却花很大的精力刻画、创造意境”。“刻画、创造意境”,这便是费穆简化剧本、人物乃至情节的真正原因。而这一创造绝对离不开中国传统诗文、绘画、戏曲等因素的参与,它们已经成为费穆这部影片中不可分割的内容。正如当代评论家陈墨所言,《小城之春》“在表现形式上熔中国古典诗词、绘画、戏曲的精华于一炉,在电影的艺术技巧和风格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试验,建立了一套耐人品味的民族电影叙事方法和技巧规则”。
中国传统诗文、绘画讲究意境。“意境”一词源于王昌龄的“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后王国维又对意境进行系统阐述:“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境界”即“意境”,并认为诗文“有意境则自称高格”。在《小城之春》中,处处可见这种“境生象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意境美学特质。例如,剧中主人公周玉纹让仆人老黄给志忱送去一盆兰花,这盆兰花便是别有深意的,它表示主人公对自己的初恋情人余情未了。影片在不同的时段对这盆兰花有相对的特写镜头,兰花在这里不是简单地起到画面的装饰作用,而是用来传情达意的,呈现了一种爱而不能的情状,这便是“一切景语皆情语”。再如,影片一开头给出的就是残山残水、残园残草的画面,这样一种布景恰恰与片中的主题、氛围、人物状态相呼应,并于此之外传达出某种不尽之意。又如,影片中有一节讲的是四人划船出游,在这一“游”的过程中,男女主人公章志忱和周玉纹既喜又悲的矛盾情感与心理状态如同园中这潺潺的河水般无休无止,这便是“情景交融”。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三处例子,在《小城之春》中这样的人物与景物,与剧情,与节奏相融不分的情景随处可见,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说费穆这部作品整个都是这样一种充满意蕴的状态,这正是导演自己所追求的“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目标。
在电影创作的生涯中,费穆导演一直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导演人心中应长存一种创作中国画的创作心情”,并且说道:“我屡次想在电影构图上,构成中国画之风格。”“中国画之风格”,何为中国画的风格?答案就是——写意。在《关于中国旧剧电影化》一文中,费穆便清楚地讲道:“中国画是意中之画,所谓‘迁想妙得,旨微于言象之外’——画不是写生之画,而印象却是真实,用主观融洽于客观。”“写意”与诗文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说的是一个意思。其次,传统绘画的“留白”观念对《小城之春》的创作亦有影响。古代诗画讲求“空故纳万境”,这是一种意境美。费穆影片中对画面布景、人物关系以及故事情节进行简洁化处理,均来源于中国画“留白”的审美理念。这样一种“留白”,转化运用在电影中呈现为一种虚灵的空间,即所谓的意境。比如,影片结尾处主人公周玉纹站在城墙遥望的那个画面,远景,大量的空间被留出,给人无限遐思。最后,这也是之前提到的——影片中“环境与人物高度融合”弥漫为一种氛围,费穆将它归为“空气”。“必须是使观众与剧中人的环境同化,如达到这种目的,我以为创造剧中的空气是必要的。”“我觉得,用旁敲侧击的方式,也足以强调其空气。所谓旁敲侧击,即是利用周遭的事物,以衬托其主题。”这样的例子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比如剧中的蜡烛,它虽表面上是一个实用性工具,但实际上却是起到烘托氛围,展现男女主人公情感心理变化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再如妹妹生日宴后男女主人公第三次客房会面时特写的明月微风,以及听闻戴礼言自杀消息时章志忱所在的外景的狂风等。所有这些都是要营造氛围,从而达到情绪渲染的目的。
某种意义上,《小城之春》受到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香港著名影评家石琪指出:“本片的纯电影风格,其实贯通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就是写情细腻婉转,一动一静富于韵律感,独白对白和眼神关目都简洁生动,又合为一体。”纵观影片本身,首先,人物已由原来的七个删并为当时的五个,剧本篇幅压缩了三分之一并修改,且在修改稿上再删四分之一,可以说是极为简练。其次,场景、舞台布置集中,构图舞台化,给人一种“画框感”。最后,动作、对白都极其简练,甚至有时略微有点戏剧化。比如周玉纹的扮演者韦伟在拍摄中就专门学习了京剧旦角的“云步”,“从动作的形式中寻找表意元素,从而使玉纹的心境能透过步态含蓄而又准确地表露出来”。此外,剧中的故事发生背景是“虚托”,“虚托”的意思是指它的背景是虚化的,是一个封闭的环境。所以在《小城之春》中我们常常感到,仿佛这座小城中只有这五个人,而这正是对传统戏曲的借鉴。“溶镜”这一手法也非常特殊,在影片中不容忽视。费穆不是简单地像舞台剧那样用溶镜来“表示时间的流逝,场景的转化,更用来展示人物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表示人物情感的缓慢流动,其中当然也包含了观者内在的体验性时间。对传统戏曲的诸多借鉴和创造性的转化与运用最终形成了《小城之春》“长镜头、慢动作”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被用来“作为塑造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物关系,以及塑造场景氛围的重要手段”。与巴赞的为了避免主观剪辑,保持镜头的客观性的“长镜头”理论不同,此处的“长镜头”是电影的戏剧性手段,是指一个较长单位的镜头,目的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由此活动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内外的戏剧冲突。“慢动作”则是指“一种包含人物动作、心理活动,进而包括叙事节奏的从容、缓慢、充分、细腻等动作因素”。纵观来讲,传统诗画与传统戏曲同理,它们共同构成了《小城之春》“长镜头、慢动作”的美学风格。
四、相关研究文献分析
本文的文献搜集来源有中国知网、独秀、鸠摩搜书、爱问、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搜寻类别有专著、硕博生毕业论文以及期刊论文。关于这些文献资料,研读后分析如下:
其一,以“费穆电影的现代性追求”为主题词进行相应的知网搜索,得出文献5条,且均为博士论文。其中,只有1条与所搜内容大致相关,即《新兴电影运动:30年代中国电影的现代性追求》。
其二,以“费穆”为主题词进行相应的知网搜索,得到文献259条,其中与“费穆”或“费穆《小城之春》”有关的文献共98条。在这98条中,与本文所讨论的费穆《小城之春》的现代性问题有关的期刊的论文只有两篇:《古典意蕴与现代品格的完美融合——浅析费穆电影〈小城之春〉》《影像、现代、民族——论费穆电影及〈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
其三,以“民国电影 现代性”为主题词进行相应的知网搜索,得到期刊文献5条,硕博论文33条,其中只有1条期刊文献与主题词相关,即《民国电影的现代性问题》,没有1篇与主题词相关的硕博论文。此外,无论是以“民国电影 现代性理论”,还是以“民国电影 现代性问题”“民国电影 现代性研究”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均得到相同的20条文献,但其中只有1条是与民国电影的现代性问题相关的,那就是《民国电影的现代性问题》。
其四,以“民国电影 现代性”为主题词进行相应的知网搜索,得到硕博论文16条,其中只有1条与“民国时期电影”和“现代性”有关,即《形象的焦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现代人”与“现代性”(1921—1937)》。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共5条,其中博士论文2篇,期刊论文3篇。两篇博士论文分别是:《新兴电影运动:30年代中国电影的现代性追求》和《形象的焦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现代人”与“现代性”》。前者所说的“现代性”包含电影的思想内容、艺术本体以及商业性等诸方面,呈现为多种现代性的状况。后者的重点在于“现代人”,即由电影银幕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这一形象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之间经常难以准确定位,不断地处于演变、塑造之中,而“现代性”就是这一形象所展现出的整体特质以及创作者与观影者对这一特质的不断创造与期待。这里的“现代性”特指内容方面。三篇期刊论文分别是:《民国电影的现代性问题》《古典意蕴与现代品格的完美融合——浅析费穆电影〈小城之春〉》《影像 现代 民族——论费穆电影及〈小城之春〉的接受历程》。而上述文章所说的“现代性”“现代品格”“现代”等内容却分别说的是:启蒙现代性以及由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分裂、分化、主体异化等现象在电影内容上的表现;关注个体人性,关注现代人的人生况味和内心苦闷,以及“长镜头”“慢动作”电影镜头拍摄技巧的运用;费穆《小城之春》接受历程上的现代特性。
如上,对费穆《小城之春》这部影片的现代性指向研究多集中在思想内容上,虽有涉及艺术本体(或电影语言)方面的文章,但多不从现代性角度去进行切入和思考。又或者,虽从“现代性”这一点出发考量,但对“现代性”这一概念阐述得含糊不清,错将启蒙现代性当作现代性的全部,进而用于电影分析。再有,费穆的电影创作处于民国时期,因此,《小城之春》在艺术本体上所具有的审美现代性特质就必然在此之外笼罩着一层本土的光晕。而本文的侧重点不在影片的思想内容上,而是在这部影片的电影语言上,分析它的“现代性指向”以及这一“指向”在创作上如何一一呈现和展开。对于这一问题的厘清,是本文的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