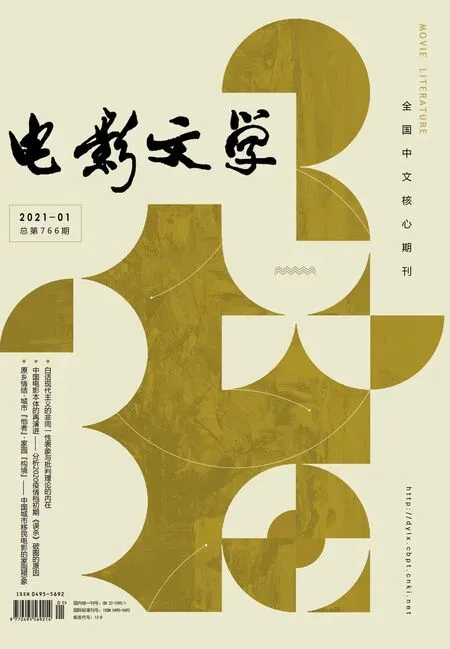“减法”原则、叙事效果与电影改编
——《一句顶一万句》小说与电影比较
沈嘉达 沈思涵
(1.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湖北 黄冈 438000;2.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小说的影视改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取材于小说文本。譬如新时期文学中早期由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电影,就取材于莫言的“红高粱”小说系列。其后,张艺谋又依据苏童、严歌苓等人的小说,改编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金陵十三钗》等诸多作品。而另一方面,影视作品也可以促进小说的生产,譬如就先有电视剧《锋刃》然后才产生了同名小说。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成功的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只能算作“少数”,大量的影视改编带来的往往是争议甚至是诟病。即便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王全安执导的《白鹿原》也遭到了猛烈批评。在学者李杨看来,电影《白鹿原》删除了“反思革命”的白灵和“回归传统”的朱先生这两个人物形象之后,将电影“主题转变为男女关系”,而且是“庸俗的男女关系”,导致电影“甚至讲不好一个情爱故事”。由此可见,小说与影视作品之间有着比较“紧密”而又“紧张”的复杂关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对小说的改编呈现的是“减法”原则
直接将刘震云的荣获茅盾文学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与由他女儿刘雨霖执导的同名电影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我们知道,作为文学类别的小说与作为艺术类别的影视作品之间,有着各自的文本规约。通俗地讲,小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影视是一种影像的艺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多重关联,譬如皆涉及人物、故事、主题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影视在当下更多的是作为“大众艺术”而存在,而小说尤其是某些富有“个性”的小说,只能是作为“小众”服务对象。
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其一定的长度和较为厚重的内容,对影视尤其是电影来说,是机遇亦是挑战。一方面,小说为影视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选择即判断,判断即舍弃,这也就意味着在有限的一两个小时之内,电影多半是在做减法。当然,也存在做“加法”的影视作品,也就是涉及一点,发散开去,点缀成篇。譬如广受好评的电视剧《潜伏》就是根据龙一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而成。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一开始就表明,它只是根据同名小说的“部分章节改编”。准确地说,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以下简称“电影《一句》”)在有限的100分钟内,只是选取了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下简称“小说《一句》”)下半部部分内容。本来,小说《一句》共分上下两部,36.5万字,叙写了至少五代人、杨氏牛氏等多个家族的数十年历史;小说中,100多号人有名有姓,涉及河南山西陕西等多个地域和县府、乡村、城镇等诸多场域。这样一种“大水漫灌”式的文学扇面叙写,再加上并没有“典型”人物贯穿始终,显然是不适合依样画葫芦拍成电影的。换言之,就只能是有所取舍,为我所需。
电影《一句》依照电影的基本原则对原著做了个性取舍。就人物设置来看,舍去了诸多与“中心事件”关联度不大的人物,只推出了牛爱国庞丽娜夫妇、牛爱香宋解放夫妇爱情婚姻故事。进一步说,就是牛爱国与庞丽娜离婚、牛爱香与宋解放结婚故事,这样,就让电影情节更加紧凑,人物更加集中,冲突更加激烈,主旨更为明确。对于配角,电影也进行了相对处理,譬如小说中作为牛爱国朋友的杜青海、李克智、冯文修三人角色,在电影中由杜青海一人担任;小说中,庞丽娜先是跟着开摄影店的小蒋私奔后又跟着姐夫老尚出走,电影则简化为两次跟着小蒋外逃;小说中的牛爱国是个走南闯北的货车司机,而电影为固定故事发生场域,则将其定位为小修鞋匠等。
做这样的“减法”,既是导演的无奈之举亦是自觉行为。按照刘震云的说法,就是:“导演这样设计是为了拍摄的方便,如果还是开车,那拍起来特别麻烦,场景也需要不断变化。修鞋铺搭景比较容易,钱花得也比较少。”所谓“无奈”就是为了省钱,同时拍摄起来省事、方便;所谓“自觉”,强调的就是电影与小说各自的文本属性。小说作为语言的产物,可以天马行空,依靠读者的文学想象,产生艺术美感;而电影作为影像艺术,就必须“还原”现实,给观众以实实在在的现场感。从这个角度看,电影《一句》“形式”上并没有多少可以指斥之处。相反,电影《一句》头绪集中,线索简明,人物明了,更容易见出电影的基本属性来。
然而,为什么电影《一句》招致的多是批评呢?
二、小说《一句》与电影《一句》体现出迥异的叙事效果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情节并不复杂。上半部写的是河南延津杨百顺为了生存和能与人“说得着”(“喷空”),做过豆腐,挑过吃水,信过西教,学过篾匠,还在县衙种过菜蔬;入赘吴香香家,改名吴摩西,为寻找丢失的女儿巧玲四处奔波,最终改名罗长礼,以实现自己始终未能实现的“哭丧”梦想。下半部写的是杨百顺丢失的女儿巧玲,被人贩子老尤贩走后改名曹青娥。小说下半部重点写曹青娥儿子牛爱国与儿媳庞丽娜、女儿牛爱香与宋解放之间结婚与离婚故事。在这长达数十年、涉及底层民众数十种职业、一百多人的扇面叙写中,将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现实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展开。
小说《一句》实际上一直在考验读者的阅读耐性。因为小说本身并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也谈不上能够展开的事件冲突。更重要的是,作者刘震云以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用一种回环结构来表达一个主题。所谓“回环”结构指的是,上半部写的是杨百顺历尽磨难,因为“说不着”而走出河南延津;下半部主要写的是杨百顺的外孙牛爱国同样在生活(例如爱情、婚姻)中因为与庞丽娜“说不着”而四处“寻找”,最终找回老家河南延津。这其实就是在表达一个带有象征性的意蕴:无论是在延津还是在他乡,都不可能寻找到“说得着”的人和事。
小说《一句》是以“理念”取胜的。为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呢?寓意是,如果与人“说得着”,那么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说不着”,那么就是“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无论是杨百顺一家(杨百顺与父亲、与兄弟)、杨百顺与传教士意大利人老詹、杨百顺(吴摩西)与老婆吴香香,还是下半部中牛爱国与妻子庞丽娜、牛爱香与宋解放之间的恩怨情仇等,总之,人与人之间都是“说不着”——这样,便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设置、“说不着”话语的有意重复、情节设置上的历时叙事等,建构起了一个主旨:人与人之间,哪怕是最亲密的家人,哪怕是官居高位的河南省长延津县长,哪怕是过去现在和可能到来的将来,都逃不掉这样的“说不着”的宿命。也即是说,人与人之间不可能获得心灵的真正相通和精神的共振,有的只是各自的利益盘算和利害冲突。
“配合着”这样的“大主题”,作者着意展开数十年历史,营造出贯穿全书的“氛围”——正是这种挥之不去、愈来愈浓烈的人性悲凉的“氛围”让我们压抑不已,从而产生自省意识,对中国人的历史性的“孤独感”有了切肤之痛。如果推及开去,还可以将小说《一句》看作是人类命运的象征。这样,小说的主题更富有价值。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电影《一句》。众所周知,电影是大众的艺术,同时也是时间的艺术。“大众的艺术”强调的是电影的大众属性,也就是说,电影必须用平头百姓看得懂的形式、感兴趣的形式来展开,这也就决定了电影的“底层性”;“时间的艺术”强调的是电影的基本长度,一般来讲,电影不超过两小时,这就决定电影不可能全方位展现百年中国历史,不太可能在广阔的扇面上展开头绪繁多的故事叙述。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依照电影的基本属性要求来进行编导,还是尊崇小说原旨以之为圭臬?如果重在讲故事,就必然偏离小说;如果完全尊崇小说,那么该如何表现“说得着”与“说不着”的理念呢?
刘雨霖显然想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说,用电影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小说的哲学理念。这样,我们就看到,牛爱国当初因为与纱厂女工庞丽娜“说得着”而去民政局领结婚证,就在欢天喜地领证的同时,一对夫妻来办离婚。这对夫妻离婚的原因就是“仨月了今天(才)说头一句话”——这其实就是“暗示”牛爱国庞丽娜的将来结局。我们说,至少从面上看,电影导演也是遵循这个理念来拍摄的: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当年“说得着”的牛爱国夫妇,现在因为“说不着”而同床异梦;庞丽娜爱上了“说得着”的摄影婚纱店老板蒋九,跟着蒋九流浪出走。牛爱国的姐姐牛爱香,年近四十了希望“找个人说话”而与厨子宋解放结了婚,却发现婚后两人无话可说;牛爱国的中学同学章楚红刚刚与丈夫离婚,还是因为两人“说不到一块”……
正如前文所言,电影是影像的艺术,传统的中国电影需要情节、冲突来保证故事的推进、事件的解决。而这种“推进”与“解决”又离不开线性叙事和细节、场景、言行的铺垫。没有这种必不可少的铺垫,必然给观众以虚假、突兀、理念化的印象。事实上,电影《一句》之所以票房低下(累计才1777万元),口碑不佳,正在于不切实际地“用电影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小说的哲学理念”。我们发现,电影中所有人物关系因为“理念在先”“主题先行”而显得“虚假”和不可信。譬如为什么牛爱国结婚后就不能与庞丽娜“说得着”呢?庞丽娜为什么就与开影楼的蒋九“说得着”呢?电影舍弃了小说中的“氛围”营造而单独抽取牛氏姐弟故事,能代表中国人历时性的“百年孤独”吗?章楚红凭什么能说出“日子是活以后,不是从前”这样的话语来?没有情感演进,没有细节与情节演绎,没有必要的“累进”过程,仅靠演员(导演)的几句台词交代,是不能让观众产生联想效应的,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上升到哲学高度。
三、我们该如何进行小说改编?
刘震云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在谈到《一句顶一万句》的改编时,刘震云说:“从属性上说,我的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或者说,我的小说不适合改成电影。”何以如此?“因为改成电影就需要基本的电影元素,比如相对完整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人物也要相对集中,电影中的主要人物最多不超过三个。我的小说基本上是相对碎片化的写作,没有完整的故事,更没有起承转合的情节。”
“碎片化写作”只是刘震云小说《一句》的表象,真正的“内质”在理念,也可以说是“思想”。而这,正是刘震云小说的最可宝贵之处。刘震云从来就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譬如《故乡天下黄花》中对权力(大印)的从民国初年到“文革”时代的历史叙写,呈现的是欲望化了的个人叙事伦理。在这里,“故事”只是表象,“权力”才是主角。再看《温故一九四二》,从最初的“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到“电影《一九四二》的创作者采取‘尽量客观的,不融入个人的态度来再现那段历史’,与此同时却不失温情和关怀”,从而成就了这样“一部史诗作品”,实在是具有天壤之别。电影《1942》其实已经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没有什么思想与情感关联。
电影《一句》的编剧就是刘震云本身,应该说个中滋味他是杂陈于胸。“当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到底会影响到小说里面多少特性。特性也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小说的精神实质,还有故事和人物……我认为改编后对这些方面产生影响和伤害是对的,没有影响和伤害小说的电影不是正常的,因为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注意,刘震云明确说到是改编后的电影“影响和伤害”了原著。而导演刘雨霖则有着不同的看法:“虽然是基于小说而改编,但到电影的时候它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了,这个孩子有自己的长相和命运,和原来的母体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拍成影视剧对原著并不是消耗,因为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生物。”
这里其实就涉及一个重要的命题:电影该如何改编小说?尤其是像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思想小说”该如何改编?
从一般意义上讲,既然是“脱胎”于小说“母体”,改编后的电影完全抛开小说变成“另外一种生物”,这本身是做不到的。小说作为IP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粉丝资源,更重要的是,为编导提供了电影故事、人物、情节、主题等,这也是许多观众追逐电影的情感逻辑起点。尽管刘雨霖称电影会“填补和流失”某些情节、人物等,但是,这种“填补和流失”决不应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初导演要改编小说,难道不是首先发现并看重小说的某些“硬核”吗?没有这些“硬核”,电影导演完全可以另起炉灶,重新编写故事,又何必对小说进行改编呢?就张艺谋来讲,他看中的当然是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中的“生命意志”,这才让火红的高粱、嘹亮的唢呐催生余占鳌、戴凤莲不羁的生命活力。如果撇开这些,还能叫“红高粱”吗?冯小刚导演的电影《1942》之所以饱受诟病,并不是因为演员阵容不够强大、故事不够煽情,而是因为电影《1942》衰减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尖锐的民本思想(这是小说硬核),虽然足够正能量,却已经完全偏离了小说主旨。
就笔者看来,小说的影视改编是极其复杂的“问题”。这里面涉及诸多内容。譬如对小说文本的认定问题、对电影美学属性的认知问题、对市场的迎合态度等。套用一句现成的话就是,我们要进行的,只能是电影对小说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何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一般原则上讲,首先强调的是电影是一门独立的创造性艺术,不可能全盘照搬小说的人物、情节等。实际上,由于时长、线索、投资等多种原因,电影也无法横移照搬。电影需要按照自己的“规则”来拍摄。其次,笔者认为,电影的改编重在对小说“硬核”的继承与拓展,做到“扬长避短”。只有将小说原著的“硬核”准确把握住了,再将之推向极致,才可能说是“创新”与“创造”。脱离或是偏离了小说“硬核”的改编,要么是投机取巧,迎合市场,要么是化“金”成“石”,弄巧成拙。再次,小说的影视改编肯定要兼顾艺术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小说渐渐趋于“小众”,而电影还是大众艺术。导演必须考虑到投资、上座率等因素,同时还得顾忌行政审查,那些过于尖锐、前卫、另类的“思想”,是难以有机地与大众结合起来的。这也就是说,改编什么,不改编什么,是要慎重考量的。否则,电影改编就变成了费力不讨好的囧事。最后,电影具有独立生命,其本身就是一门综合艺术,牵涉到演员表演、录音、拍摄等多种因素,与小说的个体创作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在评说电影时,也应该怀着更加宽容、平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