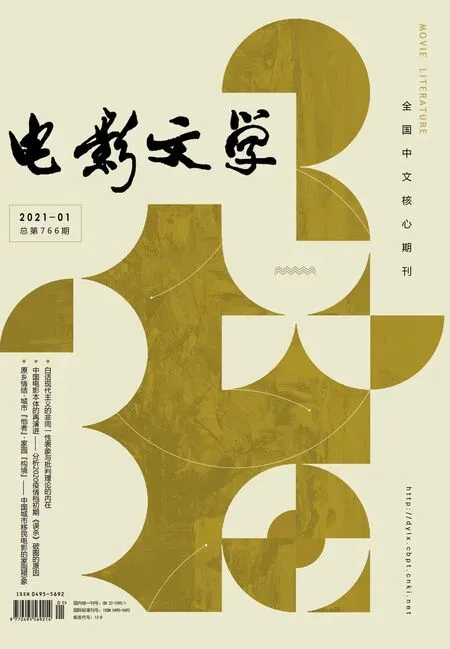类型美学视角下的娄烨犯罪电影
李 云
(世宗大学,韩国 首尔 05006)
对于第六代代表人物娄烨,人们普遍承认他在国产独立电影制片运动中的地位,赋予其“不与市场妥协”“个性化”等标签。却较少有人注意到,娄烨从未弃用类型电影的工业生产模式与美学范式,他对个人电影道路的执着探索,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寻找艺术与商业间的平衡,接受类型与非类型的渗透融合。事实上,娄烨的几部犯罪题材电影是贴合类型电影形态,并较好地达到了预期观影效果的。安德鲁·都铎曾指出:“类型是我们共同相信的一些东西。当看一部惊悚片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惊悚片。事实上,在我们看之前就知道什么是惊悚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需要知道影片的内容,就能认出这些有着广泛的文化共同点的类型电影。”娄烨自《危情少女》到《浮城谜事》,再到引发热议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片,无不拥有着犯罪类型片的文化共同点,值得从类型美学的视角进行剖析。
一、叙事动力与道德平衡
生活于工业信息社会的当代观众,有购买快感与梦幻,丰富情感生活的需要。这正是类型电影叙事模式的立足点,一个能驱使观众情感涌动,具有快感导向的故事无疑能给观众制造巨大的消费动力。在犯罪电影中,叙事的类型化模式主要体现在:一是以跌宕起伏、快节奏、戏剧化的情节营造叙事动力;二是在矛盾的制造与解决上,迎合公序良俗,不违背观众的道德平衡,不破坏观众的心理认同。
就叙事动力而言,犯罪类型片要求故事构思巧妙,矛盾集中且激烈,与大多数观众枯燥重复的现实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如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叙事起于一桩离奇的碎尸案,甚至有食客在饭店的面条中吃出眼球,恶心呕吐这样的离奇情节,这无疑能极大地吸引观众;类似地,苏有朋的《嫌疑人X的献身》尽管一开始就让观众知道杀人者是谁,但却以石泓的具体脱罪手法为悬念,再杂以石泓与陈婧的感情纠葛,以至于情节一波三折。而如陆川的《寻枪》则是“淡化了类型形态,使观众不再产生类似的期待”的范例,电影并没有以“偷枪者是谁”为支撑全片的叙事动力,而是展现主人公马三惨痛的人格异化问题,这无法让观众进行一场思维冒险。
娄烨犯罪电影选择的便是戏剧性极强,疑案谜团为清晰叙事动力的叙事范式。一个或数个人的非正常死亡或失踪会在一开始抛出,如在《危情少女》中,少女汪岚的母亲突然跳楼自杀,父亲不知去向,这导致了汪岚情绪不稳定,常做噩梦;《浮城谜事》一开始,富二代们开跑车将女大学生蚊子撞成重伤,随后为怕被讹诈而将蚊子踢打而死,但警方调查显示蚊子在车祸前就已身受重伤,她的悲剧另有元凶;《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故事起于建委主任唐奕杰来到混乱的拆迁斗殴现场调解矛盾,次日却被发现从五楼坠亡,而警察杨家栋在调查时,发现唐的死与多年前的连阿云失踪案有关。人物血腥死亡与失踪,是观众恐惧而又渴求看到的激烈冲突,而电影中又大量制造巧合,让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如修车工秦枫喜欢死者蚊子,又是警察童明松的挚友,因此能参与破案;又如杨家栋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就在怀疑一具烧焦女尸是连阿云之后被陷害遭遇车祸而失忆,正方力量于公于私都有着追查真相的强烈动机。这样的设计就使得观众的好奇心被牢牢抓住,能主动加入杨家栋等主人公的真相推理活动中来。
就道德平衡而言,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成功的类型电影势必要传达主流道德观念,以避免观众难以产生移情。对于犯罪类型片而言,“惩恶扬善”便是其必须恪守的原则。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曾提出一种经典叙事模式:平衡存在—平衡被打破—平衡被恢复。犯罪类型片中人物触犯法律就是打破道德平衡的行为,而善良正义者找回真相,恶人得到惩治的结局则是修复道德平衡的行为,缺乏了这一结局,观众将无法得到抚慰。如忻钰坤的《心迷宫》中,肖卫国再想包庇儿子肖宗耀,最终也不得不与肖宗耀前去自首。曹保平的《烈日灼心》中,辛小丰百般隐姓埋名和行善赎罪,依旧逃不脱被执行注射死刑的结局。娄烨电影亦然。在《危情少女》中,汪敬在害死妻子,杀死情敌刘家新后又想害死汪岚,最终被汪岚男友路芒所杀,帮凶林护士也命丧黄泉。《浮城谜事》中,殴打蚊子的陆洁,将已头破血流的陆洁推向马路的桑琪,杀死拾荒者的乔永照等,都面临着法律的制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姜紫成在房车中和杨家栋搏斗而死,林慧自首后自杀身亡,就在观众误以为一切结束时,杨家栋在调查另一桩案件时发现了将唐奕杰从楼上推落的竟是唐的“女儿”,杨的女友小诺,小诺被捕,至此案情终于水落石出,每一个扭曲堕落者都付出了代价。至此,观众在体认到了犯罪作恶,打破道德平衡的感受后,其“善恶有报”的心理认同又得到了满足。
二、视觉符号与乱序剪辑
类型电影的成熟,包括了在视听语言上的模式化:“我们所说的某一类型的标志性特征,除了指其主题、人物、叙事等,另一重要的直观的标志便是其造型风格、视觉图谱等。”什么样的造型元素,怎样的剪辑效果,能引发观众什么样的心理效应,已经在大量类型片创作者的实践后成为定式。如西部片的荒漠、小镇、山谷等地貌符号和大量大广角镜头,运动感摄影造型等,已然自成一格。在犯罪类型片中,为影片增加理性感的真实时代场景(如董越《暴雪将至》中20世纪90年代的小城工厂背景),黑色电影奠基者保罗·施拉德提出的夜景布光(如《白日焰火》、丁昇的《解救吾先生》、李扬的《盲井》等,无不将大量的叙事置于夜晚或伸手不见五指的井下),好莱坞电影反复使用的枪械、流血、飙车、爆炸等元素等,都已成为影片创作者和接受者默定的美学策略。娄烨犯罪电影也不例外。如在视觉符号上,娄烨也喜欢大量使用让观众切实可感的真实场景,并令其与案情结合。《浮城谜事》中的背景在武汉,陆洁在带着自己的女儿安安、丈夫与别人的儿子宇航两个孩子漫游武汉的时候,坐在缆车上俯瞰城市,此时头顶的天空是阴暗孤旷的,而脚下则是踏空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更是充满了广州、番禺、香港和台湾各地元素。各类身体以及受伤、死亡的视觉符号也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如《浮城谜事》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都有大量伤痕、黑斑等特写,蚊子、唐奕杰几乎面目全非的尸体,连阿云的焦尸,惨烈的、一地狼藉的连环车祸等,都被娄烨作为视觉奇观呈现。
此外,娄烨还善于运用乱序剪辑,即杂耍剪辑,这一剪辑方法能有意识地打散破案过程,在多个段落中隐藏线索,具有极大的娱乐意义。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1989年、1990年、1992年、1996年乃至到2006年连阿云被杀,2012年唐奕杰坠楼身亡等,各种时间线交错,能起到迅速调动观众观影心理,抹平线性时空枯燥的作用。如在1990年唐奕杰和林慧兴高采烈地坐上婚车离去,画面接下来出现的却是2012年同样走在这条街上,调查唐林过去的杨家栋。在《危情少女》中,现实规定情境不断被打破,观众拥有了一个刺激的观影过程。
三、现实观照与人文言说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人又必须为诱惑观众走入电影院,给予观众新的审美欢愉而不断“破格”,违背成规,而如娄烨这样深受“新浪潮”影响的电影作者,更是会保留自己的个性,如在视觉语言上娄烨一贯坚持的手持摄影(包括刻意营造的伪手持镜头),让画面几乎时刻处于晃动状态,给部分观众造成不适,就是对类型片迎合观众原则的违背,是娄烨突破类型片模式化的一种表现。而在文化表达上,娄烨及其他中国电影人则选择了以一种精英立场“破格”。一般来说,类型电影与消费时代关系密切,是市场的自觉选择。犯罪电影更是素来有“以小博大”之称,即能以较小的投资换取较大的票房回报,这靠的便是人们普遍具有的窥视邪恶的心理机制。但中国尤其是内地电影人在拍摄犯罪题材时并没有盲目强调商业属性,妥协于大众文化,而是以严肃旨趣对大众文化做出了鲜明的指导姿态。高群书的《神探亨特张》、贾樟柯的《天注定》等莫不如是,在此不赘。
娄烨电影中的精英立场体现在他对现实的观照以及其中充沛的人文情怀上,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姜、唐、林、连复杂的四角关系中,娄烨实际上为观众做了一个历史进程的微型还原。电影触碰到了真实的2010年广州冼村强拆案事件。在电影一开始娄烨就以移动镜头为观众展示了那片被高楼包围,破败混乱,孕育着动荡与不安情绪的城中村,时代发展下,阶层的分化被直观呈现。唐奕杰和姜紫成的关系更是娄烨对官商勾结,权钱色交易的一种无情否定。正如唐奕杰在KTV里对连阿云吹嘘的,正是他运用权力出卖了寸土寸金的土地。姜紫成开发的一个个豪华楼盘,唐奕杰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背后正是新世纪以来南方地产业狂飙突进造成的历史创伤,是一个个默默死去的连阿云、王秘书和老A助手。甚至连一般电影人不愿意贬低的执法者,都被娄烨所批判。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杨家栋在林慧的酒楼中见到自己的上司在和姜紫成推杯换盏,杨家栋本人在遭遇命案后惊慌失措,与林慧贸然发生关系堕入“艳照门”等,也体现了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浮城谜事》虽是借一场离奇的车祸命案来讨论男人出轨的话题,但其中不乏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如片中富二代给警方施加压力,一度让案件以私了结束。这一叙事立场,体现出娄烨作为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在揭露社会顽疾时,娄烨表现出了对人性,对生命真实状态的深度解读。《危情少女》中,汪敬之所以要杀妻杀女,是因为发现汪岚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并且他要夺回自己的豪宅。与之类似的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唐奕杰发现小诺其实是姜紫成的亲生女儿,并且妻子林慧与姜紫成旧情未断,因此才用家庭暴力的方式折磨林慧,并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在从小诺口中得知妻女和“姜叔叔”要一起去香港过一家三口的生活时,恼羞成怒决定要毁掉姜、林二人。而作为一个职业官僚,他又能够在刚刚和小诺厮打后,马上因为接到城中村斗殴的消息而改换面孔,迅速组织出另一套语言。《浮城谜事》中,桑琪因为妒忌而故意设计陆洁发现乔永照出轨,一心想要金钱和儿子兼得的乔永照游走于两个女人之间,蚊子的母亲在痛失独女后,在富二代的巨额赔偿下很快答应和解等,无不都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反应,这与类型片中的英雄叙事迥然有别,体现着一种现实主义表达倾向,并渗透着导演的理解与同情。
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发现,娄烨犯罪电影是完全适用于类型批评的研究对象的。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电影中,娄烨承继了犯罪类型片的创作模式,电影在叙事、视觉语言上,均满足市场审美需求,同时,娄烨也以一种精英立场在犯罪片中刻画现实,关注人性,丰富国产犯罪片的文化价值空间。这种向类型化的靠拢,并不是对“娄烨标签”的削弱,而恰恰是对它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