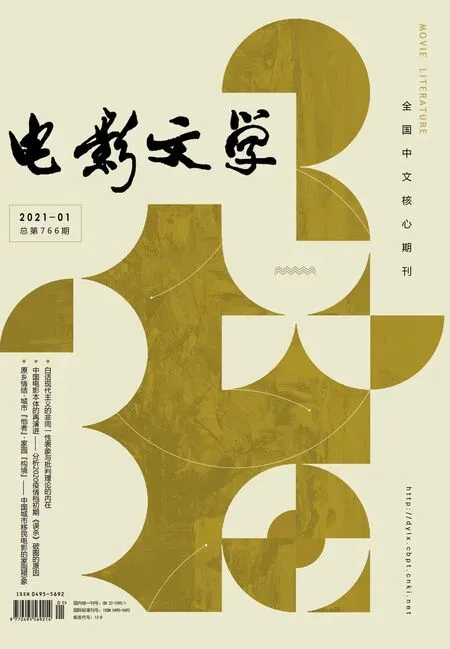《土生子》中比格·托马斯的创伤书写与引路人疗伤机制缺失研究
张 军 魏竹涵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电影《土生子》是由拉希德·约翰逊执导的剧情片,于2019年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该片改编自美国著名黑人作家理查·赖特于1940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该小说被誉为“黑人文学的里程碑”,并与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和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黑人文学的典范。
影片在保留原著关键情节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顺序调换和删减,用电影艺术的形式将矛盾冲突具象化且充满情绪张力,揭示了主人公比格·托马斯的多重创伤,向观众传达了20世纪美国黑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了种族主义与阶级主义给黑人群体带来的深切创伤。然而,影片存在着人物形象单一化、成长弧线扁平化的问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缺乏适当引路人的引领,导致人物未能跳脱已有设定的桎梏,情节的复杂性也有所欠缺,削弱了影片在主题上的表述力度。
反观小说原著,引路人疗伤机制作用下的创伤治疗无疑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但在电影中此机制却无从体现。由此入手,本文旨在揭示电影中的创伤书写,而后以小说中的引路人疗伤机制为参照,探析电影中此机制缺失原因,揭露《土生子》从文学原著到影视作品这一互文性改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
一、电影中的三类创伤书写
影片的主人公比格·托马斯是一名普通的黑人青年,但不同于常人的是,比格对于周遭世界有着独一无二的、超脱世俗的见解。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所构思,认为周围的人“像一群老鼠一样窜行,他们都被蒙蔽了双眼,以为自己是按部就班,但实际上是故步自封”。他看透了资本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转的基础规律,他未被主流社会所同化。
显而易见,电影在一开始就给比格设定了特立独行的形象,将他塑造为有思想深度和敏锐感知的“新黑人”,这显然是将他放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高度。在美国文学中,黑人形象通常被简单化为几种原型形象,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温顺而服从的山姆大叔形象,以及充满暴力而邪恶的黑人罪犯形象等。这些原型形象,无疑与美国维持其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话语的意愿息息相关。正如周春教授所言:“新黑人和旧黑人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去除了美国大众想象中的将黑人视为低等人类的原型形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比格的思维的独特性、缜密性和自省性在黑人群体中属于佼佼者一类。然而,这并没有使他的生活免受创伤阴影之扰。
《土生子》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创伤性事件,从各章节题目和影片主要事件中,其创伤性质就可见一斑。主人公比格是各类创伤事件的受害者,而后却又成为杀人凶手,制造了更多创伤源。影片中比格的创伤主要来自三方面:种族创伤、阶级创伤和文化创伤。
比格的种族创伤主要表现在他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上。即使比格有清晰的目标——“我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也有自己的一套行动纲领方法论——“我不能急功近利,我一点也不蠢,很多事情我都能做得很好。”然而白人至上的社会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物质资源和途径来允许比格拥有体面的学历和工作。电影开头部分亮相给观众的,就是这样一个有志有识却依旧无所事事的黑人青年。种族创伤并不总是需要通过设置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正面冲突来表现,影片中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渲染,最为明显的一处便是比格与他的黑人朋友之间时常以“黑鬼”互称,与其说是调节气氛的自嘲,不如说是种族创伤下的无奈。由于长期在种族间泾渭分明的社会生存,对白人的畏惧与疏离已经渗入了比格的血液,直接导致比格误杀玛丽。
阶级创伤则使比格始终无法融入道尔顿一家,即便他们都对比格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尊重与友好,阶级差别依旧阻止着比格与他们一同欣赏文学名著、聆听贝多芬演奏会以及参加每周日的教堂礼拜。此外,当比格成为道尔顿家的司机,得以共享他们较为富丽优渥的居住条件时,他的黑人朋友杰克却表现出了狭隘的阶级主义,将比格排挤于黑人群体之外,称他为“披着黑人皮,长着白人心的‘奥利奥’先生”。
比格的文化创伤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众传媒和主流舆论的滥觞,图书、报刊等文化传播媒介几乎都充斥着对黑人的盲目偏见。影片中,在玛丽之死被发现后,报社第一时间就给比格安上了“黑人奸杀犯”的罪名,电视台则更是以“黑人一出生就是有罪的”这类偏激言论来引导舆论导向,将黑人群体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愈加逼向绝境。
电影中这三类创伤书写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使得比格虽有自我定位,却找不到人生方向和自身价值所在,长期受限于他人眼光之下成为白人凝视的客体,而缺乏黑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导致行为能力受限而无法真正融入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引领比格走出创伤阴霾、实现自我价值的引路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小说中的引路人疗伤机制
与影片相似,小说中的比格·托马斯也深受三类创伤之扰。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原型充斥着更为尖锐的激进、暴力、愤怒因素。畸形的美国社会所塑造出来的“土生子”比格在愤怒和激进情绪的催化下主导了两次杀人行为,与白人社会进行了一场心智谋略的博弈。与电影相比,小说有着更为清晰的内在篇章脉络:前两章节为比格的创伤书写和困境表征,第三章节则集中体现了引路人疗伤机制是如何在比格身上发挥作用以治疗他的创伤。分析小说中的引路人疗伤机制,有利于为比较电影的呈现方式提供参照,也为探究电影中这一机制缺失原因提供了可借鉴的有益视角。
小说中的引路人疗伤机制遵循了创伤治疗的三个基本阶段,而引路人则是黑人牧师哈蒙德和白人律师麦克斯。首先,对于频繁经历两次杀人事件的创伤性闪回和长时间逃亡的比格来说,是不具备任何安全感的,任何外界环境对他来说都是疏离和威胁。比格入狱后,黑人牧师首先来到他的身边,试图以宗教信仰和教条教义来使比格敞开心扉,实现自我救赎。虽然起初比格对于牧师的说教持有排斥和抵抗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牧师哈蒙德的宗教引导确实使比格仿佛置身于一片空虚混沌中遨游,身体和内心都渐渐变得有力量。至此,在引路人黑人牧师哈蒙德的引领下,比格已经达到了创伤治疗的第一个阶段:对周围的环境和人建立起了基本的安全感。
随后,在白人律师麦克斯向比格表达了想要帮助他的决心,耐心地引导比格去回忆自己的整个创伤经历,并将其讲述出来。引路人麦克斯的耐心开导使比格第一次“引起他想要坦白、想要说话、想要暴露他感情的强烈欲望”。至此,麦克斯引领着比格披露创伤真相,重构创伤故事,使比格将分离的创伤记忆转化为了被整合的叙事记忆,完成了创伤治疗的第二个阶段,是创伤愈合或精神康复的必要途径。
最后,虽然比格摆脱不了走向电椅的命运,但在黑人牧师哈蒙德和白人律师麦克斯的引导下,比格终于重新思考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主动修复了自身与他人的关系,终于摆脱种族创伤的桎梏,愿意直呼白人先生简的姓名,以全新的自我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很大意义上比格最终走出了创伤的阴霾。
三、电影中引路人疗伤机制缺失原因
《土生子》是一部反映生存困境、引人深思的剧情片。除开表层的故事情节,内层的人物情感认同机制的建构也同样重要。电影以人物为中心制造认同感,通过人物的价值选择,在影片结尾象征性、想象性地解决现实问题,以达到让观众认同和接受的目的,影片的主题也借人物的情感得到深化。可惜的是,电影中的角色塑造缺乏足够成长弧线,人物的内在情感机制也趋于单一化,情节叙事欠缺复杂性与流畅性,究其原因是没有设置恰当的引路人疗伤机制。
如上文所说,主人公比格从出场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自我思想,随着情节走向,他只是体现出情绪的波动,而没有实现对新的价值观、情感机制及人生哲理的感悟与收获。比格在电影的一开始便有着跳脱于世界之外的“上帝视角”,到了影片后半部分,当他失手误杀了玛丽之后,对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认知越发强烈,认为“所有人都是盲目的”,“唯一比瞎了更糟糕的是视而不见。也许每个人都是盲人,甚至是我”。直到他走投无路被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之时,他脑海中残存的也还是这一清晰却无奈的认知:“这个世界尚未改变。”就这一层面来讲,影片中缺乏足够的成长弧线来促使人物转变,虽然传达出了主人公对于深刻性、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事件体验,但未能改变其认识观,使之“摆脱幼稚、无知、单纯、浪漫和天真,变得成熟、经验、世故、现实和理智”。比格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类生活悲剧性的清醒认知从一而终,这样的角色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的层次感。
再者,纵观整部电影,构成情节发展的比格人生重要事件节点,都是由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所主导和控制,他人对于他的影响微乎其微。整部影片的高潮和中心事件,无疑是比格误杀白人小姐玛丽。表面上来看,玛丽作为白人资产阶级的代表,她与比格交谈、互动的本意虽然是追求平等、表达友好,但却使比格被迫感知和承受了来自白人社会的压迫感和优越感,无形中加深了比格对他们的异化感、疏离感和自卑感,最终使他走上歧途。那么在这一层面上,能否说玛丽充当了反面引路人的角色呢?答案是否定的,她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将比格引向生命的歧路。深层次来说,她也只是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杀死玛丽的并不是她吸毒后的神志不清与放纵,也不是比格的冲动与暴力,而是比格内心对于白人社会的畏惧与疏离,是种族创伤、阶级创伤以及文化创伤。
因此,直到影片的悲剧性结尾,比格都没有受到有益的引领而走出创伤阴霾,可以说,比格带着创伤凄凉地死去了。对于电影中引路人疗伤机制的缺失,笔者分析认为原因主要有二。其一,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影是视觉艺术,二者所使用的艺术手法不同”,加之影片时长的限制,小说在被改编成电影过程中,对故事情节的改动是必要的。为了最大限度渲染悲剧性氛围,达到反映社会问题、引起观众共情、引发深入思考的目的,影片删去了小说中最后一部分比格得到引领而升华的内容,而是选择将结尾定格在他的悲剧性死亡上。
其二,制片方考虑到影片上映地区而为了迎合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舍弃了黑人牧师与白人律师对于比格的共同引领作用。受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舆论导向影响,加之种族主义在美国社会的影响以及白人中心话语压迫,黑人群体本就处于社会边缘状态,黑人作为被迫的移民群体,与传统的非洲文化分裂,又难以融入白人统治下的主流文化。因此,白人律师引领黑人杀人犯在部分白人眼中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黑人并不具备被引领的资格。再者,如果不删除白人对黑人的引领,那么向观众全景展示主流社会操控黑人的过程与原因,这无疑也是电影制片方所不愿意添加和看到的。
以上两个因素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影片《土生子》中引路人疗伤机制缺失的原因,当然这样的缺失也导致情节的复杂程度及影片所想要传达的伦理道德力量都被削弱了,在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方面也未能达到观众的期待:即塑造洛克所指出的“不仅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创造精神财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着崭新的心理,在民众中有着新的精神觉醒”的新黑人形象。
四、创伤视域下的人道主义观照
《土生子》作为黑人文学的里程碑,发表70多年来评论界众说纷纭。总体来看,主人公比格·托马斯被认为是新黑人代表、存在主义式的英雄、现代反英雄、环境的产物、野蛮的黑人原型再现等。从电影制片方对于比格形象的塑造定位上来看,无疑是赞同且秉承了他作为“新黑人”这一象征性社会符号的重要历史意义。原著作者理查·赖特将比格塑造成了一个充满愤怒、暴力、激进的亚人类形象,是想向美国社会传递振聋发聩的抗议信号,在文学意义上来说此举无疑是成功的。但正如鲍德温所指出的那样,“比格的形象不仅加深了白人眼中暴力、兽性的黑人刻板印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能对真正的人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行有意义的探究”。因此这样的人物形象并不适合被搬上银幕。
因此,在《土生子》被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制片方“从电影艺术的特殊性出发,对电影的故事情节进行必要的改动以适应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及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尽管引路人引领疗伤机制的缺失影响了电影的呈现,但瑕不掩瑜,制片方选择偏重于在揭露创伤的基础上更多地加入人道主义的照拂,将原本尖锐的人物棱角化为环境压迫下的无奈产物,更强调“人性”而非“兽性”,这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这种人道主义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电影共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Fate命运”“Fear恐惧”和“Flight逃跑”,而小说原著中的篇章顺序则以“Fate命运”作为最后一章节存在。究其原因,小说中的比格是“亚人类怪物”般的存在,面对社会压迫他愤懑、暴力、激进、狡猾,而他在拼命挣扎后却还是被白人社会踩在脚下,他的命运才终于迎来终章。影片中之所以将“Fate命运”设为第一部分,实则是意在强调命运的牢笼虽不是可感知的、具象化的实体,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作为个体的小人物无论怎样挣扎,都只是在命运牢笼内的无意义举动,改变不了其最终走向。如此一来,影片最大限度刻画了美国社会对黑人群体的压迫排挤已经达到了不可抗力的地步,由此增强了比格悲剧性人物的渲染,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情。
其二,如上文所述,影片中虽存在引路人缺位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的可塑性和被引导性却比小说中更强。电影中的比格对于朋友的领导欲、控制欲和攻击性不强,愿意倾听建议,暴力倾向更低,不是一个纯粹的自我主义者。例如,小说中的比格主导抢劫计划,暴力且激进地将计划失败归咎于同伴格斯的迟到而不是自己的懦弱,而电影中他则作为从属成员,在抢劫与否的十字路口有了被引导的机会和自主选择的权利。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可见,电影更偏向于将比格塑造成为有独立人格的弱势群体,而不是小说中激进暴力的亚人类,彰显了电影制片方对于人性的关怀和对于公平的、适合心智健全发展的社会环境的追求愿景。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与文学作品相较,分析了影片中引路人疗伤机制缺失的原因:主要是艺术形式和社会历史环境两方面因素所造成。虽然影片中存在引路人缺位问题,但瑕不掩瑜的是,影片制片方所突出的人道主义观照,这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多元化的现代,不同媒介间的互文性改编愈呈欣欣向荣之势,在极大地丰富精神文化的同时也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兴起繁荣。文学经典作品《土生子》能够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再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是文学与传媒两个领域的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