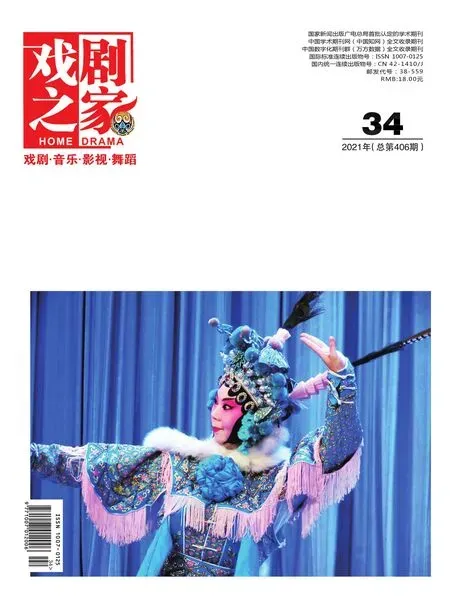论诗人纪录电影的艺术特征
——以《掬水月在手》为个案
张浩鑫
(平顶山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诞生出了一批优秀的纪录电影,比如说《二十二》《冈仁波齐》《摇摇晃晃的人间》等,这无疑引发了人们对于纪录电影的关注。2020 年上映的《掬水月在手》更是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关注。《掬水月在手》通过诗性唯美的视听语言和独特的叙事结构,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出了诗人这一群体独特的个人魅力,折服了大批观众,也赢得了业界的口碑。
然而学术界对于纪录片的研究大多数都在“真实性的辨析”“叙事策略的研究”“视听语言的运用上”等,很少对具体的某一类型的纪录片进行研究,特别是当纪录片作为一种商品上院线的时候。与《掬水月在手》比较类似的纪录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也主要是集中于视听语言、人物形象上的分析。作为新上映的《掬水月在手》,相关的研究就更少了。
《掬水月在手》作为一部诗人纪录电影,纪录片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受众不可能像商业电影那样多,而讲述诗人的传记又会使本来就不多的受众变得更少。因此这类电影的票房不可能像商业电影那么高,但是相比较而言它依然取得了同类电影中的高票房。目前学术界对于《掬水月在手》的研究,只有寥寥几篇,且集中在审美特征上。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以《掬水月在手》为个案,对诗人纪录电影的艺术特征进行论述,为探索诗人纪录电影的发展方向作出贡献。
一、诗人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
(一)双线叙事构建全片
纪录电影尽管有着“客观真实”的要求,但不可避免的是,一部纪录电影的诞生离不开导演在其背后的推动。但是,相对于商业电影来说,纪录电影中导演的介入相对来说要少许多。对于《掬水月在手》来说,导演的存在就是用影像沟通叶嘉莹先生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的个性创作。然而,电影的时间有限,与整个人的一生相比电影的时间不过是一个记忆的瞬间而已。只有通过讲述传主生命中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散发出无限的人性光辉。而《掬水月在手》作为一部诗人传记类纪录电影,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诗人从自身的生命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诗歌精华。所以,影片既采用了叶先生的诗歌来作为叙事的脉络,又用四合院的院落结构进行叙事。
诗歌始终是影片的主要元素,叶嘉莹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咏莲》《咏菊》等初作的诗歌是当时尚幼的叶先生对于当时情景的所思所感。《哭母诗》则是对母亲突然去世的悲痛之情。来到台湾后“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是叶嘉莹先生与恩师的师情和友情的见证。叶先生对于诗词的理解越来越深厚,尽管身处乱世半生漂泊,她却从未消沉和自怨自艾,而是从诗词里面得到救赎的力量,从自己所作的诗歌中得到灵魂的解脱。年过半百之后,叶嘉莹先生就已经开始辗转各个地方,讲解杜甫、陶渊明等人的诗词,传播中国优秀古典文化。诗词伴随着叶先生的一生,她用诗词构筑了自己的生命章程。影片运用诗歌作为脉络,既表现出叶嘉莹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又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诗词的意境和审美价值。诗歌就像是一条时间轴一样,揭示了叶嘉莹先生传承中国优秀古典文化的一生。
除了诗歌之外,另一条叙事线索则是四合院的院落结构。影片用四合院的院落结构,把全片分为六个章节。大门讲的是叶嘉莹先生小时候的经历;脉门讲的是叶嘉莹先生所受到的诗歌熏陶;内院讲的是叶先生的求学之路、与恩师的情谊以及诗艺的成长;庭院和西厢房则是讲叶嘉莹先生对于中国优秀古典文化的传播;而最后一章,则是“无”。这个无,代表的是叶嘉莹先生从故居离开辗转漂泊的一生,到头来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也暗示着叶先生精神层次的提高,代表着叶先生进入到了深邃的精神世界,也是叶先生超脱广阔的生命空间的象征。
诗歌的时间顺序叙事和四合院的空间结构叙事,两者相辅相成,生动形象展现了叶嘉莹先生命运多舛的生命经历和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得叶先生的人物形象更为立体化,摆脱了只有文字叙事的单一叙事结构以及可能出现的对于文学理解的偏离和断裂。诗词时间的深结合了四合院结构的厚,构建起了全片立体的叙事框架。
(二)传主与他者相结合的叙述
诗人就是一座行走的宝藏,生命的经历激发其创作灵感,从创作中又能使生命更加的纯炼。诗人纪录电影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影像呈现出来,让诗人的精华滋养更多的人。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需要影片的真实性,而纪录电影无疑是最好的题材。然而纪录电影的拍摄手法很多,对于诗人这样的群体,显然自我陈述式的模式更加适合,也能够更加的真实一些。
运用传主的自我陈述的回忆式纪录,能够对当时的人物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真实的描绘。通过叶嘉莹先生的陈述我们能够准确地知道她一生的经历,年少时的受教育经历、离乱的半生、不惑之年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竭力传播等。在这些描述中,一个漂泊一生、经历坎坷、富有诗性的女子形象亭亭玉立在观众的脑海里。也使得我们看到了诗歌与叶嘉莹先生之间的关系,叶嘉莹先生的苦难经历成为诗歌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来源,反过来诗歌的创作又使得叶嘉莹先生能够站在审美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影片通过叶嘉莹先生的自我陈述,来展现叶先生自己的一生和精神所得,这样做尽管能够使得影片更加的真实,然而,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情”难免不让人怀疑其真假,所以影片又采用他者的描述,即叶先生的学生和熟人。用他们的话来进行对照和补充,对影片来说,多了一个视角丰富了影片的叙事结构,对于叶嘉莹先生的人物形象塑造来说,则更加的丰满可信。比如说,叶先生自创之词“弱德之美”,在文中叶先生自己对其进行了解释,就是说“弱德之美”不是说人的软弱、弱小,而是说,一个人在面对不断来临的苦难和悲痛的时候,他能够不断地前进,能够一直拥有良好的心态,能够心态平稳。影片又通过叶先生好友的叙述对叶先生如何体现这个品质进行了描绘,叶嘉莹先生在晚年面对女儿和女婿的突然去世,万分悲痛,然而叶先生也只是第二天面对人的时候眼圈红了一下,就过去了。这不正印证了之前叶先生所说的“弱德之美”的含义吗?
不管是传主的自我陈述还是他者的评述,这些都是导演有意为之。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和表达一个影片的主题,使得零散的采访材料系统化、条理化。对于《掬水月在手》来说,陈传兴导演如此作为,是为了表达诗歌与个体的存在关系。也从中可以看到,陈传兴导演对于叶嘉莹先生与诗歌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体现出陈传兴导演对于人文历史传承的责任心。从《他们在岛屿写作》到《掬水月在手》,进入陈传兴视野的文化名家们大多出生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半世飘零几多艰辛的生命历程,见证了现代中国从内忧外患中走向现代性国家的历史轨迹。个人的身世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的生命历程是中国走入现代历史的一个个缩影,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文修养是对文化传承的有力推进。
二、诗人纪录电影的视听语言构建
(一)象征、隐喻镜头的运用
诗人纪录电影主要是讲述诗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面对的人生抉择,以此透过诗人的生命经验窥探诗人的精神世界。每一位诗人都是与当时的时代息息相关的,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关系,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构建起诗人与诗歌以及他们与当时时代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叶嘉莹先生作为一位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几乎相符的一位古典诗词学者和诗人,影片应该怎样拍摄才能构建起诗歌与个人、时代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同时又能体现导演的创作风格?所幸《掬水月在手》这部纪录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比较完美地构建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掬水月在手》作为一部诗人纪录电影,为了展示传主的诗性与人生境遇,采用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的镜头影像。运用大量的空镜头来表现古代壁画、孤舟、枯荷等景物,其中用枯荷、旗袍等物件来暗喻叶嘉莹先生人生漂浮、命运多舛;用古代壁画、石雕等文物来表现叶嘉莹先生自身的文化沉淀。每一个空镜头都有自己的使命和韵味,开始的“荷花”不就是叶嘉莹先生小时候的名字,当然这只是第一层的含义,第二层含义不就是暗喻了叶嘉莹先生和荷花一样吗?荷花生长于淤泥之间,却清丽自然,洁身自好。叶先生出生于中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却在人世的沉浮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绽放了自己的精神之花。“孤舟”作为一种意象也出现在影片当中,暗喻叶嘉莹先生命运多舛、孤身漂泊的一生。像“荷花”“孤舟”等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多表示诗人的修养德性和身世漂泊,这样的构建无疑就会使人想到诗人命运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关系。《掬水月在手》就是通过大量的空镜头来隐喻诗人的生命经历,而同时又能够表达从中得到的审美感受,构建起了一种诗意的空间。
这些象征、隐喻空镜头的运用,也构建起了诗歌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关系,正印证了王国维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表现出“现实命运”与诗人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命运多舛的一生使得叶嘉莹先生经历了常人所无法经历的事情,而叶嘉莹先生从小培养起来的诗情又使得这份经历转换成了一种自我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成就了如今的叶嘉莹。如若不是母亲突然的去世,也不会激发叶嘉莹先生写出悲戚之作《哭母诗》,也正是因为创作了《哭母诗》,叶嘉莹先生才能从另一种维度得到心灵的慰藉。叶嘉莹先生从诗词中得到慰藉和救赎,也从这些慰藉和救赎中成就了自己的诗歌。
(二)以音乐构建个体与诗的关系
在一部纪录片中,创作者更多会在构图、色彩、镜头运动等视觉艺术部分下足功夫,而对于听觉艺术方面则只是单单地运用同期声、解说词等,音乐在纪录片中运用的很少。归其原因可能是认为,纪录片要保存其真实性,而音乐的运用却是过于主观了,可能会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性。其实不然,在一部纪录片诞生的过程中,在一开始的策划阶段,就早已注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但是,这个主观意图是基于对拍摄者的长期走访、调查建立起来的,其本身就有一定的真实性。音乐完全可以根据整部影片的基调,进行听觉上的再创作,把音乐元素和其他元素构建在一起,服务于影片的真实性。这样把音乐元素加进去,反而更能体现影片的主题,增强影片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在《掬水月在手》这部电影中,导演陈传兴为了使得影片与传主达到一种诗意的和谐,不仅仅在镜头上下足了功夫,在影片的音乐上也卯足了劲儿。陈传兴远赴日本请来佐藤先生为这部影片创作雅乐《秋兴八首》。而《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先生重要的诗学成果。叶先生对杜甫的诗歌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谈到我国旧诗演进发展的历史,无疑唐代是一个足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杜甫是这一座大成之诗苑中,根深干伟,枝叶纷披,耸拔荫蔽的一株大树,其所垂挂的繁花硕果,足可供人无穷之玩赏,无尽之采撷。”《秋兴八首》是杜甫所作,表达杜甫的身世之悲,离乱之苦,是杜甫生命的写照。以此谱曲并作为贯穿全片的音乐,无不是在暗喻叶嘉莹先生与杜甫的某种情感共鸣。
把《秋兴八首》谱曲成为音乐用于全片:其一,是用音乐来服务于影像,烘托主题。影片中有着大量的关于文物的空镜头,这些充满文化气息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物加上深沉、浑厚、委婉起伏的音乐,增强了影片的文化氛围,突出了影片诗歌与个体存在的主题。表现出诗歌文化的厚重以及个体从诗歌文化中感受到的生命意志和审美感受。其二,是参与叙事,完善叙事,体现节奏。纪录片尽管是一部真实性的纪录电影,但是它和其他故事电影一样,也需要有一种节奏。诗人纪录电影尤其如此,显然一直听着传主的陈述,会有些烦闷和拖沓。而音乐的加入,不仅能够缓和观众的浮躁情绪,还能够参与叙事表达传主的精神境界,更能使得观众透过音乐产生审美的享受。用《秋兴八首》里面的诗作词,谱成曲,既能表达原作者诗歌中的审美境界,又能够为影片增添艺术氛围和诗性,从而观照叶嘉莹先生的精神世界和她的文化沉淀。
三、结语
《掬水月在手》作为一部诗人纪录电影,无疑是成功的。导演运用唯美富有诗性的视听语言以及独特的叙事结构,既表现出传主的文化沉淀和精神境界及其一生的经历,又表现出导演自己的个性创作和导演自己的表达意图。无论是叶嘉莹先生还是陈传兴导演,他们都是文化的摆渡人,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叶嘉莹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研讨会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