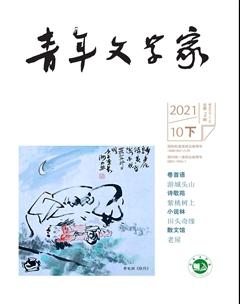《论语》文论与《诗经·小雅》的关系研究
周婷
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文论,文论与文学家的创作关键、人生理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和孔子弟子的言行,其中蕴含着儒家思想深远的文论内容。而《诗经》也是孔子整理出的文学名著之一,所以以上二者势必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便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刻论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代表,其中,《论语》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的言行,是孔子思想关键、文学定位的主要蓝本,可见,孔子的大量文学思想、观念定位都融入其中。《诗经》是孔子整理的诗文集,其中,准入原则、诗文内容都与孔子的看法和理念具有深远的关联性,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才能够一探究竟。
一、《论语》文论的立论基础
(一)关注现实人生
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滥觞便是《诗经》,其中的绝大多数诗歌都展示出了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现象。在《论语》中,这种创作内容也有很多,例如:“务民之义。”在《论语》中,孔子对前世今生之说敬而远之,将绝大多数的研究重心都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学习、修身中,将这种生活理念传递给学生。
根据文献研究能够看出,孔子在文学领域内已经逐渐转变了传统意义上“往生”的思想,认为生而为人,应当关注自身的生活和学习,将重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自身发展中。往生是虚无缥缈的,而个人的品质和学识是能够后天养成的,孔子在教学中力求能够提升学生的品质和风骨,这些都需要努力刻苦地学习,并不是一味敬仰往生。与其敬畏这些若有似无的“神仙”,还不如关注民生,解决生活中直观的问题。由此能够看出,《诗经》中的现实主义色彩十分浓烈,对民生疾苦的关注程度十分鲜明。
(二)未体现人的天性与自然规律
物候诗在《诗经》中的比重也很高,这类诗文详细描述了自然规律的变化和形式,但是讨论的重点却不单单局限在这一方面,将自然现象作为农耕生活中的“基础”,强调的是人们通过的后天努力,获得丰厚的成果。“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见,每一个人出生之后的天赋是不同的,通过后天培养能够获得良好效果,这也是孔子教育观念的集中体现,他并不在意人出生时的能力,而是竭尽所能对其进行培养和教育,也是关注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表现之一。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见,只有在付出了全部努力之后,才能够将自身的成长和未来“听信天命”,在付出全部努力之后,没有任何遗憾的同时也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结果。
(三)避谈人的来世
《诗经》中的作品对于人们前世、死后的内容研究较少,最“大尺度”的言论则是涉及死亡的论述,强调人们应当珍惜和享受现在的时光,例如《论语》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指的是,你对现在的生活都不甚了解,那么又怎么能够奢求知道死后的生活呢?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人们应当关注生活本身,而不是费尽心思探究死后会面对怎样的境地。一旦过于执着某一时间段的情况,就会忽视当下面临的生活。可见,孔子对生活的态度是谨慎中带有积极因素,不执着、不武断,以饱满的热情面对生活中的点滴,而对于来生,也仅仅是沉默。
二、《论语》中的文论
(一)“兴观群怨”说
《论语》中的文论有二,其一是“兴观群怨”说。这个文论主要关注诗歌对现实的作用。“兴于诗”指的是,正统的诗歌应当有指引人们前行的作用,在写作、学习诗歌的过程中需要从中学习端正的观念和知识。
“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认为,不学习诗歌礼乐就不能讲话,也不会讲话,诗歌和礼乐在人们成长过程中具有教化、指引的重要作用。诗是“群”的基础,使人能够融入社会群体中。由此也能够看出先秦时期对诗书、礼乐的重视程度,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生活的需求、性情的养成、价值观念的塑造。在《论语》中,对人性、品格的最高标准便是“君子”,只有成为了君子,才能够明理、儒雅、大气,成为社会中的表率。《诗经》中也有大量对礼乐的定位和追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便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述。
(二)“思无邪”
对“兴观群怨”說作补充的是“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语出《駉》:“思无邪,思马斯徂。”其中,“思无邪”的意思是思虑但没有邪魅。孔子利用这首诗来展现出《诗经》的正统和纯粹,也成为后世长久以来对《诗经》的评价之一。“思无邪”的评价标准是基于诗文的社会意义产生的,要求诗文中能够展现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但是却没有邪魅、歪曲的理念,即便文章中的整体基调呈现出思念、困顿,但总体的情感也是积极向上的,能够给予读者激励、引导。通过对《论语》的研究能够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引导人们积极入世、努力学习的,关注社会个体对时代、国家的作用,二者的思想理念一脉相承。
三、《诗经·小雅》对《论语》文论的体现
(一)《诗经·小雅》与“思无邪”
《诗经》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成为后世儒生作诗的典范,并作为固定教材流传于世,其雅正的思想得到了古来儒生的一致认同,成为诗歌思想性的要求。《诗经》中选录的大量内容都能够看出“思无邪”的理念,即便是对战争的反对、对亲人的思念,其中也能够寻得哀而不伤的韵味。在《采薇》诗文中,详细描述了戍边战士的辛苦,但是这种苦痛的来源却被作者定义为“玁狁之故”,诗文整体的风格和表现十分正统,其中暗含着的情感也是绝大多数百姓的真实感受,能够充分展现出“思无邪”的特点。
《南山有台》中的表现形式略显风尘,但是此时的君主统治的确可圈可点,社会局势安定,百姓生活较为富足。其中,从“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中能够看出,当时的文人认为,稳定的国家是百姓生活的基石,统治者需要将“法制”和“人文”观念联合使用,才能够治理好国家。而儒家思想中对于优秀君主的定位也是如此,二者观念趋同。
根据上文能够看出,《诗经·小雅》中的内容与孔子强调的“仁”“礼”不谋而合,既能够展现出社会背景,也能够体现出人生追求,展现出文论与《诗经》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出孔子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别样基调。
(二)《诗经·小雅》与“兴观群怨”
《诗经》中的诗文主要表现形式是“兴”,主要表现效果则是“观”,最终的表现目标则是“群”。而“怨”主要体现在怨刺诗中。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也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除了写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以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赋、比、兴是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四、结论
孔子在先秦诗歌中甄选出“诗三百”,也是自身文学理念、哲学研究方向的展现。在《诗经·小雅》中能够看出与《论语》文论的相通之处,从《诗经》中能够看到孔子的文学态度,从《论语》中也能窥探出孔子的文学思想。这一论题将是众多文学家、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需要不断挖掘、逐渐拓展,为我国传统文学研究填补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