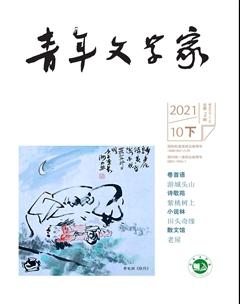五哥
赵天赐
“山湾”是个不大不小的盆地,四周环山,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松花江,如过客一般缓缓驶入,静静流出,从不打扰“山湾”里的世间万物。老一辈人经常对小辈念叨,“山湾”是命根,从“山湾”里走出的孩子要有德行,不能忘本;老一辈人还说过不要妄想逃出“山神”的手掌心。
老人们说过很多的话,有的留下了,有的被遗忘了,本来这些话是要集成册子或刻在石碑上的,但至今都没有人能完成这个“宏大”的工程。我很困惑,曾用白菜心大小的脑容量认真分析老人们说过的话,却总也想不出个子午卯酉,更不敢嘀咕出来。五哥比我勇敢,在我眼里心上他是个勇士,是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为什么说他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五哥也曾这样问过,我告诉他,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兼思想家“鲁老爷子”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五哥每次听我这样的夸赞都会搓一搓头发,抹一抹脸。他说这是先人借用我的口对他的鼓励与鞭策,凭我这锃亮的脑袋是绝对说不出这样伟大的醒世格言。五哥说要向“鲁先生”看齐,要悬壶济世,要批判社会的不公,要正一正社会的风气。在我们眼里,社會很大,山以内的都叫社会,山外的是什么?我只听五哥说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秋”,所以我觉得山外有青山,有高楼,有西湖,有歌舞,五哥说我是个土包子,只会啃书本,不知世界之大,不知烟波浩渺。五哥说得没错,我只会啃书本,仅能记住书上的几句话,仅会背几首课本上的诗句,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山外面到底有什么。
“五哥勇士,你说山外面还有啥啊!”我递给他一个夹了咸菜的馒头,“咸菜是我妈做的,她说你瘦,得多吃点。”
“这个嘛,说多了你也记不住,知道那么多干啥!”他斜了我一下,躺在稻草垛上,咬了一口馒头。
“五哥,我也要做勇士,不,是做勇士的跟班,谁要欺负你,我就揍他。”
“就你?瘦得像狗尾巴草,风一吹就倒了。”他又咬了一口馒头,望着天上的云怔怔出神。
“五哥,别舍不得吃,我家还有猪肉馅的包子,这就给你拿去。”我欲起身,五哥便把我唤住了。
“天儿,你看这云一会儿变成羊,一会儿变成马,一会儿变成鸟,一会儿变成鱼,地上有的天上都能变出来。”他叼起草棍,跷起二郎腿,把我按了回去。
“山外面有人,他们都背着书包游山玩水,山外面有楼,比五指山还要高的楼。天儿,我要做天上的云,自由自在地飘,想怎么飘就怎么飘,高高在上地飘,要飘到上面去,飘到比五指山还要高出一个五指山!”
“五哥,那飘不出去呢?”我担忧地看了他一眼,“听奶奶说咱们都命中注定要待在山里伺候庄稼,插上翅膀都飞不出去。”
“没出息,看你那针鼻儿大小的胆儿,挖地洞我也要把这座山钻出一个窟窿。”五哥腾的一声站了起来,油亮的头发上插满了细碎的稻草,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一瞬间迸发出来,直冲云霄。天空的老鹰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后飞走了,电线杆上成群结队的乌鸦刹那间四散开来,村子里不知谁家的狗大声地叫,远处飘来了一股旋风,卷起了一堆又一堆枯败的稻叶,带着一粒又一粒尘土飘向远方。我思绪杂乱,无处安放的眼神终于找到了指甲缝里残留着的深绿的咸菜叶,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呼唤声将我拉了回来,在挪了一小步后便撒开了腿奔向家里。
我好像忘记了离别时对五哥的鼓舞,但我会如往常一样一直鼓舞他:五哥是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我的头发剃了好几茬,剃头的次数少了,见到五哥的次数也少了,从半个月一次,再到半年一次,最后一年一次。头发春天剃掉,冬天留起来,就像我家里养的那几头羊一样,剃头的推子也是剃羊的推子,我就是羊,羊也是我,谁是羊,谁是人,在我眼里都不及五哥重要。我很憔悴,像一根黄瓜一样,由外到内的憔悴。憔悴到看见水银便想起了时间。
时间凝滞般缓缓地流动,与其说流动,不如说“蛄蛹”,往前一段的同时,也得向后退一步。在我的意识中时间就是这么个样子:头发剃掉了,个子长高了;山羊下崽了,老羊卖掉了。我好像窥到了时间的流动,却瞧不明白五哥的心思。五哥说得对,脑袋锃亮的我,想也想不出什么东西。在我眼里,月亮一天一个样,不是大一点,就是小一点;太阳也还是那个太阳,再怎么变换颜色,我依旧能认出它。当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不再观察太阳和月亮了,与山湾里的孩子一样,走上了父辈祖辈都曾走过的路—伺候庄稼。山湾里的人都说庄稼是绿色的,我看不出绿色,从远看往近瞧,即便拿出放大镜看,庄稼的细枝末节也都是砖青色的,这种颜色只有我和五哥见过,还是他告诉我的,山外有山,有楼,有青砖青瓦的楼。
在我刚刚学会如何播种,如何插秧,如何撒肥的时候,五哥来看我了。他衣着朴素,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我在阿花的身上闻到过这种香味。五哥长高了,他背了一麻袋的书放在我家里,说是送给我的,但被我母亲扔了出去。五哥与母亲大吵了一架。转天一早,母亲给我带了干粮,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我和五哥送上了前往山湾尽头的牛车。牛车缓慢地走着,我和五哥枕着用麻袋包裹的行李,身下的杂草细软抚人,天空中的老鹰带着小鹰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着。五哥说他已经走出了一条路,也想带着我走这条路,他说人就是云,云散云聚,缘生缘灭,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但是过于自然也不好,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崇拜地看着五哥,他搓了搓头发,抹了抹脸说道:“是‘鲁老爷子说的。”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得自然、洒脱,空中的老鹰踩着云朵划走了,渐行渐远,只能听到风声与老牛的响鼻声。
我记不清什么时候坐上开往县城的客车,更记不清什么时候上的中学。对我来讲时间就是一堆藏在地窖里的白菜,存得久了就烂了,也像仓子里摆放的一颗颗大葱,时间长了也就枯干了。我意识到人得往前看,向前走,毕竟时间总体上还是前进的,跟它掰腕子、摔跤,永远赢不了。于是我蹲在宿舍里,躺在操场上,不断地看书。为什么看书呢?我不知道。但是五哥临走前告诉我,真正的勇士是需要读书,因为勇士得面对惨淡的人生,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我问五哥缘由,五哥说,读书就像插秧,插秧前得买种子、化肥,但是这些都不够,还得支大棚、育苗,火候到了,才有资格插秧、施肥,最后才会有收获。我非常认同五哥的说法,也更加明白,做什么都像插秧一样,得认真踏实,还得有远见、有计划。五哥就是我的远见,就是我的计划,他说我不仅身体弱,精神上更弱,警告我别胡思乱想,做好功课,多读书,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