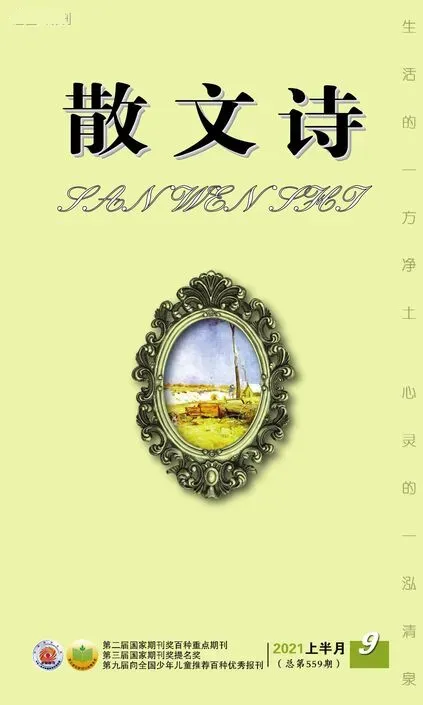答在问处
◎张首滨
一句不做一句答
来就来,还带一缕风来,
那只会说话的鸟说。
来人自寻一石小坐,并问之:冬樱见到雪都说了些啥?雪是自个儿来的吗?我看一眼天空,见一朵云飘过,便答:雪与云是一起来的,与冬樱说了什么没听到。
那只鸟说:这风有一味,上不在上,下不在下,可入定。来人闻声问鸟:你来自哪里?谁教的这话。鸟说:来来去去不一个。
枝上有光闪动,红又起,冬樱无语,花瓣片儿片儿落地有声,是窸窣不可翻译。
我问来人:这风缭绕不散,有另外一种古隐的范儿,很幽玄。来人顾左右而言他:清明时节身后是不是草长虫叫的五月?这一树冬樱花怎么说没就没了,去了哪里?
来这里只为这个?
那只鸟听后,一句不做一句答。
去就去,还领一缕风去。
我的名字
他喊第一声,我没有听到,听到的是第三声。我怎么知道是第三声?他说了这么一句:喊你三声了,咋才听到。
我说我正在梦里,我有个午睡的习惯。他不再啰嗦,抬手把信件递给我。这个信件从哪里来,谁寄的?我问。他说:自己看。随后转身没影了,样子一点儿也不像是送信的。
我紧忙打开信封,见里面一片空白。我用力抖了抖,接着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声音,从里面不慌不忙地落下。这是什么?我带着疑问弯下腰看了一下,不看不要紧,一看大吃一惊:
那不是别的,正是他刚喊过的那三个字——
我的名字。
一波动众波皆动
阳光从八点处斜横过来,光芒仍灿,
照在逶迤的水上,烟波千里。
我在岸边小憩,不是无聊,是有点闲意思。距我三至五米远,忽落一白鹳,如雪里出,白得耀目,蹲在一块石头上。它不挽裤脚即是不想涉水,如我一样在做一种姿态,在等待一物?然而,终不见一物的出现。
半个时辰已过,我觉得臀下有东西蠕动,欠身一下,一只甲虫出现,活蹦乱跳,像个旧相识,问是谁家的,为何在此,它不点头也不摇头,不知无不知。于是,我避让挪向一垂钓的人,那里的安静也是最多,便有语无声与他看钓钩。
钩有饵,这个鱼看不到,我却知钩去处,这样也就不迷惑。随后一道水从我的虚怀里,那般轻盈,圆融,无惊,一滴未失地倾入到远方。呃,俗世间有这道不惹是非的水真好,潺湲、潋滟、荡漾、绿如蓝。
就在我内心感叹的一刹间,那垂钓的人叫了一声:该来的来了。他说的是什么?我似懂非懂,只见一条白浪一跃,有影无形顺着钓线爬上。
——这时候万籁俱寂,
一波动众波皆动。
只是一个影子
他挥一下拳头表明有力量,说小区每天都是平安的。
他是小区的保安。
无风亦无雨,
寂寂静静。
昨夜我家树上的那颗欲熟的菠萝蜜丢了。我告诉他。“怎么会这样。”他先是一惊。接着他打开监控,一段一段反复地查找,我也在一边睁大眼看着。突然,他指着模模糊糊的荧屏上说:“找到了,就是这个人!”我听后紧忙对他说:“赶快去找啊。”
时钟在墙上,
嘀嗒复嘀嗒。
他看了看我,然后原地未动,摇摇头,
无可奈何地说:“这个人留下的,只是一个影子。”
留在门上的声响
那个人究竟敲了几下门?
有没有谁数过?
芳菲不是自己走过来的。属于粉末状的情感花粉,大多生长在寂寞上,而嗅觉灵敏的蛾子,挣脱夜晚的怀抱,从一排阑珊的夜色后面、我的面前过去了。怎么过去的?没看清楚,急匆匆,急匆匆后还有一个扑朔迷离的莫名其妙。
恍惚啥时都有,此刻一片叶上的露珠,分不清明暗的关系,爬入一只眼睛里。在我说到它时,它已被一只鸟啄住,但刹那间,那只鸟又被另一只手拿走,无常,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
留在门上的咚咚声响,
风轻轻吹着。
不是心的东西还有多少
风来风去,都是片刻。
去年栽种的芭蕉,今年长高了多少?宽大的叶片,在这虚实参半的夜里婆娑,自言自语。
有鸟归来不入巢,因巢中动静不明,
叵测的事,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虫鸣空更幽,推开又关上门的和尚探头三五寸,悄问夜深,深到几许了?这时有云走来,而且不止一朵,都抱着东西。
天气预报说,十二小时内局部有雷阵雨。远处奔驰的车轰隆隆,一会儿从东边过来,一会儿从西边过来,有雷是否也带雨,无从知晓。
夜不归的稻草人是草里汉吗?
画一方土为居,也是一番小自在。
哪里也不想去了,半生都在曲折的路上蹒跚,该静下来把堆放在胸里的俗事整理一下。真的,我这样做不为什么,只想知道:不是心的东西,在心里还有多少。
秋的白
霜来自哪里?落到地上,凉凉如孤寞。
从画面外走来的鸟,趔趄也是鸟,俗名叫寒鸦。叫寒鸦也未见寒到哪里去,当然,霜后腿脚的肤色会浅一些。
得再说一次,霜还在路上,怎么个霜法?路上是否光滑、难站稳脚跟?朦朦胧胧,只有一个人可以透露一点消息,那就是谶言的持有者,可他又往往把话讲得晦涩,不易解析。
西风常见,西边不常去,但西的西边有个影子不浓不淡,依稀可见,恍惚如昨,也许是那个人,也许不是,弄不清楚那便是想见而不得见的。我这般敷衍,是有黄叶要来了,黄叶的事,一般都比霜的事来得突然,飘忽而揣测不定。
霜来了会是啥样?啥样都是这样。
翘首举望——所有的色都不是霜的色,只有秋的白。
已不是雪的事
无叶生发的寒日,
很久没有看见的梅,偎依着雪而红。
始自岁月深处的风,为何来?在沉寂中辗转、飘移,像是跟随着什么往虚空里去。
这时来一杯酒,不温自热,怀里升腾着一缕耐品的古意。雪在哪里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白,但雪在这里有白不说白,只说如月光,其余的话不说,玄奥就在这里。
举望大千世界,天苍苍地茫茫,众生相皆在熙熙攘攘里躜动,然而,大凡是雪都要化去,落在心中的雪化去后做什么?
做什么都有个讲究,这个不说谁都知道,
那已不是雪的事。
不经意处
来去,无需留声。
可以冥想,也可以睁一只闭一只眼,此处只有一个自己,坐着也累,就此躺下也无妨。松软的草亦不是寺院里才有,能化蝶的虫亦不是春天里才出。
随心所欲,任性是一种活学活用的方法,
不惹尘埃,在哪里都会踏实。
那是啥时候的事?还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不如这般:让梦做梦,让幻变幻,自己闲着。那样,可以进一步去感知:云的白怎么个白,花的香怎么个香,石的凉怎么个凉,所以,我愿在喧闹之中取喧闹之外的静,一切都是纯真澄怀的好。
这时,除了我这样还有谁?
在不经意处——角落的那地方站着一棵小菊。
清静不会落在别处
云有卷时,
也有舒时。
据讲,那场风,大于想象,吹去了周围所有的颗粒,也包括大小的响声,然而,你的心思一丝没有动。
平稳,不是什么,
却坐得安静。
胸中的旧事物一个一个去了,那个新的一步一步走来。路宽且漫长,你没有嫌慢,只言耽误不得。
等,是迎的过程;
迎,是等的进程。
此刻远和近之间,有鸟无影悄然划过。
你坐于一扇有郁郁芭蕉的窗前,喝着一壶茶——做着眼里没有天下,胸中没有自己的状态。但是,不管啥时候,清静都不会落在别处。
你喃喃自语:
那时这样,
现在也这样。
那风走动有回声
风里有风的那个风,
咋说来就来了?
我转身坐在一把凳子上。第几日了。无应答,自己问自己,不用应答。神在一隅的龛中,时钟在粉刷过的墙上,其他的,也按部就班在其位。
关上那扇门,闭户读书,读的是哪一个自己?抬头望一眼隔着一块玻璃的天空,如隔着一段恍惚的记忆,模糊中似有云彩走过,我听到了往日斑鸠叫的那么一两声。
为之我喝下一杯老酒,旧情复发。在昨天与明天之间,一个不晓得孤独而孤独的人,从微信里走出又回到微信里,蜷起自己柔软的情绪。一朵已知是湿还湿的云,似梦非梦,在枯寞的枝上做了一个雨的回首。
然而,那风来与怎么来,我都能感知到——
那风走动有回声。
要凿的不会是它
晚上,听见楼道里有人在凿墙,叮叮当当,我没在意,因为邻居是新搬来的。
凡是新搬家的都会干这样或那样凿墙的事。早起我下楼出门,顺便看一眼墙上被凿的地方,只见一个手腕那般粗的洞,边缘残破,里头黝黑幽深,不知道邻居在凿什么。
正当我发懵时,突然从洞口处,莫名其妙钻出一只有头有脸的蜘蛛,只见它整体灰调,东张西望一下,叹了一口气,又不慌不忙转身回去。怎么会这样?
然而惊讶之余,我内心疑云顿起,反复诘问:是玄奥、梦幻,还是魔术?不懂就是不懂,小迷成大惑。但我可以十分地肯定,邻居要凿的不会是它。
雨,还在下
雨,落多时了,
还没有停下来。
这一日,是2009年1月8日。
望了望叫天空的天空,已不像天空,浑浊从上而下弥漫,仿佛是一种沮丧,一片乌蒙蒙,我对此有些不知所措。
什么时候开始看云能以不做看云状而观云的呢?气温零度的灰暗属于一种伤害。我怀揣一颗古典主义的胚芽,蜷曲在一团朦胧与困惑里。
气象台播报近7日天气情况都是阴雨,还用了一个有趣的词:“继续阴雨,阳光寡照。”就这么一个“寡照”,使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抑郁穿不穿雨具,亦是抑郁。
雨,还在继续,
然而,皆落在一个滴答里。
那个来不是这个去
来来又去,去去又来,
来去——是指什么?
一副药方子说:这病痛自己不痛别人。他认可后又问:痛即不痛与不痛即痛,哪个会更好一些?
新雨浇旧草。门外的事仍在门外几度发生,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则小短信,是古人比较雅兴“问梅消息”的那种。
一只从梦里起飞的乌鸫,不知落在何处。他向瞭望的地方看了看,没有一丁点动静。
今天是大寒第三日,谁也没有讲下雨,某一种雨飘至他的无遮拦处,湿了一片,一片有多大?不可说。
然而,有的还是要说的。什么是要说的?
他想了想:那个来,不是这个去。
带着雨离开
一只猫头鹰不是什么,顺着风向,
蹲在还是三维的空间里,在做不是说明性的响动。
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懂,一缕属于缥缈的光亮,从一支蜡烛的门缝走出,向那里张望一眼,没有了下一步,那里是哪里?
尽是无言,有言是一根琴弦在做着旧日的叙述,而翻飞的落叶如蝶,看见无大,看不见无小。当下许多事都不用了旁白,解答用心觉。
而此刻我要问另外的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他为啥要带着雨离开?
那里有个东西
这块石头什么也不是,就是石头。
看得见时是,看不见时也是。
一生的孤独,一生不问左右。
一生不上不下,一生守着内心的寂静。
有些事情很玄妙,他突然指着这块石头说:“那里有个东西,早晚要出来。”
“那会是啥?”
“什么也不是时,会是芽。”
这就对了
那是钉子生来应该在的地方。
但凡在高处,有仰望就应该挂点什么。
他执拗而痴心,往那颗钉子上拴了一只气球。
他说那颗钉子亮晶晶,像星星。没有说那只气球像什么而问我。那气球口袋状很俗,随风而飘动。我抬头看了一眼,想给一点诗性,便在一旁脱口而出:像装雨的云朵。他说太缺乏现代主义冲击力了,你再往深处想一想,琢磨琢磨。我真的一时感悟不出有啥新意来,于是一口气敷衍地说:像一顶被丢弃的贝雷帽子,像一只垂死的章鱼,像一个随时要爆破的谎言……啥也不像,就是一只欲瘪的气球。
他诧异地瞪着我大声说:这就对了!
那颗钉子也啥都不是,就是一颗钉子。
那个说话的人
雨有的时候比云先到达。
听见那个人念叨之后,我看看前后:前一半是雨,后一半还是雨。
古老的屋檐下,只有说话的那一个人。
不分左右的雨点,打在瓦上,砰砰,然而那声响好像不是雨的,也好像不是瓦的。
怪异的事,总会在意料之外发生,当我走入雨中的那一片刻,潜意识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说话的人已不见了,啥时候走的呢?
那里只有空空荡荡,
这时雨大小不讲,我只说,还在下。
树有三片叶子
这棵树有三片叶子,那只鸟在啄第二片叶子,而响动的是第一片叶子。
波浪想上岸吗?跟着波浪后的风上岸去了。
没有毛发的鱼捋一捋思绪,左右徘徊,是怕被那只鸟看见吗?那只鸟正在回望一只蹦来的蛙。
那风还是从蒹葭中吹过来,怎么没有一丝远古味?
一朵从高处下来的云,一点也不像云,不含雨也不白,而如烟丝丝缕缕,仿佛在做什么纠结,那只鸟看着很迷惑。
这棵树有三片叶子,那只鸟数也数不清楚:一不是一,二不是二,三也不是三。
平常心怎么走
青烟向晚,
风声依稀。
一只猫蹑手蹑脚有模有样的,在我的眼睛里转身去了它要去的地方。
淡淡的海腥与深巷里的烟火缭绕在一起,混合成另一种味道,从路的右边飘来,而我站在路的左边,装在脑袋里的东西,多多少少沾了些。
不远处,一只半蹲在水边的鱼鹰,头尾皆黑,犹如一个孤独,在垂钓悠悠虚空里的一抹云彩,那云彩有两抹,其中一抹已经淡入淡出。这时我正在若有所思,一座百年的尖顶教堂,时钟指针正指向十八时又三刻。
恍惚是某一个段落的开始,一个陌生的声音从一座老屋拐角处露头问道:平常心怎么走,走语言之前的活路吗?闻其声不见其人,过一会儿还是不见其人,散落的黄昏斑斑点点。
我只知道脚下的这条路通向我的来时路。
此时清寂,
比路上的青石板厚。
坚果和石头
与乌鸦搭话的,不是你。
在一边手握石头砸一颗坚果的是你。
你想取出那颗坚果里的仁,一时没能砸开。
那颗坚果表面光滑,色接近黄褐,和其它的坚果没什么差异,
可是不知为啥如此的坚硬。这些不是在这里要说的。
在这里这时要说的是,乌鸦头脚齐黑,
带着的那张十分锋利的尖嘴,也是冲着那颗坚果来的。
这个你已看到,然而,乌鸦和你的眼睛都盯着那颗坚果的同时——
有一点不一样:
乌鸦还盯着你,
还有手里紧握着的那块石头。
这时的雨
今日的雨和昨日的雨没什么两样,
是否还会淅沥?
那一把灰色的伞还在灰吗?我想它还会出现在某一颗雨下,它从不躲避哪一颗雨。
说到此,那支在路边怀里装满湿意的扶桑,随着风左一下右一下摇曳着粉红。一个背着身的人在公共汽车站牌下站立很久了,在等候谁?这时谁会来。不见烦躁,暮境茫茫中,只见他点燃一根烟,吐出的烟雾缭绕在雨里,没有打结。
我时不时举目天空,乃在寻找:一是命中的意象,二是梦里的暗喻。这两个先不说了,那颗悬而未落的雨现在怎么样了,还在那根古老的横枝上吗?
云愁天暗,人忧情伤。
此时的雨再怎么淅沥,
也只会这般落:
一滴跟着一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