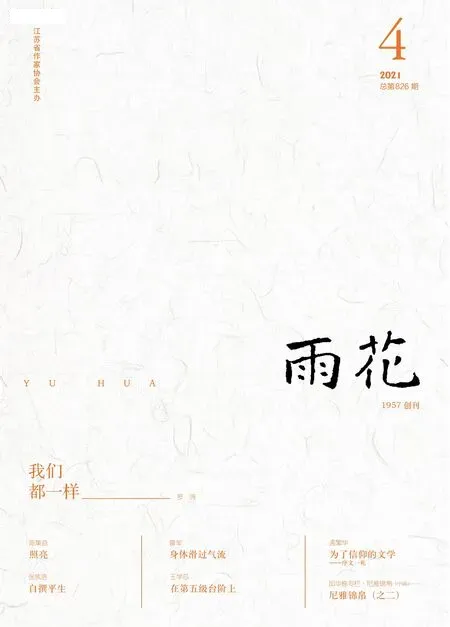青绿有神
宵夜帖
乡村秋夜,如墨水洇开,偶尔见光。闻虫声如织如雨,如玉米林里万籁流走,如梦如幻如棋中的匹马爬岭过岗。草窠里,叫乖子(雄蝈蝈,多像羞怯的男孩)一声促短,一声吟长,类似当年祖母纺织时的“唧”“唧唧”“唧唧”,岁月的金梭银梭啊,在织一匹梦的土布。间或停歇下,旋即复起。夜露深重,各种虫声近在眼前,却不知其所在,其所终。古人说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将入我床下。九月的乡村之夜,远看近看山色乃天色所化,混沌一块,墨色一片,黑暗深处却似藏有锦绣一团。我想起往日田野,稻茬约莫一寸高,风吹来,刮起干枯的草衣,还有着渐渐升起的黄月亮,一起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今夜月亮的黄铜锅子,沸起草木香、泥土腥气、缓落的秋露和牛羊鼾声,以及一大群不知名的静极的声息。四野阔大,一团奶油似的黄月亮,升起在东山。万物交会的一刻,我像大地的孩子贪婪注视:今夜月亮的黄铜锅子,掉进了土灶旁的大水缸,清水晃荡,它在孤独地舀啊舀,舀啊舀……
盆地
昨夜我梦见古皖之地的冶溪镇阔美、润圆。周遭无边荡荡的山峦、森林、悬崖似要倾扑擒伏——雨滴的音符铮铮,而法术的野兽、山妖、神仙以游鱼般出没不定之势,集体调整着暗黑中的身姿与呼吸。荆棘山道逼仄崎岖,月光如水,铺满银杏、古槠、香樟、枫香、紫柳、桂花,恍若舞衣锦绣斑斓,沿山而上,又有山鬼似的寂寂杉木、柳杉、马尾松、栓皮栎、青冈栎、黄檀层层包抄,围拥出驳杂奢侈、闪闪发光的扁头鲢一样腥凉的气息……一个吴楚过渡地貌的盆地,以盛放父性的初生山水为荣耀,是母性之硕大红盆的虚幻呈现和沉陷,亦是插秧伐薪采茶农人的劳绩之所。圆拱如月的卷棚桥下,人影、树影、桥影、花影相扶,人家墙角去年的南瓜如此浑圆,令人耽溺,像桥边永不会醒来的古老原野梦境:忧郁胶着的阳光如同红绿奔腾的雨水,持续灌入荒田里一匹睡卧的黑牛体内。
庚子年三月二十日,我在一马平川的冶溪镇晃荡。按照网上万年历所言,该日宜祭祀、祈福、开光、求嗣、斋蘸、纳采、订盟,忌开市、动土、掘井、开池。四野鸟儿发情,群群蜜蜂茫然得不知所向。广漠田畴的油菜花或开或谢,半开半谢,渐渐粗实隆起的茎干,如同女巫的绿色权杖悬垂膨胀的松果,溅起松烟阵阵——万物的枝条像一首叙事长诗,溢出了处处肥沃的山地雌性美学体系。
山中小盆地多有未名之美,人性之力,本心之爱,以及未名之美里永难言说的致命清新——
亦南亦北,冶溪乃女性古中国积雪映白的情意别册,在太湖、岳西、英山三县的结合部,浸润稻米之乡的妖娆和慈祥。摩托轰响,小车“突突”,沿地跨鄂豫皖三省四市的大别山南麓攀援,北达古寿州(一部分隶属皖西六安市),飘散霍山黄芽、六安瓜片的迷魂之香……西抵湖北黄冈,交杂板栗、酥糖、桃花、老米酒和甜柿湿漉漉而安静的晨梦……西北远赴河南信阳,与固始鸡、鲌鱼、麻花、高桩馍、商天麻、神仙饺在锅碗和药罐之间摇荡……而这里众多的森森古木,朴素深褐的历经千百年的木纹上,闪过新石器、殷商老器、犁耙、插秧机和大棚石斛的熹光,本色,自然,劳作,轮回,镌刻着生而为人的温憨和忍耐。
沿街漫步,翠光荡漾的茶叶、黄泥腌裹的鸭蛋、舞灯人、说书人、橡栗子豆腐、烤得半干的焦黄小河鱼、河汊的米虾,一种浓郁的菜市场属性的叫卖声,充满家常和市井的微妙与凌厉,是腌臜的、粗鄙的、块儿八角的,也是热烈的、喧闹的、生机勃勃的。
——清超幽迥又怅惘的绿国,灼烫为峰顶、天空、稠密的枝杈、破旧祠堂,以及黑发少年暗红发芽的情思。
老茶记
在姚河竹山,茶是春日的丝弦。
天空像个靛蓝的瓦罐,古老安静地卧着一些麦种。惊蛰、春分,麦种起身,孵出万千云朵、巉岩、沟壑、豺豹,以及广阔植被、蓬头山鬼和流速不明的溪水,山色被鸟声叫深了几寸。白云皴染,烟光、日影、露气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满山黄荆槎、南京椴、山拐枣、杜鹃、青冈栎、枫香、山桐子、冬青,枝叶或疏或密。而一丘丘、一畦畦的茶,在田畈上密不透风,只留几条狭窄的沟垄,供茶姑往来,背篓里似是星光阵阵。斜坡多乱石,乱石间多茶棵,均粗服乱头。我曾以为是“粗茶乱服”,“粗茶”与“乱服”才是绝配,门当户对。记得小时候偶尔在乡下割麦,着破衣破裤,眼前是令人眩晕的金黄一片,镰刀带来的却是望不到尽头的绝望,不到半小时,便腰腿酸软、汗流浃背,最后干脆一屁股坐下,拿起大茶壶,“咕嘟嘟”一气灌下,随即舒爽,筋脉通达四海五湖。这种茶叫黄大茶。
黄大茶不是明前茶,不是雨前茶。黄大茶是夏茶,皮老肉糙,凌厉的滋味像武师打拳。牛饮一碗后,却沉浮起肉体的欢愉。
黄大茶是堂鼓马锣的秦腔,繁闹轰鸣,泥沙俱下,回肠荡气。
明前茶是江南丝竹,清声泠泠。雨前茶是山地花开,蕊飞花瀑。雨后茶是苦行僧,叶气夺过芽气,如古刹映黄叶,灯下夜归人。
竹山的茶树老到风霜三五百年。三五百年够长,多少兴废,不问兴废。古茶园里,矮小蓬勃的二十多棵老树。其中两棵枝叶交缠互抱,主干碗口粗,苍老遒劲,附生绿苔。老叶上头簇簇新,俏立一芽,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依旧新嫩一片。新嫩像画在宣纸上的绿墨,有春水濡湿的糯软。老叶青碧,老叶里有苍苔气,味厚质苦。老叶苦心孤诣,捧起的新芽似乎不沾尘俗,如同游动的一滴滴清水,功到造化。树干不过一两尺高,苍褐深寂,老节拳拳突起如旧疤。皖地的茶棵不算树,亦不算草,亦草亦树,顶多灌木而已。与滇黔速生高大的乔木茶相较,虽小如累卵,一样日月悠长。
不多的农户,屋前屋后被春茶簇拥。茶园四布,散散落落的白墙黑瓦,像人神合谋的风景。
竹山人刘会根一生在山里浪荡,辟园种茶。他开车带我们从古茶园上山,坡陡弯急。其下深壑千尺,其上接云壤日。待抵达一狭长坪畈,注目苍苍处,新绿唧唧,阳光如煮,万种或翠绿或灼红的鸟声似剧烈的窑火历久不息,不舍昼夜地锐叫、跃窜,游映并铸出堆如山丘的浓香,波动的白云在天空邈远而又寂然……
凌云俯视,山腰的池塘如绿豆,人家的黑瓦卧伏如黑豆,采茶人如芝麻,只有蜿蜒的公路如白丝带,快系不住茶园的绵延奔放了。空气中膨胀滚烫的新绿,像从大砂锅里溅出的浓美汤汁。
一个小小的坪畈,地开两县。山北是舒城县白桑园,灌木和松杉葳蕤,迹近无路——舒城小兰花的经典产地。山南是古竹山,横柯上蔽,疏条交映——岳西翠兰的发源地、核心产地之一。偶见有茶农采得满篓鲜叶,视危崖若无物,开车或骑摩托飞速下山,我疑是现代版的乘鹤神仙。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云深处,刘会根与老茶树的彼此知遇,业已五十九年。多少白云苍狗中,他是制茶的神仙,他是自在的神仙,他是神仙中的化内之人。曲意款款心意相通,茶人的化境,树是人,茶是人,人亦是一壶大肚难言的茶啊。
青绿有神
天堂寨在金寨县。从岳西到霍山到金寨,一路肉色粲然。岳西是腴嫩的火腿,山高风响,山山层绿,柔韧交错,健美有力,山风映照游溢回旋出草木香。霍山也山山交错,山树形色似猪蹄,一碗风月宜红烧,宜酱拌。金寨是东坡肉,整整齐齐似麻将块儿,红得透亮。
红得透亮也是家常。家常最好,家常有肉最好,无肉也好。
岳西家常,霍山家常,金寨家常。好风景如家常话,好风景如一吊好肉,吊在火塘上,肉味年年香。
暮春初夏,一镇子羊肉香气飘远。不远处的天堂寨似在暮色中挂着,被风吹透,肉味鲜透。风干的羊肉多浅白深红,如落日西照,落日如大公鸡,从民宿的树巅迈步,间或古奥鸣叫: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老木桌旧纹簇簇,夜色披浓,灯火亲善。端上来的却是吊锅鸡。本来想吃吊锅羊肉,不吃也罢。
食肉长精神。遗憾也长精神,留待下次再吃。
家常烟火好在触动人心,莫名其妙。忆起我乡岳西从前的冬日,柴屋或披屋里总有火塘,松火烁烁,影亮人脸,上方用铁丝悬垂一口吊锅,漆黑柴烟如松墨,锅里渐渐“咕嘟咕嘟”,伴人声絮絮,满屋都是暖老温贫的静美。
民宿也好,好在不雅不俗,一派本真。门后有山,山上有泉,门前有田,院内
有树,风吹枝叶晃荡,喜庆得像个刚定亲的小地主。
是夜,中庭枫杨如积水,人影如小舟几只。是夜月色蓬蓬,像肉松面包蘸了层西红柿酱。
清晨被鸡鸣推醒。鸡鸣涌出少年般的浩瀚、温暖、湛蓝,一鸣跨三县。安徽金寨、湖北罗田、河南商城,三县齐鸣。
新阳历历,门前畦畦稻浪翻滚,山间枝头数千鸟声各自起伏。街头有精瘦老人粗服乱头,穿长靴扛褐棕走过。鸡鸣喈喈,依然和先秦一样欢实,青绿有神: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飞土,逐肉;断竹,续竹……
雨或梦:枇杷
枇杷的青雨在夜与星的旷地逐走,苍蓝倾织。青雨之夜,星子无比硕大,在吴楚之地的皖西南,仿佛架着柴火的夜色在噼噼啪啪燃烧。满天金黄的星子,从少年的额角舞溅并汹涌喷吐出熏翠枝叶,甜蜜,郁蓝,充满民间山坳的神游记忆——雨声渐息止,星子悬垂在农家檐角,和夜色混为清冽的炊烟……绕东坡而去,似一位古人于山里弹琴——琴音飞散如肉色累累沉沉的枇杷子,浆液的彩瀑倒流入无边深邃的湛蓝天空——无数的枇杷叶,无数缩微的琵琶,音符像要溢破薄薄的果皮和沉夜的幕布……枇杷欲作琵琶响,琵琶暗藏枇杷香。琴音的青雨复大,雨珠像繁体的木刻汉字,音乐的终极目标是为取得神奇的音色和音效,随一幅幅流动的旧画而呈现、分解(有时候如林椿、赵佶的《枇杷山鸟图》,山雀栖枝欲啄而食之——自足酣畅的世俗的暖意;有时候如虚谷和尚的《枇杷图》,萍踪浪迹的枝叶蓬乱——显露一派峥嵘的怒意;有时候如齐白石的《枇杷》饱满艳烈欲滴,我读到的题诗“果黄欲作黄金换,人笑黄金未是真”——抠门老人流露直白的真意……)。农历四月山中收藏的时间乐谱,因偏僻天真的梦境而湿润成漾漾溪水。烁白的溪水,像要把凸凹披绿、静怯安详的无名村落切割下来。无名村落,因无名而熠熠闪亮,像悬挂在山间和天际——朗素的粼粼月影,里面流淌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无穷过去,以及,用幻绿安慰未来的清澈质地(但愿如此)……
独墅湖歌
昨夜微醺。记忆里糯软的老苏州,似乎也在微醺,人影晃晃,桥影晃晃。
当年的夜市,灯火可亲,卖菱藕的担子,载绮罗的春船,和杜荀鹤的诗句一起悠悠晃晃。
湖水携带着荷莲清气漾上来,湖水的丝弦真挚而诚恳地劝解:虚妄的我,在独墅湖图书馆中穿行;独坐的我,在独墅湖畔自说自话。
场景一:书里的云朵游移不定,烟波是古人的烟波,两个女大学生(大概)斜靠书架而坐,悠闲,专注。
场景二:湖水蓝得一丝不苟,映出久违的神祇的幻影,镂刻湖水的细纹,满眼幽冥、平静……
这是独墅湖,在照彻一个俗人内心的黑暗,照亮我血液里的褶皱,连同暮云般的心跳。心中有湖,于是便有光——无限的自在,此在的无限……
立冬日忆上书洲
城中有湖,湖滨有书洲,一个俊美书店,上书洲。
推窗见湖,白日东太湖清气逸动,仿佛翅翼绒绒初生,黄昏便有诸多氤氲水汽萦绕扑鼻,一湖的日落金璨,携归帆点点。上书洲以书卷古气为最,一本本老苏州的书,人文旧事风俗吃物赏玩,风雅宋,民国范,当代日常,流动人情之美。推窗亦见湖边的儿童乐园,老少叫嚣乎东西,枝叶隳突乎南北,均怡然自乐。湖因洲上书页沙沙而涟漪轻起,映照一湖书卷气,洲因湖光洒一身幽静,这是读书人的别样景致,渐生欢喜心。
我对苏州向来喜欢,苏字繁体“蘇”,有芳草有嘉禾有鱼鲜,鲜美生味,跃于纸上。州字多水,淋漓润泽,蕴含鱼米水乡的美意。又使我忆起古人穿州走府、以脚丈量天地的劲气。文人需节气,书店要静气,当年金圣叹蛰伏苏州,孤灯下评《水浒》,批《西厢》,身姿不动如松,心里应是藏着一个上书洲,用笔却如刀解剖人性,劲气勃发。
苏州趣味尤多。情趣多在风月,风来月来,似一枝红杏窈窕出白墙。闲趣多在鱼鳞瓦,鸟落乌檐,如人在舟上散淡几粒。苏州多风趣,多异趣,多奇趣,如素丸清蒸,如鱼在盘中,如车前子在酒席中放诞,如皎皎情种被一双纤手揉进了评弹的丝弦。上书洲则多真趣,爱书人多有真趣,因书而生偏僻心,书籍大略如厚土,高天厚土,厚德载物。斯文在兹,和罗伟章、胡竹峰、李宁、李黎诸兄,闲聊书中风月,不觉日落,不觉厚土被暮色覆盖。出门在湖边遛一圈,苇蒲葳蕤,初秋的风打在湖水和蒲苇上,沙沙中一片寂然。
湖水轻摇,似乎上书洲浮在湖上。
十多年前我到过苏州,在拙政园、留园、虎丘、寒山寺、忠王府、五人墓流连游荡近十日,见景是景:诸多亭台楼阁,鱼鳞瓦片,高高的叶子从窗和墙上悠悠垂下,影子便疏疏洒落,一时光影虽在流动,但看着看着,看客就在恍惚间跳出时间的法则之外。也仿佛十多年后,在上书洲,见物非物,十多年不过是抚摸一本旧书的瞬息。或者如明代的唐寅,癫狂作歌:“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桃花庵歌》在冬至日凛凛的皖西南午夜听来,似倏忽过了五百余年,不见桃花,耳畔仍交杂洲边湖边的水声、风声、书声。上书洲,上书舟,且登上书舟。放眼四看,舟头虚静,洲头万古,让人顿生空明之心,渺小之意。
座谈间隙,曾和数人偷懒,在树下盘礴而坐,姿容不拘一格,跳荡如毛边书。
“一醉又驱黄犊出,冬晴正要饱耕犁。”是陆游《今年立冬后菊方盛开小饮》中的句子。阳光跃起,几只腿是几张犁,似乎身下的太湖是万顷良田。陆游诗句温晴,宜晒书,宜晒上书洲,宜在上书洲晒一晒。
且坐坐
到花山,且坐坐。
夜色浓如焦墨,花山挺如巨柯。花山如一团焦墨挂在窗前,夜色轻颤。夜色淹没了山风,又被山风掰碎。投宿民宿“花山隐居”的一夜,是听风的一夜,似乎也是滴露的一夜。听了一夜花山,感觉四围是山,四围是巨柯在飞。我坐了半夜,梦里听了半夜,一把巫女的扫帚被山鸟骑着,在飞,在飞。
凌晨即起,在庭院小坐。清池小桥,流水飞花,嶙峋奇石,老竹新叶,庭廊曲回,窗牖格物,古老的东方式的庭院,享有清逸而奇异的审美,欲飞欲舞,宛如时光倒流,心情为之一荡。这是苏州的山水范式,和山水相对一坐,和绿树相对一坐,和园林相对一坐。
入得眼的香柚,庭院里东一棵,西一棵,棵棵圆圆满满,青青绿绿,枝叶间躲闪的柚果,圆润似春水。天地间无风,霎时庭院孤寂,人声与蚁语无异。柚树均不高大,无风自摇。
入得眼的都盈盈一握,南方的精巧和秘密可堪一握。
在餐厅用过素食,友人上花山,约三五六七人。
三五六七人,与橡栗、枫香、榉树、枫杨、牛鼻栓、白栎为伍,看山种,赴出尘关,似星辰坠宿花间。上法界,越凌风栈,走鸟道,山风吹帽落。三五六七人,一路下来,历数百数千年,状如斑驳石刻。
我在山下独坐。苏州的隐居是翠绿交融,相叠成荫。我在苏州独坐。
苏州在座。苏州是南人南相,花山是南人北相。
在花山独坐,我是北人南相。
我且坐坐,状如蒲团。闲暇来坐坐,何必要登山。
芭蕉二三
芭蕉一身绿,绿火晃满了头、脸、手、脚。在泾县查济,绿火之力蔓延到整个皖南,丘陵、山地以及无法言明的婉曲溪涧,似乎是横琴在野。芭蕉是琴弦之一,弹奏古老的岑溪、许溪、石溪,鸟声出溪。我所至的是许溪,溪水说是深碧也可,说是透澈也可。溪水昼夜在翻刻云影,群山如黑绿木刻,岸上古民居如黑白木刻,岸边有农妇和老头老太洗衣、洗菜,宠辱不惊,宠辱偕忘。水边的一株芭蕉映照之下,溪水仿佛蕴藏了泾川万物,自足而骄矜,她沉淀的绿的质地、层次,在我久居山野的内心,竟然雕刻出南方中国的惊悸和肃然。
在对岸,另一株芭蕉似绿云扑面。绿得寂寂。几乎无人打探,静享山水之气的沐浴和浇灌。亦似被遮蔽的风暴,不知何时它能鲜活爆发。旁有一门户,墙角浸了青苔,瓦缝生出蕨草。是元的、明的、清的、民国的,直至……壮烈的荒凉绿色。
一路晃过青檀树,大木构架,石雕、砖雕、木雕,榫卯结构,晾晒场,石臼,青石板水槽,烘纸的泥墙,草木灰的清香,青砖小瓦。查济的迷途小巷和清溪之旅,在旅行即将终结的弯曲墙角,突兀出一株:枯黄的,似天火烧熬过的,芭蕉!像渐熄的冷火灰烬。
落日将至,像冷火灰烬中的星粒!那些枯叶,如同先民时期的夜色散落于无数民居,以及,仰头所视的,是所有花的灵魂在夜空中狂欢和聚会,和老茶罐一样的月亮,构成山峦和音符战栗起伏的大地钢琴,茶汁般奋勇溅出……
游榆树村
深秋天气,响晴易生懒,遂和妻女带狗往榆树村一游,锤炼身子骨。
榆树村四面环山,山水一绿,绿到恬然。绿中有黄有红有紫有褐,杂如彩毯,野性勃勃。山中云如鹤,凌凌欲飞,巨石松木野栗,被风吹得自在悠悠。河边良野平畴,葡萄藤架、风车、卵石、荒芜草茎,昔日花海一派苍凉流逝颜色,偶有格桑花零星点缀,被暖阳映照,腾起烟色伴柳色,却有几分春色味道了。
沿河堤慢行,偶遇妻子的二年级小学生,叽喳吵嚷,追逐不止。小狗一身白,小人一身黑,一人一狗钻入花丛草丛中撒野,步态超然。小狗欲跃渠沟,却被草根绊倒,洗了个秋澡,旋即翻身而起,兀自湿嗒嗒地在原野上昂然跑步,其清高孤冷之姿,似不屑与人言。殊为好笑。
大别山中山水殊好。山中春色夏色冬色均好,秋色是水落石出,长天一色,一切如产后的平静,万物欲酣睡。秋色正是酣睡前的那份慵懒风致,过渡于收获与颓然之间的疏朗明净。落于群山之腹的一片起伏、丰满的丘陵,赠人间一个蔼然摇篮。
北山上,茶坡绿意沉静。远望一亭如翼,又如美人回眸,神光定格在湛蓝空中,与白云相齐,诞下旺盛的美和神秘……
不写字
这半年状态不好,几乎不写字。不写字也好,也是修行。写好字需有神设,如瓦片覆霜,叶落山空,但无风不动,风是神意,无风便无深意。风也是意趣,无风便无真趣。趣味不到,则神态不到,下笔无神,似木牛流马翻山。一页书是一座山,两页书是两座山,三页书是三座大山,庄周的书是山,博尔赫斯的书是山,山山相连。大山盖顶,不如推书而起,管它几座山。
今日小雪。今日却无雪。小雪节气里,想一些心事,或什么都不想,摊书酒煮,灶煖茶烹,无雪也罢。窗外乌云渐逼,亦适宜走走。去年的花果山上,曾踏着积雪,看花间雪,看乱雪,看枝上雪,看新人旧人披雪而过,看古人像一个个篆体、隶体,冒雪而至,世界发出“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山,桥,水,树,旷野,一篇雪文章。童话般的雪与光,红雪,绿雪。一时心情纷乱,辨不清今夕何夕,亦不知去年今年。山里的雪地,可能会有一匹受惊的白马,从山坳中猛然跃出。这是我私藏的想象。
一匹马是一匹雪白的汉字,一匹白马是雪化的神意,在虚静中追逐。文章的神思是马,李白一骑绝尘,苏轼一骑尘绝。好文章都是百骑绝尘,一骑之后,更是尘绝。
好文章是在灯笼里画豹,青空里泛舟。提笔是雪,纸上是雪,心头是雪,宣纸化雪。
雪要下了。今日提笔写字,落雪为念。
大风歌
翻开1985年的文物普查记录:琥珀嘴高出平畈几米,断面文化层自然深裂,达2—3.5 米,上层以灰陶为主,下层以平沙红陶为主,在断沟底部发现石杆、石斧等磨制石器,据标本和文化堆积层分析,上层为殷商时代文化遗址,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黄的纸页潦倒中辉映别样锦绣,陶石之音依然动荡如金阳晃晃,而它此前是静止、专注、内蕴,万年前的大风吹动先民的木叶,呜呜呜呜呜,大风在泥土的内部筑陶成巢,鸟飞起落……一个原始部族或村落的肌理涌起古陶的斑斓红鳞,老陶如唇,天地律动的声响,沉寂,泛起,沉积,浮起……
大别山顶上,几朵白云停在上面,草木是站立的风,石头是凝固的风。青铜枝下,整个琥珀村沉入乳白色的雾中,白墙和白雾不分彼此,只有黑色屋顶浮在上方。黑黑白白,像许多人的一生。
溪边的枫杨和坡上静静的土坟,如此的安宁。叶子翻过去翻过来,像许多人的一生。
妩媚
花影落进河面,像给平常岁月点了几粒胭脂红。水波潋滟,水草间有游鱼星星点点。鹅卵石裹了些青苔,亦如一枚枚卒子,被时光消磨得圆润。
好在春来花发了。春天终究是来了。春天来得浅,春天来得深,浅一脚深一脚,深深浅浅是脚下的草,踩在草尖,脚痒痒的,心痒痒的,让人产生远行的冲动。置身花丛,桃花红红的,像个小姑娘;杏花白中带红,像个小丫头;李花白中带黄,像个小女孩;梅花白白的,像个小女神。她们或雀跃,或娴静,或天真,或文雅,花光如颊,温风如酒,一派不谙世事的美好,又是年华锦绣。春天真是毫无心机,如河滩上的活泼稚儿,晃晃悠悠,处处皆景。
天上鸟飞过。天上晚霞飘过。天上还有斜挂的夕阳,贴在西山,似周昉《调琴啜茗图》一帧,着色苍黄。
周昉用笔秾丽多态,法度谨严。画内却似有天籁音,一琴一盏,三五慵懒闲人,听琴品茶。闲庭之雅,听琴不在琴。随心所为,坐听无弦。
忽想起天地之弦,天地皆为弦,草是弦,花是弦,鸟是弦,风是弦,卵石是弦,夕阳是弦。人是弦,人心亦是弦。拨弦的是夕阳,是卵石,是风,是鸟,是花,是草。人在处,人心在处,天地一弦。我这么说有点玄的意思。春天是玄而又玄的美妙,春天是娓娓道来,春天是兴之所至,无所不至。
忆得那年到睡佛山,山南山北,一边春深似海,一边白雪皑皑。山脊上的杜鹃,红浪翻滚,一浪一浪地耸立着,走远了,隐隐约约间,可闻涛声。山北之白雪,又如铺天盖地的白梅花、白杏花、白梨花堆积,突然我就听到了雪声、花声,声声慢,声声急。山是弦,云在拨,有悲怆,有激昂,有幽寂,有焦灼,有安抚,有吴音,有楚声,恍恍惚惚,竟一时忘了是醒还是梦。
冶溪地处吴头楚尾,山水的印记就颇有吴楚之风。吴音四声八调清浊对立,吴歌温柔敦厚含蓄缠绵,楚声参差错落自成妙响,楚歌即兴而来悲凉哀婉。人到中年,渐渐喜欢楚歌更多一些,比如《采薇歌》《易水歌》《长铗歌》,“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憯懔惨悽,愀怆伤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嵇康《琴赋》)楚歌在荆楚大地源远流长,庚子年的春天于我听来,悲慨之气尤甚。
但吴楚之歌在乐器的选择上惊人地统一,笙一支,笛一管,节一块,琴一把,筝一张,琵琶一面,瑟一具,仿佛衣食同源。大弦嘈嘈,小弦切切,淙淙之音里悲喜交织。吴歌如春风拂耳,楚歌似银瓶乍破。
吴楚之地是表兄妹,吴楚之歌骨秀神清。
临睡前在朋友圈里翻阅,见杭人李利忠录一联:
花气争窥,矜持春晓;
莺声可数,妩媚山深。
人生妩媚为好。忽想起,山深处,万物腐熟而不朽,比如满山的茶籽,比如稚儿擎瓜柳棚下,细犬逐蝶深巷中。味淡情深,乃妩媚之致。
莫名其妙
天柱山之偏僻后山,远观山峰百态。满山郁郁苍苍像青雨一样密实,山被阔绿淹没,山几乎无主。青雨一样密实的竹海,竹海一样清冽的青雨。在盘山道看竹海突然冒出两个词:雨滴硕大,莫名其妙。雨滴硕大本来就莫名其妙,而竹海,确实青雨一样的密实清冽。青翠发冷的竹枝、半黄半绿的竹竿和麻色长笋之间,小车拖拽着的盘山道像根胡乱堆放的清凉丝绳,欲捆绑群山中几百类鸟百十层次的胡乱鸣叫,叫声堆叠和潜山人的呓语一般。暮春的潜山市(2018年8月前尚称为县)在芭蕉肥叶下像短促又时而悠长的旧梦。蝉鸣交杂,程长庚(1811—1880)呓语在芭蕉肥叶下,像京剧《捉放曹》的老生出场,他认领山峰一个。张恨水(1895—1967)呓语在芭蕉肥叶下,像《金粉世家》的金粉剥落,也认领了山峰半个。坐标:龙潭乡万涧村,竹喧如海,如海,从清末到民国到2020,他们演绎艺术的后山之巅……莫名其妙。艺术就是莫名其妙。艺术也是龙潭万涧。一幅《春山图卷》,绘者商琦似要从元代的云烟中扑来——五月潮湿的青雨在反复灼烧山脚田畈,拥挤,喘息,阳光的电露在我们黝黑的肌肤上划下金黄的稻痕,新凉的、疼痛的,冲动在人心深处的广袤艺术山河。
羊桃记
远山有包浆气,树木经霜,枝枝微醺。山风鼓荡,一时万籁俱静,枝头的红果粲然,似乎一忽儿就簌簌挂起了。
主簿镇地近皖西,峰壑交错。盘山道上,往往山花烂漫。山花,烂漫一片,兀自这里那里,拐角冒出一枝,山坡突兀一片。山里好颜色,四季好颜色,尤其春来,在一山惊喜颜色里,芭茅草青青轻轻倩倩摇荡,映射出一个花花世界的好颜色。
四季斑斓的油画册页中,春日杜鹃、野樱、桃花、棠梨、兰草、八月楂;夏季荷花、格桑花、金银花、桂花、百合、牵牛;秋天山茶、金桂、木芙蓉、木槿;寒冬蜡梅、结香、小苍兰。花花世界,凡百数十种。难得山花烂漫,难得人心烂漫。烂漫之心,在乎山水之间。烂漫之花,自在人心,美得本色。山地一派天籁和野性,犹如小路斜伸进草茎中,似无迹可寻,又隐约在远处露出一线白。中国画的留白。“飞星过水白”的白,“露从今夜白”的白,渐渐,“密雪埋溪僧未扫”的白。
秋日山色乃天色所化,天青色,有元青花的姿容和媚态。
松果跌落,空山更空。松枝如弦,松树下引弦而发的是漫山羊桃。空气里那种毛茸茸的甜香,和枝蔓交缠,枝蔓间又夹杂了松脂香,萦回鼻端,酥软手足,警醒视觉,旋被山风送远,令人七窍讶异。主簿镇以羊桃著名。村野田畈山坡,一片愉悦欢喜的金色,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仿佛小时候口袋里装了几颗糖。
羊桃皮色黄亮,肉色清逸,酸甜别致,未熟期生硬如铁,酸味袭人,成熟后切开即食,甜度远超酸度,肉质润和,汁水十足。主簿的羊桃品种甚多,金魁、海沃德、阳光金果、东红、红心,各自滋味绵长。
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
石泉饭香粳,酒瓮开新槽。
岑参《太白东溪张老舍即事,寄舍弟侄等》诗句,如习习微风中,酒瓮半开,石泉煮饭,其情其境,是山里才有的风味。山里味,有腊肉香、蔬笋气,嘈嘈切切。
岑参说的是“猕猴桃”,“猕猴桃”即是羊桃。《诗经》说“隰有苌楚,猗傩其华”,“苌楚”则是羊桃的古称。
“苌楚”这个名字难免拗口,“猕猴桃”形象却失之浅白,“羊桃”好听,惜乎俚俗。我乡靠近太湖,方言源自赣鄱,俗称“杨桃”,或许是因为其酸酸甜甜类似杨梅,风味渐出。又有人称之为“洋桃”,但它似乎并无洋气。我习惯称作“阳桃”,春阳大块赠我好文章,阳光如瀑,好文章翻山越岭在主簿的瓜棚豆架下等我,酸酸甜甜如阳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