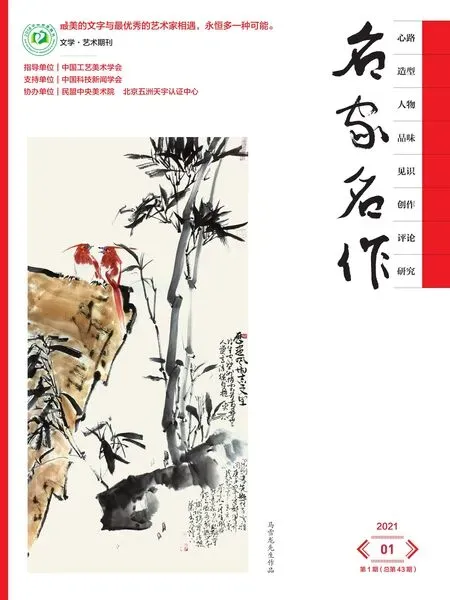比较文学视阈下的李商隐诗心探微
刘嘉娟
20 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对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在贫病交加而又居无定所之际的《人,诗意地栖居》一诗进行了哲学的阐发,从而引发了与诗心相关的探讨。当代,诗心在我国正逐渐成为一种诗学新概念,上升到生命意义的层面。晚唐诗人李商隐不以诗为诗而以诗为心,开辟了人类心灵的小宇宙,我们沿着中华诗歌的血缘脉络,追寻诗词长河里一朵朵“意象”浪花,寻访晚唐诗人李义山。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独具一格的象征主义意象派审美情感的意象如“美玉生烟”,隔着时空的沧海微茫吸引着我们,召唤着我们。李商隐的象征意象正是“诗心”的投射,融入诗歌的肌理血脉之中,成为中华诗歌“使人心不死”的生命密码,寄托着华夏生命生生不息的诗家情怀。
一、空灵的主观意象
李商隐是继李白、杜甫、韩愈之后独具一格的心灵大师,是典型的主观之诗人。他的诗歌对人类的心灵世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呈现,他开辟了从未被前人如此深入表现的人类心灵世界。晚唐低迷苍凉的唯美情调淹入了他的性灵,他以超常的感知力深入领悟光怪陆离的自然和人生,达到了物我相通之境。
诗人灵心彗性,以飘忽之思,运空灵之笔,其诗歌中的种种意象已经达到了整体神合的境界:天涯暮春、流莺落花;凤凰梧桐,丹丘万里;春蚕蜡炬、蓬莱青鸟;龙宫石枕,割得秋波;月中桂花、西池凉露;巴山夜雨,灵风梦雨;瑶池阿母,无端锦瑟;晚晴幽草,霜月嫦娥;柳、荷、石榴;梅、菊、牡丹……大陆长空之间的万事万物:春夏秋冬的更迭,朝夕阴晴的变化,乃至那些流离无依、纤弱美好的小生命的啼鸣都成为他善感的心灵映象,与此同时,诗人那交织缠绕着家国之悲、身世之感、古今之情、天人之思的锐感心灵也随着诗人个体生命的种种变故磨难和苦乐悲喜碎裂成千片万片,从而幻化出一串串如此鲜活的诗歌意象。诗人随着内心感情的跌宕起伏,信手把一个个饱含着心血的感性意象郑重地安顿在他的古诗、绝句、律诗等所有题材的诗歌作品中。因而他的每一首诗歌都呈现出空灵的世界、恍惚的真实。诗人以“同情”于万物而与天地造化一样深美的诗心映照一代末世贤人君子对大唐盛世繁华的追忆与耽溺;一个晚唐衰人的悲剧人生、理想幻灭和痴心不改;一个生命个体对青春、梦想、爱情的追寻和祭奠……他把心碎都藏在这些意象里,拼图成诗。由于诗人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物象少有目接而多以神遇,因此其诗歌难以索解,空幻缥缈,其意象之美、情感之美与哲思之美并存。
二、象征意象解读
李商隐把个体生命情感的抽象性和不稳定性具体化为颇具现代象征色彩的意象群落,化现实景物为诗人心灵之虚境,创造出种种个性化的主观意象作为象征个体生命心灵的载体,使人类生命的内心世界之波澜具体化、形象化,从而静照人类生命最高的心灵世界深处的细微反映及变化。李商隐诗歌较之传统诗歌之所以难以解锁,主要源于他的意象运用已经从传统比兴中人与物的单纯比附发展到离形取神的象征境界,他往往因物兴感,淡化具体情事,凭借直觉和幻想创造现实之外的真实,化抽象的喜怒哀乐为具象的世间丰物,深入展现生命个体的心灵世界。少年李在《春游》中写道“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青年义山在《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中有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在诗人几近生命尽头的《暮秋独游曲江》中有叹“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以上诗歌中的“荷”“残荷”“春袍”“庾郎”等典型意象分明有直指人心的象征意义。李商隐著名的《蝉》诗虽然其创作背景不详,但是被现代文坛普遍认为是咏物的哲理诗,其中“蝉”意象则是李商隐个性化的典型象征意象。此五言律诗之颔联曰“蝉鸣”,曰“碧树”,此二意象本是外物,而作者用意不离乎人心;而颈联曰“漂泊枝”,曰“故园芜”,此二意象本是诗人内心幻影,而作者立象以尽意,真乃情景交融、追魂索魄。由此可见李商隐的意象运用不仅具有直觉的美感而且情味隽永,更可贵的是“离形取神”颇具哲思之美,达到了整体神合的象征境界,因而更接近于现代文学的“象征意象”。
象征意象这一概念来自现代的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是19 世纪末发端于西方的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基本创作美学。象征主义者笔下的艺术形象即象征意象一般是一种或几种客观具体的事物代表一种或几种抽象主观的事物,如西方象征主义者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就是两个典型的象征意象,诸如此类的象征意象大多具有审美求解性或荒诞性。19 世纪末的西方象征主义者不愿正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因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向内转的创作风格即象征主义,他们主要通过创造象征意象描述个人幻影与内心感受,其作品流露出一种凄迷徘徊、迷惘孤独的情绪即所谓的世纪末情调。蒋勋认为19 世纪末英国象征主义代表唯美主义者王尔德是注解生活在9 世纪中国的诗人李商隐最好的版本。叶嘉莹认为生活在中国风雨飘摇的晚唐时代的文人李商隐和19 世纪末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时代的象征主义作家卡夫卡具有颇多可比性。其实李商隐的象征意象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兴传统但却超越了传统的比兴,这些象征意象及其组合正如现代的象征意象并非固定下来,总是处在不断生发、微妙变化之中,形成“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效应,能够转出复杂多变的美和恍惚的真实。然而万花筒营造的效应看似缤纷迷离,但其内部组成并不繁复,正如义山的种种象征意象虽令人目眩神迷却都源于诗人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古希腊的柏拉图说:“Every man is a poet when he is in love.”诗与青春、热爱的含义固然相通,刹那激情、瞬间喜乐以及你侬我侬,都会触发片刻的诗情,但要达到诗心彼岸的理想境界却需要心灵的升华。于天地之间,沐浴日月精华的诗人心灵即在月光凝结出沧海明珠上的一滴泪痕,阳光升华了蓝田美玉的一缕烟魂的刹那间,即在每每由动之静,反观自照的刹那间升华为诗心。
三、诗心微探
李商隐不以诗为诗而以诗为心,无论在他的抒怀咏物、托古喻今还是无题诗中的象征意象都是“诗心”的映照,寄托了诗人的高情远意,同时也浸透了诗人的审美情感,是诗人心灵的沉淀、情志的抒发。《毛诗序》曾经情志并提,“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的情志即诗人的内心感受及其变化。“诗言志”初见于《尚书·尧典》中的“志”,本意指人类心灵深处的志趣、抱负;《论语》中的“志于道”中的“志”也是这个意思。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将其意义扩大为人类的心灵。汉代时“诗言志”的内涵基本明确,即诗歌主要用来抒发个体生命的内心情感,呈现个体生命的心灵世界,因此从《诗经》开始,包括后来的唐诗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大多主情不主理,而李商隐诗歌的意美情深正源于此脉。
但是李商隐诗歌在呈现人类生命个体的心灵层面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他所生存的时代,他秉承了一种异于常人的以心灵取胜的特质,这种特质固然受个体的生物学因素影响,但同时也是一种与晚唐社会关联最密切的人格特征,因此义山诗歌不仅是唐诗主情的典型代表,达到了唐诗情感深美的巅峰,而且突破了历史的局限而颇具现代象征主义审美求解性的哲思意味。李商隐的诗心即自度,是诗人超脱现实从而升华自心为不朽诗心。“诗心”在中国传统诗论中虽未作为一个专门概念出现,但在唐代之后的诗歌中已经屡见不鲜,如唐代齐己的《谢灉湖茶》《寄郑谷郎中》,曹松的《送陈樵校书归泉州》,清代秋瑾的《失题》等诗歌中都有“诗心”一说。在“诗心”说出现之前最先在汉代的诗论《诗纬》中出现了“诗者,天地之心”的阐述。后来意义相近的“文心”说出现在南北朝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诗心”说正是基于“文心”说,而后出现的“词心”说则是“诗心”的延续扩展和迁移。在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中有生动的“词心”阐释:“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别有动吾心者。”由此可见“文心”“诗心”“词心”之说都与我国传统诗论一脉相承,现代国学大师顾随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叶嘉莹都对“诗心”有所论述:人可以不为诗人,但不可无诗心,诗心是诗歌中最宝贵的感发生命之本质。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认为艺术心灵即诗心。由此“诗心”在诗学中可以扩大理解为一般诗歌创作的诗人之心乃至读者之心。“诗心”是诗人与读者之间乃至人类与自然界的大生命世界之间的心灵相通的部分。
晚唐李商隐的世纪末情调与起源于西方的象征主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或诗人的心灵抽离现实苦难,完全专注在美好之初而达到了某种超现实的解脱境界,这种超现实的象征境界体现在作品中则有意或无意间影射了现实社会的困顿与复杂,投射出诗人对艺术、爱情及人生完美而纯粹的追求,在表现手法上,诗人把真实的人生体验糅合进自己的心灵信仰,用非常主观的、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意象串联,表现人类生命最基本、最深刻、最内在的感受和意义。李商隐诗歌中的象征意象正是人类生命个体超越时空的灵犀相通之所在,追寻着诗人那些象征意象组织起来的感性脉络,逐渐深入他那“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心灵世界,感受那份生命的执着和美好,沟通那些朦胧凄迷的情思,分享那些至纯至美的梦想,转化那些岁月的迷惘和忧伤,探寻生命个体的精神升华和一种真正的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