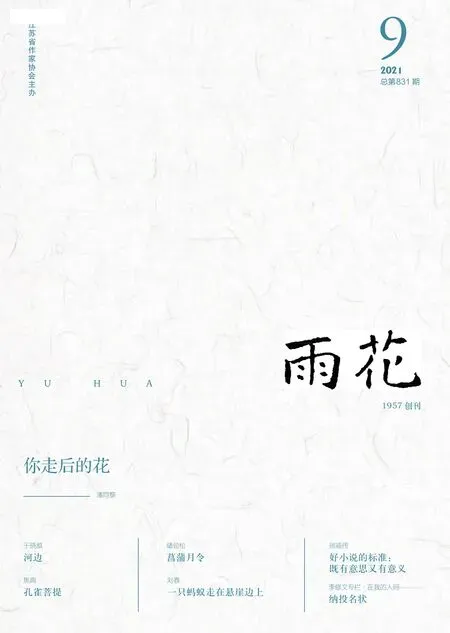云影
倪 苡
马海平成年后,见过娘两次。
刚过中秋,“噼噼啪啪”如水鞭子的秋雨停了,叶片被洗刷得晶莹透亮,闪着宝石般的光芒,风吹在脸上,软硬正好。这么好的秋天,老伴却愁绪汹涌。她说,年怕中秋,月怕半。这中秋一过,年就快来了。老伴已经闹到用不吃饭的手段,逼着马海平接娘回家,这事闹了有一阵子了。马海平从家里出发后,一路上不停地深呼吸。他感受不到这恰好的风,空气又变得稀薄了。这么多年来,他只要一想到娘,就开始一口接一口地深呼吸。他生活的城市,海拔只有四米。有时他在与人交谈时,猛然就来几口深呼吸。大多数人都认为马海平心脏不好。
马海平选择步行去养老院,他脚步沉重,仿佛有铁镣铐着。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一鼓作气把娘接回家,他更情愿自己后悔,转身,回家。可不接娘回家,怎么向老伴和儿子交代呢?儿子开的超市面临倒闭,事情的确很急。事情如果都和预想的一样,那就不是急不急的事,而是件很糟糕的事。
从家步行去养老院需要四十分钟,穿过中山路大街,就到了滨溪公园。马海平想到公园歇歇脚。中山大街不是很长,可马海平像在长途跋涉,每一步都迈得那么艰难。儿子的超市就在中山大街上,马海平经过超市门口时,扭头朝超市里看,时间是下午三点多,超市里一个顾客也没有。儿子在给四五个店员训话。看着清清冷冷的超市,马海平贼一样缩回头,匆匆走开。儿子的超市不大,商品品种不够齐全。上个月,在离儿子的超市几百米的地方,又新开了一家大超市,这是致命的打击。父母帮不上儿子的忙,没钱给儿子投资,确实有错。
马海平继续埋头赶路,路两边长着高大的梧桐树,可空气中像是源于秋季的本能,到处飘着桂花香。这香气撩拨得大街上的行人神清气爽。只有马海平像个病人,他神情阴郁,皱着眉头,双唇紧闭,似乎被这香气熏得想吐。他有些迫不及待地走到滨溪公园,在最靠近公园大门的长椅上坐下,耷拉着眼皮,几口深呼吸过后,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草一木。
右前方的那棵银杏,是马海平童年最重要的玩具。他抬头仰望银杏树那宽大的树杈,以马海平目前的视力,已经看不出那树杈是不是还那么光滑。童年时的暑假,马海平大街小巷地窜着窜着,就爬上了这棵银杏树,那宽大的树杈是他纳凉的好地方,他甚至可以在上面睡午觉。马海平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他们家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大把大把的无聊时光没处打发,他就干走街串巷、爬树捉鸟这等事。
马海平望着那棵银杏,他听见了自己童年的笑声。他小时候是调皮鬼,最快乐的事是欺负弟弟马毛毛。他拎一下马毛毛的耳朵,然后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这棵银杏树,坐在树顶的枝丫上,晃荡着两条腿,朝树下笨熊样胖乎乎的马毛毛大笑。马毛毛两手抱着树,两只脚底像装着滑轮,一步都上不去,只能放弃。除了踢着树干喊“你有本事就下来”之外,别无他法。马毛毛在树下叫,马海平就在树上叫:“小爷我要撒尿了。”说罢,他去解裤子。马毛毛赶紧皮球似的滚远了。马海平在树上笑得整个人连同树枝一起颤抖。想到这里,马海平嘴角一动,不禁滑出一个微笑。如果马毛毛不溜,他会做出什么促狭事?他不确定。他小时候很浑蛋的。
童年的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欺负马毛毛。马毛毛比马海平小一岁,可长得比马海平大一圈。于是在穿衣服这事上,马海平只能穿马毛毛的旧衣服。过去日子艰苦,衣服是“新老大旧老二”,这不是什么稀奇事。马家却是“新老二旧老大”,谁让你马海平长得没个老大样儿呢,只配穿马毛毛嫌小的衣服。新衣服马毛毛先穿,马毛毛块头大,穿旧了,马海平的身体也正好长到旧衣服那么大,旧衣服就归马海平了。马海平没有身体上的优势,却偏偏喜欢欺负马毛毛。不欺负马毛毛,他的怨气怎么发?
马海平十岁后,就不再欺负马毛毛了,而是恨,当然更多的是愧疚。这么多年来,每逢暴雨天,马海平无论是在阳台看雨,还是在窗前看雨,马毛毛都会从暴雨里冒出来,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别看马海平人长得瘦小,可他最喜欢称自己是男子汉,他小时候就没哭过。谁给他委屈,他就还回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事。后来的事是他欠娘的,欠马毛毛的。
马海平成年后第一次见娘,是在父亲的葬礼上,也就是四年前。父亲一咽气,老伴就让马海平即刻去料理父亲的后事。她说,马毛毛死在九岁的那场雨里,父亲的儿子就剩你一个了,你去是顺理成章的事。马海平当然清楚老伴的意思,她不就是惦记着父亲的那点遗产吗?十岁后,他没踏进过娘家一步,现在忽然亲儿子似的,马海平有点心虚。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当过他们十年的儿子。
父亲咽气的第二天,马海平非常忐忑地出现在娘家里。娘茫然地看着马海平。马海平艰难地叫了一声“娘”。马海平话音刚落,娘就老泪纵横,不一会儿,娘哭晕了过去。他和娘的这次相见,居然没说几句话。不知道娘是不是还恨着他。
娘年纪大了,丧事由马海平操办。父亲生前的亲朋好友并不多,前来悼念的也没几个真正伤心的。在马海平离开的这几十年,父亲是怎样对待生活的呢?跪着烧纸钱的马海平使劲回忆着父亲对自己如何,却忽然发现他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也就是说,他来给父亲办丧事,不是亲情使然,他潜意识里也是和老伴的意图一样?他不禁抬头看了一眼父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父亲慈祥地看着他,他羞愧地低下了头。听说人死后,还有不死的灵魂,父亲那只剩21 克重的灵魂是否就藏在眼前丝丝缕缕的烟雾中,一丝不差地看穿了他的企图?
现在的马海平反复咀嚼细节,他确定,在父亲的葬礼上,他忘记了流泪。银杏树下,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摔倒了,一位年轻妇女奔过来,抱起小男孩,年轻妇女泪如雨下,泪星子被风吹得四散开去。马海平望着向公园外小跑的年轻妇女,觉得自己脸上凉凉的,似乎那位年轻妇女的泪被风吹到了他的脸上。时间一下子回溯到几十年前,那夜,马海平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父亲不在家,娘也是这样泪珠子不断,抱着马海平,小跑着去医院的。
马海平痛苦地想,天下的娘都是一样的。
马海平站起来向养老院走去,一片银杏树叶应和着一声长叹,悠悠地落在他坐过的长椅上,他决定去看看娘,不一定接她回家。他还没来过养老院,长大后第二次见娘是在一年前。
一年前去见娘,也是老伴逼着去的。老伴让他去向娘借房产证,儿子刚开超市,需要贷款。那时娘的身体已经不景气了。马海平去的时候是下午两点,想不到这个点娘居然在吃饭。娘吃的是稀饭和咸菜。看到马海平,娘问马海平有没有吃饭。马海平说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啊。娘笑笑说,娘都老糊涂了。说着,喝完了碗里的一口稀饭。娘站起来问马海平,我这是要干什么的,怎么一眨眼就忘了?她两手撑着桌子,悠悠站起,身子摇摇晃晃。马海平赶紧扶了娘一把。娘说,娘的事还没办完,不会死的。
马海平看着娘拿着一只空碗、一双筷子去厨房的时候,百感交集。他甚至忘了说一句客气话。娘八十多了,背驼了,走路颤颤巍巍的,跟着颤动的是额前还有两鬓垂下的几缕白发,风烛残年大概就是如此这般吧。马海平又看看桌上的一只咸菜碗,一点肉星子都没有,娘是有退休工资的人,钱哪里去了?马海平悲楚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娘洗好碗,从厨房里出来,看见马海平望着桌上的咸菜碗出神。娘的笑眼眯成一条缝,说,平儿过来看。说着,娘拉马海平去了冰箱那儿,从冰箱里捧出一个大瓷碗,满满一碗咸菜肉,端给马海平吃。马海平记起了小时候,家里偶尔买一两斤肉,回家一洗,往清水里一放,煮熟了,切成几块,埋进干咸菜罐里。娘等两个孩子肚子里实在没油水了,就从罐里摸出一块肉切成肉片,给两个孩子解解馋。调皮的马海平常常趁家里没人时,从咸菜罐里偷肉吃。娘今天端着咸菜肉给马海平吃,看来是知道马海平那时偷吃咸菜肉的事,可马海平从没有因为偷吃这事挨过打。马海平心头一酸,用手拿起一块咸菜肉放进嘴里嚼起来。
娘关上冰箱说,时间紧啊,来不及啊。娘说着就去了阳台,阳台上有一把藤编的椅子,椅子上放着棉布坐垫。娘坐到椅子上,戴上老花镜,在肚子膝盖上裹上毛毯,织起了一件黄色毛衣。
看见黄色毛衣,马海平一阵哆嗦,他悲痛地闭上了眼睛,好像那黄色毛衣闪着万丈光芒,刺得他睁不开眼。说起来别人都不会相信,马海平长这么大从没穿过黄色毛衣。黄色毛衣是他心头的一根刺,一根永远也拔不掉的刺。
马海平生下来一个月就给叔叔家抱过来了。叔叔家条件还好,只是结婚好几个年头了,婶婶生不出孩子。马海平在家排行老四,父母为一家人的生计整天愁眉苦脸。经大人们商量,马海平就过继给了叔叔家,马海平称婶婶为娘。马海平来了没几个月,娘就怀孕了,后来就生下了马毛毛。
马毛毛生来块头大,马海平一直很瘦小。外人看着两个孩子的身形差距越来越大,暗地里都说这亲生的跟抱养的就是不一样。其实在吃饭问题上,马海平确实没有被欺负,只是马海平食量太小。关于穿衣,马海平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份恨,就是来自穿旧衣服。只有在过年时,娘才特地给他做一件新衣服,平时的他只有穿旧衣服的份儿。更可恨的是,马毛毛每穿上一件新衣服,都在马海平眼前走来走去,配上那骄傲的表情,神气得像威武的将军。马海平气不过,也质问过娘,为什么他总是穿旧衣服。娘让马海平以后要多吃饭,吃得身体壮过弟弟,弟弟就穿旧衣服。马海平听了,真的努力吃起饭来,但他怎么吃都吃不过马毛毛。马毛毛每顿都会比马海平多吃半碗,吃饱了的马毛毛依然骄傲地在马海平面前拍拍圆滚滚的肚子。
马海平的反击是在他十岁生日那天。娘在前一天织好一件黄色毛衣,说好了这件毛衣归马海平,算他十岁生日礼物,可穿惯了新衣服的马毛毛哪肯罢休,要知道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毛线衣,以前穿的都是卫衣。第二天,当马海平要穿上那件黄色毛衣时,马毛毛抢着不罢手。父亲已经上班去了,娘在忙早饭。马海平和马毛毛为一件毛衣大打出手。娘闻讯赶来,夺下了毛衣,给了马海平,还给了马毛毛一巴掌。马毛毛放声大哭,哭声盖过了外面下着的倾盆大雨。马毛毛的哭声穿透力很强,像强电流击中别人的心脏。这哭声让马海平心烦气躁,他想,这生日的新衣服,要被马毛毛的哭声搅黄了。他脑中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拥有新毛衣的幸福感一下子跌进了那个大洞里。就在马海平恍惚的那一刻,马毛毛跑进雨里,一屁股坐在地上,仰着头,张着嘴,他哭一声咽一口雨水,再哭一声,再咽一口雨水。娘拼了全身力气去拉,也没能将马毛毛从地上拉起来。娘没了办法,她让马海平把毛衣给马毛毛穿一天。马海平咬着嘴唇,埋头看看毛衣,忽然狠心地将毛衣扔进外面的雨中,并冲上去踩了两脚,然后对娘喊了一句:你偏心!
马海平冒雨向自己家走去,结束了他的抱养岁月。亲爹亲妈劝他回娘身边去。马海平说,如果你们不要我,那就让我去流浪好了。
马海平不再去娘家,这事也不算什么大事。娘因为马毛毛生病,也顾不上喊马海平回去,但壮如牛的马毛毛因为那么一次淋雨,居然高烧不退,没能活下来。马海平就没有脸去见娘了。娘后来也没请他回去过。
我可不能毛衣织不完就去见你爹啊。娘说话的功夫,眼睛不离毛衣,她左手的大拇指直着,拿针的姿势有些奇怪。在娘拿碗的时候,马海平就发现了,估计这根手指头是废了。这么大年纪的人,有根不中用的手指头也不足为怪。马海平看着娘的手指头,想着自己的身体也常常这疼那痛的,真是老了啊。自己老了,哪一天去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不放心儿子。儿子快三十了,还是犟着不肯结婚,硬是要先立业再成家,非得认为只有出息了有钱了,才能娶上漂亮姑娘,但这立业哪有那么容易呀?
娘织的毛衣是最老款的那种,清一色,没有花样,都是平针。织毛衣的竹针也是最老实的细细的那种,不是现在时髦的棒针。是的,这是过去毛衣的织法,娘现在织着的这件毛衣,非常像马海平和马毛毛拿命去争的那件,如今看来,真是没看头,颜色、花样、针法都有蒙尘的味道。现在谁还穿这样的毛衣啊?娘真的是老了,不知道现在淘宝上随便一件几十块钱的毛衣,都会把她织的这件毛衣甩出十条街。马海平猜不透娘织这件儿童毛衣的用意是什么。
马海平想着小时候的事,不知如何跟娘开口。自己那么小就离开娘家了,没有孝敬过爹娘,又有什么脸面跟娘借房产证?娘自顾自说,你小的时候,家里穷。马海平赶紧接上话,说,娘,现在我也穷,你把房产证借我去办点贷款吧,你孙子要开公司,还差点钱。
娘说,什么房产证?
马海平说,就这房子的房产证啊。
娘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看马海平,又看看西斜的太阳,太阳被万千迷离的金色包裹着。娘说,太阳快要落山了。
马海平说,娘,不说太阳,我们说房产证,我只是借,难关一过,就还给你。
娘说,平儿,不急,快了。
娘说完,又埋头织毛衣。马海平站在一旁,他不知道娘说“快了”,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娘还是不说房产证的事,她唠叨着毛衣,说现在她老是犯困,一件毛衣织好几个月也完不成。马海平还是看着娘手中的毛衣,她织儿童毛衣干什么呢?马海平没有心思研究毛衣,他站在一旁,娘不是说快了吗?再等等。可娘说着说着,手里拿着毛衣,居然在椅子上睡着了。马海平推醒了娘,又问,房产证在哪?娘又重复着那句,什么房产证?
马海平觉得娘是故意装呆,这故意装呆就是精明。房产证肯定是要不到了,他就回家了。老伴说,不求她,这么狠,看她死了谁给她收尸。儿子也是一肚子的不开心。马海平也觉得娘有些不近人情。就这样,马海平一家跟娘赌气,再也不提房产证的事。
马海平依然艰难地走在去养老院的路上。梧桐树的叶子黄了。马海平不喜欢所有黄色的东西,就算梧桐树的叶子像仙子那样在空中飞舞,他也不喜欢。几十年后的今天,马海平不喜欢黄色的东西成了一种习惯,不像刚开始的那几年。刚开始的那几年,他看见黄色的东西就会想起那件毛衣。今天,他除了想起那件毛衣,还想起了马毛毛。他走到文昭路最东头的桥上,麦芒样的雨在风的催赶下,斜斜地射在马海平的脸上,他想到了那场雨,想到了被那场雨带走的马毛毛。顿时,马毛毛像是坐在他胸口上大哭,使他胸闷难忍,他大口大口地深呼吸,像当初伤心欲绝的马毛毛一样,马海平也一口一口地吞咽着雨水。
他哪有脸记挂娘的房产证?老伴说,马毛毛都不在了,你是养子,家产归你,你要替毛毛给二老送终的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房产证不给你,难道烧成灰,带下棺材?
你不要棺材棺材的,娘又没死。
她都八十三岁了,死也死得,活也活得。我如果能活到八十几岁,我的命随时可以交给阎王。
这次争论,老伴把自己都搭进来了,马海平没再吭声。
就在上个月,娘过了八十三岁的生日。老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没事就在家里转来转去,嘴里念叨着,不是说大仙通灵的吗?
儿子每天很晚才回家,超市生意不景气,他脸阴沉得能拧得下水来。一年前,他对父母说过,怎么算,你们这几十年来多多少少有点积蓄吧?可父母真的没有存钱,才想去借娘的房产证贷款给儿子。父母没能拿得出钱支持他,自此至今,儿子一到家就沉着脸,好像即使父母这辈子没欠他的,上辈子也肯定欠了他的。
马海平在家处处小心,老伴和儿子像火药桶,一碰就爆。马海平已经不是小时候的马海平,他的厉害都在小时候用完了。自从马毛毛出事后,马海平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对任何人都小心翼翼的。
马毛毛的命丢在马海平手里,马海平常常噩梦连连,他这辈子都不想再有意外出现在他身边。他甘愿做个受气包,谁心情不好,都可以拿他出气。他像沙袋,任你拳头如雨点,他也不会反抗的。
如今老伴来真格儿的,她从昨天开始绝食了。马海平只能硬着头皮来养老院接娘回家。
养老院坐落在城的最东头。马海平走到养老院时,雨停了。他站在养老院大门口吁了一口气,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此刻感到的不是陌生,而是荒凉。这所养老院是水泥大门,水泥路面。现在是下午四点多,天灰蒙蒙的,天上像是也铺上了一层水泥。养老院门前一棵树都没有,铺天盖地只有孤独的水泥,就连天上刚巧飞过的一只麻雀,也是这灰灰的水泥的颜色。马海平将这灰色定义为老年的颜色。
他进养老院时,心里是不安的。自从娘进了养老院,他从没来看过她,这一来就是要接她回家。好孝顺的儿啊,马海平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恐慌。
马海平进了大门,院内只有四排老式平房,从房子的外观看,是上世纪建成的。这显然是政府扶持的收留孤寡老人的养老院,而不是配套齐全的护理医院。马海平问了两位散步的老人,就寻到了娘的住处。
门是开着的。娘背对着门在叠衣服。屋内陈设很简单,一张平板床,一张小方桌,一把木椅,洗脸架上放着毛巾和脸盆。床铺对面的南墙上有一扇小窗户,屋顶悬着一盏电灯,电灯没开,光线很暗,所有家具都披着老年的色调。
马海平站在门外不作声,他看着娘微微弓着的背,忽然觉得她很可怜,这世上也就他跟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亲情关系,她活着的痕迹一点点被抹去,即将归零。她只剩这最后的呼吸,却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向她的口鼻伸去,夺去她呼吸的权利。
娘叠衣服的动作不利索,一件衣服重复着叠。马海平进去喊了一声“娘”。娘转过身,揉揉眼睛,看看马海平,娘笑了,说,平儿,怎么知道娘今天要回家的?
娘,我就是来看看你,不是接你回家的。马海平慌忙说。
来了正好。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今天回家。
马海平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样。他来时路上都在犹豫,要不要接娘回家。现在是娘自己要回家的,可怪不了他,这么想着,马海平就上前去帮娘收拾。东西并不多,装在一个背包里,娘手里还拎着一只小包。马海平叫了计程车,娘让马海平也坐后排。一路上,娘只拉着马海平的手,并没有说任何话,她安详地闭着眼睛,头微微侧向马海平。马海平看着娘,他又开始深呼吸。司机五十多岁,跟马海平年龄差不多,听到马海平不停地深呼吸,问要不要开窗户。马海平说,不用了,娘在睡觉呢。司机说,如今的年轻人都是嫌父母唠叨,也只有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才心疼起父母,我的父母不在了,不如你有福气哦。
马海平没有答话,他看着窗外的景色迅速后退,这像极了人生,什么都在迅速退去。
到了娘家门口时,马海平喊了几声“娘”,娘真的睡着了。她睁开眼问,这是到哪儿了?马海平说,娘,咱们到家了。
娘愣会儿神,终于明白过来。
打开门,家里有一股霉味。马海平先去开窗,娘拎着她的小包去了房间。马海平去开房间的窗,他看见娘从小包里拿出一件毛衣,一件绿色的儿童毛衣,放在床上,再打开衣橱,将一件件毛衣拿出来,放在床上。
马海平怔住了。整整七件毛衣,赤橙黄绿青蓝紫,光彩夺目。幽暗的房间里瞬间添上了一道彩虹,亮堂了。
毛衣放好了,接着,娘趴到地上。马海平吓了一跳,他看见娘从床底下摸出了一个文件袋。她想再爬起来时,就做不到了,她手臂发软,撑不住衰老的身体,爬不起来。马海平赶紧将娘扶了起来。
娘坐在床边喘着气,说,老了,不中用了。说着,打开文件袋,拿出了房产证和工资卡。她把房产证和工资卡放在那堆七彩毛衣上,对马海平说,平儿,都拿走。
马海平立在床边,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娘说,我的身子我自己清楚,我的日子不多了。
马海平说,娘长命百岁。
娘说,毛衣没织完时,我和老天斗过,我不会轻易走的。娘停顿一下,接上一口气,说,我也承诺过,等我织完毛衣,老天随时可以来取我这条老命。
马海平又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难道娘听到了什么风声,自己和老伴那卑鄙的想法被娘知道了?
娘说,这屋子太闷了,你赶紧拿了走。娘说着又开始喘气。
黄昏正悄悄降临,房间里除了闷,光线也不是很好。
马海平还是站着。娘说,平儿,娘很困,没力气了,你自己拿啊。后半句娘是闭着眼睛说的,她真的要睡觉了。
马海平伸出手,他浑身都在抖。他的表情瞬息万变,惊讶,羞愧,悲痛。娘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马海平有些眩晕,他觉得自己的心狂跳不已。他伸向毛衣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怎么也够不着床上那堆闪着彩虹光芒的物体。
老伴的话清晰地响在耳边:我们儿子的超市都快垮了。你说你娘也真是的,八十几岁的人了,霸着房产有什么用?那个大仙算命从没失手过。说了你娘今年就算熬过生日,也不可能熬过中秋。现在中秋已过,她为什么还好好的?一定是她住在养老院,捉她的小鬼找不到她,你得赶紧去把她接回家。
外面狂风大作,房间里蹿进丝丝凉气,一片移动的乌云遮住了黄昏仅剩的薄薄光线。黑团团的云影透过窗户,先罩住了马海平伸出的手,慢慢地又罩住了马海平的身体,最后整个房间都黑下来了。
马海平的手依然在半空中抖着,房间里仿佛真有小鬼,小鬼没有去捉年迈的娘,而是捉住了马海平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