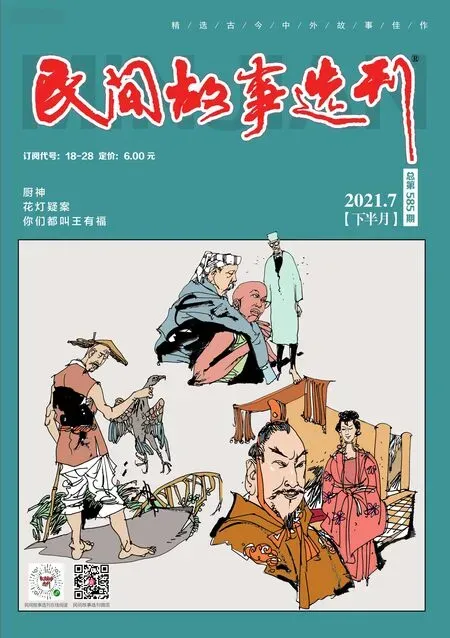鉴家的择赏选
◇文/ 张东兴
宋朝庆历年间,东京汴梁有家书画苑叫听石斋。听石斋的老板听石先生是个书画鉴赏权威,书画在他面前一过,优劣真伪登时显现。所以能够在听石斋立足的书画,立时声名鹊起,身价百倍。
书画是给人看的,可是听石先生却是个盲人,盲人如何鉴赏字画呢?
靠用鼻子嗅!听石先生有种独特的嗅觉,好书画闻起来清香扑鼻,使人心旷神怡;差的书画闻起来恶臭刺鼻。听石先生每天白开水一杯,凭鼻子买进卖出,生意很是兴隆。
这天,听石先生刚开门,一个书生夹了个卷轴进来。此人叫周润碧,在书画界小有名气,平日里,富人借他装点门面,他借富人装点腰包。
伙计见是熟人,赶紧招呼道:“周先生,又有大作?”
周润碧笑笑说:“有,却不是我的。我受朋友相托,请先生鉴赏一幅画。”说着展开卷轴。
听石先生坐定,他刚想用鼻鉴赏,忽闻一股奇臭,赶忙捂着鼻子摆手不迭。周润碧的脸立刻红了,知趣地把画卷起来,放在门外,同时,伙计把窗户都打开了。
听石先生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埋怨道:“润碧先生怎么开这种玩笑?”
周润碧赶紧解释道:“对不住,我也不得已呀。汴梁巨富钱家三公子,是个书法爱好者,成名心切,想请先生美言几句。”
听石先生连忙作揖:“您饶了我吧,别把我的牌子给砸了。”
周润碧从袖子里取出一包银子,朝柜台上一放,苦苦哀求道:“那么借宝店一隅,挂这幅画总可以吧?钱公子愿多出些钱。”
听石先生见对方纠缠不清,就来了气,干脆地说:“行!但钱要足够多——要足够我搬家的。留这画在这儿,我走人!”
周润碧求了半天,一无所得,只得夹起卷轴走了。
第二天周润碧又来了。这回没拿卷轴,捎来了钱公子的话:“三年后,我再拿画来请你鉴赏!”
听石先生心想:这种富家公子,一时兴至玩起书画,但未必真肯下苦功,过些时候就忘了,所以也没把这句话当回事。
谁知三年后的这天,还没开门呢,就听到外面“哐哐”锣响,接着就有人砸门。伙计开门一看,街心停着一乘八抬大轿,两旁站立着两班衙役。衙役见伙计出来,递过一张大红拜帖,神气地吩咐道:“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伙计不敢怠慢,赶紧跑到后堂,一看:一壶白开水还冒着热气,听石先生人却不见了,只是壶底压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交来人”。伙计只得拿了茶壶出去禀报。
壶递进轿子,半晌没有声响。伙计那个紧张啊,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山响。终于,壶又递出来,衙役还传下话来:“我们老爷说了,三年后还来!”
一个“还”字,伙计猛地想起了三年前的钱公子。
到了晚上,听石先生回来了,伙计忙问:“您怎么知道是他?”
听石先生点点头,说:“三年前的臭味,现在三里外都闻得到了。嗬!当了五品大员,就了不起了?看来他功夫是没少下,只是没下在学书画上,而是下在买官上了。”
伙计还是觉得奇怪,不解地问:“他怎么见了您的茶壶就走了?”
听石先生捋捋胡子,微笑着解释说:“茶尚温,人远遁,足见他的书画臭味远扬。五品大员还要顾及面子,所以没敢用武力强迫我说他好。”
转眼三年,又到这一天。这回伙计没忘,心说上回是两班衙役,这回不知是什么排场。万一听石先生仍不接他的画,他恼羞成怒,不定怎么收拾咱呢。伙计一想到这儿,心里就一直七上八下,不得安宁。
谁知一个上午过去了,没有动静;下午过去了,仍没有动静。眼看太阳落山,要关门了,还是没见人影儿。伙计向外看看,不由松了口气,今儿是没人来了!
正在这时,一个青衣仆人抱着个卷轴走进门来。听石先生眼睛好像忽然复明了,他径直走过去接过卷轴,然后递给那青衣仆人一千两银子,又指指自己的鼻孔,最后是摆摆手。
青衣仆人似乎是看懂了,他一言未发,接过银子转身离去。
伙计在一旁看得一头雾水,问:“这是谁呀?”听石先生紧闭着嘴,只是不住地示意伙计赶快把卷轴拿到后面的库房去。
伙计回来,只见听石先生正从鼻子里取出两粒药丸,长长出了口气,说:“就这么两粒防臭丸,花去我一百两银子!时隔六年,想不到这幅画更臭了。”
见这就是六年前周润碧拿来的那幅画,伙计更是惊得张大了嘴:“既是劣质卷轴,那您怎么还花一千两银子买下呢?”
听石先生摇摇头,说:“惹不起啊,那钱公子现在是吏部天官啦!但我仍让他的仆人看看我鼻子里的防臭丸,让钱公子知道:我瞎子眼瞎了,鼻子并没失去嗅觉,所以买下他的画,不过卖给他个面子,省得一趟一趟来熏我。再说还有一笔不小的赚头。明儿你把那幅画挂起来,非二万两不卖!我出去避避,这臭味儿就是带着防臭丸都受不了。”
“这臭画您不愿闻,难道就有人愿买吗?二万两啊!”伙计还是不明白。
听石先生说:“这你就不明白了。画是不值这么多钱,但吏部天官的名可值两万,也许更多呢!”
第二天伙计刚把那幅画挂上,周润碧就领着一群闲文人进来了。他们摇头晃脑地对那幅画大捧一通。一些巨商听到消息竞相前来抢购,最后竟以十六万两出手。钱尚书遂成京都著名书画家。
听石先生自觉遗祸不浅,终身不再品画,只做防臭丸广为布施,以减轻自己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