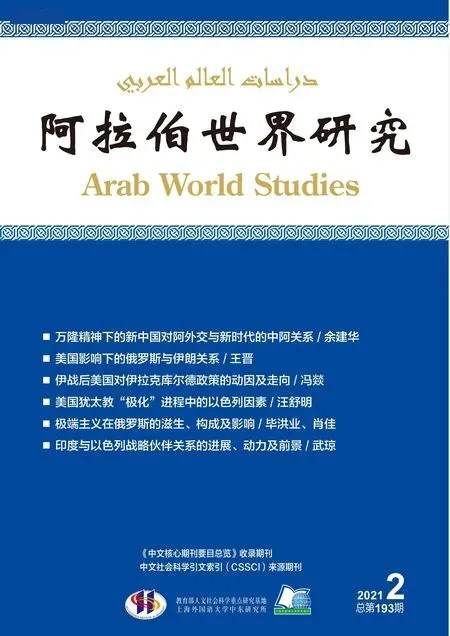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的建构与治理研究*
张婧姝
边境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作为国家领土边缘和与他国紧密相邻的区域,边境有主权象征意义、维护安全、建构认同等功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跨越边境的要素流动与社会交往丰富了边境的意义与功能,同时也重新塑造着边境的定位与特性。 边境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甚至洲际交流互动的特殊区域,是理解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关系发展及文化认同形成的一个重要场域。 边境虽然是国家或者超国家联盟的边缘地带,但边境治理却是维护国际关系和保护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边境问题甚至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国内重大举措的实施。
冷战时期的边境研究已成气候,主要聚焦于边境防御功能与边民生活的研究;自1990 年代后期以来,边境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逐渐形成了边境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跨学科研究路径。 研究关注点包括全球化与边境空间流动、去殖民化与再领土化、流动、混合性、后现代性、新自由主义等。 如今,边境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固定的界线,或者是墙壁、栅栏等领土和主权的实体化形式,它更是一个动态空间。 因此,边境的建构也具有过程性、动态性特点。 尤其是自21 世纪以来,在相关学术讨论中,边境已经从“领土分界线和政治实体的功能”转向“社会文化交融和摩擦中的动态空间”。 这一转变并不是忽视边境的屏障和筛选作用,而是不再只从边境本身出发,通过拓宽研究思路,从超越地理与时间的局限性的视角,研究边境空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公民和移民身份的转换等过程。研究者愈发认识到身份、文化、语言、符号和情感等要素在边境建构中的重要性。
休达(Ceuta)与梅利利亚(Melilla)地处非洲西北角,北临地中海,与西班牙隔海相望,东西南部与摩洛哥内陆接壤。 两国都宣称这两座城市是本国领土,两个城市的归属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鉴于此,本文认为,这两座城市为争议领土,文中按照学术界惯例,使用“西班牙飞地”一词。 这两座城市的边境空间不仅承载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还面对多种二元相对的复杂关系,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繁荣的北部与贫困的南部的矛盾、前殖民者与前殖民地身份意识的遗存、欧盟领土与非欧盟领土的交流等。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一块“西班牙飞地”已经成为欧洲南部边境外扩的重要阵地。 它不仅关乎两国自身利益,也成为欧盟与非欧盟国家,欧洲与非洲之间互动和较量的阵地。
自摩洛哥1956 年独立后,各国学者关于西班牙与摩洛哥争议领土及双方边境的研究不断深入。 西方学者提出了多个研究框架:威廉·沃尔特斯(William Walters)提出身份、功能、合理性与偶然性三层次研究法。他认为,申根边境兼具国家边界、地缘政治和生物政治边界三重性质。 杰姆·安德森(James Anderson)认为,只有通过研究“边界的选择性与渗透性”“边界的差异过滤效应”与“政治经济学的矛盾统一体”,才能更好地理解边境的申根化、渗透过程与再边境化过程。 莱姆·奥多徳(Liam O'Dowd)从屏障、桥梁、资源和身份符号四个角度研究边境现象,尤其关注西班牙飞地边境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提出边境可以成为“连通性引擎”,它不仅不会阻碍流动,反而会对经济要素流动有促进作用。 泽维尔·费雷多(Xavier Ferrer-Gallardo)提出了三维研究模型。 他认为,地缘政治、功能作用和象征性意义三个维度是分析西班牙—摩洛哥边境建构过程的重要标准。 他进一步指出,自1986 年以来,该边境有三条建构路径,一是地缘政治格局由与西班牙—摩洛哥关系相关转为与欧盟国家—非欧盟国家关系、欧洲—非洲关系相关联,二是边境的功能作用兼具政治隔绝和经济互动的双层特性,三是边境的象征意义转向“欧洲要塞”“为生计走私的通道”等隐喻,这三方面的建构过程影响了边境地区的日常活动以及边民认同。克里斯托弗·莱特(Christopher Leite)和肯·埃米尔·穆特鲁(Can Emir Mutlu)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政策分析、田野调查三种方法进行研究,他认为,休达和梅利利亚的案例显示出边境地区更容易受到边境机构或政府的指挥,因此,在研究边境管理时要关注边境活动中参与主体本身的多样性。 作为过渡地带,该边境存在非公正化活动与非法活动,而政治言论也是影响边境建构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边境建构是一个多维建构过程,集管控措施、经济活动、双边或多边关系、地缘政治格局、文化认同于一身,而重大事件的发生也会引起这些维度的变化和再建构。 休达与梅利利亚边境空间的特性本来就复杂, 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边境空间的活动由此出现新动向。 研究这些变化及其引发的问题,有助于描绘该边境空间的地缘政治图景,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国家之间的边境特性。 本文在对休达与梅利利亚成为飞地的历史概述基础上,分析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之间的边境治理政策与理念,从屏障功能、桥梁作用、认同建构三个层面探讨该边境的建构过程及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再建构趋势,进而总结该边境对地缘政治、经济互动、边民认同的影响。
一、 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的形成及其政策
西班牙和摩洛哥边境问题包含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 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曾互相占领和统治过对方的领土,尽管主体领土并不接壤,但却留下了很多突出的飞地和离岛等边境问题。
(一) 殖民时期的休达与梅利利亚及其所有权归属
休达与梅利利亚扼守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大陆隔地中海相望。 从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人统治时期开始,它就是非洲北部的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地,曾受罗马人、汪达尔人、西班牙西哥特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 公元8 世纪起,它成为北非伊斯兰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1415 年,葡萄牙占领了休达,并开始广泛传播基督教。 1580 年,西班牙人攻占休达。 至于梅利利亚则在1497 年被卡斯蒂利亚征服,此后卡斯蒂利亚人和葡萄牙相继占领了北非马格里布地区。 1492 年,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运动(Reconquista)结束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地中海的西部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边境,这条边境经过15 世纪至16 世纪的政治影响、文化渗透和领土划界后,成为今天欧洲—非洲边境的雏形。 自15 世纪起,西班牙统治者开始意识到,非洲西北角的地中海海岸线是西班牙国土安全的生命线,任何其他国家对摩洛哥海岸线的控制都将对西班牙国土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摩洛哥地中海港口城市的控制。 1668 年1 月1 日,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Carlos II)和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六世(Afonso VI)在里斯本签订了《里斯本条约》,葡萄牙正式把休达割让给西班牙。 至此,休达与梅利利亚由西班牙控制。
在西班牙的管理下,这两座城市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殖民渗透的基地。 西班牙通过这两座城市向北非内陆扩张。 1863 年,休达和梅利利亚获得自由港地位。除了驻防功能外,该地区开始有频繁的贸易活动,西班牙因此收获大量的经济福利。 1906 年,《阿尔赫西拉斯条约》签订之后,摩洛哥被分成了两个保护国,法国为主要的宗主国,占领摩洛哥大部分领土;另一个宗主国就是西班牙,主要占领摩洛哥北部丹吉尔、里夫和耶拉巴拉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部的塔尔法亚、西撒哈拉的金河,所占领土约为摩洛哥领土的三分之一。由西班牙管辖的北部沿海城市,贸易兴隆,人员交往活跃,如丹吉尔被称为是“放置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文化的十字路口”。 在保护国时期(1912~1956 年),西班牙统治者认为,休达和梅利利亚并不是殖民地,而是西班牙广阔领土的一部分,他们成功地将摩洛哥纳为西班牙文化和认知的一部分,但这种扩张的逻辑在保护国末期逐渐弱化了。
(二) 摩洛哥和西班牙的争议领土与双方的边境政策
1956 年,宗主国——西班牙、法国的统治结束后,西班牙宣布其管控的摩洛哥获得独立,但依然保留休达、梅利利亚及地中海上的佩雷希尔岛(Perejil)、戈梅拉岛(Gomera)、胡塞马群岛(Hoceima)、舍法林群岛(Chafarinas)等无人岛屿的控制权,并宣称这些领土为西班牙所有。 与此同时,摩洛哥政府也宣称这些城市和岛屿是摩洛哥的领土,并一直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实际上,休达与梅利利亚由西班牙控制和管理,并有军队常驻。
摩洛哥从未放弃夺回休达和梅利利亚的努力。 自1956 年独立以来,摩洛哥一直要求恢复国家北部仍被西班牙控制领土的主权,并利用一切机会重申其立场。 首先,摩洛哥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提交给联合国的第一份文件就是与西班牙未解决的争议领土的清单。 1975 年1 月27 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提交了一份《A/AC-109-475 备忘录》,要求将在西班牙控制下的摩洛哥北部领土都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中,其中就包括休达和梅利利亚。哈桑二世国王(Hassan II)于1987 年1 月提议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旨在讨论休达和梅利利亚的未来,但西班牙政府没有做出正式回应,并一直拒绝与摩洛哥就这两个城市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 1994 年3 月3 日,哈桑二世在其继位33周年之际,再次呼吁设立专家委员会,并重申摩洛哥对这两个城市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穆罕默德六世国王(Mehmed VI)在2002 年7 月30 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要与西班牙进行对话,还重申了其父哈桑二世国王关于设立委员会的建议,要求与西班牙共同研究并解决摩洛哥北部地区的主权问题。2007 年11 月6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访问休达和梅利利亚,激化了摩洛哥和西班牙有关争议领土的矛盾。 摩洛哥强烈谴责这次访问,认为“西班牙政府公然藐视1991 年两国之间《友好合作条约》的使命和精神”。
西班牙紧握休达和梅利利亚的控制权。 在国家层面,1995 年3 月14 日,《西班牙自治法》生效,该法将休达和梅利利亚划为西班牙的两个自治市,为“西班牙飞地”身份提供了法律依据。 自此,西班牙从国家法律层面将休达和梅利利亚纳入本国国土。 在超国家层面,1986 年西班牙加入欧盟,1991 年又加入《申根协定》,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的意义有了重大转向,即“欧洲化”(Europeanization)与“申根化”(Schengenization)转向,休达和梅利利亚成为欧盟在北非的领土。 这两座城市的边界不再只是两个国家的边境,也是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之间的边境,可以看作是欧盟边境的最南端,成为一个新兴政治空间的外部边境线。 因此,边境空间的参与主体扩大了,不仅包括边境两侧的国家,还有超国家联盟和非政府组织等。 1995 年西班牙加入 “欧洲—地中海伙伴计划” (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也称“巴塞罗那进程”, Barcelona Progress),旨在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地区。 此计划标志着欧盟开始恢复其在地中海地区的活跃表现,并积极促成欧盟国家与地中海非欧盟国家跨边境的经济、文化合作。2004 年,“欧洲—地中海伙伴计划”又并入“欧洲睦邻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简称ENP)。 在此政策背景下,欧盟强调将同等对待地中海国家与欧洲其他邻国,积极加强与地中海伙伴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机构联系。除了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以外,欧盟还为西班牙的边境设防和边境事务投入了大量资金,因此,欧盟也参与了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的治理过程。
为了防止移民非法入境,西班牙在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军警,并架设高科技监视系统。 一方面,该边境空间是高度军事化的空间。 如西班牙政府在休达边境布置了300 名国家警察和近700 名国民警卫队警察,1 个军事指挥官总部、3个步兵营、1 个装甲团、1 个炮兵团和后勤保障部队等;另一方面,在休达和梅利利亚边境线上和周边有大量安全设施,如陆地上建造了长8.4 公里,高3.5~6 米的双层栅栏,上面装有铁丝网、监视器和雷达系统。 为了防止陆上与海上的非法跨境行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引进了外部监视系统(Integrated System of External Surveillance,下文简称“SIVE 系统”),由雷达、红外线摄像头、能测探远距离心跳的传感器等组成,并使用直升机、巡逻艇和警车,拦截各条路线上的非法移民。 “SIVE 系统”是逐步建成和完善的,它监视着直布罗陀海峡、安达卢西亚海岸和加那利群岛海岸等边境地带。 而这些部署建设得到欧盟大量的经济支持。由此可见,这两个城市的边境问题已经得到欧盟的认可和重视。 此外,西班牙于2015 年对《公共安全法》进行了修正,并得到国会批准,该修正案为将非法移民立即驱逐出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法案并没有注明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在执行该修正案时,它可能会违反《日内瓦公约》或《欧洲人权公约》等条约中列出的有关特殊人群享受庇护权、不被驱逐等权利保护的条款。
西班牙加入欧盟后,该边境治理向两极分化发展:一方面,在边境线上强化物理屏障作用,以期对边境进行严格的封锁和管控,阻止非法移民的跨境行为;另一方面,2010 年“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计划”(EMFTA)启动后,欧盟致力于实现经济“去边境化”(economic debordering)。 西班牙作为欧盟成员,一直在边境空间贯彻实施上述发展理念。
目前,该边境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首先,从古典地理学和古典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条边境依然是传统的地理边境,是政治地理界限。 其次,西班牙加入申根协定后,欧盟是在尝试构建一种新政治边境的空间布局,这种空间性是超国家组织的外围界限,是欧盟努力扩张边境、维护边境稳定并尝试“去边境化”的空间,具有新的屏障功能、桥梁作用和象征意义。 最后,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休达和梅利利亚虽然仍然保持着领土单位(territorial units)间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但同时又是跨国人员与经济要素流动频繁的区域,现已成为一个模糊地带。 因此,该边境兼具政治上的封闭性与经济上的开放性,双边关系也一直在对抗和交流中持续。
二、 后殖民时期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的建构
从地缘政治和认同建构层面考量,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建构既是边境空间上国家间、超国家组织间政治角力的过程,也是边民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 不仅如此,该边境建构还深受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 从1956年摩洛哥独立至今,该边境空间的功能、象征意义与殖民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西班牙加入欧盟后。 随着“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的深化,其对边民生活与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断加深,欧洲—非洲边境在休达与梅利利亚边境空间中形成。
(一) 双重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
尽管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对解读边境仍然有意义,但在研究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状况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该边境在主权仍有争议的同时,其象征意义扩大化、欧洲化、申根化,因此,要从全球化视角和超国家空间建构的角度分析其地缘政治格局。
首先,休达和梅利利亚边境被赋予了国家间和超国家的双重地缘政治意义。起初,西班牙—摩洛哥边境只是普通的国家边境。 但从1986 年西班牙加入欧盟以来,该边境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再建构,即成为欧洲—摩洛哥边境,新的边境并没有抹去原有的边境,而是形成两条各有意义的边境的重叠,可谓一个双重混合体。 一方面是两个国家领土空间(territorial containers)之间的边境,即西班牙飞地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另一方面是“超国家联盟”领土(perimeter),即欧洲大陆的外围边境。 1995 年至2000 年间,西班牙建设的第一个安全保障项目费用总计为4,800 万欧元,其中75%由欧盟资助,用以修建休达周围的铁丝网围栏。欧盟的经济支持加上西班牙的警力与技术投入,体现了该边境的双重地缘政治意义。
其次,该边境具有屏障和桥梁双重作用。 该边境是进出欧洲的咽喉要塞,在地缘政治层面,具有屏障作用;而在贸易往来与人文交流层面,具有桥梁作用。欧盟作为超国家组织逐渐掌握了原先属于西班牙的边境治理权力,传统上的民族国家边境,升级成为带有“欧洲要塞”与桥梁连接双重意义的边境。 不仅如此,休达和梅利利亚还是欧洲移民政策关注的重要地区。 沃尔特斯认为,地中海边境是欧洲最重要的地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体现边缘和界限的概念。欧盟对其南部边境的治理目的有两个,一是架设有利于吸引投资和促进人员交流的跨境桥梁;二是在边境地带建设栅栏与“SIVE 系统”,以建起对非欧盟国家移民的“过滤性”和“排他性”的屏障。
最后,该边境是非洲非法移民入欧洲的重要通道之一。 彼得·古德(Peter Gold)认为,“作为唯一一个在欧盟和非洲之间的陆地边境,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非洲大陆的潜在非法移民。”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的经济差距自1986 年以来不断在扩大,由此产生的结构不对称,刺激了直布罗陀海峡和飞地边境两侧的货物和人员的非法流动。 对边境人员流动的管理,尤其是阻止非法跨境行为,成为边境治理中最重要也最普遍的内容。 启用“SIVE 系统”后,试图乘坐小型渔船非法跨境到西班牙海岸的人数并没有减少,发生变化的是非法跨境的线路轨迹,如穿越部分无监控的直布罗陀海峡海域等,不仅给移民治理带来了挑战,也增加了非法移民的死亡率。此外,这条边境上也发生过多次群体性冲突栅栏的事件,从2000 年到2015 年,大约有23,000 名非法移民越过了休达边境。大量的非洲移民通过合法与非法途径由此入欧,除了非法跨境行为以外,合法的过境资格也是有筛选的,筛选标准由过境者的经济、性别、历史、种族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所以,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边境。
(二) 边境的桥梁作用与经济“去边境化”
尽管在领土问题上存在长期争端,西班牙一直是摩洛哥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经济伙伴,休达港口与梅利利亚港口是两国贸易的重要支点。 1995 年,《巴塞罗那进程》指出要加强“欧洲—地中海伙伴”合作关系,计划到2010 年,逐步建成一个“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这个计划被认为是欧盟与地中海国家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欧盟开始从过去单方面给予地中海国家贸易特惠待遇的给予者向对等的自由贸易体制中的合作者转变。 在“欧洲睦邻政策”的框架下,欧盟加强与环地中海国家的合作,不断为架设地中海两岸经济桥梁而努力。 可见,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欧盟认可的欧洲南部边境,对推动欧盟一体化具有显著意义,它既是跨境贸易活跃的区域,也是联通地中海两岸的纽带,发挥着桥梁连接作用。
该边境独特的桥梁作用得到三个方面的保障:一是西班牙法律规定休达与梅利利亚是免税区,不受《欧盟渔业和贸易政策》(EU Fisheries and Trade Policies)等国际贸易准则的约束;二是摩洛哥不承认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领土,所以这两座城市的边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疆界,部分国际法效力在此有局限性,因此,这条边境的税收制度和贸易规则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而促进了边境两侧的经济互动;三是西班牙1991 年正式加入《申根协定》后有一项特殊条款,即允许相邻城市的摩洛哥公民免签证进入休达与梅利利亚,因此,在日常边境生活中,经济利益优先于主权,或者说主权由商品和人员流动来界定,而不完全由国家政府控制,导致经济“去边境化”特点不断凸显 。
在国家经济发展层面,边境两侧的城市从经济“去边境化”中各有收益。 从摩洛哥一侧看,边境相邻的纳多尔市(Nador)和菲尼迪克市(Fnideq)因为经济互动实现了人口增长与城市扩张;从飞地一侧看,休达和梅利利亚的经济可持续性取决于它们与摩洛哥内陆地区的互动。 受惠于欧盟对农业活动的补贴,西班牙经济大幅增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劳动力,西班牙每天都从摩洛哥进口劳动力和消费者,尤其是从休达和梅利利亚周边的城市。 如得土安市(Tetouan)和纳多尔市的摩洛哥公民可以免签证进入西班牙,但不包括在这两个城市生活但没有居住件的人,而且必须当日午夜前返回摩洛哥。这类跨境流动得到了申根协定法律框架的允许,对摩洛哥法律与欧盟政策来说,是一种例外情况。 这种特殊的司法保护伞意味着边境的屏障效应仅适用于一部分人,这就产生了 “选择性”。 边境的“选择性”与新的经济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边境经贸关系和人员结构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周边的摩洛哥城市居民的生计得到了保障,“西班牙飞地”也获得了劳动力资源,经济发展可持续。
在超国家贸易交流层面,非法贸易深化了经济“去边境化”。 边境空间内的非法贸易也被称为“影子经济”,“影子经济”在欧洲是公开的秘密,指的是偷税、漏税、走私、贩毒等非法经营活动。在休达与梅利利亚边境的桥梁作用中,“影子经济”占有重要份量,尽管两国官方都宣称该边境是严格管控的,只有“合法”的货物和人员可以跨越,但每天仍有大量的走私活动。 摩洛哥人进入休达购买商品,再通过边境,返回摩洛哥进行售卖。 2014 年的数据显示,每天约有15,000 人进行跨境走私贸易,约有45,000 人直接生活在带有非法性质的跨境贸易中,另有40 万人间接参与其中。该边境尚未建立完全“正常化”的和双方一致同意的商业交往模式,而既有的管理程序过于烦琐,因此,为休达和梅利利亚边境空的走私活动提供了平台。各类边境群体都从走私贸易中赚取生计,从而保障生活水平。 边境上的合法贸易与“影子经济”,又助力了西班牙经济发展与欧盟一体化的推进。 在这些经济活动中,边境不再是屏障而是一座桥梁。 这座桥梁的风雨楼是“欧洲—地中海伙伴计划”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政策。 这些政策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消除贸易边界,因此,该边境的经贸交流呈现出明显的“去边境化”特性。
(三) 边境两侧文化认同的建构
首先,殖民思想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深远。 欧盟不断扩大疆域并积极参与边境事务的做法,与殖民时期的扩张模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延续性。 研究近几年欧盟南部边境动态,西班牙—摩洛哥边境案例中还存在“宗主国”和“保护国”的心态遗存。 即使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欧盟外部边境与非洲的关系依然保留殖民时期的认知习惯。 曾有学者指出,“执着于关注和分析自我国家化和将对外关系国家化的社会构建主义表述,就有产出被欧洲政治正确普遍接受的文化种族主义的风险”。 也有学者指出,在某些方面,民族国家及其边境在被殖民时期形成的身份认知是根深蒂固的。西班牙加入欧盟后,便加入了一个新的非实体的超国家领土单位,在欧盟内部,欧洲文化认同度高,作为欧盟成员的优越感强。 而这种优越感延续并扩大了“领导者”与“保护者”的心态,并明确地保留了“保护者”和“受保护者”之间的区别。还有学者认为,对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居民来说,西班牙的边境监管可能是一种强化认同的做法,其目的是强化欧盟社会空间意象的界限。
其次,文化认同具有多元交织的特点。 西班牙—摩洛哥边境是建构国家和超国家、民族和超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空间。 第一,这条边境是欧洲管理其南部边界的调节器,这一调节器最大的特点是参与主体的多样性。 国家和超国家领土单位共存、边境共享。 在这一背景下,西班牙—摩洛哥边境已经不是一堵简单的高墙,而是一套“边界体制”(border regime),承担边界管理职能的不仅有边境线上的欧洲国家,还有众多超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的组织。 此外,欧洲往往会将对北非和中东移民的控制转移到非欧洲的第三国,从而形成一种边界管理外包的状况,这也增加了边境建构的参与主体。 第二,西班牙—摩洛哥边境与欧洲—非洲边境的重叠,象征着历史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经济的重新配置、冲突与弥合,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建构,自我认知与他者化也面临再建构。汉克·文·豪托(Henk Van Houtum)和汤·文·纳尔森(Ton Van Naerssen)指出了他者化的决定性作用,它让空间建构和群体凝聚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净化的行为,即寻找合适的有凝聚力的群体,在一个可对比其他空间实体的空间中活动。从这点出发,他者是被需要的,也因此不断地被生产与复制,以保持在有地域划分的社会格局中形成凝聚力。 在跨境流动、贸易交往过程中,群体认同与他者化同时被强化,促使各种边境群体更加凝聚,这些群体都是边境活动的参与者和主导者,所以这条边境上的认同是多元而独特的。 如该边境空间同时接纳了欧洲人、非洲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其他的身份。此外,它还为模糊的、复杂的、混合的身份提供了容身之地。 所以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空间具有多元交织性。
最后,文化认同的建构中隐含排他性。 欧盟致力于消除欧洲内部边界(internal border),其前提条件其实是外部边界 (external border) 的确立。 在 1986 年,西班牙加入欧盟之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移民问题,北非移民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但在加入欧盟之后不仅颁布了首部移民法案,而且移民问题在20 世纪90 年代初迅速恶化,造成了北非移民在当地社会生活空间和社会地位上的边缘化。
因此,有欧盟专家提出“欧洲要塞”这一概念来处理一体化之后的欧洲边境问题,旨在打破内部藩篱的同时又在外部扎起篱笆,实施更为严格的边境管理政策。
在这个新兴政治空间的外部边境空间中,明确区分出欧洲人和非洲人,可自由通行者、有条件通行者、非法移民,强化了边境两侧居民的身份差别。 在西班牙领土欧洲化后,边境的象征性特质有助于加深和发展欧盟的超国家集体认同,同时也制造了差异性,尤其是这条边境延续了殖民时期的区隔意识。 针对西班牙—摩洛哥边境,尤其是边境围墙出现了一些新的隐喻,如“新的耻辱墙”“金色的窗帘”“欧洲的墙壁” “欧洲要塞的护城河”等,这些词语展现着边民对边境排他性的讽刺。
三、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的重构
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本来就复杂的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形势有了新变化,边境空间活动出现新动向。 在疫情蔓延全球及欧洲疫情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摩洛哥于2020 年3 月开始关闭所有过境点,停止所有国际航班,并采取了严格的宵禁措施。 即使随后有条件开放边境,边境空间也必将有所改变和重构。 疫情的到来,一方面给摩洛哥关闭边境、严打走私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又对安全局势形成了新的挑战。
(一) 边境的屏障功能增强与桥梁作用弱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摩洛哥与西班牙的边境口岸关闭,但这并未遏制西班牙货物继续通过休达和梅利利亚走私到摩洛哥。边境的“选择性”更加突出,屏障功能不断增强。 因为在疫情时期封闭边境的情况下,边境的屏障功能尤为凸显,人员停止流动对合法经济和“影子经济”都产生重创,休达和梅利利亚的经济,乃至欧盟经济都受到影响。 疫情爆发以来,随着封锁范围的扩大以及休达港口、梅利利亚港口的持续关闭,双方经济都受到损害,边境地区的很多批发商销售额下降了30%~40%。 随着边境贸易的停止,港口关税收入也逐步下降。
目前来看,桥梁作用弱化,屏障功能凸显,经济活动将在该边境的再建构中重置,合法贸易与“影子经济”的比例也会有变化。 一方面,欧盟需要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监管非法移民,西班牙需要与摩洛哥配合,管控非法人员进入西班牙。在疫情扩散时期,非法移民依然通过翻越边境等方式进行偷渡,而疫情对原有的遣送机制和关押拘审政策提出了挑战。 西班牙政府发言人伊莎贝尔·塞拉(Isabel Celaá)指出,欧盟2019 年批准的1.55 亿美元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在2020 年援助摩洛哥约3,570 万美元,以遏制非法移民流入西班牙境内。另一方面,“西班牙飞地”需要合法人员流动。 2020 年7 月,摩洛哥计划重新开放边境,但不包括休达与梅利利亚边境,而西班牙要求与摩洛哥对等开放边境。 西班牙政府表示,只有摩洛哥允许西班牙人民进入摩洛哥时,才会开放西班牙摩洛哥边境。
综上,疫情时期,非法跨境行为仍然存在,合法人员难以流动,边境空间经济互动和经济发展停滞,治理难度增加。
(二) 边境局势严峻与认同重构
由于入境流的中断,休达和梅利利亚的金融业和商业受到严重打击,摩洛哥公民的失业率攀升,边境城市发展停滞,各项经济指数下滑,这些都对边境治理和安全稳定形成巨大压力。 边民对边境关闭表现出的愤怒,是因边境屏障功能影响了边民生计而感到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双边政府应急能力和治理智慧经受着极大考验。
在边境社会治理层面,安全局势受到威胁。 疫情爆发以后,数千名摩洛哥人滞留休达。 到2020 年3 月西班牙-摩洛哥边境关闭后,数以百计的摩洛哥人仍滞留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生活艰难。 因为边境口岸关闭,许多摩洛哥人选择从地中海游泳回国,这种行为引起了边境两国政府的担忧。因为大量公民集中在同一地区或水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感染风险,进而增加卫生隐患。
在边境社会民生层面,失业率上升,生计受损。 边境空间的非法贸易被迫停止,边境关闭使得大量的每日跨境工作人员成为失业人群,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其中多数是进入休达和梅利利亚工作的摩洛哥人。 截至2020 年9 月,休达待业在家的人数约为3,000 人,梅利利亚约为5,000 人。 据估计,休达市约有25%的市民已经失业。对于边境周边的摩洛哥城市居民来说,没有商业活动等于剥夺了边民生计。 如果生计受到影响,边境局势波动性和动荡风险性会增强。
在认同层面,边民的欧洲优越感不断弱化。 摩洛哥独立后,国家一直坚持去殖民化,而新冠疫情爆发后,边境认同受到冲击。 一方面,身处西班牙境内的摩洛哥人,出现大量的回返需求。 这与疫情爆发前的流动需求成逆向发展,边民从由摩洛哥向西班牙流动和工作为主,转为西班牙向摩洛哥回返需求为主。 在经济收益消失或者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边民的国家认同不断在强化;另一方面,两地所承载的欧洲身份受到影响,优越感减弱,两地居民感到自己被孤立了。 休达和梅利利亚的发展与繁荣的源头本来就不在西班牙,而是在摩洛哥,随着边境空间的经济活动停止,经济发展也逐步停止。 而在疫情爆发后,欧盟反应迟缓,一直未能与地中海国家形成合作协议和统一的管控措施。 欧盟几乎无法支援西班牙,而西班牙政府也无暇顾及休达和梅利利亚。 边民开始控诉西班牙政府和欧盟地忽视态度,边境居民的欧洲认同和欧盟认同随着无助感增强而不断弱化。
(三) 摩洛哥加强边境治理与边境重构
在疫情时期,国家的治理思维不能只限于遏制边境空间的流动,权力机关需要在考虑国家与地区安全的基础上,更多地从民族特性、地区稳定、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权衡治理手段。 边境管理模式表现出的政策弹性也是一种协商的手段。 而边民对国家界线的了解是长期政治宣传和国家治理的累积性结果,进而使得空间秩序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摩洛哥主导争议领土的边境建构提供了契机。 在2020 年,摩洛哥政府的三项重要举措实现了其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宣传,也体现出其对边境治理的重视,争议领土的边境将有可能出现重构。
首先,在疫情爆发初期,摩洛哥颁布了新的海事法案。 摩洛哥众议院在2020年1 月22 日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两项法案——《37.17 号法》与《38.17 号法》。其中,第一项与领海边界有关,第二项与专属经济区有关,计划在距离摩洛哥海岸线200 英里处建立一个经济特区。摩洛哥1982 年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国家海洋事务是“内部事务和主权行为”。 这两项法案在此基础上划定摩洛哥海上边界,修改和完善了摩洛哥在1970 年代和1980 年代初通过的一些现在看来已经过时的海事法条。 如1973 年提出的自南部海域塔尔法亚“阿尤比角”起,沿大西洋沿岸,至地中海海域完全封闭的政策就已不符合现状。 外交、非洲合作与摩洛哥海外侨民事务部部长纳赛尔·布里达(Nasser Bourita)认为,两项法案是根据穆罕默德六世国王有关重视海洋事务的指示出台的,它填补了国家法律体系有关划定海上边界的立法真空,将摩洛哥法律管辖权扩大到其所有海域,明确划定海域边界。 布里达还表示:“摩洛哥王国与邻国,特别是西班牙有着长期牢固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关系,摩洛哥重视多边合作和相互尊重,愿与邻国,尤其是西班牙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积极的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政策发展,但前提条件是主权不可商量。”该法律引起摩洛哥与西班牙双方有关海域划疆的争执,同时也显示出摩洛哥对其领土完整和海洋控制权的坚决态度,将会引发摩洛哥与西班牙有关飞地主权问题的再讨论。
其次,摩洛哥关闭陆路海关与港口。 其目的有三:一是通过严禁边境人口流动降低公共卫生风险,二是打击走私,三是重新调整边境经济结构。 即使边境开放后,摩洛哥人进入西班牙领土的机会和数量也相当有限。 而且在边境重新开放的过程中,摩洛哥政府明确表示,不开放休达和梅利利亚边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兰查·冈萨雷斯·拉亚(Arancha González Laya)表示,面对这一决定,西班牙政府虽然表示“非常尊重”摩洛哥的决定,但实际上,西班牙政府希望能够重新开放西班牙—摩洛哥边境,并曾通过外交部进行调解,但没有任何效果。尽管该边境地区的非法贸易帮助了摩洛哥城市居民维持生计,但对摩洛哥的边境治安和整体经济发展有消极影响。 有学者指出,这些非法的跨境流动导致了国家生产的非公平竞争,阻碍了工业单位的建设,阻碍了外国投资,导致失业。摩洛哥海关与间接税总署署长纳比尔·拉赫达尔(Nabyl Lakhdar)估计,休达边境每年的非法贸易额在60 亿到80 亿迪拉姆之间,约为摩洛哥合法贸易出口额的十倍,摩洛哥政府因此损失20 亿到30 亿迪拉姆税收。在休达和梅利利亚边境欧洲化20 年后,著名的“走私行业”似乎正在演变成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为了生存的走私行业”。在关闭边境的同时,摩洛哥加强边境治理,采取鼓励融资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等地区开展业务,对边境经济活动重启有重要影响。
最后,2020 年有关争议领土的声明对边境问题产生影响。 2020 年12 月10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沙漠的主权。 就在同一天,摩洛哥宣布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 西班牙向拜登政府表示抗议,要求撤回特朗普的决定。 有学者认为,“西班牙不会影响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决策,其举动更多是平息内部政治需要的一种营销手段。”在特朗普政府表态后,摩洛哥首相萨杜丁·欧斯曼尼(Saad Eddine El Othmani)在2020 年12 月19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休达和梅利利亚的主权归属问题一直是个僵局,这个问题已经搁置了五六个世纪,必须坐下来谈谈。”休达与梅利利亚的归属问题、边境问题再一次成为焦点,摩洛哥政府对主权与边境事务的强硬态度,体现出摩洛哥一直在为收回失地并主导边境事务和边境再建构而努力。 对于摩洛哥关于讨论休达与梅利利亚等争议领土的请求,西班牙一直冷淡应对,而在此次摩洛哥首相发表言论之后,西班牙外交部紧急召见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并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希望所有伙伴尊重其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要求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澄清摩洛哥首相的声明。”此次热议不仅与西班牙—摩洛哥边境问题有关,还与摩洛哥、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有关,而且休达与梅利利亚边境还象征欧洲—非洲的边界。 因此,一方面,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和边境问题与地缘政治格局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摩洛哥与西班牙和欧盟在农业、海洋产业等方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2020 年末摩洛哥政府对争议领土的表态,或可刺激西班牙政府就争议问题与摩洛哥进行更深入的沟通,也对西班牙与摩洛哥的经贸关系,乃至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影响。
四、 结语
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问题具有多维度的“双重性”。 第一,在地缘政治层面,它不仅是国家间的问题,也是超国家和洲际间的问题;第二,在边境空间的活动中,加强物理边界与经济“去边境化”走深同时存在;第三,在边境功能层面,该边境既有屏障功能,也有桥梁作用。 这条边境承载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重意义,也影响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 不仅如此,该边境的文化认同具有多元“交织性”。 在历史中多次重构和再边境化,建构了多元交织的文化认同,形成与后殖民主义、多元主义、超国家认同紧密相关的生存空间。 对边境的有效治理,不仅有助于边境双方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经济有序发展,保护国家完整和安全,而且对欧盟国家—非欧盟国家关系、欧洲—非洲关系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这条边境的建构具有不可避免的“波动性”。 在西班牙—摩洛哥双边关系的波动、全球经济发展和衰退、欧洲一体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该边境不断再建构。 而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新法案的出台、特朗普政府的表态等事件,再一次影响了该边境在外交关系、经济活动、地缘政治格局、文化认同层面的建构。 在边境不断再建构的过程中,能够在封闭性与开放性、合法经济与影子经济、双边关系与多边关系中找到平衡点,既有助于在跨境活动近乎停滞的同时,维持边民社会稳定,也有利于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 可以说,只有建立长期可调整的、有效的跨界互动机制,才是维护边境稳定和推动欧洲—非洲各领域交流的应有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