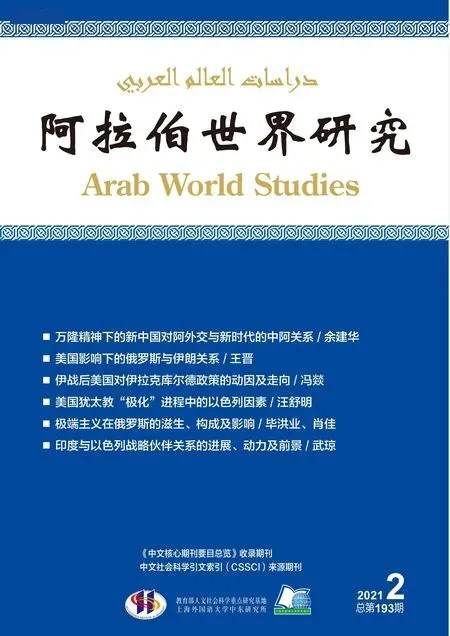美国影响下的俄罗斯与伊朗关系*
王 晋
美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面对美国的压力,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关系微妙。 一方面,在美国的战略压力下,俄罗斯和伊朗在多个领域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伊朗未形成应对美国的亲密同盟。 如何应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国,是俄罗斯和伊朗双边关系中的主要分歧。
一、 问题的提出——既未结盟,亦未“搭便车”
学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和伊朗之间是“亦敌亦友”的伙伴关系。 双方尽管保持着多领域合作,但彼此间的不信任感一直存在。正如有学者所指,俄罗斯和伊朗“尽管强调‘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但从未真正推行过相关政策,莫斯科和德黑兰并不信任彼此。”
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共同的强敌,将促成其他国家采取“联盟”或者“搭便车”的措施来应对。 无论是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论述下“两国或者多个主权国家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样“正式”的“军事联盟”,还是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提出的“为了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者扩大其影响力,不同国家间组成的使用或者不使用武力的国际机制”,亦或是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olt)笔下“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国家间结盟的形式和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无论哪一种联盟的定义,都没有出现在伊朗、俄罗斯和美国的互动关系中。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联盟”是实现“均势”和构筑安全的重要手段。 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提出,一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同另一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之间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状态,是维系国际和平的重要手段。 摩根索提出,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增强自身实力、依靠其他国家权力或者阻止对手增强权力,其中第一种策略将导致军备竞赛,而第二种策略和第三种策略,将导致结盟的产生。 他进一步指出,国家是否会选择结盟,以及如何选择结盟,是根据外交形势而灵活变化的,其目的在于维持“权力平衡”,并提出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或者差异性对于结盟政策并没有太大影响,“同物质利益无关的纯意识形态联盟只能是不成功的联盟。”
沃尔兹(Kenneth N. Waltz)也将联盟视为维系国际结构“平衡”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认为小国往往会通过团结一致的方式来“制衡”大国的压力。斯蒂芬·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中提出,国家选择结盟是为了应对“威胁”而非“权力”,并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对于其他国家形成威胁,主要从综合国力、地缘近邻性、进攻性力量和进攻意图四方面来衡量。
国家也可能通过“搭便车”(Bandwagoning)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护。 斯蒂芬·沃尔特提出,国际社会之所以没有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实力太过强大。 “制衡可见的威胁并非唯一的结盟动力,在一定的条件下,国家可能选择追随政策而非制衡政策,尤其是他们相信抵抗将毫无效果,或者通过接受对方的方式,能够化解危机的时候。”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在斯蒂芬·沃尔特观点的基础上,加入了国家内部视角来分析结盟的动因。 施韦勒提出,结盟并非仅为“应对威胁”,还可能是为了扩大利益而选择与强国“搭便车”。 施韦勒进一步提出,国家可以被分为“现状国家”(status quo)和“变革国家”(revisionist)两个类型,其中“现状国家”往往追求安全,而“变革国家”则往往选择“搭便车”来获得更大的收益。格伦·斯奈德也认为,国家是否选择结盟,不仅要考虑到盟友的意愿,还需要敌对国家的反应,在增强自身安全和避免冲突激化之间,做出合理的决策。
俄罗斯和伊朗被美国视为“变革国家”和挑战者,美国国内也有拉近与俄罗斯和伊朗关系的呼声。 在美国看来,俄罗斯谋求与美国平等的国际地位。 “俄罗斯精英视这个世界建立在多极国际格局的基础上,西方将持续衰落,俄罗斯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获得自己应得的国际地位。”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变革性”(revisionism),主要体现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上。 “尽管美国具有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潜在的挑战者,尤其是在普京上台执政之后。”美国国内有观点认为,中东地区,美国应着力与俄罗斯实现合作,共同遏制伊朗。 “在中东地区寻求共赢的战略对美国和俄罗斯双边关系,以及国际体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对伊朗能够施加强有力的影响,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走近,能够帮助美国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保卫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安全和利益。”
伊朗外交战略的“变革性”表现在谋求成为中东地区秩序的主导国。伊朗希望在巴以问题、库尔德问题、伊拉克战后重建和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努力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施加更深刻的战略影响。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话语体系,决定了伊朗通过不断挑战现有地区秩序,来捍卫政权的合法性。”美国国内有观点认为美国和伊朗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俄罗斯。 布热津斯基将伊朗定位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认为“伊朗……能够为中亚新的政治多元化进程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伊朗控制着波斯湾东海岸。 尽管伊朗目前仍然敌视美国,但伊朗的独立能够阻碍俄罗斯在波斯湾地区对美国利益构成任何长期的威胁。”布热津斯基提出,美国应当对伊朗进行“拉拢”,遏制俄罗斯在中东和中亚的扩张。
现有的联盟理论,无法解释俄罗斯和伊朗关系。 俄罗斯与伊朗,并未因为美国的共同战略压力,而形成紧密的联盟关系,也并没有选择跟随美国“搭便车”的外交战略。 一方面,伊朗和俄罗斯都具有“变革者”的诸多特征,且美国国内也有观点要求发展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伊朗和俄罗斯应追随美国“搭便车”,而非与美国对抗。 但美国仍然是俄罗斯和伊朗的主要对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伊朗,都没有选择与美国组成任何形式的同盟。
另一方面,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威胁,俄罗斯和伊朗也并未“结盟”。 伊朗总统鲁哈尼将伊朗和俄罗斯关系总结为:“我们双方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保持着沟通,但是我们并不是盟友。”俄罗斯也认为,不应过度强调与伊朗的关系,“两国的合作仍然是理性和现实的,难以超越现存的模式和范围”。美国的威胁,并未促成俄罗斯和伊朗缔结同盟。
本文认为,俄罗斯和伊朗对美国的解读,是由俄罗斯和伊朗“大国”的自我定位决定的。 一方面,俄罗斯和伊朗的“大国”自我定位,使得两国难以选择“搭便车”的政策追随美国;另一方面,俄罗斯“世界大国”的自我定位,与伊朗“中东大国”的自我定位差异,使得两国在如何发展与美国及其盟国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阻碍了俄伊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二、 俄罗斯与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威胁
对于俄罗斯和伊朗来说,美国是国家安全的重大外部威胁。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争夺和博弈,涵盖了从中东欧、外高加索、里海、中亚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就是向其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及信息压力;北约不断增强实力并违反国际法准则发挥全球职能,成员国不断加强军事活动,北约东扩并向俄罗斯边界持续推进军事基础设施——所有这些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伊朗与美国同样处于激烈的对立状态。 美国视伊朗为“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希望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打压伊朗。 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如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伊拉克什叶派“人民动员军”(Hashd al-Sha'abi)等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威胁着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安全和利益。 “美国与伊朗的对峙……是从意识形态到地缘利益的全方面对峙,因此难以调和。”
面对美国的压力,俄罗斯和伊朗重视彼此的合作机遇。 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使得俄罗斯决心加强与伊朗的合作。2012 年普京在俄罗斯联邦议会的演讲中,提出了“向东看”(Turn to East)战略,即“在21 世纪,俄罗斯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东方。”2014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遭到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制裁措施。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崛起,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换,俄罗斯希望进一步增进与“东方国家”的关系。 2015年,普京在俄罗斯瓦尔代(Valdai)峰会上,提出了“大欧亚”(Greater Eurasia)的概念。 普京解释道:“我们提议建立一个大欧亚伙伴关系,谋划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并邀请与我们国家关系密切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加入这一组织。”“大欧亚”战略是俄罗斯为了应对美国和欧洲的制裁和围堵,而采取的战略应对。在此背景下,俄罗斯重视发展与伊朗的关系。
伊朗将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为打破美国封锁的重要手段。 近些年来,在“向东看”战略的引领下,伊朗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等“东方国家”的关系。 “向东看”战略,最早由伊朗强硬派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于2008 年提出,通过发展与俄罗斯、中国、印度、拉美和非洲等“非西方世界”的关系,破除美国和西方国家针对伊朗的制裁与封锁。 2018 年美国重启针对伊朗制裁措施,伊朗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鲁哈尼政府提出“向东看2.0”战略,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等“新兴强国”的关系,摆脱美国的制裁压力。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表示,伊朗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关系非常深入,将会继续为构建地区安全和稳定发挥关键作用。”
伊朗总统鲁哈尼曾经将“经济合作、核工业与打击恐怖主义”,列为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基石。首先,在经济合作领域,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贸易额不大,但是双边贸易量长期保持稳定。 俄罗斯和伊朗的贸易额有限,2018 年两国贸易额仅为17 亿美元,占伊朗2018 年对外贸易总额的0.3%。伊俄两国贸易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领域。 俄罗斯出口伊朗的物品主要包括机械、钢铁、木材、植物油、小麦和牛羊肉等,而伊朗则向俄罗斯出口丝织品、蔬菜和水果。 2017年伊朗与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经济联盟”(EEU)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2019 年10 月生效。 根据协定,总计840 种商品将获得“优惠关税”(preferential tariffs)待遇。 受到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2019 年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即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的贸易总额,已经突破10 亿美元。在金融领域,伊朗和俄罗斯积极开展两国银行间的直接结算机制。 2019 年9 月,伊朗中央银行和俄罗斯中央银行正式建立了银行间结算机制,以保护伊朗和俄罗斯的金融贸易“免受第三方制裁的影响”。
其次,在核能领域,俄罗斯是唯一一个与伊朗保持合作关系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萎缩,俄罗斯的核能工业体系也受到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亟需开发外国市场来弥补资金缺口;伊朗谋求发展核能力,捍卫国家安全。 在此背景下,1991 年俄罗斯和伊朗商定建设核电站的有关议题,在1992 年伊俄两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议》。 1995 年伊朗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俄罗斯承建布什尔核电站工程。 尽管在西方的影响下,俄罗斯在布什尔核电站项目上的建设进度多次延期,但仍在2011 年建成并交付伊朗使用。 2015 年,俄罗斯与伊朗达成合作协议,俄罗斯将为伊朗提供核燃料,维持伊朗核电站的运转。 2017 年9 月,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承建的布什尔核电站二期建设项目开工,预计在2026 年完工,项目金额达到100 亿美元。
再次,在军事领域,伊朗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 俄罗斯是伊朗重要的军火采购来源国。 俄罗斯曾经向伊朗提供了“道尔”(TOR-M1)防空导弹系统,并在2016 年向伊朗出售了先进的S-300 防空系统。 受制于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的“武器禁运”,伊朗无法从其他国家大规模的采购军备。 2020 年10 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 号决议规定的向伊朗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期限即将到期。 虽然美方努力说服俄罗斯等大国支持延长禁运的决定,但是俄罗斯明确表示,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应该废止。俄罗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展与伊朗在军购领域的合作。 从2019 年伊朗开始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希望购入苏-30 战机、雅克-130 训练机和T-90 坦克等总价高达100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增强伊朗的国防力量,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
最后,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和俄罗斯也有着相近的立场。 一方面,俄罗斯和伊朗一道,共同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 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伊朗力挺叙利亚政府。 伊朗与俄罗斯还先后直接出兵叙利亚,帮助叙利亚政府军不断收复失地。 伊朗和俄罗斯在多个场合,呼吁叙利亚问题相关当事方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势力对叙利亚事务的干涉。
但是,俄罗斯并非伊朗心仪的合作伙伴。 对于伊朗来说,来自于俄罗斯的合作,只是美国制裁下的“次优选择”。 在美国的制裁下,伊朗难以直接与西方世界展开贸易和交流,在核能工业和军工领域,只能寻求来自于俄罗斯的帮助和支持。 相较于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伊朗更希望与西方世界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从2015 年7 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到2017 年10 月美国谋划重启针对伊朗的制裁之前,伊朗与外国公司新签订了总额达860 亿美元的合同,其中与俄罗斯签订的合同金额只有14 亿美元。 俄罗斯驻伊朗大使就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在我们的帮助下,伊朗的制裁被解除……伊朗说不会忘记受到制裁时期的艰难困苦,但是又购买波音和空客的飞机。 俄罗斯的飞机在哪儿?”
三、 美国“镜像”与俄罗斯伊朗的分歧
尽管伊朗与俄罗斯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共同点,但是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这些分歧,反映出俄罗斯和伊朗,对于美国及其主导的中东地缘政治体系的认知差异。
(一) 对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角色的认知差异
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与伊朗就如何看待美国的角色,存在巨大分歧。 俄罗斯认为,美国是叙利亚问题的重要当事方,需要将美国纳入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伊朗则认为,美国仍然策动反政府武装发动针对叙利亚政府的袭击,美国的盟友以色列还继续“非法占据”戈兰高地,战事仍未结束,因此反对大规模撤离叙利亚,更反对邀请美国参加叙利亚战后重建进程。
俄罗斯认为,叙利亚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美国已经无力影响叙利亚问题的走向,所有外国的军事力量应该从叙利亚撤离。 俄罗斯甚至认为,“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的重要障碍。 伊朗的支持,给叙利亚政府带来了不切实际的期待。”普京总统提出:“随着叙利亚政府军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不断取得胜利,以及政治进程进入了积极的阶段,外国军事力量将会从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土地上撤离。”俄罗斯所要求撤离的外国军队包括“土耳其军队、美国军队、伊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伊朗赋予叙利亚问题以政治和宗教意义。 伊朗是建立在什叶派“教法官监国”政治原则上的国家,而叙利亚是一个什叶派占据政治主导权的国家。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伊朗不仅直接帮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还积极的协调和动员来自黎巴嫩、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什叶派民兵进驻叙利亚,帮助保卫叙利亚政府。 伊朗认为,“其他国家在叙利亚战场上胜负都无所谓,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只能胜利。 不能在叙利亚取得全胜,那么不仅会给伊朗带来巨大灾难,也将给什叶派带来巨大的灾难。”伊朗宣传中,将叙利亚视为自己的“第35 个省”。伊朗希望能够留驻在叙利亚,保卫叙利亚政府的稳定,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彻底击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统一叙利亚全境。
俄罗斯将叙利亚视为与美国全球博弈的一部分,因此认为在局势趋于缓和的前提下,可以同美国影响下的叙利亚反政府政治和军事团体,展开和平谈判,早日开启叙利亚和平进程。 “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是两国全球博弈的一部分。 俄罗斯通过介入叙利亚问题,获得了对美关系上的筹码。”与俄罗斯不同,伊朗将叙利亚问题视为国家安全的攸关议题。 伊朗将叙利亚危机,视为与美国地缘博弈的战场。 对伊朗来说,“叙利亚冲突是意识形态、教派竞争和地缘政治的多重竞争,涉及伊朗与所有敌对势力的博弈。”伊朗难以在叙利亚问题上做出妥协,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参与叙利亚问题。
(二) 与美国中东盟国的关系
在中东地区政策上,俄罗斯与伊朗有着不同的利益关切。 伊朗将以色列和沙特视为主要的地区竞争对手,扬言要“消灭以色列”,推翻沙特政府;俄罗斯则谋求发展与以色列和沙特的友好关系,不认可伊朗对以色列和沙特的敌视态度。
伊朗对以色列的敌视和仇视长期存在。 首先,伊朗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 伊朗认为,“美国是邪恶的‘大撒旦’,而以色列是邪恶的‘小撒旦’”,伊朗将以色列和美国视为中东动荡的原因。 伊朗认为,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在中东建立,并在多次中东战争中击败其他阿拉伯国家,其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大力支持。 在伊朗看来,以色列代表美国的利益,是美国在中东欺压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帮凶”。
其次,伊朗指责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挑拨离间”,分化中东国家的团结。 为了维系国家安全,以色列一直尝试利用不同中东国家间的民族、教派和意识形态纷争,来谋取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 “在阿拉伯封锁之墙以外,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中东和非洲国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伊朗和土耳其。 尽管这两国都是伊斯兰国家,但是他们的外交政策是出于政治利益,而非宗教情感。”伊朗抨击以色列介入中东国家间纷争,认为以色列的干预,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主要原因。
最后,伊朗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极端派别。 2007 年之后,巴勒斯坦分裂为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占据的约旦河西岸,和由极端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占据的加沙地区。 国际社会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鼓励法塔赫与以色列通过政治对话促成巴以和平的实现。 伊朗则支持哈马斯为代表的极端派别,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来促成“巴勒斯坦人民的最终解放”。
伊朗长期批评和否定沙特的政治体制。 一方面,伊朗认为沙特的“王国政体”,有违伊斯兰教义。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的君主制度被推翻,确立了以什叶派“教法官监管”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沙特阿拉伯保持沙特家族治理下的、尊奉逊尼派瓦哈比教义的君主制度。 伊朗认为,沙特君主制度,有违伊斯兰教义中“认主独一”(Tawheed)原则,是建立在专制君主之上的压迫制度。另一方面,伊朗认为沙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代理人”。 伊朗认为,沙特不仅与以色列一起,压迫巴勒斯坦民众,还保持着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是美国干涉和压迫中东国家的工具。
与伊朗对于以色列和沙特的敌视不同,俄罗斯重视发展与以色列和沙特的双边关系。 一方面,俄罗斯和以色列关系紧密。 以色列国内有大量俄罗斯裔犹太人,这些俄裔犹太人成为以色列和俄罗斯双边关系的重要纽带。 普京总统曾指出,“以色列一半人会说俄语”,朝觐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东正教徒也一直受到以色列的保护和欢迎。俄罗斯重视以色列与美国犹太院外集团的作用,希望以色列成为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传话人”和“协调员”。
在巴以问题上,俄罗斯承认以色列的中东大国地位,反对巴勒斯坦各派别发动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默许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发动针对伊朗军事团体的空袭,默许以色列继续控制戈兰高地。正如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Sergei Ryabkov)所言,“我们从不否定以色列安全的重要性……以色列人知道,美国人知道,伊朗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都明白这一点。 保卫以色列的安全,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俄罗斯重视发展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对于俄罗斯来说,沙特在军售领域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沙特与俄罗斯在核能领域的合作同样潜力巨大,俄罗斯与沙特重视彼此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俄罗斯与沙特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家,双方在管控国际油价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俄罗斯是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2019 年,俄罗斯石油储量与产量为1,062 亿桶与每日1,144 万桶,分别占世界总量的6.1%与12.1%。不过,由于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大多集中在西伯利亚地区,生产综合成本高达每桶30 美元,对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也更为敏感。所以,俄罗斯需要与沙特保持理性的合作关系,防止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俄罗斯希望能够加强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火贸易。 俄罗斯希望挑战美国在中东军售中的“霸主地位”,扩大俄罗斯军事工业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军火市场的份额。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总裁亚历山大·米赫耶夫(Aleksandr Mikheev)在2017 年曾表示,出口到阿拉伯国家的武器装备,占俄罗斯武器出口总收入的20%,其中巴林、埃及、摩洛哥、沙特和阿联酋等国,是俄罗斯军事装备在中东的主要买家。2019 年10 月访问沙特期间,普京总统就多次表示,希望进一步增进与沙特在军事工业领域的合作,鼓励沙特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购买更多的俄罗斯武器装备。

表1 中东国家武器进口数量和主要进口来源国(2015~2019 年)
美国在中东的盟国沙特和以色列,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世界大国”俄罗斯,在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军事合作问题和能源生产等问题上,与以色列和沙特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 美国接受了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主导性作用,而俄罗斯则尊重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和关切。 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俄罗斯与美国的中东盟国,也能够发展理性务实的合作关系。
伊朗将以色列和沙特视为美国的“马前卒”。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对立,“不仅体现在军事和安全等高级政治层面,而且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低级政治层面”,是一种全面的对抗状态。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对立,尽管“未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根植于政治分歧和宗教教派,以此为基础在中东地区划分成了两大对立集团,激化了地区矛盾,在地区弱国开展代理人战争。”因此,伊朗与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难以调和。
四、 地位差异——俄罗斯与伊朗障碍根源
如何与美国打交道,是俄罗斯和伊朗关系中的重大分歧。 “世界大国”俄罗斯,既要应对美国的压力,也要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保持合作;“地区大国”伊朗,面临着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巨大压力,因此难以消除敌意,无法认同俄罗斯与美国的合作关系。 自身定位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政策分歧,是俄罗斯和伊朗难以形成同盟关系的重要障碍。
(一) “世界大国”俄罗斯——保持与美国关系
俄罗斯自视为“世界大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与互动。 “自罗斯公国时期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俄罗斯一直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以追求国家强盛和领土扩张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实现俄罗斯民族的复兴、追求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成为俄罗斯最高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主旋律。”俄罗斯总统普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统一、强大且有国际声誉的国家,以此重新构建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避免成为美国和西方的追随者。 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利比亚问题和巴以问题上,俄罗斯都谋求与美国实现“对等地位”,并发挥关键作用。
俄罗斯不希望与美国全面对抗。 在“世界大国”身份的指引下,俄罗斯的对美政策表现出“既对抗又合作”的特征。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尽管存在着竞争关系,并在某些地区问题上产生了直接的分歧甚至冲突,但俄美两国并非全面对抗的关系。 俄罗斯希望与美国一起,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重大的全球性议题。 “俄罗斯与美国不会重回冷战的高度对抗状态,西方国家也需要与俄罗斯共同合作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
俄罗斯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警惕美国的战略压迫和围堵。 俄罗斯认为,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不仅有违国际公理,也威胁着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北约在中欧和东欧加固防卫,美国与其盟国一道,力图通过‘新遏制’(new containment)政策来威胁俄罗斯。”俄罗斯反对美国和西方肆意滥用“人权”“道义”的工具,认为应当尊重当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美国和西方的干涉和介入。 在中东事务上,俄罗斯反对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制裁伊朗。
俄罗斯努力避免被美国针对第三国的制裁所波及。 2018 年特朗普宣布重新退出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后,俄罗斯航空企业担心被美国的制裁波及,因此放弃了与伊朗的合作关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指挥官侯赛因·阿莱伊(Hossein Alai)批评俄罗斯:“俄罗斯人曾经许诺要将三架苏霍伊客机租给我们,这款飞机是俄罗斯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研制的。 他们与我们商谈了两年,随后俄罗斯驻伊朗大使告诉我们,他们无法将该飞机租借给我们,因为其中有大约10%的部件来自美国。 我告诉他,你们俄罗斯人总是声称自己是大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现在,这种在你们本土制造的飞机,你们都不敢租给我们?”俄罗斯需要考虑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不愿因为与伊朗的合作,而伤害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全球利益。
“世界大国”俄罗斯需要平衡中东地区的各方利益,谨慎处理复杂的地区议题。 俄罗斯学者认为,在中东的地缘纷争中,俄罗斯应当采取中立姿态,而非倒向其中一方,“一味支持什叶派打压逊尼派,将是自杀式的行为。”俄罗斯的“世界大国”身份,意味着俄罗斯需要在复杂的地区议题上,需要与美国相互协调与让步。
(二) “地区大国”伊朗——与美国的全面对立
伊朗自视为“中东大国”。 伊朗拥有绚烂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防力量,以及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 “无论是巴列维王朝时期,还是在1979 年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伊朗都力图在中东地区发挥独特的领导作用,并力图在与美国、苏联和俄罗斯的交往中,保持国家的独立。”伊朗希望能够成为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模范”,进而主导中东地区事务。
在“地区大国”身份的影响下,伊朗的外交战略有着鲜明的特征。 首先,伊朗反对“世界大国”干涉中东事务。 20 世纪80 年代,伊朗强烈批评苏联入侵阿富汗,抨击苏联压迫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群体。 在1989 年1 月写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就批评苏联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认为“苏联的失败之处,在于你们发动了针对真主的战争,这场战争延绵不绝,但徒劳无功。”尽管冷战结束后,伊朗和俄罗斯关系逐渐缓和,但是伊朗仍然重视“泛伊斯兰主义”政治观念,与俄罗斯在一些敏感地区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两次车臣战争期间,伊朗曾同情车臣极端分子;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也力图占据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权,动员什叶派军事团体,向以色列发动“圣战”,“收复耶路撒冷”。 而这些战略动意,都与谋求叙利亚局势缓和的俄罗斯背道而驰。
其次,伊朗对“世界大国”有着强烈的不信任。 伊朗在历史上曾被“世界大国”屡次欺凌。 19 世纪沙俄侵占伊朗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为防范纳粹德国而入侵伊朗,一度策动库尔德独立运动在西阿塞拜疆省建立“马哈巴德自治共和国”,都是伊朗历史上沉痛的记忆。 20 世纪80 年代伊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苏联支持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军队,伊朗和苏联关系一度陷入僵冷。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仍然磕磕绊绊。 2007 年俄罗斯和伊朗曾达成出售S-300 防空武器的协定,但是俄罗斯担心受到西方制裁伊朗的影响,直到2016 年“伊朗核协议”签订后,才交付伊朗使用;伊朗核能力建设重要项目——布什尔核电站——由俄罗斯帮助建造,但是俄罗斯也曾经多次中止建设;此外在里海划界问题上,俄罗斯与伊朗也曾存在较大分歧。 这些因素,都使得伊朗民众对于俄罗斯缺乏信任。
最后,伊朗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会被“世界大国”出卖。 2016 年8 月,俄罗斯曾提议租借伊朗的哈梅丹(Hamedan)的诺捷赫(Nojeh)空军基地。 但是俄罗斯的提议,引发了伊朗舆论的强烈担忧。 伊朗议会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法拉哈特皮什(Heshmatollah Falahatpisheh)就指出:“我代表的是两伊战争期间,遭到一千多枚导弹袭击的伊朗城市。 这些袭击的导弹中,80%都是由苏俄制造的。 俄罗斯非常善于精打细算,考虑每一步战略布局。 如果俄罗斯人将伊朗的秘密军事情报贩卖给了敌视伊朗的国家,那伊朗的领导人们应该如何向国民解释?”最终在舆论的压力下,时任伊朗国防部长侯赛因·德赫恩将军(Maj. Gen. Hossein Dehghan)不得不出面,表示伊朗无意将军事基地租赁给俄罗斯,不允许俄罗斯军事人员进驻基地内部。
“世界大国”的俄罗斯,希望能够在中东事务中,保持一定的“中立”态度,以获取平衡地区国家的关切。 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希望主导中东事务,必然与“世界大国”的俄罗斯,出现分歧与矛盾。 自我认定为“世界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的身份差异,是俄罗斯和伊朗两国难以实现联盟的根源。
五、 余论
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关系,是应对美国“威胁”的反应。 伊朗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阿莱丁·博若杰尔迪(Alaidin Boroujerdi)承认,美国对伊朗的打压,是促成伊朗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重要原因。 “美国人计划向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也强调,由于美国的制裁压力,伊朗重视与东方国家的关系,重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应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俄罗斯也认为,美国和西方的围堵,是俄罗斯与伊朗关系的重要动因。 俄罗斯将发展与伊朗关系视为“实现俄罗斯外交战略目标的工具”,俄罗斯希望通过介入伊朗核问题,“使国际格局朝着结束美国单边主义、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的世界新秩序”的方向不断靠近。
俄罗斯的“世界大国”情怀,源于自身独特的民族历史、宗教情怀和国家版图,“横跨世界两大洋,介乎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一只胳膊紧靠中国,另一只紧靠德国,我们理应在自己的身上将精神天性的两大因素——想象和理智结合起来,让全球的历史统一于我们的文明之中。”在2011 年中东动荡爆发之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政治上,俄罗斯与伊朗和土耳其一道,通过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和“索契进程”,扩大了叙利亚问题上的话语权,进而提升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在经济上,俄罗斯以能源为着力点,通过和沙特、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等中东能源国家密切合作,力求构建新的国际能源供应格局;在安全上,俄罗斯扩大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并积极扩展与沙特、土耳其、埃及、苏丹、黎巴嫩和索马里等中东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
伊朗自视为“中东大国”,试图重塑中东地缘政治秩序。 悠久且辉煌的历史,塑造了伊朗民族心态中的大国骄心态,敢于对抗西方的制裁和压迫;而独特的“教法官监国”体制,使得伊朗希望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在中东复制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种严重违法外交豁免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核心原则——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尽管进入21 世纪后,伊朗外交逐渐放弃了激进的“输出革命”理念,转而谋求务实的外交政策,但是伊朗仍然希望能够主导中东地区的敏感议题。 在伊拉克问题上,伊朗与美国形成了竞争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与俄罗斯争做主导权;在巴以问题和海湾什叶派议题上,伊朗分别于美国的中东盟国以色列和沙特长期对立。
俄罗斯与伊朗各自不同的战略定位,使得两国关系难以实现“亲密无间”。俄罗斯和伊朗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深刻地反映在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关系上。 “大国”身份的自我定位,使得俄罗斯和伊朗无法接受扮演“美国小兄弟”的角色;“世界大国”与“中东大国”定位之间的分歧和差异,阻碍了俄罗斯和伊朗同盟关系的形成。
- 阿拉伯世界研究的其它文章
- 极端主义在俄罗斯的滋生、构成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