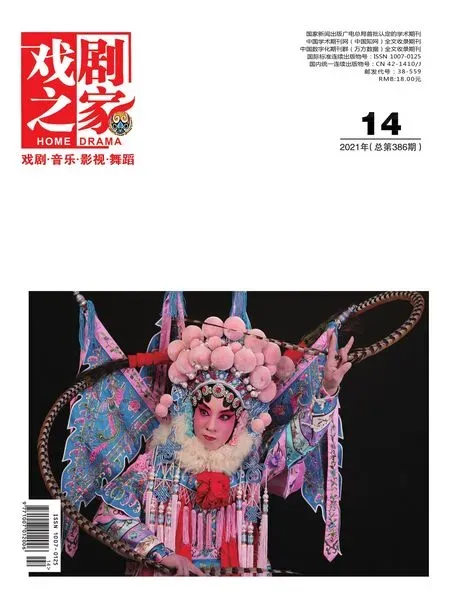文学是对人精神的关怀
孙 勇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一、引言
在物质发展方面,人类的进步需要知识的引导,需要科学的发展,科学就是发展物质生活的主要力量,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文学的确比不上科学。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类的发展并不只有物质这一个方面,人的精神同样需要得到发展和满足,科学在某些时候也意味着一种障碍,科学也能变成生命发展的负面力量,完全依靠科学技术和逻辑、知识等,并不能构成一个健全而有趣的社会,科学往往只能解决表象的、物质的问题,但根源性、深层次的问题是人的精神和心灵上的问题,所以人类还需要诗,需要文学,需要“文”化。文学并不侧重于对外在表象和物质的理性把握,而是强调精神层面的感性体验,是对生命存在的主观反映。
君子可以在梅兰竹菊中找到自己,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往往也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从而得到象征性的释放与替代性的满足,在一次次的阅读体验中,感受人物的悲欢离合,通过感受他人一生的经验,来慰藉自己的心灵,获得适用于自身的人生经验,以至得心法、启性灵、开慧根,最后获得快乐。“文艺由于它的虚拟性而有一种特殊的心理补偿作用,许多一般人难以经验或根本不可能一睹而又对其或向往而不可得,或恐惧而又好奇的领域氛围,人们靠文艺的体验而得了心理补偿,这多半是有益身心也有益社会和谐稳定的。”科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理性,而文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明朗万物的素养和情趣的健全发展的人,文学对人精神的关怀主要体现在给人以审美享受,给人以道德熏陶,给人以思想的升华。
二、文学的美育作用
审美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造就审美的人,而文学则是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人类三大永恒价值真、善、美里面,美能积极引导人求真、向善,因此文学能够引导人类积极地进行求真、向善、审美活动,从而塑造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文学的审美教育属于精神层面的教育,它是科学知识教育所不能替代的。文学的审美教育在于能够全面发展自由的人格,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造就“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人”。文学的审美教育还在于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丰富人的情感。文学的审美作用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直接的效用,是一种无用之用,但这并不等同于没有作用,可以说文学的审美本质就决定了文学注定是无用之用,它没有任何现实功利,却在潜移默化中,如春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默默地涤荡我们的心灵,净化我们的精神,提高我们的审美趣味,远离恶俗。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美育的实质是情感教育,其特点应以情动人,以美感人。”文学本质上是审美文化,文学作品的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故事美、画面美、音乐美、形体美、摄影美等都是人们的审美对象。审美主体是指在创造美、发现美、欣赏美的过程中的主体,而人们是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审美主体的有机统一。作为审美主体,人们有审美需要,因此需要通过文学等途径来获得满足。审美主体有什么样的审美需要,就喜欢什么样的文学,文学作品的阅读绝非偶然,它总是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社会现实的反映。
作为审美主体,人们要主动培养自身的审美能力,即创造美、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审美意识支配审美主体的意识创造、审美发现和对美的欣赏,因此文学作品是人们在培养审美意识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审美意识包括审美理想,审美理想对于创造美、发现美、欣赏美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文学的美育作用就表现在此。审美心境是审美时的具体心理状态,是否具有审美心境以及审美心境的状态,直接影响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
美育是熏陶、感性,旨在使人的精神得到激励、净化和升华,带有一定的趣味性。文学通过跨界的融会贯通,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思域融通的能力。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人们的想象力得到提升进而使创新意识得到升华。文学可以带给人们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活跃的思维,它们可以点燃人们创新创造的火花,让人们产生灵感,开拓创新思路,实现思维的突破。通过各式各样文学作品的阅读,人们可以获得美的欣赏,从而有助于缓解、调节快节奏社会生活的各种压力,让人产生精神上的愉悦,获得宽广平和的心态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有利于避免心理问题的产生,文学的美育作用就在于奠定了人们的心灵根基。
三、文学的德育作用
近些年,社会上广泛掀起学习国学的热潮,这股热潮的背后其实是对全民族人文素养的反思,反观现代教育存在的问题,力求找到古今道德教育衔接的纽带,古为今用,传承经典,净化心灵,实现真正的德育教育。文学作品中的种种人物形象是基本人伦精神的具体表现,是外在形式和内里精神的统一。对个人而言,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形象能够从正反两方面来规范人的行为;对于社会而言,文学教化成为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人际交往和睦的良器。文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内涵,作为人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产物,文学的本质不光是审美的,也是文化的,是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文学是历史发展中逐步积淀下来,以传统的方式出现的时空文化连续体,是一种历时持久的、由社会传递的文化形式,它始终以某种精神约束力支配着个体行为,是一种人为构建的,在社会中规范着人们的言谈举止等行为,影响并制约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高度的文化。
文学可以从表象到内涵对人进行理性和情感的教化,可引导人们培养情怀、风化道德、移风易俗,以达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每个时代,都会有变革在发生,可是每个时代都无法抛弃精华文化的积淀。文学作为民族文化载体,己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包含了许多值得人们吸收和继承的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文学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人们可以根据文学的丰富性,一方面结合现实的需要,一方面结合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悟,对文学进行创造性的阐释,揭示和发现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在现代语境下新的价值。
人们在观看、诵读文学作品以后,似乎并没有获得什么直接的裨益,大量阅读文学经典与著作未必对现实生活直接有用,但是,经年累月,人们会越来越喜欢文学。人们如果读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不仅仅接触了诗歌,而且会与人生相联系,从而清清楚楚地看到人生中所存在的优点和缺陷,便会更加努力,以实现那美满的理想。文学有助于塑造好自身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借此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文学的这种功效,就是德育的意义了。既有教育意义,才能有益人生。而且文学的德育又不是一般的教育,它能实际启发自觉、勇猛、力求进步的精神。
四、文学的无用之用
文学除了美育和德育的作用,还能启发人们积极探寻生活的规律,并能帮助人们找到人生的真谛。文学虽然在逻辑分析方面不如科学那么严谨,但是生活的规律和人生的真谛却蕴藏在文学作品当中,人们在瞥到那只言片语的一瞬间,便犹如步入桃花源一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未来的人生道路瞬间明亮了起来。
《论语·为政》篇中,子曰:“君子不器”。君子不应该像一个器具一样,只有有限的才能和用途,而应该做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君子不应该容量有限,而应该宽容大度,海纳百川;君子不应该思想僵化,不懂变通,而应该为人处世的过程中灵活应变。人们不应该以“成器”为目的,不应该带有强烈功利性、目的性去学习,而应该成“君子人格”,把提高自身修养作为奋斗的动力和目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不应该成为某种器具,成为某种达成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一个真正的君子往往不是实用的、功利的。在功利的人眼里,他往往是无用的,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这个“用”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讲的,君子或者说贤者和圣人志于道,不会刻意追求实用之学,成为一种人形工具,而是超越这个工具。
鲁迅认为,从纯文学的观点说来,一切艺术的本质,都在于使观众和听众能感到振奋和喜悦,它完全脱离实际利益,也不是穷究什么哲理,不过,世间上自从有了文学,人们便因而接近满足了。鲁迅走上文学之路是为了文学的“用”,但这个“用”不是鄙狭的个人实用,而是超脱于个人功利之上的民族命运的大“用”,是“不用之用”。所以,文学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它的功用决不在科学之下,文学可以用来指导科学发展的方向,回溯历史的发展,科学上的突飞猛进往往伴随着诸多问题,而唯有通过文学沉淀下来的人性方可逐一化解应对这些问题,因此文学的作用更加显赫了,根源上的问题解决了,表面浅层次的东西也就不成问题了。
五、结语
人们往往以实用作为权衡万物价值的标准。凡是有直接和实际效用的事物,就认为它有价值;没有直接和实际效用的,就认为它没有价值。殊不知许多东西的用处虽是间接而不显著,然而其重要性却远超过了那些有直接效用之物。文学是“某种增强灵魂的自我实现的东西,它不但以它给人的那种直接的愉悦来证明自己的意义,而以它对深层意识的(自我实现的)训练作为证明”。人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不要仅仅注重物质的富足,也要追求精神的愉悦,不要把物质层面的实用和功利性的价值追求作为最终目的,追求看似无用的大道比追求一时有用的小术更可贵,精神层面的升华与满足远比物质层面的利益更加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