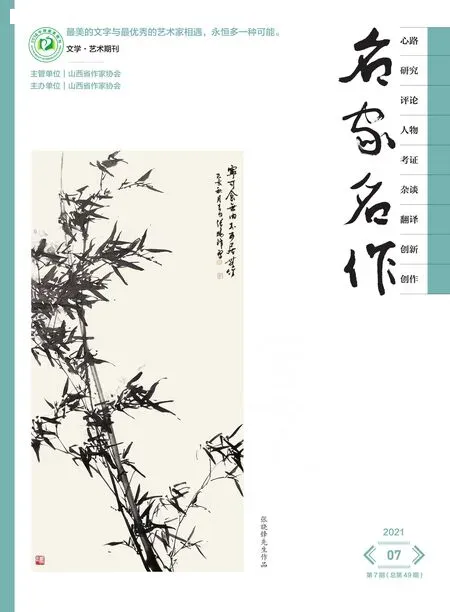深耕文化沃土 笔绘心灵图像——谈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之方法论
杨 妍
王晓明是一位带有较为强烈的个性意识的批评家,著有《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所罗门的瓶子》等。其批评文字虽然不具备出色的思辨理性意义,却令人读来酣畅又亲和,有值得品味的空间。批评文集《所罗门的瓶子》于2014年1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旧文新版,将王晓明20世纪80年代所撰写的文章集中带到新世纪读者面前。作为运用文化心理批评研究方法较为成功的范例,此集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一、从鲁枢元到王晓明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发展流动的长河中,批评者自我意识的回归是一个突出的转变特征,批评标准和价值判断中的许多集体因素也为个人化因素所替代。在此前,注重外部因素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学理念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主要方法。本体论的出现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学内部,呼唤批评家们关注作品内部因素。
鲁枢元站在威廉·冯特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理论的肩膀上,创造了文学心理学理论。文学心理学理论的诞生,打开了从心理世界出发去考察文学作品的新路径,建立起作家与作品的联系,展示了作家内在精神世界的图景。在此影响下,一批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作家作品的成果接连涌现,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便是其一。但王晓明有所发展,将心理批评引向了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批评是以心理为视角,主要运用现代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作家作品及读者接受的内涵进行深入探析和评论的模式。”王晓明注重人的意识结构和心灵的结构特征,将文化心理批评方法用于现代文学,考察了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作家的精神世界。孙郁指出,这种批评方法的思路其实更接近于思想批评。
黄子平总结王晓明的研究是“生平文本”和“作品文本”之间的互文。在王晓明看来,作家的传记材料并不绝对可靠,作品可弥补作家传记的局限性,从作品入手推测作家的心态是相对可靠的选择。“要分析知识分子的心态,总得由具体的现象入手,而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我能够用来作分析对象的,就只有作家。”
二、心理世界的潜流与漩涡
王晓明论述作家的角度是独特的。他不断探索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主体性,注意作家试图掩盖的东西,用深潜的姿势追踪和描绘作家内心世界的旋涡与暗流,总结作家的认识习惯,把握其创作心理的流变。
(一)创作心理的探析
王晓明认为,少年遭遇家道中落,饱尝人情冷暖,听闻腌渍眼睛的怖事等使鲁迅形成偏重阴暗面的认识习惯,这是造成其着力深挖民族精神缺陷的深层原因。“感受习惯和逻辑判断的分歧,对病态精神现象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的认识分歧,最终都造成了他整个理性世界的分裂。”在独行的道路上,鲁迅的内心始终充斥着深广的孤独,深恶与达观互相补充,处处接近绝望,又无不反抗绝望。通过追溯,王晓明一定程度上还圣人鲁迅为真人。
探索茅盾的生平,可瞥见其始终热衷政治生活的内心。他的灵魂,一部分是指向政治的热情,一部分闪烁着敏感的文学天赋。《幻灭》和《动摇》是茅盾被社会浪潮击打所打造出来的“自救之舟”,《虹》和《三人行》更表明他无法抑制自己关心政治的那一半灵魂。两个灵魂的斗争,使茅盾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上都显示出分裂,以至于茅盾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即使妄图从抽象命题出发,非理性因素也不觉占据主导地位。
张天翼自小善模仿,具备快速抓住对象突出特征的能力,而王晓明认为张天翼的局限恰在于此。他习惯将一切都交代清楚,过分偏重逻辑,将人物心理变化梳理明白,缺少一丝朦胧与深沉的意味。在刻画人物方面,张天翼仍像揭示理智思维那样采用突出主导倾向的方法,不免表现出单一和抽象的弊病。因此,张天翼总倾向于将“复杂的精神现象还原到一个最简单的内核中去”,片面强调人物的某一种心理品质,这是现代作家在认识论上的幼稚表现。
深入张贤亮的内心,王晓明则从其作品叙事人的姿态入手。1980年后,张贤亮抛弃他擅长的传统叙事方式,制造了一个名为章永璘的叙事人。他持续关注叙事人的背叛行为,描绘生活压迫造成的精神病态。衣食足而知荣辱,当温饱还无法得到满足,灵魂和道德就成为无法被顾及的存在,章永璘和张贤亮皆如此。张贤亮赢得了生存的胜利,却付出了心理变形的代价。他企图从审美的目光去回望过往,却被道德的镣铐困住手脚。王晓明认为,感受记忆和理智意图的矛盾,是张贤亮选择这种独特叙事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在对地理、历史著作的阅读中,王晓明得出,“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和“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深扎苗族人民心中,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也在沈从文的文字中暗自流淌。王晓明将沈从文定义为“湘西社会的逆子”:笔下眷恋湘西,却安居城市;嘲讽教授先生们,自己却也成为一名教授。“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的整个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
(二)个案与普遍的交融
在对作家个体的深入探求中,王晓明之笔并不囿于作家个体的表现,而是融入大的历史背景,推论出群体的普遍文化心理,这不仅增加了论证的可信度和容纳空间,也深化了批评文章的内涵。
“但同时,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又使我感到担忧,中国作家要在对内心情感的忏悔式的解剖中达到真正深入的程度,恐怕先得排除掉那种完全只依据理性观念去解释的冲动。”谈论张贤亮时,王晓明慨叹中国知识分子苦难之深重。中国作家遭受苦痛,生发出外向的忧患意识,也生发出内省的忏悔意识。要想从苦痛中恢复,作家们必须释放出痛苦的感情,从生活的遭遇去解释和辩护,以求得精神的平衡。
中国新文学是反思的文学,如何看待知识分子是重要问题。王晓明由对张贤亮写作方式和理念的分析,上升到中国作家群体面对苦痛的写作出路问题,这蕴含着他对20世纪文人群体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特点与局限性
王晓明的文章多是逐层深化的结构。他较完整地梳理作家创作历程的心理变化时,仿佛在一层层剥下洋葱的表皮和肉瓣。“层层剖析对象世界的话语方式,不仅在感知的细腻上让人赞叹不已,更主要的是灵魂解析过程的那份严峻和冷静”。面对批评对象,他手握解剖的手术刀,不紧不慢,独乐其中。
于《读〈沈从文文集〉随想》篇尾,王晓明坦言自己试图分析作家内心世界面临的较大的研究困境。他以自我经验激活文本,注重个人阅读感受。但阅读感受是一种主观常新的东西,若要尽力显得客观一些,确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当然,归根结底,所有的文学批评都可以说是一家之言,理解和剖析本就是在尊重客观事实基础上的能动性表达。
王晓明拥有较强的审美能力,我们应当肯定他体味和思考精神价值的深刻性。然过于注重那些非确切、非理性的因素,也侧面表明他对确切因素、理性因素一定程度的忽略,从而使探析略显狭窄。孙郁指出:“艺术其实与人的心灵有着复杂的、非线性因果的联系。如,谈论张贤亮的时候,如果单纯地把作家某种心态的畸形与艺术的畸形等同起来,在方法论上就显得简单化。”
四、结语
王晓明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但从瓶口中涌出来的不是魔鬼,是丰富灵魂的无数个心灵的侧面。“先分析作品,再一步步推论出作者的心态,乃至普遍的文化心理”,这种思路是对传统演绎式方法的颠覆,充分呈现批评者自我观念,也融入了历史的考察。王晓明推崇批评家与文本和文本中的对象融合互渗的批评方式,其批评和作家的文本与心灵构成了真正的对话关系。为作家的心灵画像,挖掘作家的心灵困苦,直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王晓明提供了一种内外结合的文化心理研究范例。用孙郁的话来说,就是“以理论家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散文家式的雕塑人物的过程”。三十多年前的批评曾引起关注与争议,如今虽时代变迁,却尚有参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