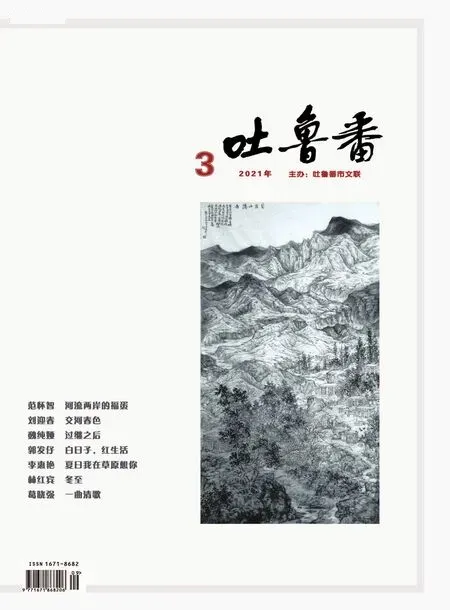一曲清歌
——读高维生《归去来兮陶渊明》
葛晓强
收到作家高维生兄寄来的新著《归去来兮陶渊明》很长时间了,这期间,我除了读些其他杂著,写些兴之所至的小诗与短文,能够置于床畔且给我以心灵抚慰的,就是这本不厚的小书。说句老实话,在阅读之前,我是没有下笔写些读后的想法的,缘由无它,一则元亮先生是我心底追慕的先贤,二则维生是我的兄长和老友,他的文字我是熟悉的,他内心的明澈之慨我也是了然的。也就是说,读好友写自己倾慕的先哲,是一件十分安静与愉快的事儿,是否有必要写些自己的感受,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显得有多么的迫切与重要了。而在断断续续阅读这册小书的过程中,心中终会次第生发出一些拉拉杂杂的念头,既如此,我也就“听众心的指令”,行行止止地记下一些读余的零墨。
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纪实与虚构》一文中曾说:“优秀的画家从来不画建筑的正面,而是取仰角或俯角。任何东西都不如带有经过精选、闪耀着某种虚构色彩和时代热情的巧妙细节的事实描写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维生兄的这本新著,作为一部生动可感、质地十足的传记,无疑具备了俯仰之间的观察,以及基于历史事实之后的细节精描。比如,“细雨从东边吹来,雨声挟着湿润的风,陶渊明翻动着面前的书。”又如,“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树枝拱出新绿的芽,风传播泥土的清新气息。他倒满一杯酒,对着天地举起来,在酒中寻到了欢乐的满足。”这样的描述与推断,虽为想象,却是以“可能性”为铺垫,就具备了“想象的真实”;虽为虚构,却以“再现的投影”为情境,就拥有了“虚构的力量”,正因如此,维生先生的这本传记,才处处流淌着人的血脉,散发着人的温度,折射着人性的光芒。更为可贵的是,维生兄并未停滞于浅表的叙述与描绘,更以哲人的眼光打量元亮先生“挥兹一觞,陶然自乐”背后的旷达之意,思索元亮先生“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的苍凉之叹。在维生兄看来,在元亮先生身上,既有“读书娱己”的生命大享受,也有“壶中日月”的生命大痛快,更有着?“生如层云迭荡”“死如落叶飘坠”的生命大悲欣,以及终极意义上“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的生命大解脱……因此,维生兄在全书的结末,充满深情地写道:“秋一天天地深远,结束在晋代的寻找。陶渊明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他的诗,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傲骨。”
信哉斯言!元亮先生正是以不群的文章,精拔的辞采,甘于寂静独处、守于清贫峻洁的风神,让后辈书生尊为“穷则独善其身”的高山与大树。不是吗?在元亮先生以一己之生活为底色,以无法抵达之梦想为蓝本,构筑了纸上风光无限的“桃花源”胜境之后,之于“世外桃源”的追蹑与描述不绝如缕。其中附丽者众,最为代表的是诗画双逸的王摩诘,他在《桃源行》一诗中写道:“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人。”当然也有反其意而抒怀的,比如韩愈在《桃源图》中写道:“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吾虽腹笥简陋,只有茫茫沧海中微末的米粒之芒,也因钦慕先贤,写过一首关于元亮先生的小诗呢:“放下篱笆上的矮云,也放下/手上起伏远去的南山/让我们把午后的阳光和女贞子的/摇晃,一起送给过路的陌生人吧/平原上,你弯腰注视过的蒲公英/落花了,但树上麻雀的叫声/仍像昨日一样放肆地盛开/还有会唱歌的鸢尾,一场小雨之后/略显无辜的彩虹,还有新鲜的/桃叶,剪剪的晚风,都在你/长长的叹息与相持的酒中/斜过黄昏活到了今日,它们/在某一时刻被我发现,仿佛/阔大的天空从未被人搬动,仿佛/纸上的光阴一下子重新倒流”(《丁酉年初夏再读陶潜》)记得写罢这首小诗,自己正坐在初夏乡间的睛窗前,念及日月推迁,自己徒增虚岁,或恐白首无成,心中不禁黯然,竟倏然泪涌,然又想元亮先生以出尘之思之履,放达于山水之中,已为吾辈乡野后生指引了一条清澈田园的人生小径。那小径上,即使无明灭可喜的纷繁桃花,亦会有无名的野芳,以及起落有致的牧歌与雀噪,于晨暮之际,为着露的衣袖染上幽芬吧。而更为庆幸的是,维生兄为元亮先生作传,我为元亮先生写诗,我们都是从心底无限热爱元亮之人之文的人,如果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么,作为一个读书的人,一个写作的人,吾与维生兄心曲相通,寄意相融,“与君同好”,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