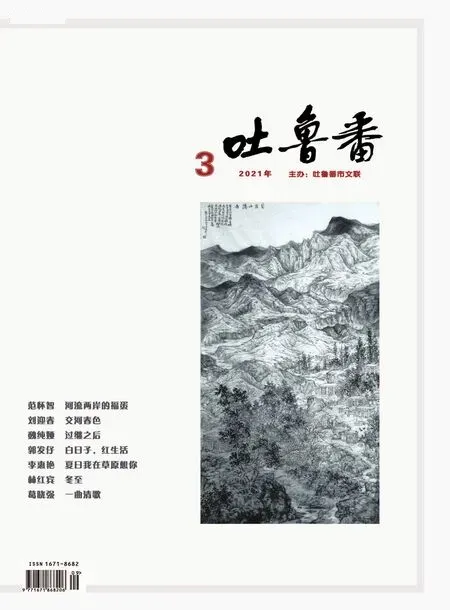白日子,红生活(外一篇)
郭发仔
汪曾祺说,四方吃食,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确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风物。在故土的烟火里,日子是白的,生活却红如焰火。
一
“在那掩没了/前因后果的草丛里/总会有人躺卧/嘴里含着草叶/凝望云朵/发愣”。我不知道辛波斯卡是否于某个冬日生发如此感慨,但总觉得萧杀的时光似乎是从昨天开始的。风的后劲一上来,草丛开始摇摆。而我,就是那个躺在草丛里发愣的人。不过,我嘴里惦记的不是草叶,而是白菜苔。
立冬是一声口令,一喊,冬就立起来了。一立冬,菜苔便抽出心来,脆嫩,胶凝,尖上挂着花骨朵,淡雅如黎明前的星星。白菜苔是乡间冬寒的日常,自古便是如此。唐朝戴叔伦《崇德道中》诗云:“暖日菜心稠,晴烟麦穗抽。”可见,在以丰腴为美的唐代,白菜苔就是席间一味了。不过,时过境迁,如今的白菜苔不在暖日中吐露菁华,反倒长在晨霜暮风里,一身气节。
南方的冬天是从北边流窜过来的,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冬天一进村,爬上房顶,一切都服服帖帖趴下了。那时的生活清苦,碗里的日子全靠菜园子延续。菜园子是脸面,也是态度。冬寒菜、上海青、胡萝卜、大白菜,青葱一片。隔着篱笆,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对生活的敬畏。白菜苔是少不了的,从菜心里冒出来,吱吱地拔节,霜华如柱。或清晨,或傍晚,去菜园子里把白菜苔掐了,咔嚓,咔嚓,声如击缶。洗净,择拣,大火把油烧热。在油烟腾起时,白菜苔入锅。瞬间,锣鼓喧天,花红软轿,席间一杯米酒下肚,人生得意尽在须臾间。
白菜苔出锅,父亲总是双手捧着,嘴里吹着气,小心翼翼的,如同捧着我单调的童年。白菜苔躺在白瓷蓝花的海碗里,肉质的菜杆晶莹透亮,玉石白光,凝脂滑膏,如同款款出浴的贵妃。夹起一小把入嘴嚼着,唇齿间咯嘣脆响,一股清香的汁液滑过喉咙,肠胃里有虚虚实实的饱足感。饭间不说话,屋子里只有切切的咀嚼声。那时,人们的嘴里素净,白菜苔不输一顿难得的荤腥。
白菜苔应了节气,但吃一节少一节,每摘一次,菜园子就矮了一截。大多数时候,嘴里都是菜叶子的腻味。
小时候,我仿佛就是村子里的白菜苔。我一次又一次从学校里拿回奖状,又在村人赞赏的目光中一步步离开村子,进了县城,定居在大城市。跌跌撞撞中,我邂逅了红菜苔。
红菜苔和白菜苔,同属十字花科蔬菜,但红白之间总有些牵牵挂挂,不由得怀疑二者恰是不出五服的血亲。其实,老家的土地里并不种红菜苔。第一次看见红菜苔,是在我从乡下搬到县城里租住以后。那一年,爱人以一位乡下普通中学教师身份考入县重点中学。我也从另一所破旧的乡村中学到外地去读研究生。从乡下到县城,我们似乎手脚无措,拍拍身上的土,看夜色里闪亮的路灯下身影一寸寸拉长,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文明。那一年,我们似乎还没准备好,一转身就成了红菜苔。
红菜苔,红殷殷如旧时戏子,就连墨绿色的叶脉也晕着红。不过,那是一个虚幻的意象,红菜苔并不轻浮如此。在咬破红杆脆皮的那一刻,满心的大欢喜就遭遇晦涩的苦味。其实,这种轻微的抵触是红菜苔对味觉的故意挑逗。试想,哪一种美好会赤裸裸地廉价奉送呢?
唐代韦庄早就摸透了红菜苔的心思。“雪圃乍开红菜甲,彩幡新翦绿杨丝。”也许,疏旷通达、不拘小节的韦庄,因为这红菜苔之好,才在花间吟出了清词俪句、情致婉曲的一代词风。
关于红菜苔种种,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它的故乡在湖北武昌洪山,在唐代是一味贡品。今人仍笃信,生于武汉城东宝通寺的红菜苔味道最纯正。宝通寺的钟声是否通灵,在塔影里暗自拔节的红菜苔是否悟出了生命的另一种况味,我无从知道。但从我游走的经历来看,红菜苔始终都是一种先苦后甜的味觉感受,在干枯的北方如此,在温润的南方也是如此。
有人说,白菜苔就是小时候的床前明月光,红菜苔是心中挥之不去的朱砂痣。这种微妙的情愫只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出现,像白玫瑰和红玫瑰,在人情世故的菜园里争争吵吵。于我而言,白菜苔是乡间老屋里的世交,红菜苔则是城市霓虹灯下的红粉。
人到中年,时时处处都是经年的滋味。
二
冬日寒冻,乡间无力的烟火里,萝卜常常是救急的一味。“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民间将萝卜的吃味总结成一种传统,也将萝卜的世俗功用在舌尖上掂量出诀窍来。
坊间所称萝卜,大多指白萝卜。乡下的土地翻不出富足的日子,村民们的嘴里白得如同瓷碗里的天空。但菜园子里的萝卜是饱满的,一畦畦,能孕育出一层薄薄的春色。白萝卜叶宽而肥硕,锯齿一般,互相咬合着,如同河滩上奋力拉绳的纤夫。萝卜叶子张扬,白萝卜则有些内敛,将身入土,酝酿心事一般,一点点鼓胀,一天天舒展。待到隆冬的霜风雪雨封冻了大地的一切时,白萝卜春心荡漾破了土,酥胸微露,白里透着烟雨青,尽显潋滟风情。
白萝卜出身土冢,却得天地精华,其味极佳。宋代林洪所著美食专著《山家清供》载:东坡与子由饮,酣甚,捶芦菔(白萝卜)烂煮,研白米为糁食之。忽投箸抚几曰:“若非天竺酥酡,人间决无此味。”清代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浚,也盛赞白萝卜:“琼瑶一片,嚼如冷雪,齿鸣未已,从热俱平。”古人斯文,一枚普通的乡间萝卜竟吃出了仙界诗味。
年幼时,民间饥馑,以食为天,白萝卜几乎成了一日三餐的常味。或清炒,或炖煮,日子匆匆,单调的白萝卜竟也让一家老小过得精气神十足。一次,爹扛着锄头回来,手中捏着半只白萝卜,嘴里咔嚓咔嚓地嚼着,很带劲。我好奇之极,曾溜进胖子家的菜地里,拔了一颗大肚萝卜,用袖子揩了泥,塞入嘴中。不过,那味出乎我的意料,青涩,寡淡,还有一股生涩的辛辣味。也许,白萝卜才是那时生活的真实滋味。
倘若萝卜家族上演的是一出民间程式化的生活剧,白萝卜便是絮絮叨叨的宾白,而红萝卜则是戏台上的表演者。
红萝卜与白萝卜同宗同族。不过,与白萝卜晶莹剔透、白白胖胖不同,红萝卜秀气柔媚,小而圆滚,周身嫣红,就连茎秆和叶脉,都透出胭脂之气。
老家在南方,红萝卜不多见。居家西南后,这红彤彤、水灵灵的红萝卜竟成了风气。不过,此地的红萝卜似有慵懒之气,小巧玲珑,仿佛树上采下来的一颗桃。川人智慧,常用红萝卜做泡菜,酒饭之前,来一叠,红皮白瓤的萝卜丁,酸爽生脆,开胃极佳。成都的居民小巷子里,常有专卖泡菜的店铺,里面摆满了一溜透明的玻璃坛子,切成条块的红萝卜,躺在卤水里,白里渗着嫣红,红中泛着脂白,鲜活而俊俏,就像闲情逸致的当地人。
老家的红萝卜其实叫的是胡萝卜。叶子披针形,绿茵茵如同半开的纸伞。胡萝卜体型颀长,肉质红润,绿缨红唇,俨然情窦初开的婀娜少女。其实,胡萝卜误了乡人,其与萝卜无干。十二世纪,胡萝卜随胡人入主中原,以鲜美胜出,终究以假乱了真,跻身坊间,成了普罗大众最随和的一味。
尼采说,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生活。胡萝卜自然不谙人事,但从异域涉尘而来,却在乡间贫瘠而乏味的生活中超凡脱俗,出了自己的味,于炊烟缭绕间,独享一份人生的宁静与幽远。
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上下几千年,如此成了传统。白萝卜、红萝卜,各有一色,也自成一德。
三
有人说,一个时代是可以磕出味道的。年少时的味道在泉塘村,干巴巴的,如同嘴里嚼着砂子。
泉塘村水田多,谷子却不成器。收割后的稻茬,残留着村人的叹息,在清晨冒出泪珠来。后来,有好事者承包了一大片稻田,种上甘蔗。夏熟时一大片,高大森然,仿佛平庸的村子里长了反骨。金秋十月,甘蔗开始拔节,再拔节,最后长成了一片林子,周边的水稻黯然失色,少了去年的风骚。
甘蔗不多见,每次经过时我就不停地啃手指。爹会瞥我一眼,操了操干瘪的口袋,堆着笑,与守护人耳语几句,便钻进甘蔗林,挑了一根粗大的拔了来。那一回,我第一次吃到了甘蔗,植物粘稠的甘饴,甜到口齿发软。
后来方知,白砂糖,便是用甘蔗加工而成的。不过,在我明白之前,那片在风里哗哗作响的甘蔗林早就消失了,低矮的水稻占领了那片水田,在风里招摇。没有高度的生活,虽有起伏,但更多的是喋喋不休。
白砂糖不止提点生活的滋味,还能补益身心。其味甘性平,归脾肺经,可润肺生津、止咳益肺、舒缓肝气。《诗经·大雅·绵》曰:“堇茶如饴。”郑玄笺:“其所生菜,虽有性苦者,甘如饴也。”先秦古人便知制糖之法,可见忆苦思甜、苦中求乐,是一种逍遥活法,有出世的隐逸,有入世的快意。
那时日子薄苦,白砂糖难得,春节时才备点,为待客上品。新春佳节,亲友来拜年。“初一仔,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姑娘。”长幼之序,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亲人们相约拜年,说说笑笑,互道福喜后,便落座入席。先行“封杯”礼数,吃酒的满上,不善酒的一杯白开水,半调羹白砂糖。小孩口馋,再加点。用筷子转着圈搅几下,送入嘴边。甜味一爬上来,悬吊在高凳上的小腿甩得欢,幸福得不着边际。
小时候,家里的白砂糖藏在木楼上一堆坛坛罐罐中,不好找。上楼拿东西得干脆利落,否则瓦罐的碰撞声便会出卖我的慌乱,爹对此很警觉。不过,我一般都能发现白砂糖的藏处,轻而易举。小心打开纸包,用舌尖舔舐薄薄一层,美了天上人间。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学任教。年过九秩的奶奶,长年卧病在床,伶仃如孤灯。奶奶非亲奶奶,是爷爷的续弦,但待我如血脉之后。我欲去探望,却犹豫不知如何才妥帖。爹说,买两斤白砂糖吧。其时已有物华天宝气象,白砂糖已成大众之物,总感觉有些器小,但最终还是提了一包,拘谨地去了。奶奶洪福高寿,两眼迷离,白晃晃的泪水里全是岁月的咸淡。见到我去,奶奶大有喜色,仿佛看见一道光。我泡了一杯白砂糖开水喂她,她竟喋喋地致谢,似乎一下气顺了许多。
确实,对于见惯了春秋的老人来说,白砂糖既是烟火,也是人情。
白砂糖白成了日子,红砂糖欣欣然做了白砂糖的伴娘。其实,红砂糖是白砂糖的升华。甘蔗榨汁,加入磷酸、硫磺、石灰水等脱色;多次提纯,仍未脱色的糖渣,便成了红砂糖。红砂糖,红褐色,粉末状,是补充虚体能量的佳品。
那时,泉塘村的早晚冤家一般,一头冷一头热,像极了两个为了鸡毛蒜皮斗嘴的邻居。从土里刨生活的村人虽说百炼成钢,但难免脑热心虚,哼哼唧唧没了神思。家境稍好的,生姜切片,几勺红砂糖熬水冲服,逼出一身黏糊糊的汗水来,翌日必定神清气爽,元气如初。那时家穷,我身体不算强健,偶感风寒,便觉头重脚轻,村子开始横着飘。严重时,鼻息中的热气柔弱得如灯泡中的钨丝。寒家无贵子,爹从一棵叫“辣叶树”的老树上折下些枝叶,用干稻草点燃,熏出滚滚浓烟来。爹托着我的身子,像摆弄一只干咸鱼,在烟火上方画了三个圈,嘴里念念有词,然后虔诚地道声:好了,好了。竟也奇怪,不出三日,我竟又活蹦乱跳起来。时隔多年,那呛人的烟火气还残留在记忆里,真羡慕《红楼梦》中的林妹妹,宝哥哥端了一碗红砂糖水,一勺一勺地喂着,眸子里都是煽情的怜爱。
红砂糖的味道未及细品,奋斗的青春渐渐丰满,恰在戊寅年的本命年圆了一场姻缘。翌年,妻子怀孕临产,痛苦之声肝肠寸断,于是急送医院剖宫产。又一个凌晨时分,小儿呱呱大哭,横空出世,妻子在产房昏然入睡,青丝零落,汗湿衣襟。我日夜守护在病房,襁褓中的小子也不睁眼,哇哇直哭。医生告诉我,这是饿了,可用红砂糖泡水喂他。那几日,我一小勺吹凉,送入嘴边,小子横竖不论,大口吞食,褐色的甜水瞬间见了底。后来证实,小子多矫情,毕竟是在糖水里长大的。
旧时光全是陈年的气息,现在的吃食多了,白砂糖、红砂糖的味淡了。但于我而言,它们曾激活过一个时代。
烫皮,烫皮鸡
各地风物不同,自有不同的烟火味。对于远走他乡的人来说,吃在四方,尝尽了人间烟火,却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游离感。前几日,有老乡提及湖南老家安仁县的一味吃食烫皮,隐藏在舌尖下的根脉似乎游离出来,故乡也就含在嘴里了。
老家泉塘村坡坡坎坎,嘴里的日子也粗粝。金秋十月,农人弯下腰去,着急忙慌地把晚稻收割完,原本饱满的秋日便瘦成了萧索的初冬。此刻,太阳早降了火气,柔柔的,尚余一丝温热。收拾妥帖的晚稻米,温润如玉,细腻紧致,粘稠度适中。冬闲时间,农人琢磨日子,也琢磨嘴里的细节,于是将这单调的大米做出细腻的烫皮来。烫皮,便成了老家人藏在心思里的那根肋骨。
新鲜的晚稻米浸泡后,用手推磨磨成浆。舀一勺米浆倒入方形的铁皮框内,晃一晃,浆液在铁框内均匀地荡开,然后放入烧开水的铁锅中即可。看起来简单,火候、手法决定了烫皮的味道。我不知道爹从哪学来的技术,爹做烫皮的时候娴熟而老道。其实,爹很多细活都会做,酿米酒、霉豆腐乳、做盐辣子、做扑豆角,凡是坊间有的,他都会。就连缝衣服打补丁,也做得有板有眼。爹光着膀子系了围裙立在灶头,身子筛糠般一抖,铺了米浆的铁皮框便托在左手了。妈的头上罩了一块灰手帕,迷离着双眼,迅速往土灶里丢一把干稻草,“嚯”的一串火苗,照红了酱红的脸,也照亮了家里泛白的日子。爹一掀锅盖,从一团白色的雾气中迅速抽出铁框,用筷子在框的四周一划,光着手就揭下一张半透明的烫皮来。
爹掀下一张烫皮的时候,太阳正不温不火地照在院坝的竹篙上。竹篙早已洗净,用木杈支好,光溜溜一条,上了胎釉一般。刚出锅的烫皮摊在竹篙上,一张一张,像挂着无数张脸帕,在太阳下冒着淡淡的热气。阳光把脸贴在烫皮上,似透非透的,洇出一层红晕来。屋檐下,老门板被拆了下来,搁在两条长凳上。隔壁的花嫂子一身蓝花衣,两条发辫粗大乌黑,在竹篙间灵活地穿行,丰腴的腰身左右摇摆,仿佛一只醉花阴的蝴蝶。晾晒得半干的烫皮收了来,递到胖婶子手边。胖婶子端坐在案板边,绷直的两腿叠放着,脸上堆着笑,像一尊慈祥的雕像。她把烫皮叠层一小卷,菜刀一提一按,“沙沙沙”,雪亮的刀刃下,烫皮被切成均匀而光滑的丝条状,摆放在竹簟上继续晾晒。
泉塘村的日子是粗的,乡人的脾气也是粗的,经常会为鸡毛蒜皮的事吵上半晌。爹为了田里的一股流水和胖婶家里骂过架。为了鸡飞进菜园子,妈和花嫂子也红过脸。不过,这没什么,磕磕绊绊、斤斤计较,似乎是乡下生活本来的样子。其实,乡人更多的时候就像沟壑里的黏土,一捏就成型,重世故,更重人情。在贫瘠的生活空间里,更多的时候,乡里乡亲经常互相帮衬,一起扶正东倒西歪的日子。
灶房里,爹不停地哈着被烫红的手指,又掀下一张烫皮来。按照惯例,烫皮做到约摸一半,要吃热烫皮。案板上,有一碟红辣子灰,和一碗用酱油腌好的芫荽菜。将烫皮摊开,抹一把辣子灰,一口烫皮就一口芫荽菜,辣子灰的辣、芫荽菜的香,加上稻草杆熏出来的米香,素食里可以吃出荤腥的饱足感。在乡下,粗糙日子的细腻味道,都是精心拼凑出来的。
烫皮是难得的辅食,也是最朴素的人情。晒干的烫皮一卷一卷的,在瓦缸里收好。平日里一般舍不得吃,只有在节日或者待客时才食用。远客进屋,热情地招呼着落座,一边嘘寒问暖,一边架锅烧水,抓两卷烫皮丢在滚水里。几分钟后,葱姜蒜切末,半勺猪油,一把红辣子灰,轻挑着搅拌,烫皮淡淡的米香漫上来,撩得蹲在门槛上的黄狗不停地卷着舌头舔嘴皮。当然,乡人待客从不怠慢传统礼节,烫皮里要加三个滴水蛋,埋在碗底,含蓄但不失厚重。
小时候吃烫皮,很多时候顶了一顿饭,没有吃出太多的细节。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中学教书,离家远了些,虽然也会从家里带些烫皮到学校里吃,但那烫皮似乎少了某种味道。其间,偶尔也会跑到县城菜市场去吃烫皮。那里的烫皮有绍子菜,或者胡萝卜炒肉,或者豆芽炒肉,烫皮与菜肴搭配,仿佛田土里多了城镇的气息。再后来,为了在生活的理想里找到理想的生活,我辗转来到千里之外的西南都市,泉塘村反倒成了挥之不去的他乡了。每次春节回去,在泉塘村的草木里穿行,总想找到一些过往的记忆。然而,村子留给我的,全是一些疏疏淡淡的影子。
有一年去北方,人间四月天,风大得出奇,没有由头,也没有方向,一身劲,呼呼地吼。其实,这风没什么,很多事情都是从风里来的,又很快消失在风里。习惯了就好。我不习惯的是一日三餐的面。寻了一条街,烩面、卤面、板面、炒面、饸饹面,面面俱到。胡乱要了一碗,很快,高大壮实的女服务员端上前来,还赠送我一个结实的笑。接下来吃了一周多的面,吃得肠胃泄了气,松松垮垮。于南方人而言,面条到底粗犷了些,筋骨老健,有走西口、闯关东的武行之气。其实,北方的劲道,始终烧不出南方绵远的烟火。
曾经,我总以为我是一颗村子里飘出来的蒲公英种子,到哪儿都能长出一个春天。事实上不是,妻曾经对我说,移植过来的树再大,根也不会扎太深的。我若有所悟,自己不过是一颗无法掌控春天的蒲公英种子。
蛰居西南都会多年,不觉人到中年,青丝染了霜白。我对吃食并无挑剔,倒是见多了风物,总觉得秋水星河之间,自己误了春风,只是一匆匆过客了。去年春节回家过年,父母大喜,东张罗西招呼。我帮不上忙,颤巍巍的手脚无措,一时我竟成了自家的客。与父母相处几日,话说不上几句,只牢牢记住了他们的苍老与力不从心。临走时,他们有些失落和不舍,执意要我带鸡鸭回来吃。乡间生活不易,我说,就带一些烫皮吧。爹说,村里早没人做烫皮了呢,青壮年都进城打工去了,留守的老人连水田都扒不动了,又不少吃的,谁还有做烫皮的心思?我不禁有些惶然,心想,家里的味道是带不走了。
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在县城转一圈,看看县城拔地而起的新楼房,日益拓宽的新街道。临街的小巷里,熙熙攘攘的聚了人气。这里开了很多卖烫皮的店子,烫皮已经成了菜单上的一味。不过,招徕生意的已不是单纯的烫皮,而是四处招摇的烫皮鸡了。鸡和烫皮是怎样的一种撮合,我很诧异。爹绝不会将柔滑的烫皮与精瘦的鸡肉霸蛮地搅合在一起,将就一顿辅食,浪费了席上一碗硬菜。不过,用鸡汤来煮烫皮倒是吃过几回,鸡汤的绵远与烫皮的滑爽在嘴里化开,荤与素在肠胃里和解升华。
烫皮鸡一上桌,粗鲁得令我有些猝不及防。端上来一大盆,烫皮也不是均匀的丝状,而是一片片的菱形块状。大块大块的鸡肉,肥硕而丰厚。烫皮的随意与鸡肉的大方,似乎彰显了老家人富足的生活。老板说,回乡的人吃烫皮鸡成了一种风气,原来粗粝的烫皮不受欢迎,于是都进行了改良。看着满满当当的一大盆,烫皮在鸡肉间流转,烫皮吸了鸡块的膏腴,鸡肉得了稻米的醇香,仿佛城乡之间日益缩小缝隙的日子。
烫皮鸡做出了日子的好,但我始终吃不出这豪华的味,总感觉少了某些细节和过程。每每回家,我常常会伫立在老屋的土坝上,默默地看着父母佝偻的身影,看着被草蔓吞噬的原野,和那日益生长但有些寂寞的村庄,寻找最原生态的味道。不过,终究是寻不见了。
我有时怀疑,我是否已经背叛我的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