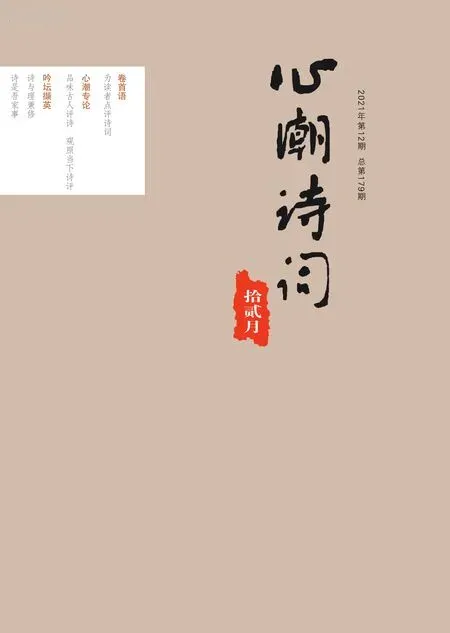谈谈作为批评与创作理论资源的传统诗论
——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说起
莫真宝
(作者系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副主任)
十余年前,当代诗词从复苏走向复兴的话题就常常被诗词界高调言及。有人认为当世固然无单挑李白、杜甫之人,岂乏贾岛、姚合之辈?若一对一进行团体赛,今人未必输给唐人;有人甚至自信地喊出“超唐迈宋”的口号,以之为当代诗词不受人待见而叫屈。这种自信心固然可贵,只是响应这些论断的人恐怕颇为寥寥,而且一直以来,诗词界普遍认为,与轰轰烈烈的旧体诗词活动及蓬勃发展的旧体诗写作现状相比,当代诗词评论与研究始终是一个明显的“短板”,这个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代诗词创作从高原向高峰的攀升。诗词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一边为推动当代诗词评论与研究水平大声疾呼,一边积极主动地召开各种类型的诗词研讨会,出版当代诗词论集;国家社科基金陆续支持了一定数量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词的研究课题,部分学术刊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向现代诗词研究论文敞开了怀抱,相关诗歌网站如已经划归中国作协诗刊社旗下的中国诗歌网,以及相关机构所属的中国诗歌网、诗刊社、中华辞赋、中华诗词等微信自媒体,和诗词界同人主办的小楼听雨诗刊、云帆诗友会等为数众多的微信自媒体,不少平台都高频次地发布当代诗词作品点评与评论,但人们期待中的诗词评论与诗词创作互相促进的局面并非出现,诗词研究与评论于诗词创作的推动效果远远未能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不过,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点,是象牙塔里的现代诗词研究的对象基本局限在1949年以前,鲜有涉及1949年以后的诗词创作,无论古代诗词研究,还是现代诗词研究,都与当下火热的诗词现场存在明显的“鸿沟”,或者说是“脱节”现象;第二点,是活跃在当下诗词写作与诗词评论圈的人,大多未能接触或者不屑接触这类诗词研究成果,也无力运用西方诗论于当下诗词评论与诗词研究,甚至对古代诗史与古代诗论、诗学知识也所知有限,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很难有效掌握古代诗学理论这一“批判的武器”,从事诗词评论与研究时,倘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未免隔靴搔痒,甚至方枘圆凿。一个诗学观点的提出,往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场景,其适用范围大多有一定的局限,削足适履,以此就彼,常常出现胶柱鼓瑟的现象。
比如,明代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所谓比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寄托,形容摹写,反覆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其中的“托物寓情”和“寄托”,即指《诗经》中的比、兴手法而言,而“正言直述”说的是赋的手法。正言直述,固然可以指向抒情、议论,但无疑更多地指向对“事实”的描述。这段话的结论是“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为今人概括出来的中国诗歌的抒情特质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脚。如何看待“诗贵情思而轻事实”这一诗学命题呢?我们先从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说起。
自《左传》提出“诗言,是其志也”之后,“诗言志”一直是笼罩于春秋战国乃至两汉时期的主流诗歌理论,《尚书》《庄子》《荀子》等众多选秦典籍都记载了相似或相同的论断。其他关于诗歌的看法,多围绕诗言志而展开,以至朱自清把“诗言志”视为我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战国末期的屈原,在《九章·惜诵》中虽然发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的呼声,但这里并非将“抒情”作为诗歌表达的要求提出来。汉代《毛诗大序》在解释“诗言志”时,连带涉及诗歌抒情的问题。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是在“志”与“诗”之间,插入一个“情”作为中介。直到魏晋之际的陆机,才在《文赋》中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观点。“情”“志”二分,不利于大一统的思想的推行。在经历了六朝诗歌“情”的泛滥之后,唐代孔颖达最早在《毛诗序正义》中提出“情志合一”的论调,他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这一论调,使“言志”“缘情”得到统一,诗的“抒情本体论”随之得以确立,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的成熟。与此相关,自《礼记·乐记》提出“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便是音乐领域的“物感说”,至西晋陆机《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形成了“物感说”的诗歌创作理论。经钟嵘等诗论家的发挥,感物与缘情相结合,夯实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理论的基石。
但是,诗歌的表现对象远非情、志二端可以涵括,诗歌中的情、志也不是一空依傍的存在,而是毫无例外地有事作为支撑,凡诗之作,或缘于史事,或缘于本事,或直陈其事。可以说,从诗中情志与诗中之事的关系而言,无事之诗至为罕见,即使偶尔有之,也难以成其为好诗。由此引申而出的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另外一个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上古歌谣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叙说了先民砍伐竹子制作武器,并与掷石子相配合进行狩猎的过程。《击壤歌》所述“日出而作,日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场景,至今思之,仍然历历如在目前。两汉时期的《诗经》学者,在解释“诗三百”的具体作品时,重点围绕“诗六义”,特别是围绕作为表现手法的赋、比、兴来阐释诗中之“志”,尤重比兴,甚至有“独标兴体”之说。“诗三百”中的“志”并不是孤立而突兀的存在,故汉儒释诗,毫无例外地要给不同的诗篇寻求一个背后的“事”。《诗经》每篇的“小序”不遗余力地试图将诗作与史实挂钩,如《载驰》《烝民》《采薇》等篇背后的史实是确定的,很少有人提出异议。这里不讨论全部小序所钩沉的史实的真实性与可信度,但从中反映出的诗中有事的诗歌观念相当明确。其实,除了诗篇背后的史实,落实到篇章和表面文字上,《诗经》中的诗篇,绝大多数也是围绕事件展开的。除《大雅》中被认为是周民族开国史诗的《大明》《生民》《公刘》《緜》《皇矣》《文王》等几篇之外,大量的诗篇也都是围绕“事”来展开叙说的,如《静女》写男女间的约会,《溱洧》写上巳节大会男女的风俗,《硕人》写出嫁的场面,《氓》叙写一位女子与男子相恋、嫁娶、婚后生活和被弃的过程,等等。即使纯用比体的《硕鼠》《螽斯》《鸱鸮》这三首诗,其共同的特点不仅是以物拟人的“比体”,而且都是诉诸形象化的寓言诗,在直抒胸臆的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描写与叙事意味。《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很好地概括了诗中有事这一现象。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体是“乐府”,尤其以乐府民歌为后世所称道,乐府民歌的叙事意味即相当浓厚。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两汉乐府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指出乐府民歌因事而兴感的创作动因,其中不少作品几乎将所有篇幅都用在叙事上,如《妇病行》《东门行》《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都是如此。比如《十五从军征》,就叙述了一位十五岁从军,八十岁时才退伍归来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悲惨遭遇。胡大雷教授在论及乐府民歌的特点时说,其中有两点“对后代的影响最为持久,这就是多吟咏他人与重在叙事”“就重在叙事而言,虽说乐府民歌叙事的作品与抒情的作品都有,但优秀之作,大都是叙事的”。唐代杜甫既像前人那样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同时也写作即事命题的乐府诗。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更是大量写作即事命题的乐府诗。即使汉魏之际的曹植等人逐渐增强了诗歌的主体性抒情,在写作五言乐府诗题的同时,把乐府诗改造成所谓文人五言诗,也难以改变汉代乐府民歌叙事的特征对建安、魏晋文人五言诗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晋宋之际,陶渊明的诗歌的叙事意味都是很浓的,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游斜川》《乞食》《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等,一看题目便知其本事。即使抒情意味浓厚的《归园田居》,其情感亦“缘事而发”,如第一首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全诗八句,一句接一句,前六句都在不动声色地连贯叙事,结尾才顺势言及事后的感受。这类诗作,大部分篇幅用来叙事,叙事与抒情说理毫不相混。此类特点在谢灵运等人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再者,引用古代诗论评价当代诗歌,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诗歌体裁。诗、词本来轸域分明,叶嘉莹论及歌辞之词、诗人之词与赋化之词,乃至哲化之词,以此梳理词文体的发展演变脉络,揭示出词文体与古近体诗相互交融的特点,似乎揭示出诗、词文体特征的界限有逐渐模糊的趋势。二十世纪以来,受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寄托”说、“词亦有史”说,以及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常常诗词对举并标榜“境界说”的影响,“以诗法为小词”成为一时风尚。人们言及传统诗歌各种体式,乃至具体的诗歌批评,往往“诗词”合为一语而言。如谈论诗歌的表现内容,当我们一遍遍地引用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序》中“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以及《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等语,强调白居易重视诗歌应该关心社会现实,表现重磊社会事件以期实现他“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禆补时阙”的政治理想时,却有选择性地忽略了白居易把自己的2700多首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等四大类的事实。大体而言,前三类为古体诗,后一类“杂律诗”为近体诗。且讽喻诗只有173首,仅占约6%。那么,我们可以说,白居易强调诗歌表现社会生活的功能,多指乐府体和古体诗而言。杜甫的《北征》《兵车行》《悲陈陶》《洗兵马》,乃至“三吏”“三别”,体现的仍然是“多吟咏他人与重在叙事”的特点。即使同样运用七言歌行体表现重大时事题材,以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为代表的“元和体”,与以吴伟业《圆圆曲》《鸳湖曲》等诗作为代表的“梅村体”亦殊为不类。遑论乐府体、魏晋古诗、唐代古诗之间内容与形式及风格上的差异?即唐代古诗,也有深受近体影响古诗,与有意避免律句的古诗,其有意避免律句,与近体诗形成之前的自然韵律的古诗,也存在着内容与风格上的显著差异,这些都需要仔细分辨,而不是混为一谈。明朝人说“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正是看到了唐代古诗与前代古诗的差异之所在。倘若我们选择乐府体和古体进行写作和评论,不能不留意这一点。
又如谈论诗歌的表现手法,或直接将适用于《诗经》的赋、比、兴,套用在对后世诗歌的分析,而不顾及后世大量诗歌难以直接套用赋、比、兴手法对之进行分析的新的特征;或谈论前代诗歌,使用“情景交融”“意象”“意境”等概念,而不顾及用后代产生的概念去套前代诗歌作品可能产生的不适应;或将近体诗的理论用之于古体诗,或将古体诗的理论用之于近体诗,都难免会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诗歌,既然都是诗歌,当然具有其共同之点;虽然都是诗歌,但既然是不同体裁,就必然有其差异之处,包括同为近体的五律、五绝、七律、七绝,乃至五七言排律,其适用的内容与风格都各有独特之点。就写法方面,以“情景交融”而论,蒋寅教授在分析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卿宿别》的颈联“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时说:“(这)是用一个空镜头摄录了两人挑灯夜话的环境:室内孤灯暗淡,窗外阴雨淅沥,……夜深雨止,在黯淡的灯光下,幽暗的竹丛湿气弥漫,如烟似雾。……这惝恍迷离的景象可以说就是诗人心境的外化,两句中的景物根本就不是观照、描写的对象,而是表情的媒介,是典型的意象化表现,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并指出:“古人论诗以景物描写为虚,以抒情言事为实,讲究虚实相生,以获得含蓄不尽的效果。近体诗字数无多,如果句句写实,所能表达的内容极为有限,只有以虚济实,虚实相生,才能用有限的文字传达丰富的意蕴。中唐以后,古典诗歌逐渐形成以情景交融的意象化表现为主导的审美倾向,原因就在这里。”用情景交融论中唐以来的近体诗,就比较洽切。
古体诗虽有句式严整的五古、七古,但理论上篇无定句,句无定字,其不受篇幅、平仄甚至用韵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可以运用散文句法,像散文那样相对自由地叙事、抒情,多采用线型结构,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偶尔间以直接写景、抒情,以便上下勾连,结构清晰而分明。与之相对而言,近体诗则受限过多,故其字法、句法、结构,以及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与古体诗相比,更多其独特之点,形成独具一格的所谓“诗家语”。如果像当下很多人那样,不加辨析地使用古代诗论话语体系谈论当下的近体诗和词,而不对体裁加以区分,就难免出现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于诗词创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又如何能对创作有所助益呢?
自从白话诗运动以来,西方诗论对我国白话新诗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朱光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诗论》,却侧重于“西学东渐”。他在一九八四年给三联书店重版《诗论》所写《后记》中说,这本书是他“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并称:“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我们把采用中国古典诗歌样式创作的作品称为旧体诗词,然而,直到今天,旧体诗词写作受到西方诗论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人们也极少采用西方诗论的视角来评论当代诗词。不仅如此,一般人谈论当下诗词,在古代诗论资源的利用方面,也存在知识储备不足和知识运用方面的误区。
一个时代具有标志性的诗歌理论,往往是对前代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对彼时诗歌创作进行“理论指导”,因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产生的诗歌理论对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有些诗歌理论的产生,往往带有地域色彩和流派色彩,甚至是对受前代诗歌理论流弊影响的纠偏救弊,常常带有意气之言和过激之言的意味,我们不能因为“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但至少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各种不同诗学观点适用的中心和边界。回顾自《诗经》以来近三千年来的诗歌发展史,诗歌的内容与体裁,题材与写法,类型与风格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与之相关的诗学理论命题也不断出现,在新的诗学理论名词不断产生的同时,也不断地给旧的诗学名词贯注新的内涵,如果不加以历史地分析,贸然使用,就难以恰到好处地实现其批评效果。诗是专门之学,我们不必苛求作者与论者在写作之时,都能掌握系统的诗歌史知识和诗学理论知识,都能具备深厚的理论修养。不过,当我们谈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总会存在一个需要跨越的基础性的“门槛”问题。如果谈论当下诗词时,只是简单地拿“诗言志”“诗缘情”,或赋比兴,乃至情景交融来说事,显然是不够的。明代李东阳主张“诗贵情思而轻事实”,只是站在诗歌抒情的一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近体诗,而非适用于所有诗歌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