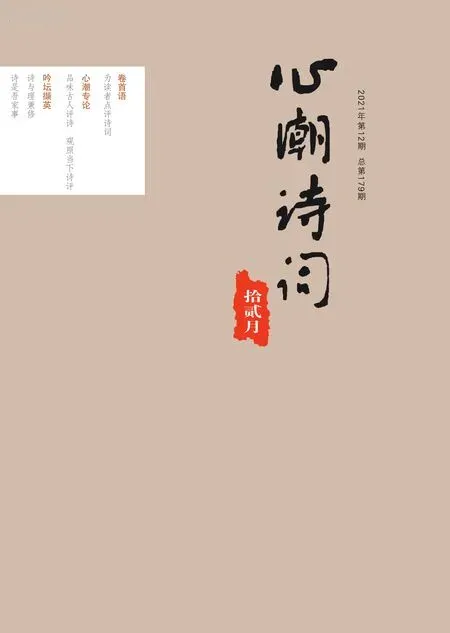诗是吾家事
安全东
(作者系巴山诗社社长)
平生少暇,到老学诗。屈指算来,迄今一十三年矣。然而却万不敢以诗人自命。何为者?盖诗词一行,高深莫测,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强中自有强中手。又尝言江海之鱼龙,小者泼剌,大者渊沉,我虽年近古稀,犹止小鱼一枚耳。这是前话,言归正传——
2008年11月17日下 午,我 自乡 下 回城,路经一堰塘,其时夕阳西下,满天云霞倒映水面,满塘都在燃烧、蒸腾、翻滚,我一下被这景象惊呆了,挪不开步子,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要写诗的冲动。奇怪的是,这种冲动,却不是要写新诗的冲动(此前写了近三十年的新诗),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要写一首旧体诗的冲动。然后一路走一路想,居然有了四句。天知道写的是什么,到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不过从那天起,心里的那颗种子开始蠢蠢欲动。虽然我祖上三代贫农,略无家传,但我从小读书用功,尤偏好语文,多多少少读了一点古诗词方面的书籍,直到那个下午之前不久,我还手抄了厚厚两本历代诗词选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在电脑上关注诗词方面的动态,首次发现居然有专门发表诗词的网站、论坛,于是一下像找到了“组织”一样兴奋。再接下来就顺理成章的注册,登录,写诗的兴趣日见高涨,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时至今日,还为自己偶然成为“诗人”的机缘感慨不已,认为是上天的赐予。十余年下来,有成功,有失败,有喜悦,有苦恼,如今都成了我自珍自宝的财富。言及心得,我以“诗是吾家事”这句现成古语概括之。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个体精神劳动的产物,别人是无论如何代替不了的。所以,尽管从古至今诗人无数,诗词无数,洋洋大观,但无一不是每个作者青灯黄卷呕心沥血的产物,无一不打上诗人自己的烙印,跟别人了无干涉。而且我还认为,“诗是吾家事”的“事”,至少还包括这样三层意思:一是要把写诗当成一个事业,全身心的投入,甚至于要有“呕出心乃尔”的殉道者精神。二是所写之作品只能姓“吾”,而不能姓万金油百家姓或别的什么,要以“吾”的独家面目特立于世。三就是诗中要有“事”,那种望空结想下笔千言不及一事的作品,说到底就是一纸空壳。以我十余年的摸索实践,要真正验证并且做到诗是吾家之“事”,以下三点是必须的。
首先就是前面说过的,诗中要有“事”。关于这个,我自己在学诗之初始阶段是走过一段弯路的。那时才入诗门,兴致勃勃,见什么写什么,自以为是,结果什么都不是。有一次,我竟只用了三天就把唐代诗人钱珝的《江行一百诗》给步了下来,兴之所至,洋洋自得,殊不知全部是凭空“捏造”,了无个事。还美滋滋把它们收入我的第一部诗词集中。然而没过多久就后悔了。现在回头再看,这个步韵诗,无事、无人、无情,是名副其实的“三无”产品。回想起来,这样的“三无产品”在我初学阶段占了不小的比重,内容空泛,无诗找诗,还给自己找了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叫做练手,玩儿,实际是没有在“事”上着力,下功夫。然则什么是事呢?换句话说什么是诗中之事呢?以我的体会理解,大凡国事家事天下事,大事小事,新事旧事,山石林泉,风花雪月,无不可以成为诗中之事,就看我们如何采入,以成诗中之“事”。我们读古人一些诗集,往往有这样的体会,读其诗,即知诗人一生行状,像读他的日记,读他的编年体。比如老杜,一千多首诗中,少有无的放矢空泛无事之作。读其诗,仿佛那个忧时伤世、诗酒飘零的瘦弱老病的老头就在目前。当然马勃牛溲事无巨细都写入诗中又未免琐甚。当今有些诗人,生活面既逼窄少事,于是成天闭门造诗,每诗不离鸡鸭猫狗,雀鸟蜂蝶等等,千篇一律,以为是“事”,我曾讥之为“动物园园长”。
其次是诗中要有“我”。没有“我”的诗永远缺乏灵魂,只是一堆字码。但这个“我”也可能真是我,也可能是我之外的人。也可能是一件物事,一个风景,也可能是一段感情,一个感慨。总之作品不要是一件玻璃器皿,看着满盈,实则是虚,赏玩一过,什么都没有。这个“我”,跟王国维之“无我”“有我”略有区别,他说的是诗词之境界,我指的是诗词之涵纳、个性。同时这个“我”,无论小我、大我,因人因诗而异,并无孰高孰低之界定。还拿我那个步韵一百首说事,那里面,几乎没有自己,有的只是干瘪瘪的毫无生气的字词,不过变成韵语说出来而已,既无“事”,也无“我”,所以后来被我视如敝屣也是必然的。其实换一种说法,把诗中有“我”理解为诗中有“情”也未为不可。我即是情,情即是我,或者直言“人、情”也是可以的。太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里面有太白这个“我”,也可能是李白之外的“人”。那么,骆宾王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有“我”吗?我认为也有——那是活泼泼跳动着的一颗童心。我们读着这两首诗的时候,分明就见着了一个望乡的“我”和一个观鹅的“我”,虽然他们都没有直接出现在诗里,但却能让读者感知到他们的存在。而反观我自己的,如“头白青岩子,端居厌世争。耕山同旦暮,听惯乱泉声”、如“蛩声吟断续,萧瑟正秋时。乡思近来切,莼鲈未有期”、如“陌上采桑女,劳劳不胜情。昨宵魂梦里,夫婿在江城”等等,要么伪作清高,要么杜撰乡思,要么代拟怨妇,诗中有的只有矫情,而失掉了“我”。好在随着见识的提高和觉悟,后来的诗中这类东西逐渐减少,“我”在诗中变成了一种自觉。写云南大旱,则“人居环境几酸咸,涝旱交加苦不堪。若是春风能化雨,乞分一缕到滇南”,写汶川十年祭则“梦里茫茫何处村,子规声断月黄昏。十年儿女灯前泪,手拨寒烟认墓门。”,写中秋则“不见家家小语温,中秋月色照山村。逢人莫说打工事,每到今宵有泪痕”。这些诗虽不能说都好,但却都有一个“我”在其中。即便是写景,也尽量把“我”放进去,以使所写不致流于照相模式,死板,空洞。如写冬日银杏,则“眼前一树三千丈,尽是西风劫后金”;写秋柿,则“疑是农家秋社又,满天云幕挂灯笼”;写溪口蒋母陵园,则“养儿若是真龙种,不信离魂望至今”。等等。这样的诗正可谓:“看来也止寻常句,一有真我便不同。”其实诗中这个“我”,说白了就是一点事加一点思想,但却偏偏成了很多人诗学路上的拦路虎,百悟不透。
最后是诗中要有艺。有艺,说通俗点就是要有技术含量。判定一首诗之优劣,除了有无“事”与“我”外,还跟作者技术之高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艺”不但包括自古以来讲求炼字炼句炼意的诗词传统外,还包括思想的涵纳,角度的选择以及风格的独到等等。于今社会结构多元,生活节奏提速,人心浮躁少静,体现在当今诗词创作上便是诗人多如过江之鲫,作品粗制滥造,诗人名心太盛。加上现在诗词公号、诗词微信群、各级没有稿费的诗词刊物的推激,使诗词的生产量大得惊人。就中虽不乏佳作,但大多属于无“艺”之作,要么是顺口溜打油诗,要么不讲声韵格律,要么一味学古,要么坠入斗尖弄巧之恶道,还美其名曰创新。凡此种种,都是弘扬传统诗词的反动。这样的诗基本属于无自身特点,无事,无我的“大路货”,与“诗是吾家事”的旨归相去甚远。
以我的体会,要提高诗艺,无外三点:一是向古人学习,掌握大量的诗词语汇。中国两千多年的优秀诗歌实践,涌现了数不尽好诗人和好作品,作为今之诗人,尤其是初学者,这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山。我们可以学他们的对于一首诗词的经营,包括立意、选材、炼字等等,同时要有意识地积累掌握大量的诗词语汇。我常常就困惑于此,写作时每每捉襟见肘,有表达之意却无精准的表达之词,眼高手低,写时费力,写出来俗熟可厌,虽是自家事,不是自家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肚子里存货太少。所以要向古人学,向诗词经典学,只有掌握了大量的词汇量,用时才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环顾左右,当今寡学如我者又岂在少数。有相当一部分诗人,功底既薄,而又急于功名,写出来的诗要么文辞浅薄,要么俗熟少味,读不竟篇,更遑论美育美感。二是坚持走醇厚雅正的传统诗词路子。自《诗经》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华诗词无论从形式上如何变化,但醇厚雅正的传统没有变,被历代的诗人们继晷发扬下来。只是到了当下,时风滋蔓,人心浇离,这个传统似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和挑战。究其根本,一则当今之人学殖普遍不厚,因此写诗作词只能在所谓的“求新求变”上玩点小花样。二则“诗人”大量涌现,良莠不齐,使得“油滑体”“老干体”大行其道。三则各种诗词大赛,也有意无意催生了一大批尖新奇诡的“参赛体”。还有就是当今某些以弄巧为能事的大咖们的引领,都对雅正诗风形成一种反动。我自习诗以来,尽管写得不好,但必以雅正来约束准绳之,对滑易滥俗之作避而远之。三是下足雕琢锻炼之功。有好的题材好的立意还不算完,进入到写作中,一定要做到字敲句酌,字烹句炼,用最好的字词表达最完美的“事”和“我”,把水平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写作者应有的态度。这与其说是一项技术,毋宁说是一种精神,一种责任。往小里说是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往大里说则是为继承优秀的诗歌传统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首好诗。前人说“诗不妄作”“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可惜这样的诗人现在太少了。最后一点就是语言。语言必须有自己的特点,是自家语。换句话说,必须姓“我”。一个成熟的诗人,必有自己的语言定势,语言习惯,有些喜欢平易,有些喜欢雕绘,还有人喜欢隐晦,在完美表现“事”与“我”这个前提下,原无高下巧拙之分。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无可厚非。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更多的会把语言写得更“我”一些,句子写得更美一些。我们常常听人说某某诗像王孟,某某诗像李白,某某诗像白居易、李商隐等等,除了部分是因为内容题材相似外,很大原因就是语言风格的“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标志。
所以,说“诗是吾家事”,其内涵至深至广。可以是“吾家”事,“我心写我诗”,(如今听说有作诗机软件,此又另当别论)也可以是“大家”之事,即众人之事社会之事,因为它一旦问世,终究是要给人看的,是有教化功能的。因此我们即便没有以诗鸣世或传之久远的想法,也应该尽可能把诗写得好看一些,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当下这个文化勃兴的大时代。
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