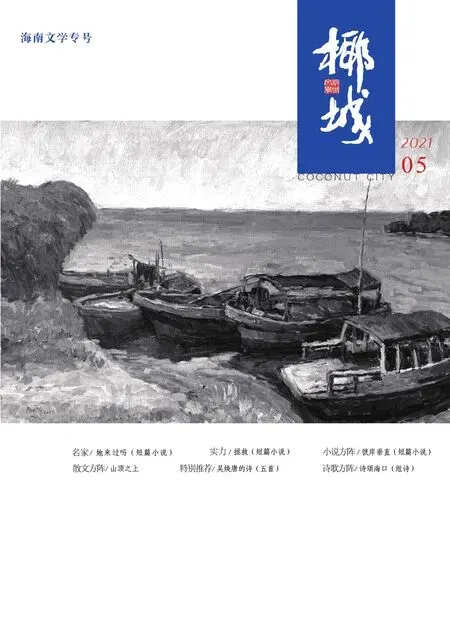拯救(短篇小说)
◎符浩勇
一
苏武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有个声音在喊:“老苏,是老苏在屋里吧?快到楼道里接电话,有电话找你!”
他翻身起床,嘴上应了一声:“来了。”心里却觉得好笑,自己大学还没毕业呢,怎么就变成老苏了?真有那么老吗?然后又纳闷:谁呀?有谁会给自己打电话呢?但不管怎么样,先接了电话再说。他穿好衣服,就出门往楼道走去。他压根就没想到,因为这个电话,自己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楼道电话间里,苏武拿起话筒,礼貌性地说一句“你好”!还未来得及问清对方是谁?对方就哇啦哇啦地说开了,就跟竹筒倒豆子似的。“你是苏武吗?我是区公署房管所的。刚接到报障,西郊老城区陆丰路41 号聚居楼发生事故,急需有人去抢修一下。我们这里的人都下班走了,你现在去一下吧!”那种口气,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他心里有点不大高兴:你们都下班走了,可我今天也没有安排值班呀,凭什么就一定该我去呢?他感到很困,本想借故推掉回屋再睡,可转念一想,自己是个实习生,是来学习的,这种态度不对。于是就说:“好吧,我稍后就去。”本想再问一下具体的联系方式,对方已经挂了电话。窗外,天色灰暗,几近黄昏,他不敢懈怠,匆匆下楼,骑上那辆借来的自行车,往西郊方向赶去。
他是北平国立建筑大学管道工程专业的学生,大四了,三个月前与五个同学来到山西桐城这个城市,在城西的区公署房产管理所实习,具体的任务是学习探测并评估楼房管道存在的风险和隐患。实际上,这些天他们除了学习探测楼房管道风险和隐患,还随带班师傅深入到各个居民点排忧解难,帮助疏通下水道或焊接楼层间管道等工作。恰逢国庆纪念日,算上周末,一共有几天的时间休息,一同来实习的五名同学都已离开小城,回家与家人团聚去了,只有他报名留守待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何偿不想回去!但他的老家在遥远的南方,也就几天的假期,就算全都打发在路上还不够呢!若是回到北平那个校园去,孤零零的一个人,其实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原地休息,而且留守还能赚点津贴补助,所以他就留下来了。中午他去火车站给同学送行,回来躺下刚迷糊一阵,就被那个敲门声叫醒了。
路旁的桐树上挂着红灯笼,青天白日旗随风招展,“砰——叭——”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爆竹,提醒人们节日的到来,却没有多少喜庆的气氛。苏武踩着自行车,两腿紧绷,一左一右,不停地轮回,希望在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之前赶到报修的地方。
紧赶慢赶,到了西郊的陆丰路,他辨认着门牌,找到了41 号,楼道上面果然有“聚居楼”三个大字。这时,路灯一下子亮了起来,他发现自己长长的影子颤颤悠悠,像是被水中的涟漪托起,忽然觉得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才记起来时着急,忘了要先吃点东西。饥渴难耐,他想找个地方填一填肚子,又想,还是先把事情办完再说吧。
聚居楼是一栋筒子楼,只有一个楼道口出入,楼道口上方有一只带灯罩的小灯泡,灯光发黄发暗。楼下一层隔开大小相等的若干间,有的上着门板,有的拉下了卷闸门,显然都是做小生意的零售店铺,但不该这么早就打烊。苏武把自行车往楼墙一靠,就匆匆地进入楼口去了。
他快步走上楼梯,只见长长的楼道像一个直筒子伸过去,蜂窝煤、废炉罐、破铁锅、旧纸箱、烂皮鞋等,有用的、没用但又舍不得扔掉的,各种杂物见缝插针,随意堆放,有的地方仅容一人通过。楼道两边的人家,各家各户的大门开阖不一,但都挂着门帘。楼道里光线昏暗,混杂着食物、烟火等各种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他记得报障人家在四楼。这时,从上面的楼梯走下来一个打扮妖艳的少妇,弯弯的眉毛一挑,猩红的嘴唇一咧,对他挑逗地一笑,含糊着说了一句。他听不清楚她说的是什么,但能猜出她大概是个什么货色,不理睬她,赶紧躲开,直往四楼上走。
苏武来到那个报障人家门前。屋里一个瘦得像排骨一样的男人正埋怨一个胖乎乎的女人:“我看你就是猪脑,烧煤也不记得停火,把砖墙都烧焦了,水管能不爆吗?”女人的火气更大,大声回骂:“你厉害!那你干什么去了?整天什么活都不想干,就会说别人!要是没有我,你恐怕……”苏武敲了敲敞开着的大门,那两个人停下争吵,一齐看过来。苏武自我介绍说:“我是房产所修管道的。”排骨男好像要借机发泄心里的火气,埋怨说:“你怎么这时候才来?”苏武正想解释,胖女人说:“不要跟他废话!”走过来拉着他去看爆裂的管道。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墙体被蜂窝煤烧焦的地方裂开碗口大的裂缝,这简直难以置信。他看了又看,然后说:“这么严重的爆裂,一时半刻也修不好,我只能暂时封住爆裂的管道口。”忙乎一阵后,他用手电筒靠近照看那个裂缝,似乎光柱透过了墙体,穿越了大楼外面的黑暗。
那个排骨男嘟哝道:“今晚怕是要洗冷水澡了。”胖女人马上拿话噎他:“你不洗一晚会死呀?”男的说:“不洗臭烘烘的,怎么睡?”女的说:“臭也好香也好,都是你的,没人会挨近你!”
苏武怕排骨男继续纠缠,赶紧退出门去。走下楼道的时候,匆匆之间撞倒一个旧瓶罐,“哐当——”随着一声剧烈的响动,不少人家开门露出头来要探看个究竟。
出了聚居楼,绕到楼面后头去,他用手电筒照向楼体,原来从楼顶直到墙基不知什么时候已扯开一道歪歪扭扭的裂缝,初步目测了一下,整的墙体已经倾斜一侧。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几乎叫出声来,感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说不定今天或明天,整幢楼就会瞬间坍塌。他不敢怠慢,捡起自行车就匆匆往回赶,去时觉得路程遥远,回时一溜烟就到了住处。他匆匆喝了一口水,就坐到灯下,找出书本,对着案例,反复建模检测,眉头紧锁,自言自语:不会吧?是不是自己算错了?他不敢相信推算的结果,又推倒重来,同样的结果再次出现,而且危险程度还变大了。他跑到楼道间,拨打房产所管道科的电话,一连摇了三次都没有接通,显然,那个节日值守偷懒了。
事不宜迟!他顾不上饥渴,骑上自行车,直接去找人。
二
苏武一开始是要去找房管所的,后来一想,就算找到那个值班的人也没用,就房管所的那帮人,会耽误事的。事情重大,只有立即上报老城区区公署的最高行政长官,才能得到妥善处置。于是他改变方向,直奔区公署。
区公署院内一片漆黑,只有值班室那里还亮着一点暗黄的灯光。苏武重重地敲了三下门,却没有回响。人都去哪儿了呢?他几乎快要绝望了,打算离开时,又用脚猛踢了一下大门。终于屋里传出声音:“别吵了,我才刚刚要睡下呢!”
他喊叫说:“出事了,我要找区公署领导汇报!”
屋里的声音说:“你瞧现在什么时候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他又猛踢了一下大门,仿佛是在踢屋里装睡的人:“等到明天,死人了,你值班的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一阵静寂之后,屋里传出声音:“要找区长,你到翠湖酒店去,区公署正在那里举行新年晚会。”
几经周折,问过几个路人后,苏武终于找到了翠湖酒店。翠湖酒店是老城区最高档的酒店。酒店的宴会大厅里,灯影闪烁,乐曲缠绵,宴会已经结束,舞会正值高潮。苏武心里装着事,只顾往里面走,却在门口被拦下了。他说:“我是房管所的,有事要找区长。”门卫说:“有事也不行,无关人员不得入内。”他说:“事情紧急,耽误了你负得起责任吗?”嗓门很大,一副急吼吼的样子,非要往里闯。这时,从门内走出一个人,问了情况,就说这个事要请示一下,让他稍等。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出来了,向他招手,他随之进去,跟着来到一个看上去还算年轻的女人面前。女人长相靓丽,气度不凡。“这是我们的区长。”那个人介绍道。美女区长流露出被打扰的不悦:“年轻人,有什么事不能等到明天再说吗?”她显然仍沉浸在晚会的喜庆氛围中。
他觉得自己被误解了,心里一急,就说: “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打扰区长您的。”女区长好像很不耐烦了,冷冷地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苏武看了看左右,见别的人都陶醉在舞步之中,就将危楼的情况、自己的推算和判断向女区长说了一遍,并且建议区公署立刻采取紧急措施。
女区长听了,将信将疑,大概是也意识到事情重大,当场责成区公署城建部的负责人立即核实此事。城建部的那位负责人马上叫来监测技师,让他负责此事,带上苏武,去现场进行调查核实,要求客观严谨。女区长还特别安排了一部专车,派了一名区公署警卫队的警督专程陪同,说是为了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同时还一再交待,不管情况如何都要注意保密,避免走漏风声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苏武突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暗自庆幸这个假日自己选择留下来,还是一个实习生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他们先去房产公司楼管科拿出原始资料,然后赶往聚居楼现场。此时的聚居楼已入梦乡,寂静一片,只有楼道口那只昏残残的夜灯,在夜幕下还在与天上的残月相映照。
他和张师傅仔细查看楼层裂缝,对照原设计图纸,用仪器进行探测,张师傅终于说话了:“小伙子,你的专业学得不赖,能够通过推算发现了这个问题。”苏武心里一喜,暗暗得意自己的发现得到了专家的证实。张师傅又要他爬上楼顶去,让他从墙顶往下落石,这让他大惑不解。张师傅告诉他:“只有测量楼顶与地基的偏离度,才能得出最终的结果!”他佩服张师傅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于是按要求做了一遍。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大楼建造存在严重的偷工减料问题,早应该在五年前进行大修,楼层断裂情况严重,危楼可能在24 小时内倾崩倒塌。
事情过于重大,苏武随张师傅向区长报告现场勘查的情况,告诉她大楼可能很快就会坍塌。区公署连夜开会。苏武提出让张师傅和他列席会议,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大楼楼层断裂程度和倾斜度等准确数据,以利于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列席申请被区长拒绝了,但要求他们原地待命,不要离开。
其实,女区长所说的开会,不过是把她那几个心腹找到一起密谈,商量着该如何应对聚居楼这件事。她怒不可遏地责问:“聚居楼是怎么回事?那个工程是谁搞的?简直是豆腐渣!一定要把那个建造商抓起来,严惩不贷!”这时,有一位心腹低声告诉她,说前几年这栋楼该进行大修了,专项资金已经拨出去了好大的一笔钱,但被挪作他用,她是批准的,且眼下不好说明资金的去向。女区长听了,一时神情凝重,不再作声。她知道那笔专项维修资金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心里也很清楚,聚居楼事关四百多人的生命安全,一旦真的坍塌了,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她能做什么呢?且不说区公署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这四百多人的安置问题,就算是有能力,她也不能动,因为只要有所动作,事情就会暴露,到那时,受严惩的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了。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最后,她咬咬牙,决定铤而走险。
这些事,苏武当然一点都不知道。他和那两个人在一个小会客厅等待下一步的处置任务。这时候已是下半夜,尽管困得两眼睁不开了,但他还是很兴奋,在为自己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服务社会而得意洋洋。
三
吉普车摇晃了一下,苏武恍然醒过来。他感觉自己刚才只是打了个盹。他将目光投向窗外,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车子追着前面的灯光,在崎岖的山路上拐来拐去,一路狂奔。
车里静得出奇。他盯着司机问:“我们这是去哪儿呀?”司机全神贯注,只管开车,不说话。他心里发毛,听说郊县一带的山里常有土匪出没,深更半夜的,要是遇上土匪打劫,绝对是凶多吉少。
“我们这是去哪儿呀?”他又问了一句。
“你说呢?”后座上有人反问,很不耐烦,还有些愠怒。
苏武扭头看向后座,黑暗中看不清楚,但从话音中他认出是那位警督,这才略感心安,却又不由地有些羞愧。他不是不知道,此行是带着任务的,要救人于危难之中。他只是觉得,车行在山路上,有些不对劲。
车后座还坐着技师张师傅,他补上一句:“这个时候了,亏你还睡得着!”
是啊,这个时候,苏武不应该睡的,可他实在是太困了。自从昨晚事发后,他就没有合过眼,刚才扛不住了,就打了个盹。
吉普车终于在一处荒僻地带减慢速度,苏武心里掠过一阵从未有过的紧张与慌乱。他记起来了,会议结束时,几个人匆匆忙忙从会客厅门口经过,脸色冷峻。最后,女区长出来了,单独见了他。女区长说:“小伙子,好样的!辛苦了,你是从北平建筑大学来实习的学生,凭你出色的才学及时发现了隐患,避免酿成重大灾难,我代表区公署衷心感谢你!我们将向你的学校通报你所做的一切,包括你的贡献!此事区公署已做周密安排,将得到妥善解决。你情况熟悉,最后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我们将为你请功!”然后他就被安排上了车,就是那时候他顿觉疲惫袭来,一迷糊就累散了架。
车停稳后,警督先下车,然后一把将苏武也拽下车来,然后一个反手,将苏武扭跪在地上。苏武一下子懵了,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已经有冰凉的枪口顶着自己的后脑勺,这可是索要自己的小命啊!他感到一股颤栗从腹腔升起,瞬间传遍全身,“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苏武话音颤抖,几成哭腔。“对不住了,小兄弟,没有人想为难你,是老天不容情!”警督说。他几乎是喊叫了起来:“我可是立了大功的!是我及时发现了隐患的呀!”。警督冷冷地说:“你要是不立这个大功,也许命不该绝。你把那个烫手山竽从火堆里掏出来,谁接烫谁的手,要命得很!你说该怎么办呢!”苏武稀里糊涂,不知道警督话里说的是什么,但心里很清楚,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自己逃不过这一劫了,便不再说什么,双眼紧闭,只能听天由命。忽然张师傅说话了:“他只是一个吹哨的,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算了吧!小伙子还年轻!”警督大概是动了恻隐之心,迟疑了一下,张师傅又说:“还不快跑!滚得远远的,永远不要回来。”苏武听了,便头也不回地往前跑。才跑几步,身后一声枪响,他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却发现子弹并没有打在自己身上,又爬起来继续逃命,一头钻进山林里去了。
山林里漆黑一片,无路可走。他不顾一切,跌跌撞撞地往前钻,估计已经跑出了几百米,才放慢脚步,喘口气。回望身后,山野死寂,他猜想没有人追上来了。惊魂甫定,突然又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然后很快又陷入一片死寂。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思来想去,最后拍了一下脑袋,好像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所有撞见这个秘密的人都必须死!张技师、警督,还有那个司机,一个都跑不掉!自己只是侥幸捡回了一条小命。
那么,这事是谁干的呢?也许是土匪,或者一个阴谋的勾当……他禁不住胡乱猜想起来。但有一点他根本不会想到,聚居楼那个他不知其为何人的建造商,在另一个地方也已经命丧黄泉。
从树梢顶上望出去,晨星寥寥,天就快要亮了,但树林里好像更加黑暗了,伸手不见五指。有个声音窸窸窣窣,由远而近,到了跟前,稍停片刻后又嗞溜一声迅速离去;头顶的树杈上,突然发出一声哀号,然后是翅膀扑棱棱的声音,飞向远处。苏武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一个人置身于荒山野岭之中,心里非常害怕。不过,他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山里的飞禽走兽,而是执意要置他于死地的那些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是一个是非之地,他只是侥幸地逃脱了,危险依然存在,必须尽快离开这座城市。
天色微明,苏武在晨雾中辨认方向,寻找道路,他要尽快回到城里,坐上火车,离开这个城市,一刻都不能延缓。城市就在山外,成片的建筑依稀可辨,他估计徒步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在他打算下山时,突然又多了个心眼:他们会不会发现死者当中少了一个人呢?说不定他们已经布下大网,只等自己上钩呢!还是等等再说吧。
一直等到下晌时分,苏武才斗胆拐上山路,朝着城里的方向,悄然前行。
四
苏武还算运气好。他顺利地到达火车站,而且很快地买到了一张车票。现在,他已经坐到车厢里的座位上。他把帽子压低,两手在胸前抱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却又忍不住偷看车厢,又看看窗外。窗外,一位妇女从衣兜里掏出几个鸡蛋,塞到一个男人的手里;一个少妇抱着小孩,另一只手里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有个列车员顺手帮了她一下。旅客们在列车员的引导下紧张而有序地上车,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他松了口气,觉得自己应该没有被跟踪追捕。再过几分钟,火车就要启程,到那时,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在火车就要开动的那一刻,他又想起老城区那幢危楼,想起那个排骨男和胖女人,想起那个嘴唇猩红的妖娆女人,想起煤罐“哐当”响起时从门帘后面探出来的一张张惊慌的脸……四百多人啊,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楼一塌,可就全都没了。他又想起张师傅,因为他的一句话,自己得以侥幸逃脱,也许这是天意,要留下自己去拯救危楼里的人。
苏武终于下了火车,他不能见死不救!
时值黄昏,路灯初亮。苏武饥肠辘辘,迈着沉重的脚步,匆匆的又来到那聚居楼前。望着楼上的灯火,他恍若隔世,从昨天到现在,短短的一天,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这时是吃晚饭的时间。楼道里回响着锅碗瓢盆交响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酸甜苦辣的热气,聚居楼里的人们与往常一样,送走了一天的劳累,迎来了黄昏时的家常欢乐,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家人危在旦夕。
苏武冲上四楼,径直去到昨日那个报障人家门前。这幢大楼里他一个人都不认识,唯一打过交道的就是昨天那个报障的人家,他的话排骨男和胖女人应该相信,他想通过排骨男和胖女人的配合去通知各家各户,效果会更好一些。伸手要敲门时,一眼瞥见门上贴着钟馗,凶神恶煞的样子,十分恐怖。昨晚进门时好像没注意到,此刻蓦地一见,顿感一股腾腾杀气袭来。他迟疑了一下,思量着应对的辞令,终于还是敲了门。半晌,门才开了,挤出来瘦排骨的一张长脸,他脸上先是装出笑容,待看清是苏武,铺展的笑意瞬间消散,说:“你不是说今天要来修的吗?怎么这个时候才来?你们真的是不管老百姓的死话!”看上去不像是喝醉了酒,却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凶。
苏武没时间多作解释,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是来修水管的。事情已经非常明了,不仅仅是你们家水管爆裂的问题,而是整个大楼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大楼很快就要坍塌了!事情紧急,请你们相信我,一起去通知各家各户马上撤离。”
排骨男脸色陡然一变,显然是误解了苏武的意思:“这不可能!好好的大楼怎么会突然就倒塌呢?你一个修水管的究竟想干什么?想蒙我吗?别再无中生有、制造混乱了!”然后不由分说地把苏武轰出门外。
苏武很失望,觉得多说也没用,不想再纠缠就退了出来。斜对面有户人家,屋里声音嘈杂,看来人不少。苏武走过去,斗胆敲了一下门,屋里忽然静下来,就像音响断了电源,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又敲了一下。这时,大门开出一条缝,他看过去,原来是几个人正在玩麻将,显然是疲惫恋战,输赢都写在脸上。边上还围站着几个看热闹的,所有的人都往他这边看过来。开门的人探出半个脑袋,问他:“你找哪个?”苏武心里一急,冲着屋里就喊:“你们赶快跑吧!楼就要塌了,再玩就没命了!”屋里的人一时都不做声,但很快就有个声音说:“神经病!”又有一个声音说:“楼要塌了吗?是不是你娘告诉你的?”然后是哄堂大笑,接着又继续忙着搓麻将,没人再搭理他。赌博有个坏习惯,会让人上瘾,赢家常常会趁势追击,连连翻庄,赢了还想赢。输者呢也不服气,不相信手气会永远差下去,还是坚持磨,磨劲上来,就是想着把输出去的钱再赢回来,但大多是越赌越输,脚下的路是进深渊,拔不开也走不掉,根本没有退路,久而久之,赌资输没了,就欠着场上的赖着场后的。苏武这才想起,应该跟他们作些解释,可门很快就“砰”的一声就关上了,不但不给他机会,还把他的额头撞出一个大包。
苏武没办法,只好走开,想想,又去敲另外一家。开门的是一个蓄着胡须的男人,一边开门一边还在怒气冲冲:“你肯定不用心,这么简单的题怎么会错?”矮凳上坐着一个孩子,低下头不敢吱声。男人把着大门,训斥了孩子,这才转过身来问他:“有事吗?”他说:“大事,是关于这幢大楼的事。这幢大楼马上就要……”还没等他说完,男人就挥挥手,说:“我现在没时间听你说这个。大楼的事,楼下有物业,你找他们说去。”说着把门也关上了。苏武觉得这时候不再去说什么,否则,会让蓄着胡须的男人心生火气迁怒到孩子。
苏武下了三楼,见楼道中间有户人家有些热闹,话赶话随灯光从大门里淌出来,他直奔过去,却是一对夫妇在吵架。女的说:“你再这样,我就去跳楼了!”男的说:“要跳你去跳呀!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一看,很失望,心想,算了,他们连死的心都有了,跟他们说大楼的事还有什么用!苏武想起自己的父亲母亲也经常没有来由地吵,他常常闹不清没吵的时候,父亲偷偷用私房钱为母亲买了商业保险,仿佛准备为母亲去死,但没有理由或起因很勉强吵起来时,双方都会出口要让对方去死。
苏武一时很绝望,却又心有不甘,他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发疯似的跑来跑去,像酒店的叫醒服务一样,挨家挨户地敲门,一边敲一边高声喊叫:“大楼就要倒塌了,赶快逃命呀!”“赶快逃命呀!大楼就要倒塌了!”敲门声、喊叫声惊动了整幢大楼,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他继续喊叫着,恳求大家赶快下楼,可还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这时,那个有着猩红嘴唇的妖娆女人闪出来,苏武见了,一把拽住她,要她赶紧逃命。猩红嘴唇问:“大楼真的马上就要倒塌了吗?”他说:“我没有乱说,我们测量过的!”猩红嘴唇说:“昨天半夜里围着大楼偷偷摸摸爬上爬下的那几个人就是你们吗?”他说:“对,就是我们那几个人。你难道没看见大楼有一条大裂缝吗?再不跑就没命了!”猩红嘴唇“呀”的尖叫一声,然后提起裙摆没命地往楼下跑去。猩红嘴唇一跑,有几个胆小的人也慌慌张张地跟着跑下去;然后,那些将信将疑的人也一边看着他一边开始往楼下跑。
楼前的人越聚越多。一阵寒风吹过,有人着凉了,连连打着喷嚏;有个老人弓着腰一阵又一阵地咳嗽,像是眼看就要断气似的;还有个小孩仿佛被人故意掐了一下,厉声哭叫起来。人们眼瞅着大楼,仿佛在等待着一个结果,一个把他们赶出家门、在寒风中担惊受怕的结果。
苏武绕到大楼背面去,墙体上那道裂缝触目惊心,仿佛一头巨兽张着血盆大口,只一口顷刻就会将大楼吞没了。可是,大楼虽然看上去摇摇欲坠,却始终没有坍塌。
他又转回楼前。这时,众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楼要塌了,这么大的事,应该是区公署出面处置的,怎么会由一个陌生人来通知?有人说,这件事十有八九是假的,很可能是恶作剧。有人说,那个年轻人就是个疯子。忽然,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大喊一声:“我们都是傻子,怎么被那个该死的疯子骗了?!”
于是人群移动脚步,涌向苏武,终于不知是谁一下子把他推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