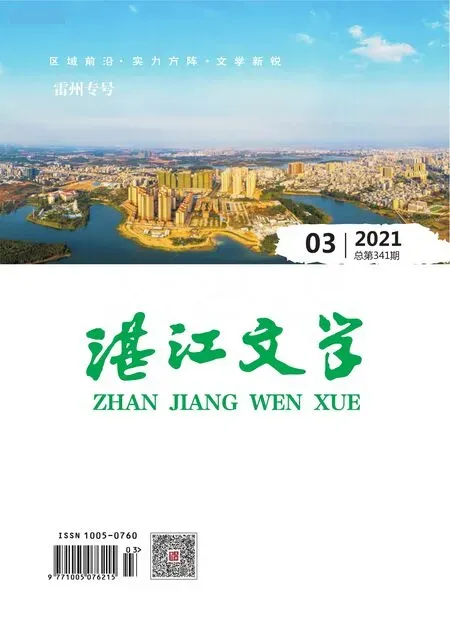木麻黄
周文兴
我的故乡是北部湾畔一个名叫港彩的村庄。
我曾多次写过我的故乡,怕久之不写慢慢会忘记,从而导致故乡也把我忘记了,这不是我能承受的。
故乡没有高山,只有矮矮的山坡。村庄临坡靠海,山坡与海边长满了木麻黄,一棵连着一棵,一片连着一片,手拉手,肩并肩,围成一个绿色的天然鸟巢。它们像我的乡亲,挺着最直的腰干,披着最柔的秀发,黝黑粗拙,憨厚素朴,本分地守着村庄,守着炊烟,守着早出晚归的风帆。
寄居在城市里的我,被繁华喂养得不想离开,只能在远方想着我的村庄,想着坚守村庄的乡亲,以及村前村后的木麻黄。木麻黄,那令我牵肠挂肚的木麻黄啊,经常在梦中被故乡的风吹得哗哗响,仿佛在轻唤着我的乳名。
我是木麻黄养大的,也是木麻黄教大的。
现在的农村,很多人家都是使用煤气煮饭了。我小时的故乡,烧水煮饭都是用木柴,木柴基本上都是木麻黄。那时候,每家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木麻黄树林,空余时间就去剔除多余的枝条,既能让树木得到更好的生长,又能把砍下来的枝条带回家当柴火。
村庄靠海,多台风,每次都有树被掀翻折断,断枝断叶的更多,乡亲们总是等台风过后去捡回家。小枝用手折断即可,稍大一点的用刀砍,如再大的需用锯子锯断,每段约60厘米长,然后用斧头劈开成小条状,晒干当柴火。村庄是半农半渔的,木麻黄的材质坚硬,如树干比较大,可留下来做家具,若经过海水浸渍或防虫防腐处理,可用来制作船底板。不管是化为灰烬,还是家具船板,木麻黄只不过换了一种活着的方式而已,就像故去的乡亲,隐身于山坡的深处,陪着村庄,守望着子子孙孙。
我第一次跟父母去捡树枝时,看到有的木麻黄被连根拔起,有的拦腰折断,露出不屈的白骨,倒挂在地上。但不论怎样,它们的腰干依然直挺着。从那时起,木麻黄就在我灵魂里植了根,大小不一的根系成了我的血管,通直的树干硬化我的骨头,时刻矫正我的腰骨,不至于畏惧风雨,卑躬屈膝。
木麻黄藏着火焰,藏着炊烟,喂养着村庄,其叶棒状圆柱形,纤细柔软,易燃,是每家灶台必不可少的。母亲煮饭时,先抓一把干树叶放到灶心,上面放小树枝,火柴一点,树叶吱吱吱就着火了,一会小树枝也跟着噼里啪啦地唱起歌来,大枝条需待火烧旺后才能添加。农村的灶台,都是几个灶连在一起,烧水、煮饭、炒菜一起来,只要一 个灶台有火,其他灶台就可以引火了。 不久,饭香开始弥漫,温饱着饥饿的日 子。如遇到番薯收获的季节,母亲心情 好时会很大方的拿出几个小番薯埋在火 炭下面,那熟透的香味,让整个村庄都 流下了口水。我每年春节都带儿子回老 家过年,小小年纪的他竟对烧柴煮饭饶 有兴趣,总喜欢搬一小凳子坐在奶奶身 边,学着添柴加火,有模有样的,逗得 我母亲眉欢眼笑,说:“我这个孙子今 后饿不到啰!”母亲没读过书,不懂得 大道理,但懂得善待生命。她认为一个 人只要能耐下心来给自己及家人煮饭, 就差不到哪里去。民以食为天嘛,能吃 饱穿暖就知足了。
当灶台边的树叶烧得所剩无几时, 就该我们小孩子出力了。不管是海边, 还是山坡,哪里的木麻黄树叶多,哪里 刚耙过可能要等几天,我们了如指掌。 一到周末,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约好,各 自带上一把铁耙子及两个小麻袋屁颠屁 颠就去了。我最喜欢去海边的树林耙树 叶,耙子在树林里穿梭,畅通无阻,像 将军般召集着涣散的士兵。耙子过处, 一条条树叶被收拢,卷起,滑过的痕 迹,折射出沙子洁白无瑕的人生。
树叶是耙不完的,风一吹,刚耙过 的地方,又有树叶簌簌而下,就像我的 乡亲,有新生,有老去,新旧替代,生 生不息。
麻袋装满,就可以偷闲玩我们百玩 不厌的“打仗”游戏了。我们人不多, 分为两队,每队三四人,规则是谁被对 方发现谁先“死”,全队“死光”,就 输了。赢的一方是有战利品的,那就是 下次耙树叶时可优先选一块树叶多的地 方。这是一条大家都喜欢的规则。也许是游击队电影看多了,游戏前我们每人都会折几支柔软的木麻黄枝条编织成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既能遮阳,也便于隐藏不易被别人发现,然后再寻机伏击对方。游戏中,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如那位的脚底不小心被仙人掌刺到(儿时穷,鞋舍不得穿,赤脚玩),“啊”的一声大叫,其队友听到,知道坏事,心急欲制止,跟着叫一声:“小声一点啊!”全被对方发现而“死”。更有一次,小胖子二狗找到一个偏僻而隐蔽的地方,藏着躲着不知不觉地趴在沙子上睡着了,害得我们找了半个多小时,此事一度成为我们村庄的头条新闻。
港彩小学位于村西,离海边180多米。校园内没有其他树,仅有五棵盘虬卧龙、郁郁葱葱的凤凰木,每年夏天,满树的火焰,拼命地燃烧,欲烧掉贫穷的日子,烧红我们的锦绣前程。校园外,却是密密麻麻的木麻黄,像卫士一样守着村庄,护着校园里小小的花朵。我记得,二年级上学期,我们几个调皮的学生经常逃课去海里抓螃蟹,然后到木麻黄树林里捡干枝叶,掏出从家里“偷”来的火柴,直接烤螃蟹吃。那浓郁的香味,现在想想还直咽口水。有一次我们刚从海边溜回来,就被我们班主任温国伟老师看见了。他瞪了我们一眼就出了校门,我们以为没事,谁知道仅几分钟温老师就拿着一支木麻黄枝条转回来,叫我们到教室外面纵向列队,把树枝给最后一个同学,要求按次序后面一个打前面一个的小腿,打完一轮就180度后转,反过来打,每人十次,不能假打,否则重来,美其名曰:接力赛。最后他狠狠地丢下一句:“谁今后还敢逃课,看我不收拾你!”那时候,社会上不存在不允许体罚学生的论调,反而家长还希望老师把他们的孩子管严一 点,怎打怎罚请自便,“严师出高徒” 嘛。温老师用他独特的惩罚方式,让我 们这帮调皮鬼“自相残杀”。
我们的小学是村小学,学生都是本 村的。温国伟老师也是我们村的,他家 就在我家背后50米处。故我们几个在学 校被惩罚的事,风轻轻一吹,我母亲就 知道了。中午一回到家,母亲也是抓起 一木麻黄枝条狠狠地抽向我的小腿,咬 牙切齿:“叫你不读书!不想读就不要 读了,回家放牛去!”这让本来就痛的 小腿痛上加痛。我忍着痛跑离了家,跑 到木麻黄树林,对着树一边脚踢手折, 一边骂:“叫你打我!叫你打我!”直 到累了,才靠在一棵树干上,久久地凝 望着头顶上柔软的枝条。它正努力地伸 展着,为我撑出一片阴凉,在海风的吹 拂下,不停地洗擦着蓝天白云,梳理着 我的心事。我渐渐地平静下来,目光随 着枝条变软变柔,忘了痛,忘了老师及 母亲的打骂。我突然发现,树越大,它 遮阴的范围也越大;越高,把人的目光 抬得也越高,而它头顶上的天空也愈远 愈蓝。
高考前,我报考的志愿是当时比较 热门的“微机”,学校录取时却把我调 配到“园林”专业,阴差阳错成为一名 “护花使者”,让我与木麻黄的缘越结 越深。我从书本上了解到,木麻黄属于 常绿乔木,原产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 屿,适生于海岸的疏松沙地,是中国南 方滨海防风固沙的优良树种,被称为 “岸边卫士”。怪不得每次台风中,村 庄安然无恙,木麻黄却少腿断臂,原来 都是它舍命护着我们。
关于木麻黄防风固沙的作用,《东 山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东山环海多沙,解放初,多个村庄被风沙埋没,当地人也曾经想过种树固沙,相思、苦楝、黄桦……十几种树轮种了个遍,无一成活。1955年,谷文昌担任东山第三任县委书记,为了找到合适的海防林种,他与技术人员翻尽资料,大海寻踪。听说广东电白县成功种活了一种名为木麻黄的树,谷文昌立即派人前去取回苗种。1958年一开春,一连4天,数十万株木麻黄遍植全岛,但只有白埕村有9株还活着。希望,就是从这点点绿色开始,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9株木麻黄,变成了20亩丰产试验林,又海潮般向各村漫去……从此,东山美丽化蝶,也留下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
学园林,需识树。学校的后山上有几棵20米多高的木麻黄,花卉老师带我们去认识树木时,一般先问我们认不认识,然后再慢慢解说。老师一路指着树,我都不认识,只有听的份。等他指到木麻黄时,我精神一振,第一个响亮回答:“木麻黄!”老师惊诧地望了我一眼:“不错啊!这都认识。”我忙说:“这是我们村的‘村树’!”
木麻黄是不是我们村的“村树”,我不清楚。因村里没村志,无法考究。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必要去求证的,自心认同即可。好比一个一辈子陪着你、护着你的人,不管与你有没有血缘关系,他(她)就是你的至亲,都值得你去珍惜,疼爱。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深圳。我以为从此远离木麻黄了。但令我惊喜的是,除了市中心少种以外,沿海岸边却有大量的木麻黄。我家附近的宝安海滨公园就有一大片,说着老家的雷州方言,等待着我的到来,让我倍感亲切。我一有空就带儿子去看那片木麻黄,儿子像我 小时一样喜欢在树林里穿梭,嬉戏,而 我则坐在树下,靠着树干,痴痴地望着 随风而舞的树叶,它们仿佛在晃着我长 不大的童年。
我伸出一只手,五指弯成耙子,在 地上收拢一小撮树叶,点燃。望着小小 的火花及丝丝的轻烟,我不禁热泪盈 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