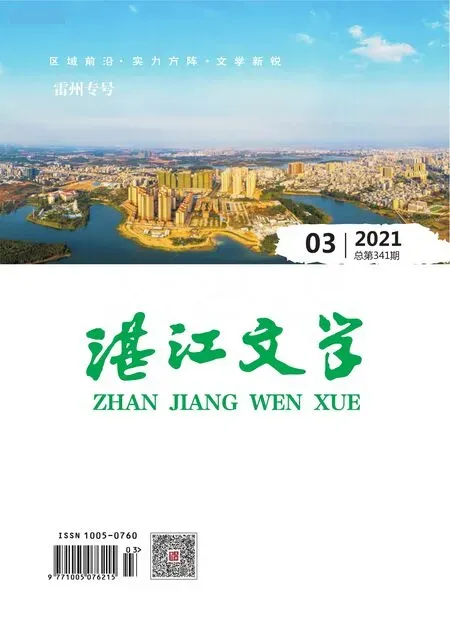母 亲
邓春贵
我童年时,雷州半岛农村处于从“生产队”向“包产到户”的转变中。“土改”虽吹响号角,但步子小、出路少,农村仍处于封闭、愚昧和落后的状态,农民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那时,家里很穷,父母长年累月泡在田里,为解决全家人的“温饱”而忙得焦头烂额。母亲年轻而勤劳,忙里忙外,少有一刻的闲暇。我帮不上忙,只能目睹她艰辛地劳作:担子堆如山,扁担弯如弓,母亲驼背负重,步履蹒跚地挑担子。回家卸担后,母亲边抹汗,边微笑地从稻草、番薯或木柴等担子里掏出地瓜、甘蔗或野果,递给我,笑道:“娃,肚子饿吗?给你的,好好吃的!”
偶尔到镇上赶集,母亲总会买回小许糖果或饼干。这时,我接过糖果,准会高兴地跳起来。——那时代“能吃饱”已属不易,零食是何其令人惊喜的奢侈!
岁月虽艰难,母爱却能暖心。我小时候的生日,母亲就办得很温馨,很难忘。那样的日子,母亲哄我起床,端来两个对合的碗。在我惊讶的当儿,她揭开上面的碗:蒸气散后,米饭的上端,就现出两个大鸡蛋。鸡蛋很显目、很壮美,像雪山巅峰顶的大岩石。
这时,母亲抱着我,慈祥地笑。她一边剥鸡蛋壳,一边快乐地对我说:“娃,快吃吧,长大了好去念书。”我品着鸡蛋的美味,心里却总有点糊涂:母亲从哪得来鸡蛋?家没余粮养鸡,市镇远在十里。
我七岁的一天,晨光明媚,和风拂面。母亲比往年都要高兴,她一大早起来张罗饭菜,仿似农事大丰收。守我吃完生日饭后,母亲甜笑起来,说:“娃,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哦!”我侧转头,只见母亲怀里多了一个新书包:麻布料,手工编织,针线粗细均匀,缝的甚厚实。阳光下,书包散发着金红色的光。母亲的脸,被光线映得十分红润,闪耀着喜人的神采。母亲把书包递给我,轻抚我的头,欢声说:“娃,你长大了!到秋季,就要上学了。你要好好念书啊!”
“你要好好念书啊!”这简单的叮嘱,仿佛种子落进入的心田:教我勤奋、教我坚韧。在背起书包的漫长岁月中,我终于十年如一日地用功,昼夜不敢懈怠,用心血浇灌这粒“好好读书”的种子,期待它在现实中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工作,母亲在故土变老。他乡异客十年后,我忍不住地思念母亲,于是便调回故土,叶落于母校。这样离母亲近些,心里甚踏实。
然而,母亲仍留守乡村,说住不惯城市,离不开土地:“只有闻着田地和庄稼的气味,心里才坦然!”母亲有空就上城看我一家,带一些新鲜的野果、地瓜或甘蔗,一见到孙女,便慈爱地塞食物,说:“奶奶家的特产呢,好吃得很!”女儿接过母亲的特产,倚在老人家的怀里,开心地笑。
这样的时刻,我默默地望着老母亲花白的鬓发,心潮便起伏难平:岁月何其无情地流逝啊。幸运的是,母亲的爱,一路温暖地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