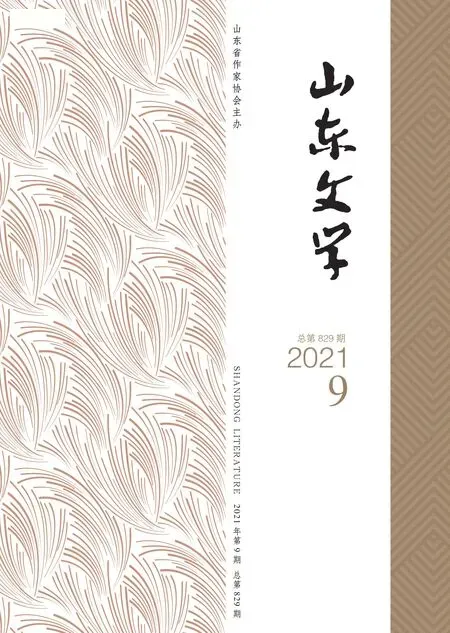心 水
李 岩
一
五天了,李心水从来没有离开家这么长时间。困扰她的事情实在太多,她不想被埋在生活这块沼泽地里。学校一团糟,已经够让她烦心了。再摊上个这样的丈夫。她像个溺水者,在最后一刻,只能眼睁睁看着屋里的光刺入眼中,却无能为力。那天晚上,她一夜未眠。一直躺在床上等着窗边亮起第一道光。简单拿了些洗漱用品,带了几身换洗衣服。临出门之前,她打开家里的衣橱,转开锁,拿了一张银行卡。李心水确定自己没有刻意放轻动作,她记得自己冲马桶的声音,开橱门的咣当声,她一度怀疑黄天是故意的。至少在那个时候,应该挽留她的。她还记得自己去看婴儿床上的蝈蝈。睡得很甜,柔嫩的皮肤上被一层柔软的光照着,长长的睫毛像扇子样覆盖下来。她强迫自己不去看他,再看下去就走不了了。
谁都想不到她就在离家不到500米的宾馆里。李心水一直把那张银行卡贴身藏在牛仔裤口袋里。她要经常摸一摸那个硬硬的卡片,仿佛那是她的定心丸,摸一摸就心安了。洗完澡躺在床上,她翻开手机,打开微信。里面的朋友就几十个,大多数还是同事。她上下翻阅着,像个流浪汉在一片杂草中挑选出一根稷子。在一个叫蚊子的微信名前,她停止了滑动。这个曾经的发小,现在已经是一个培训机构的校长了。她拨通了语音聊天。
“干嘛呢?”心水已经有好久没有联系她了。
“我还能干啥啊。都是一堆破事。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那边明显的出乎意料。
“没事,就是想你了。聊聊天。你最近怎样啊?”心水极力打破这种生涩感。
“我啊。还是老样子。每天几个校区的课程安排,每个员工打卡,都要盯着。感觉人到中年了,精力明显不足啊。真羡慕你!”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气声。
“羡慕我?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心水倒有些心虚。
“你啊,至少有个疼你的老公啊。再不济有那么可爱的孩子。你都不知道,每次看见你朋友圈晒的娃,我都羡慕得要命。”蚊子接着说,“我怀疑再过两年,还生不生得出?现在我就想去找个捐精的,直接整个娃算了。找个情投意合的,我是不指望了,能养个聪明可爱的娃,我倒是乐意的。”
心水没想到,自己的这种状态还是别人羡慕的呢。没生过孩子的人,都不明白养个孩子的辛苦。什么都得操心,再加上个不省心的丈夫,这日子就像个糨糊,越搅越浓稠,都快硬掉了。
“算了,不提这些事了。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一起爬树的那次。”心水说。
“哎呀,当然记得啦。那次一个小鸟从树上掉下来。柔软得要命,张着嘴巴像是要吃的。我们挖了好多虫子给它吃了,后来,还是你爬到树上给它送回家的。那时候,我就羡慕你,什么都难不倒你。”蚊子几乎要滔滔不绝了。
她们两个聊起小时候的话题,几乎没个完。快乐的时光在她们的嘴巴里又重现了一次。现实的时间过得也很快。直到半夜三点,不得不睡觉了,她们才终止了这次谈话。
早晨起床,李心水顶个熊猫眼进了教室。最近的课程比较紧张,就要期中考试了。她带的两个班,语文成绩都不怎么样。这也不能怪她。谁还没有拼命的时候啊。想当年,她所带的班级每次都考第一,拉开第二名至少10分以上。可现在有孩子了,她对待时间像农夫对待木材一样,劈成一条一条的,希望能发挥最大的效力。上次她看见年轻的小姑娘上的一节示范课,那PPT,图片做的是美轮美奂,再加上富有磁性的嗓音。整个一节课下来,就是美的享受。
课后,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想了半天。终于觍下脸来,去请教那姑娘。那姑娘在电脑上快速地点来点去,只见她的头像拨浪鼓一样摇来晃去。至今那个PPT还在她电脑桌面上,可是她只打开过一次。
最近,她带着孩子们复习所学的四个单元内容。她转身在黑板上板书,底下就开始像蜜蜂一样嗡嗡声不断。她没有转身,继续写字。她知道是坐在墙角边上那个叫孙飞的孩子在讲话。不一会儿,这种嗡嗡声在不断蔓延,像是有声的瘟疫一样,到处都是孩子的说话声。
血液开始上涌,脑袋有些发涨。紧握着粉笔的那只手,加大了力气。她明显感觉到指甲缝里塞满了粉笔的细末。她转过身,眼神里喷射出火龙般的恼怒。她觉得自己已经明显感觉身体里那只狮子复活了。心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放在平时,她会睁只眼闭只眼,就这么过去了。可今天她就是要较真一回。
可孩子们对她压根儿就不在意。嘴巴里还在不停地一翕一合。她看见那个叫孙飞的孩子,一边吃着干脆面,一边在说话。
这哪里还是课堂。真的触碰到她的底线了。人家说“擒贼先擒王”,今天她就要看看这个混世小魔王到底耍什么花样。
她快速走到孙飞面前,问他,你吃什么呢?孙飞一时的笑容还僵在脸上,嘴巴里咕哝着不知道说的什么,干脆面的碎屑还粘在他脸上。他身上的衣服太大了,有一只袖子卷起来,还有一只就那样拖着,真像是舞台上唱戏的小旦。领口处被磨得发亮。头发竖立着,像个小刺猬。
她翻开孙飞的书,上面一片空白。课上讲的重点知识,他一个字都没有写。她按捺住心中的那团火,继续提问,你把李白的《古朗月行》背一下。
孙飞嘴巴迅速地咀嚼,同时发出嗡嗡的声音。终于那一大块干脆面被他吞进肚子里了。同时蹦出了两个字:不会!
心水把书往他的课桌上一放,脸涨得通红。喉咙里像被打了结一样,绞了起来。那种无力感又来了,她所熟知的那个东西,慢慢地离她而去,像是坐在一段脱轨的火车上,她也不知道生活会带她到哪里去。
心水站了一会儿,看着孙飞的脸,他没有一丝愧疚,眼神中还带着挑衅的意味。李心水拿出最后一招,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
二
晚饭后,心水不愿意回宾馆。她走在灯火光亮的马路上。这条街她不知走了多少趟了。闭着眼她都知道前面一家叫“点点母婴坊”,在门口徘徊了一阵,最终她还是进去了。
一件一件的小衣服质地柔软,她翻来看去,看中一件带有刺绣的连体裤,上面的花纹是蓝底红花,有些像飞鸟的图腾,她又翻开吊牌,100%棉,就这件了。
“老板,这件怎么卖的?”
老板头都没抬:“480元。”
心水有些犹豫,又翻开吊牌看了下:“就是普通的棉。怎么这么贵啊?”
老板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你看,这个花纹,这个手工,是人家一针一线绣上去的。”
心水抖开裤子,翻过去。“老板,你看,这个刺绣明明是机器绣的,不是手工的。”
“机器是不是需要人来操作呢。”
“是。”
“那不就是了,那不是手工的是什么?”
“这也算吗?”
“一看你这样子,就是个教师,对不对,什么都在抠字眼。”老板失去耐心,“这件最少450元。要买就买,不买就算,我们不强求。”
白天的气还没顺呢,怎么一个卖衣服的也瞧不起人呢。心水狠狠心,咬咬牙,拿出微信,扫了二维码。想起白天孙飞的破衣烂衫,也不知道孙飞的妈是怎么当的?怎么让自己的孩子邋遢成小乞丐?她拿着衣服看来看去,柔软顺滑,像是蝈蝈的柔嫩的皮肤,至少我不能让我的蝈蝈穿成那样!
回到宾馆,心水拿着小衣服,想象着蝈蝈穿在身上的样子。心里竟有些美滋滋的。说起来,这么多天没见到蝈蝈了,也不知道他闹了没有,找妈妈了没?
半夜,她被一个梦吓醒了,一看才3点半。她摸了一把眼睛,都是泪。她记得自己给蝈蝈穿上了新买的衣服,蝈蝈歪歪扭扭地走向她,突然一下,地面裂开了一道缝,蝈蝈一下子不见了,她向下一看,尽是黑洞,从洞里传来“妈妈,妈妈……”的喊声,她立马跟着跳下去,可是她怎么跳,脚都在地面上。那种无力感又向她袭来,她盯着天花板,眼神又涣散了。
反正也是睡不着了。她打开灯,走到写字台边,坐了下来。前面是一面大镜子。看着镜子中凌乱的自己,她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她。她还记得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那时的嘴角是上扬的。她还记得第一次和黄天约会的模样。她穿着背带裙,扎着马尾辫,一走一蹦的样子,青春又活力。现在再看看自己干枯发黄、还夹杂着白色的头发。脸上的斑点,自从怀孕后,就再也没有消退下去。还有裹在睡衣下的身体,已经松弛、变形。这哪里还是当年的自己。
她看着桌上躺着一支笔,还有一叠纸。纸的上方还印着这个宾馆的名字。她拿起笔来,开头写着,“亲爱的蝈蝈,我是妈妈……”一开始写得不顺,错了好些字。她想着长大以后,不能让蝈蝈也笑话她,撕了写,写了撕。大概早上五点一刻,她终于把那封信写完了。她站起身来,把信放在那条裤子的包装袋里。
入秋了,清晨的风吹在身上,还有些凉意。心水把毛衣往身上裹了裹,走进校园。今天她特意来早一些,本来早自习不是她的,她主动提出与英语老师调课。
从办公室拿着一沓课本教参,要爬上三层台阶,还需要穿过长长的走廊。今天心水提前十分钟从办公室出发,她想着到达教室还可以让孩子们多读五分钟的书。经过一间间教室,教室里还没有老师,很多学生还没有进入状态,有的在皮闹,有的在吃早饭,还有两个靠近窗户的女生在扎辫子。当她快走到自己班级的时候,她特意放慢了脚步。她想看看自己的学生,在没有老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她靠在门边上,先听一听,教室里很安静,一开始她以为没有人呢。可接下来有一个人似乎在讲台上说话。她每个字都能听得很清楚。
“你们不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吗?”教室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看看你们一个个的样子,坐没有坐样,站没有站相。”教室里还是很安静。
“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吃东西呢?”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同学们,你们说应不应该向孙飞同学学习啊?”这话昨天的课堂里,心水好像说过。
“应该!”底下似乎异口同声了。接着是一阵爆笑。
李心水怔住了,昨天在课堂上,她教训学生的话语,现在听上去那么刺耳。她感觉周围的风都向她聚拢来,在她身上形成漩涡,渗进肌骨,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她深吸了一口气,又往教室门口挪了一步。突然有个男孩走了出来,看样子是急着上厕所。经过她的时候,放缓了脚步,却并没有停下来。
“李老师好!”男孩大声问好,好像离她很远似的。
教室里的说笑声一下凝固了,像是用一张无形的网给罩住了,收上口封存起来。接着,教室里的嗡嗡声停止了,不知是谁起的头,清脆的朗朗读书声蔓延开来。
心水并没有进教室,转身站在栏杆边。灰白色的絮状云朵大块地浮在空中,像是翻倒的牛奶被什么人用脚踩脏了。远处的红色橡胶跑道,覆着一层白霜,竟有些冷清的味道。路边的几盏昏黄的灯,孤独地亮着,像是维护着最后一丝尊严。
三
终于熬到了放学。心水的心情糟透了。上了公交,她选择了后排靠窗的位置。她把头耷拉在弯曲的手臂上,绿化带两边的树木越来越细,花草越来越鲜艳。上车的人渐渐多起来。她看见一对小情侣,两个人互相谦让着一个座位。一看就是刚恋爱不久,还处于新鲜期。两个人都想展示最好的一面。可是生活的模样,不就是真实吗?
想当初,自己的脸上长了一种“扁平疣”的病毒,那种“疣”凸出皮肤表面,会顺着你的抓痕生长,颜色也由浅入深,最后整个脸上都长满了这种“疣”。可是那个时候的黄天并没有嫌弃她,带她去看了很多医生。那时候,她一度以为自己将要毁容。经历了最不堪的那一段,她毅然决定嫁给黄天。按说,她并没有那么爱黄天。感动,对,就是感动。对于心水来说,那段时间,她被自己想象出来的一种不离不弃的情感所诱惑。就这样,她谢绝了所有人的建议,奔向了自己创设的幸福。
汽车的颠簸,窗外景色的变换,让她有种时光剥离感。一个急刹车,她的身体猛得向前倾倒,“啊”地发生一声尖叫。是一个小学生乱闯马路,幸亏司机反应快,避免了一场交通事故。
“不要命啦!”司机愤愤不平。
“小鬼头的家长呢?死掉啦。”司机望着孩子奔跑的背影,骂了一句。
心水重新坐好。她理了理头发。外面站台上拥满了人。后门一开,三三两两的人走下去。前门打开,一团人围上来,向车上挤。为了生活奔波的人,都是这样。每个家就像是一个临时避难所,在外面的所有委屈、痛苦、错误,回到那个火柴盒一样的家里,都可以统统放下,用一种微弱的叫做亲情的东西去化解。可怜又可悲的人啊。
车门关闭,车子缓缓启动,心水透过站台,向后看去,那个玻璃窗上,贴着万圣节快乐的字样,旁边还有一个龇牙咧嘴的大南瓜。那是一家茶座,没结婚前,他们俩经常去约会的地方。她记得坐在靠窗边第三个位置是黄天最喜欢的。她不由自主地看着那个位置,那里还真有个人坐在那里。那个头发,也是自来卷。特别是后脑勺弯曲的幅度,跟黄天的一样,那个侧脸,也跟黄天一样,高高的鼻梁,从侧面看特别挺拔。那个男孩的对面,是一位打扮时髦的女性,长长的瀑布一样的直发,衬得她特别的娇小。白皙的皮肤,闪闪发光,饱满的额头,高高的山根,还有那富有弹性的苹果肌,标准的美人坯子。
她好像突然悟到了什么。站起身来朝后门走去。她连三赶四地按响电铃,汽车又一个急刹车。
“慌什么,刚刚做什么。车开了,要下车。”司机的声音很大,充斥着整个车厢。
心水根本不想说任何话。她急于逃脱这个满载车厢的车。她跳过花丛,越过绿化带。她不确定自己是否看花了眼,可能是昨晚没睡好,也可能是今天生气,脑回路不够清晰。总之,她在找一切借口,希望那不是真的。
快了,快到了。她就想确定一下。看一下就走。如果是真的,她就可以走得更安心了。对于她来说,这也许更能帮助她下定决心。
她感觉到自己有些紧张。或许又不是真的。还有几步就到了。如果是真的,被她当场抓住,她会怎样呢?该骂男人还是女人呢?女人可恨,看着那媚态,就不是个好东西。男人更可恨,转眼就忘了,薄情寡意,最是男人心。
整个神经绷起来了,通过脚底的摩擦,直传到心底。手指头有些僵硬,有些握不住了。靠窗边第三个位置,她来到了靠窗边的玻璃外。
空的,没有人。她记得刚刚的位置上,有一个很像黄天的人,还有一个女孩,怎么一转眼,人就不见了。她推开门,楼上楼下又转了一圈,还是没有人。
难不成真的是自己看花眼了?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长发女孩从卫生间走出来。看见心水的时候,愣了下。
心水循着她的眼神。也看着她。似曾相识的感觉。
“心水——”女孩先打了声招呼。
“你是——”李心水有些不敢确定。
“是我啊。我们昨天晚上还通话来着。”女孩很热情。
“蚊子?蚊子……”心水惊叫起来,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蚊子重新找了个座位,拉着心水坐下来。在等咖啡的时候,心水还是忍不住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出现那个男人的身影。心水装作不经意间,问了一句,你不是在学校的吗?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蚊子的眼睛一闪,接着回答也是合情合理。她说,一个客户找她合作,想开分校区的,结果没谈拢。
心水还是不死心,那个侧脸,真的太像黄天了。他怎么会无缘无故来到这个地方。而且还是跟蚊子在一起?这里面似乎有什么她不知道的秘密。心水还是不放心,有意无意间就往蚊子的情感方面引导。是不是约会呢?要不要我帮你参谋一下。我是过来人,怎么也比你经验丰富点。那心水故意问了好多蚊子的事情,也了解了很多。比如蚊子谈过十几个男朋友,结果没一个能投她的脾气的。甚至有一个都已经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最后却因为一句话而分道扬镳。
“也许,本来就不想结吧。刚好找到了借口。”
心水只知道蚊子的第一个男朋友伤她很深,不仅浪费了多年的青春,还搭上了她的积蓄。那个男人临走的时候,留下的一句话,至今让蚊子耿耿于怀。“也不照照镜子,你的青春叫青春吗?”言外之意,嫌蚊子长得老气。
蚊子一气之下,做了整容。“你看,我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一切都可以重来。”
与蚊子分别的时候心水依然记得她的口头禅,“没什么大不了。”
四
睁开眼,心水决定今天要做两件大事。她分别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黄天,一个给孙飞的父亲。
她到了市民广场,远远地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推着婴儿车。她知道那里有她的蝈蝈。可是她不能去。她看见黄天拿出一根烟,站在离婴儿车十步远的位置,开始点燃。那烟火一明一暗,像那天晚上黄天的眼睛。对着她发怒。她还记得那天晚上,黄天把她压在身下,对着她的脸,来回扇了几下。她就那么蒙掉了,脑子是空白的,天花板是空白的,自己的身子就那么不断地膨胀,僵直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那时她明白了一个词——心如死灰。
她看见一辆出租车,招手上车。时间很紧迫,她要在黄天回家之前,把裤子送回家。这是她给蝈蝈的唯一念想了。
打开门的一瞬,家里凌乱得像遭了贼,到处堆放着衣服。盆里还有蝈蝈的脏衣服,垃圾桶里蝈蝈的尿不湿已经溢出来了。还有奶粉罐都没有盖好,勺子就放在床头柜上。
她扒拉出一块地方坐在床沿上。她把裤子放在自己的腿上。从里面掏出来那封信。信上还沾着她的泪痕。
蝈蝈,我是妈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你很久了。妈妈知道这是不对的。既然生下你,我就应该对你负责。可是妈妈有自己的难处。你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生你的时候,我的一颗牙,都被咬断了一半。但是看到你健康成长,我是多么地高兴啊。可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和你的爸爸,发生了一些冲突,我感觉我们之间处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中。蝈蝈,你要记住,不管是妈妈也好,爸爸也好,我们都是爱你的。这点是最重要的。妈妈是个逃兵,不能勇敢地去面对生活。这是不对的,但是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能去保护你呢。原谅妈妈吧。
妈妈
看到这里,她拿出那张纸,拿出包里随身带的笔,在最后的署名前又添了几个字——爱你的。
是啊。爱你的妈妈,就要离开你了。蝈蝈。心水的眼泪再次落下。
回到学校,心水坐在办公室。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后,她拿出课本来备课。期中考试结束后,她决定离开学校,至于去哪里,她还没有决定好。但总归一切都会好的。
“你是李老师吗?”一个中年男人,踱着步子进了办公室。她抬头看了看,办公室只有自己一个人。中年男人头发有些花白,脸上发黑,那种闪亮的带着油光的黑。这让心水想到了一幅叫《父亲》的画。男人弯着腰站在心水的办公桌前。
心水先看见的是蓝布工作服,胸前印着“鼎盛燃气”这几个字。下面还有他的工号和名字,——孙有才。
“请坐吧。”看着这个姓,心水就知道是孙飞的父亲。
孙有才低着头站着,像个犯错的孩子。
“请坐吧。”心水再次让他入座。为了避免他的心理负担,心水站起身来,为他倒了杯水。孙有才依然像进来时那样弯着腰,不说话,像是等着心水训诫。
“这次请你来,是想让你了解孙飞在学校的表现的。”心水开门见山。
“嗯。”孙有才的嘴里蹦出一个字。
“孙飞经常不完成作业。”
“在学校还会打骂同学。”
“最近我听学生反映,他还学会抽烟了。”
……
“嗯。”孙有才还是一个字。
整个过程都是心水在自导自演。孙有才连一句硬气的话都没有。真让心水生气。
正好下课铃响了。心水看见一个身影,还是穿着那件宽大的不合体的衣服。心水站起来,走到门口,叫住了想要逃离的孙飞。
孙有才一看见孙飞,劈头盖脸就上来:“天天的,你就不能省点心,我赚点钱容易吗。”
说着孙有才抓住孙飞的头,来回拉扯着。孙飞被抓痛了,龇牙咧嘴开始嚷嚷。
“谁让你来的,你走啊,没人想看见你。”
“你这兔崽子,老子养活你,你还这样说。看我不打死你!”
孙有才一个甩身,把孙飞推到墙角边。
心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父亲,把孩子往死里打的。就在孙有才要踢孙飞的时候,心水一下扑了过来,挡住了孙有才的脚。
心水一把被孙有才拉开,对着孙飞的肚子就是一脚。心水胸中的那条龙出来了,血液一下涌上了她的天顶盖,四肢微颤,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扑向了孙飞。孙有才的一脚狠狠地踢在心水的身上。心水明显感觉自己的后腰被重击,疼得顺势倒了下去,最后她还是把孙飞往自己的怀里抱着。孙有才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招吓蒙了,站在一旁,喃喃地说,我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故意的,李老师……
被心水搂怀里的孙飞,一下子忍不住了,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妈妈就是这样被他打走的……
原来孙有才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在外面受气,回来经常打孙飞的母亲,最后实在受不了,孙飞的母亲离家出走,到现在也没有回过家。
从小到大,巷口的小伙伴们都不和孙飞一起玩耍。都说他是个没妈的孩子。孙飞的奶奶把他带大。可去年也去世了,孙飞觉得都是父亲的错。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孙飞觉得自己肯定也会像别的同学一样有个妈妈疼爱自己。
心水听着孙飞断断续续的叙述,把孙飞死死地抱在怀里,她想着,如果蝈蝈遇到这样的情况,谁会来抱着他呢?想到这,她的眼泪也顺着脸颊流下来,好像此刻在她怀里的就是蝈蝈。
那天放学,心水独自在操场上走了很久。有些人需要用一生去弥补童年的不快乐。而有些人却用童年的快乐去化解一生的痛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以后她的蝈蝈会是怎样的人生呢?远处的白云似乎比昨天的更白了,也更蓬松了。操场边一棵树上的喜鹊也回家了。心水似乎又看见那只张着嫩黄嘴巴的小鸟。那样柔软,那样无助。
突然,她很想打电话给黄天。刚拨了电话,还没通就挂了。她想起那封信,还在家里床头柜的抽屉里。想到这,她加快了回家的步伐。
在离家200米不到的十字路口,心水看着前方的红灯亮起又灭,绿灯灭了又亮,竟有些恍惚了,直到一个老人推了她一下,说,该过去了。
是啊。再怎么也得走过去啊!心水踩着高跟鞋,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家里的灯是熄灭的,难道黄天还没有回来吗?还在那个广场等她吗?这个傻子,怎么那么傻。
心水打开灯,进了卧室。家里还是她今天早上打扫过的样子,被子也是她理出来的四方形。黄天就曾经说过她,为什么非要这种方方正正的形状,不能理成长条状?黄天说,人就像蝴蝶一样,白天出去飞舞,晚上又变成蝉蛹,钻入被子里休眠。为了方便蝉蛹进入休眠状态,还是叠成条状的方便一些。可她对黄天的解释不置可否,直接来了一句,就是懒人理由多。
她弯腰把被子理开,重新铺展好。折叠再折叠,两边弯曲,叠成了四方形,怕不美观,又在边角处刻意处理成尖角状。她看着这些,觉得很满意。大学军训期间,她就是“内务标兵”,这些生活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做完这些她坐在下来,才拉开抽屉,那封信还稳稳地躺在那里。今早,她特意放在一沓说明书的最上面,现如今那封信还在那个位置。原封未动。
她看了看四周,空荡荡的房间,有的只是自己在昏黄的灯光下的动影。她把那封信拿出来,找了个打火机。一把火烧了那张纸。烧完信之后,她终于安心了。又拿出随身带的银行卡,放回到衣橱柜里。
她坐在床边,等着黄天回来。她要告诉他,今年冬天,寒假期间,要和黄天去武汉,看一看他的母校,这是他们之前讨论过的。虽然她一直想去东北,想去看看真正的大雪。但她知道,以后肯定也会有机会去的。
不知不觉,她靠在床边睡着了。睡梦中,她看见了漫天的大雪,白皑皑一片。脚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好听的声音,像是小时候咬过的脆脆的米饭锅巴,那种滋味真是香甜。她还看到了满天的星光,就在头顶,可以一颗一颗数出来。她还坐着雪橇,由几匹藏獒拉着,飞快地穿梭在茫茫一片的雪海中。可惜,她刚想从最高处的山峰上往下飞跃,半夜一声猫叫,把她惊醒了。她睁开迷糊的双眼,站起身来,每个房间依然像在梦中一样,有雪一样的冰冷的味道。
就在她穿过客厅时,茶几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封信。她打开一看,上面的字迹是那么熟悉。
心水,我走了。这些年,也许是我错了。我已经很少参加聚会,以前的朋友也很少来往。可你还是巴不得一天24小时在你的控制之下。可在一起, 你又是为了一点小事和我闹。这些年,我见过你割腕、见过你服药,我就像捧着一个刚粘上的青花瓷,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我一分钟都不能和你多待下去,我真的怕自己会疯。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吧。
不用低头看,心水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打颤,由内而外的无力感,一下让她瘫软在地。
晚秋来袭,寒露渐近。深夜里一片寂静,窗外盘旋的一阵风,带着呼号远去了。
2004年的暑假,正值心水考完大学,她拉着蚊子参加了一帮朋友的聚会。美其名曰:假日狂欢。她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释放着无处安放的青春,还有那未知的梦想。晚上,在录像店租来碟片,《泰坦尼克号》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的。最要命的是,晚上她们看《贞子》,由于胆小,心水建议喊个男生来。后来,在那个昏黄的夜色中,穿着休闲卫衣,戴着帽子,帽檐的边缘处可见一些弯曲黄发的高鼻梁男生,陪着她们一起看了那部恐怖片。在此起彼伏的惊叫声中,心水瞥见了蚊子偷眼看黄天的样子。眼神在荧光屏前,竟还有些娇羞的成分。这点,心水一直装作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