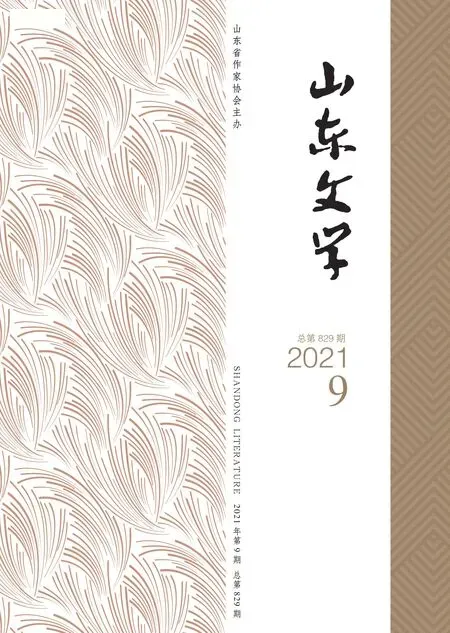那时情谊
深 海
1
因为出生在一月的缘故,在严格规定年满七周岁才能入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直到一九七五年秋七岁半才上小学一年级。
那时真是艰苦。小学一年级只有两个班,可两个班都没有教室,桌子板凳更是没有。我们只能自带小板凳在学校的小操场上课,因为操场边有个小树林,黑板可以挂在树上。而我们呢,每个同学都买了一块书包大小的小黑板,老师在大黑板上写字,我们把小黑板放在自己的腿上练习——小黑板就是我们的桌子,我们的腿,就是桌子腿。天公不作美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留在家里。
我被班主任姜雪老师指定为班长,还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了言。虽然我对于在那么多人面前用蹩脚的普通话念老师写的发言稿毫不发憷,可对于当班长这件事,内心深处还是有些反抗的——那更像是我妈的好友姜雪老师,帮着我妈戴在我头上的紧箍。
让我第一次对自己是一个班长感到自豪的,是张海峰。
小学一年级,我们上课都是有一天没一天的。一年级结束,我这个班长连班上大部分同学的名字都还没记住。幸运的是,到了二年级,我们终于坐进了教室,更幸运的是,姜雪老师因为业务突出,被调去带五年级毕业班了!
我们的班主任换了位姓王的男老师,他带的是语文课。据说他高中都没有读过,而且形容粗放,说话声音沙哑,总是用力地吼,我们都有些怕他,更不喜欢他。有一次上语文课,他带领我们读课文,读到“不能自已”这句,他读的是“不能自己”。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举手站起来纠正他,说老师读错了,是“不能自已”,不是“不能自己”(如果是姜雪老师读错了,我是断然不敢这样放肆的。当然,姜雪老师也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王老师坚持说他没错,我坚持说他错了,正相持不下呢,班上的其他五个班干部都站起来支持我,说王老师读错了。王老师几乎是龇牙咧嘴地看着我们,伸出右手指指点点着,怒吼,你们!想干什么?想造反?他把我们赶出了教室,让我们拿着小板凳到教室外面去听课。这时候,坐在第一排的一个面容清秀俊朗的小个子男生也拿着小板凳站了起来,问,老师,我也觉得你读错了,我是不是也要出去?王老师大吼一声,出去!他又问全班同学,你们还有谁跟钟晓敏、张海峰他们一样?也给我滚出去。
班上鸦雀无声。
那个眉清目秀的小个子男生就是张海峰。我以前没怎么注意他,他个子小,上课坐第一排,排队站第一个,不爱讲话,上课几乎从不举手发言,可是那天,他竟然搬起小板凳跟我们一起坐到了教室外面。
我们七个人乖乖地、却一脸不服气地坐在教室门口,跟着教室里面的同学一起大声地诵读课文。过了一会儿,王老师大概意识到让我们几个人这样坐在外面读书目标太大,他走到门口说,你们几个,拿着小板凳,到我办公室去,安静点,我下了课再来收拾你们。
我们几个一点也不反抗,提着小板凳,自觉地排着队,去了教师们集中办公的大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旁边安静地坐着。也是巧,校长进来了。大办公室本来空无一人,所有的老师都去上课了,校长大概刚刚巡视了一遍校园回来,他的办公室在大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他走进来,看到我们,吃惊地问,钟晓敏,你们几个不上课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站起来,理直气壮地把经过讲给他听。其他人也跟着叽叽喳喳地补充。校长抬起右手,用力地往下一划拉,严肃地说,不像话!我们吓了一跳,以为是批评我们。他连忙摸摸我的头,说,走,跟我回教室去上课。
我们又自觉地排成一队,跟在校长后面。穿过小操场,走到教室门口,我们停住了脚步。王老师见校长领着我们走过来,连忙从讲台下来。校长看都不看他,对我们说,都进去上课。他把王老师叫到门口,尽管压低了声音,我们还是听到了,他说,你今天在学生们面前丢了两回人!读错了字,丢人;读错了还不认错,更丢人。回去立刻向他们道歉,否则你这个老师不要干了,你还是回去跟你爹榨油去吧(后来我才知道,王老师家是开油坊的)。
王老师虽然一百个不情愿,可他还是道歉了。
2
从那时起,张海峰就成了我最好的伙伴之一。下课了,我喜欢叫上他跟我们一起玩;放学了,我领队,他站第一个,我喜欢走在他身边。他几乎比我矮一个头,我感觉自己多了个小弟弟,见他背着书包、小黑板、小算盘很吃力的样子,我总想帮他背,可他每次都拒绝。
他不让我帮他,却从不拒绝二木,甚至,主动要二木帮他拿东西。
我七岁半上学已经算晚的了,二木九岁才上学,二年级时他已经十岁了,他的大名我忘了,只记得大家都叫他的外号,二木(发音为平声)。他在家排行老二,高,胖,木讷寡言,学习总是在全班倒数,作业不能按时交,考试永远不及格。我这个班长,自觉有责任帮助他,自习课的时候我总是坐到他身边想辅导他写作业。可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加减法运算,我讲得口干舌燥了他还是听不懂不会算。我急了,吼他,拿老师给我的教鞭敲桌子。二木瑟缩着,躲着我,脸上却还在对我笑。他的眼睛很大,大而清澈,充满胆怯却又信任地看着我。成年之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童年的某些瞬间,我还时常会想起他的眼睛,特别是看到动物的眼睛,那样单纯的干净的眼睛时,我都会想起二木的眼睛。
二木没有朋友。下课了,他很少出教室,张海峰是他唯一的玩伴。有时候,张海峰被我们拉出去玩,二木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一天又一天,他的小学生活似乎就要永远这样过下去了。
一九七六年深秋,一个周末的下午,学校搞大扫除。扫除完了,同学们先放学回家,我们几个班干部留下来等老师来检查,我叫张海峰也留下,张海峰则把二木也留下了。我们七八个人一边收拾清洁工具,一边说笑打闹。二木面带微笑,安静地,慢慢腾腾地,配合着张海峰把清洁工具一件件摆放到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等老师检查完,在教室门口贴上了红色的“最清洁”的纸条,我们心满意足地锁好门,准备回家。张海峰忽然说,班长,我们一起送二木回家吧。为什么?他自己不会回家吗?他家在哪儿?
张海峰拉拉我的手,说,走吧,你去了就知道了。
天色不早了,有几个住得远又不同路的同学怕回家太晚会挨骂,先走了,我跟张海峰还有两个女同学一起,迎着晚霞,陪二木往他家走。
二木穿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深灰色旧棉袄,棉裤更旧,膝盖那里不仅补着大补丁,两条裤腿早已弯曲变形无法复原了。最可怜是,棉袄棉裤里都是空的,也就是里面没穿秋衣秋裤,也没穿袜子,一双快要破洞的单布鞋,布鞋和棉裤脚之间露出脏兮兮的脚脖子,还没入冬,那里已经开始皲裂了。
可是那天,二木的脸笑得像一朵花。
二木的家有点远。我们从学校出发,经过公社大院的院墙,转弯,经过公社的大门口,经过面粉厂前的大路,经过机械厂门口的大路,经过供销社,经过人民医院……穿过整个镇子,我们又穿过了一个村庄,走过一片荒凉的玉米地,在玉米地的尽头,一所孤零零的破旧的土坯房前,张海峰伸手一指说,二木,你到家了。二木看着他,慢慢地眨了眨眼睛,笑,不说话。我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我从没有见过人住在这样破旧不堪的地方。它应该只在我们小学课文或忆苦思甜会上对旧社会的控诉里出现过。
推开木门,吱呀作响。屋里漆黑一片。从右侧的更加漆黑的深处传来一声孱弱的问候,二子?是二子回来了吗?二木嗯了一声。放下书包,也不管我们,走到门外去,在一棵不知名的植物上摘了两片叶子,用手擦擦,又走进里屋。这时候,我们已经适应了屋里的暗,里屋北边高处有一个用旧报纸糊住的小窗,微光从那里透进来,我看到床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她双眼直视着我们的方向,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张海峰走过去,跳到床上,抓住老奶奶的手说,奶奶,我们班长,还有学习委员、文艺委员跟我一起陪二木回来的。
老奶奶拍拍张海峰的手说,是小峰啊?你看这个二子,知道奶奶看不见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奶奶说话时伴着呼呼的响声,就像有个风箱在她的喉咙里。她说着,伸出一只手在空气里摸,问,哪个是班长?哪个是学习委员?哪个是文艺委员?
我们三个女生往前站了站,站到老奶奶的手能够到的地方。她握握我们的胳膊,犹豫着想抬手摸我们的脸,却只放在肩头摸了摸,说,你们都是班干部,要多帮助我们家二子,他是难产,生得艰难,时间太长,脑子闷坏了,生他的时候他妈没了,他从小就木,可是心眼儿好,你们不嫌弃他,愿意跟他玩,奶奶每天都会求菩萨保佑你们。
我们说话的时候,二木一直站在旁边。奶奶叫他,二木,天黑了吧?你点灯了没?二木说不用,我看得见。
奶奶的眼睛怎么了?旁边的女生问。
奶奶说,长翳子,好多年了,现在完全看不见了,没钱治,小峰他妈带医生来给我看过几回,说要做手术。我老了,不想在自己身上动刀子,就这样吧……
二木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们身边走开又回来的,奶奶话音未落,他忽然从破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红枣来,递到我们面前。
奶奶似乎感应到了他的这个动作,问,二子,你拿东西给同学吃啊?是什么?干净不干净?洗了没?
二木说,是枣子。干净。
奶奶笑起来,说,你们吃啊,这是我们自家树上长的。
张海峰拿了一颗喂到奶奶嘴边说,奶奶你也吃。
奶奶伸手接过枣子,说,小峰,天黑了吗?你们快回吧,远,回去晚了不好。又对二木说,把枣子给他们带上!你送他们,送到镇上你再回来。
二木不说话,转身往外走。
我们在镇子边上跟二木挥手告别时,空中的晚霞已经散尽,镇上有些人家已经亮起了灯火。
那天回到家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吃过饭,哥哥在饭桌上写作业,我就坐在他对面,呆呆地看着他写字,脑子里想的都还是二木家的情形。
回家的路上听张海峰说,二木的父亲是独子,老奶奶一个人带大的,可是,二木的妈怀他的时候他爹就死了,二木出生的时候他妈又死了。二木的哥哥比他大六岁,没上过学……
那时候,我脑海里应该还没有艰难、悲惨这样的词汇,只知道“穷”和“苦”。这两个字,是人生还只有八岁的我,所能体会的人世间最可怕最沉重的字,它们突然活生生地摆在我面前,不是课文,也不是讲述,而是具体的,非常具体,它们在日落时分,从荒凉的地上升起来,一下子就从眼睛里一直堵到了我的心里。
在灯下补衣服的妈妈,一边干活一边没好气地说,你们两个人的脚都长了牙齿吧?双双袜子都破洞。
我哥抬头看着她笑一下,低头继续写作业。
我却面无表情。
妈妈问,小敏不舒服吗?怎么一晚上都不讲话?
我问,妈,什么是长翳子?
我妈也被问住了,说,什么翳子?
我说,我们班有个同学的奶奶眼睛里长翳子,看不见了。
妈妈看着我,问,你今天去同学家了?
我点头。她说,我也不知道。时间不早了,天冷,赶紧洗洗睡觉吧。
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想着二木家也有这样的被窝吗?二木这会儿在干什么?是不是躺在他奶奶身边了……
我忽然大声喊,妈,妈妈。我妈吓了一跳,扔下手里的活计跑过来,打开我小隔间的电灯问,怎么啦怎么啦?我问,妈妈,哥哥的秋衣秋裤有没有多的?旧的也行。我妈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想送给同学穿,他没有爸爸妈妈,奶奶眼睛看不见,他也没有衣服穿……我说着,忽然就哭了起来。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妈妈问,你那个同学个子有多高?胖不胖?
我仔细想想,二木虽然才十岁,可他的个子几乎跟我十三岁的哥哥一样高,而且比我哥哥胖(后来才知道,他那是虚胖,近乎肿)。
我妈妈说,那你哥哥的衣服他恐怕穿不了,这样,我把你爸爸的旧衣服找几件出来改改给他穿。
从那天起,课间或课外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二木拉出去一起玩。他其实也没有玩,他不喜欢动,我们玩往返跑,他就给我们当柱子;我们玩老鹰抓小鸡,他就当老母鸡;我们玩丢沙包,他就站在中间伸开双臂给我们当网子。
几天后,我悄悄把妈妈改好的一套抓绒的卫生衣裤塞进他的书包,俯在他耳边说,这些要穿在棉袄棉裤里面。我还曾经斗争过,要不要跟王老师说说二木家的事情,发动班上的同学去二木家学雷锋。斗争的结果是算了,王老师不喜欢我,他肯定不会支持我的想法。
没有特殊情况,放学的时候我和张海峰都会跟二木一起走,把他送到镇子的边上我们再各回各家。有一次,张海峰带我们去了他自己家,我才知道他家住在镇上的老房子里,是他妈妈家的祖产,灰砖黑瓦,两扇开的大木门,进门是个两米见方的小天井,天井对面是厨房,右边是两间小屋,第一间是他妈妈的卧室,第二间是海峰的房间,没有客厅。天井的地面是用灰砖铺的,从大门到厨房、从厨房到房间的部分磨损严重,少有人走的地方长满了青苔。天井靠外墙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小花坛,一棵枝繁叶茂的灌木骄傲地站在上面,这让我甚是惊奇——入冬,我家乡的绝大部分植物都会落叶飘零。张海峰说那是栀子花,夏天的时候才会开,白花,很香。还说,班长,明年夏天我每天给你带一朵。我笑而不语,心里美滋滋的。
我在他妈妈床头朱红色的五屉柜上看到一张四人合影,才知道他还有个姐姐,他爸原来是我们公社医院的医生,犯错误被革命以后,他爸妈离婚了,姐姐跟他爸爸回了浙江老家,他跟着妈妈。他妈妈是公社医院的助产护士,二木就是他妈妈接生的。照片上的张海峰还不到两岁,坐在她妈妈怀里。她妈妈真漂亮,漂亮得让我很期待见到她。
转眼就放了寒假。我跟张海峰商量好,每天到二木家去跟他一起写寒假作业,不然的话,他又会跟从前一样,每次假期的作业都写不完。其实,那时候作业很少,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作业都写完了,包括二木的作业。当然,有些是我们帮他做的。到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后,我妈不准我再往外跑了,说,你野够了没?天天往外跑不着家,你跟哥哥一起,在家搞大扫除,爸爸过两天就回来了。
正月十五之后,新学期开学,我们的班主任竟然还是王老师。
过年的时候,我许的新年愿望就是换个班主任,只要不是王老师,谁都行,姜雪老师也行。从那时我就知道了,向莫名其妙的将来许愿没用,不灵。
点名时,没见到二木。张海峰告诉我,老奶奶死了,二木过几天才能来,说是要守完头七。
开学三天后才见到二木,他胳膊上戴着黑袖箍,黑袖箍上用石灰点了个白点,不知道什么意思,代表白花?他低垂着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们叫他出去玩,怎么叫他都不理。我们就围在他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他话说。二木始终没有抬起头。
从那天起,二木看见我再也没笑过。他渐渐地跟我们都疏远了,除了张海峰,他不跟任何人走。
一个月后,没有被我的愿望赶走的王老师,忽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同学们,明天,我们的新课桌椅就来了——我们二年级时虽然有了教室,可是课桌就是地上打三个圆木桩子,上面钉一块木板,板凳都是我们自己带的。
那天中午放学我们就把小板凳带回了家。吃过饭,我们早早就跑到学校,发现教室里的旧桌子已经被拆掉,地面上圆木挖走留下的坑还没有填,我们就主动到学校外面的庄稼地里去挖土,有的用手捧,有的用书包装,还有的把鞋子脱下来装。我们热火朝天地把坑填满,踩实,兴奋得脸发红,像喝了甜酒。
我们刚刚填好坑,几辆军用卡车开到了学校。校长带着老师们全都出来迎接。
不是只有我们年级换新课桌椅,整个小学部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全都换了。新课桌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每人独立使用,还带翻盖,还刷了深黄色的油漆,椅子还有靠背。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课桌椅往自己的教室里搬,故意把盖子打开,盖上,打开,盖上,弄得啪啪响。那天下午,学校热闹得像过年像庆祝重大胜利一样。
所有的课桌椅全都摆放好之后,王老师叫我们各自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全都坐下了,二木一个人低着头站在他的位置上,那里空荡荡的。
他的课桌椅呢?
王老师赶紧跑去问校长。回来说,三年级来了个转校学生,计划里是没有他的,可人家把课桌椅搬走了,也不好再搬回来。
王老师冲我吼,钟晓敏,你这个班长怎么当的?搬的时候怎么不数一下?你不识数啊?
全班同学都看着我。
我站起来,脸憋得通红,心跳得快要爆掉了,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王老师说,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是很会讲的吗?听说你一年级就代表新生对全校师生讲话,你讲啊?现在怎么不讲了?
我无言以对,心里其实已经开始自责了——我们高兴得忘记了二木?这么开心的时刻,我们忘记了二木……我们竟然忘记了二木……
我……我,把我的课桌给二木……
什么?那你呢?你天天站着上课?
这时候张海峰站了起来,说,王老师,把我的给二木,我坐第一排,我可以自己带板凳来。
张海峰,又是你!王老师说,你这么维护钟晓敏,她是你亲戚?还是……
这时候,班上好几个同学都像张海峰一样站起来说,老师,把我的桌椅给二木!
王老师看到同学们这样互助互爱,不仅不表扬,还竖起了眉毛,瞪起了眼睛。他刚想吼,二木突然哭了起来……
二木仰着头,张大嘴巴,发出单调的啊声。
全班同学,包括王老师在内,全都呆住了。
二木旁若无人地啊着,抬起右手,擦擦眼泪,忽然喊了一声,奶奶……
张海峰几乎是惊喜地叫了一声,二木,你终于哭了!他扭身跑到二木身边,紧紧地抱住他。我也跑过去,学习委员、文艺委员也都跑过去,我们围住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会用手在他背上拍拍这里,拍拍那里。有几个情感丰富的女孩子,竟然跟着他哭起来。
4
老奶奶走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二木才发出第一声哭喊。
是没有新课桌椅让他感觉到委屈?还是看到我们要把自己的课桌椅让给他感到了安慰呢?我至今也不清楚他为什么恰恰在那个时候哭了起来。可是,他的哭不知为何竟瓦解了王老师的愤怒。
王老师的脸色缓和了很多,说,好了好了,二木你别哭了,老师去想办法,一定给你弄套新课桌椅。钟晓敏,现在离放学还有一会儿,你领着大家读读课文,放学的铃声响了我要是还没有回来,你就带大家排队,放学。
我点点头,第一次对王老师的命令执行得心悦诚服。
第二天,王老师果然给二木弄来了新的课桌椅。后来才知道,那套新的课桌椅竟然是他跟每个班的老师商量后“借来的”。怎么借的呢?谁班上有不来上课的学生,就把课桌椅借来用一天半天的。这多麻烦啦?不知道王老师是怎么说服别人的。他把这个搬课桌椅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几个班干部,我们欣然应允,大声保证,绝对办到。
从那天起,小学部的教室走廊上,每天都会出现我们抬桌椅的身影。我们抬得很欢快。
渐渐地,随着春天的到来,二木的脸上又开始有了笑意。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讨厌王老师了。他却还是像过去一样对我横眉竖眼,可我总是对他笑,无论他怎么大声吼,我都对他笑,对他说,是,王老师!好的,王老师!四月的时候,王老师对我的态度也和蔼起来,甚至,他在班上也不像过去那样爱发脾气了。
可是四月末,突然张海峰连着几天没来上课。我们问王老师,他说张海峰请了病假。有天放学后,我跟学习委员拉着二木去张海峰家找他,大门上却挂着锁。邻居说,峰娃儿病得很重,到县医院去住院了。
谁也不会想到,张海峰死了,毫无征兆的,他就那么死了。
张海峰缺课的第十五天(整整十五天,我每天都数着),下午,还没到放学时间,王老师突然把我叫了出去,他叫我把书包拿上,跟他一起去办个事儿。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王老师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女老师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他们走得很快,我要时不时地小跑几步才能跟上。女老师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地连说了好几个可怜可惜。她说,你说这周护士到底是啥命呀?男的不争气,被革掉公职,遣回原籍改造,她这些年一个人带着儿子才开始过得舒心一点,这儿子又……王老师问,我还不是很了解情况,怎么突然就这么凶狠了(王老师的原话)?女老师说,一开始是发高烧,张海峰他妈以为也就是春天感冒嘛,喉咙发炎,就在公社医院打了三天吊针,可是高烧不退,腮帮子也肿起来了,医生赶紧叫转院到县里去治,还是晚了,说是急性腮腺炎,有了并发症,一入院就下了病危通知……王老师说,他妈还不要疯了?
我跟在后面,渐渐地有点魂不守舍。他们在说什么?张海峰怎么了?腮腺炎是什么?什么叫并发症?什么叫“还是晚了”?
王老师突然对我喊,钟晓敏,你走快点,要不就赶不上了。
赶上什么?我边跑边问。
王老师说,张海峰不好了,刚从县医院回来,你代表全班同学,去跟他告个别。
……
我虽然跟着他们紧赶慢赶,可是整个人已经蒙掉了。
5
张海峰家的大门虚掩着,女老师喊了声周护士,也不等回应,推门而入。
没人回应。
我们站在天井里,张海峰的妈妈从右边第一个门里走了出来。
这里我来过一次,知道那是海峰妈妈的卧室。可是,这就是我期待见到的那个照片上的美人吗?她脸色发青,头发凌乱,双目赤红,上下眼泡浮肿得厉害,整个人轻飘飘的,似乎随时都会倒在地上。
女老师赶紧上前一步扶住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塞到她的上衣口袋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一点心意,你拿着,别推。快,让我们进去看看孩子。
海峰妈妈虚弱地点着头,转身带我们进屋。
屋子里没有开灯,屋顶玻璃瓦透进的光正好照在床头,海峰的脸就在那微光里,在白色的枕头和白色的被子之间,一张苍白消瘦的小脸,若不是他浓黑的头发在那里,若不是定睛去看,你不会以为那里还趟着一个人。
他闭着眼睛,双颊凹陷——不是说他腮帮子肿了吗?
屋子里有一瞬间死寂般安静。
女老师突然问,孩子这不是还有呼吸吗?怎么回来了?为什么不治了?
海峰妈妈说,医生早就说不行了,治不了……他一直撑着,就是要回家,天天还在想着,要上学……
我先是眼泪涌了出来,继而哭出了声。
王老师忙把我往前推了推,对海峰妈妈说,这是海峰的班长,代表同学们,来看他。
海峰妈妈说,谢谢王老师,你想得这么周到。又转向我问,你是钟晓敏吧?他每天都在念叨你,还有二木……二木没来?
我走到床边,又往前站了站,站到床头。看着海峰那张苍白可怕的脸,只会哭,什么也说不出来。
女老师说,小敏,你叫他,看他能不能听到?
我还是哭,说不出话来。
海峰的眼睛却慢慢地睁开了,睁开了一条缝。他的视线游移了一下,看到了他妈妈。海峰妈妈立刻扑过去,双手捧着他的脸叫,我的儿啊,你已经昏睡了一整天了,你想喝水吗?你想要什么?老师和同学来看你了……
他的视线移过来,看到了我,嘴唇动了动,没有声音,可我看出来,他在叫我,不是叫我的名字,而是叫班长,他似乎从没有直呼过我的名字。
我也叫他,张海峰!
不知道是光线变化,还是泪眼婆娑造成的错觉,我看到他的嘴角倏忽闪过一丝笑意。
他的嘴唇又动了动,这次他是在问二木。我忙说,明天,明天我就带二木来看你。
海峰的眼睛闭上了,可是他的嘴唇又动了动。他妈妈把耳朵凑到他的唇边问,儿啊,你在说什么?再说一遍,妈妈没有听清……
我忙说,阿姨,他在说书包,书包。
海峰妈妈哦了一声,转身跌跌撞撞地跑到隔壁小房间去,取来了海峰的书包,整整齐齐地放在海峰的头边,对着他的耳朵说,儿啊,书包就在这。说着,她把海峰的手从被窝里拿出来,让他摸了摸书包。海峰长出一口气,又变得异常安静。
我们默默地在海峰的床边站着,不知道过去多久,玻璃瓦上的光渐渐暗得已经看不清海峰的脸。
海峰妈妈叫我们回吧,说他这是又开始昏睡了,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今天。
我们站在天井里告别,女老师拉着海峰妈妈的手问,海峰他爸爸不回来吗?海峰妈妈说,好多年都不联系了,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女老师忙安慰说,您要坚强啊!海峰是个好孩子,他这么想回家,想上学,说不定,回来了会出现奇迹……
两个女人流着眼泪互相拥抱了一下。
王老师走过去握了握海峰妈妈的手,说,有什么事就叫我们,等他好一点儿了,我们来接他去上课,哪怕回教室去坐坐……
王老师的声音哽咽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流泪,也是唯一的一次。
转身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了院子一角的那棵栀子花,蓬勃油亮的叶子里,似乎已经冒出了几个胖嘟嘟的婴儿手指般的绿色小花苞……
我忽然很想跑回去跟他说,海峰,夏天快到了,别忘了你说过的话,每天都给我带一朵栀子花……
那天夜里,张海峰走了。他终于还是没有见到二木。
张海峰的后事如何办的,王老师他们有没有参与,我毫不知情。他甚至都没有跟我们多提,只说过,张海峰同学不能再来上学了,他的课桌椅就给二木用吧,钟晓敏,你们以后不用再到其他班去借课桌椅了。
可是二木不肯用海峰的课桌椅,他宁愿站着上课也不用海峰的课桌椅,总是问,海峰呢?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直到六月的某天,班上一个特别调皮的男生冲他喊,傻瓜二木,张海峰再也不会来学校了,他死了。二木直愣愣地看着那个男生,突然冲上去就对着那个男生的头打了两拳。
那两拳打得太重,一拳打破了那个男生的鼻子,一拳打破了那个男生的眼角。
家长找到学校来了。
二木的哥哥被叫到了学校,当面给人家赔礼道歉,可是,医药费他没钱赔。听说最后是学校承担了那个孩子的医药费。
二木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学校。后来,听说二木已经不在我们镇上了,他哥哥刚满十八岁就去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带着二木一起去的。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再也没有去过海峰家所在的巷子,一次也没有。直到三年级下学期,珠算老师带我们到街上的商店里去上实践课,就是带着算盘和小板凳,到供销社和各个杂货店去,请售货员当面给我们出题,让我们非常直观地理解了珠算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海峰家的旁边就有一家杂货店。在那家杂货店门口,我一道题也没有算对。
直到现在,每年夏天我都会想,海峰家的栀子花还在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