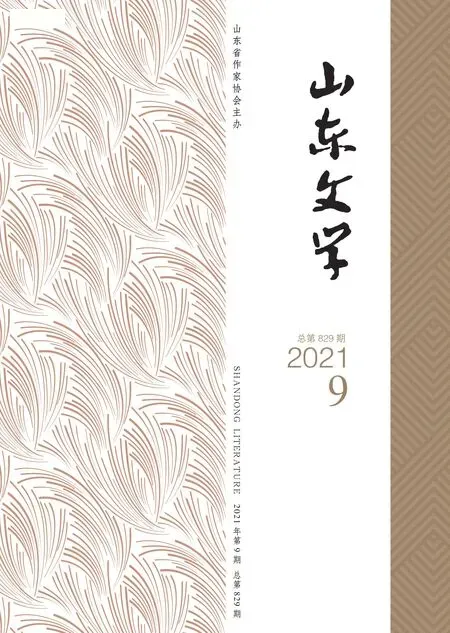小说三题
关 山
裂 缝
不进入这个房间,她似乎都忘记了自己在这里住过。都是陌生的样子,或者说是自己选择了陌生感,用以遮盖那些涌动不止的情绪。
这是她的婚房。第一处,也没有第二处了,十几年过去,她没有再婚。
这房间里从前还有一个男人的。初恋,也没有再恋过。后来的经历中,有的接近了恋爱,有的接近了床,这时,她陡然生出恐惧,挣扎而出,逃避恋爱比逃避床更彻底。
房子要出售了。她来看一下。没有什么可收拾的,随身物品早就带走,扔掉一些,剩下一些旧家具,经了几次短租,已经破损。后来索性就让它闲着,好几年的灰尘像是黄色的棉絮,密密地覆盖着。收旧货的人马上要来,保洁员也要来。然后是房子的新主人。
县城的房子价格涨得慢,十年前一千多一平,现在不过三四千,而同样的时间,自己所在的城市已经由数千涨至数万。她离开这里之后,重新进入学校,硕士博士一路读下去。并不是对学位有兴趣,也不想借此寻处高位平台,只是不想离开学校,最后如愿留校任教。
她慢慢地在屋子里走,步子轻缓,不惊动那些浮灰。也许自己早些进来,就是为了看这些,旧物,陈灰,还有些别的什么。她在等着敲门声。
门上有处裂缝,那是将重物扔过去时砸出来的。扔的是大幅水晶照片。两人的结婚照。当时没有碎,轮番用脚踏过之后也没碎。搬动起来很重,但是扔进小区外那条河里时,一时也没有沉,在水面上漂浮半晌。照片上,两人仰面朝上,瞪着蓝天白云,过往行人。两人身穿结婚礼服,笑容可掬,在河面上打了处旋,缓缓沉入水里,再也看不见了。
她收回心神,必须收回来,按下遗忘键,启动陌生感,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她博士的研究方向是植物,越来越细,比树叶要小,比细胞要小,她开始关注细胞内部的电流。只有钻进这样一个极小的缝隙之中,才能在业界立足,也才能找寻到自己的出口。她感觉自己的身体不断向内部塌陷,收缩进细胞电流之中。眼前这一粒灰尘,比自己大多了,那些旧物上的伤处,是一座座无顶之山。
清点完毕,旧货公司来了两位搬运工,拆卸家具。床是最后一件拆解的物品。两人满头大汗,想找处地方休息一下喝口水。
“不要坐床。”她说。
“哦,”一位工人环顾了一下空空荡荡的房间,对另一位说,“那加点劲干完再歇吧。”
开始拆解。
“这是什么?”一位工人嘟囔了一句,从地上捡起一件小东西,吹了吹灰。
“像是个老手机。”另一位说。
她快步走过去。
手机。是了,就是它。套着浅蓝色仿牛皮手机套,系着织绳,套子顶部绣着一朵菊花。
里面是枣红色的机身,翻盖,十几年前的流行款。花了他三个月的工资。三个月,不吃不喝的积攒。
“不,不,不。”她扑了过去。
两个工人呆怔着。
她将手机捧在手里,慢慢地坐到床上。过了会儿,对工人说:“你们,先回吧。”
那段生活中,最后一争吵,也是最激烈的一次,就是因为这部手机。
这是他半年前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她的单位与通信公司合作,搞优惠活动,给每个员工发了部手机,建立了内部系统,相互之间用小号打电话,不须话费。她已经和母亲说过,要将手机送给她,母亲正想买一部,却又疼钱。她说这是他的心意。母亲对她的婚事本就不满,嫌他家在山区农村,是个无底洞。自己这么做,也算是在两人之间加加温。而当时,他的母亲正在住院,手头紧张,他想将手机卖掉,还是九成新呢,当时二手机市场挺好。
灰尘坐上去软绵绵的,像是可以无限下陷的样子,窗外的阳光倒是尖利带刺。她打开已经成了灰黑色的机套,当年自己的手工如此精致,恨不得把手机裹在三层海绵里。里面的枣红依然闪烁,仍然是九成新。仿佛经过这些年,它更新了,红得耀眼。
争吵是怎么起来的?因为手机没了。原来,它是潜伏在十几年后,静听那场浩大的破碎之声。
“手机呢?”
“问你自己呀。”
“没了。”
“找啊。”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什么,你什么意思?”
“你想卖,也用不着这种手段吧。”
“胡扯!要这么说,应该是你自己拿了,给了你妈,反来和我闹。”
……
持续了不知多久,也许是一夜。
不知道他是何时离开的,医院里打电话催。
再也没有回来。她也没有回来。
两人办离婚手续时都隔得远远的,仿佛中间有一块烙铁。
工作人员例行劝解,机械而生硬,最后高声叫:“本子,拿好。”
打开手机,自然早就没电了。她在电线中找寻了一番,还有可以兼容的充电插头。充电缓慢,等待开机的这段时间,她像是突然记起了他的手机号码。与她的这部老手机号只差一个数字。她换了若干部手机,启用了新号,这个老手机号中的关键部分一直是她的银行密码。
照片,相素不高,但已经是当时最好的,彩色。她笑得花团锦簇,年轻的脸,放着光,是向着他笑,每张照片都是他照的。桃花,梨花,月季,那个春天,她与所有能看到的花合了影。她已经忘记这些花许久了。两人的合影在那场争吵中全部毁掉,残留的部分也在残留的怒火中被扔掉或是从电脑里删除。他留在她记忆中的样子,是一张因愤怒而变形的脸。除此之外,都是美好的样子,却被这张脸遮挡了,被自己选择的遗忘关闭了。手机里保留着所有的阳光灿烂。当时,他们手头紧张,家具是到批发市场上购买的地摊货,也没有购置家电,家里最值钱的就是这部手机了。在争吵发生之前的某时某刻,它掉落进床上的裂缝,处于关机状态,从此,静静地镶嵌其中。
生 门
生门打开,死也从这门里过去。
他认不出她来了,即使她不佩戴口罩和防护帽,保持着从前的容貌和身段。他已经丧失了辨识能力。
她也差点认不出他来,盖在一堆白布下面,蜷缩成一小坨,面色蒙着白灰。
仪器都上了,指标在危险边缘跳动,指示灯和电波闪烁不定。医生护士们忙了一阵,去休息。她是临时抽调过来的义工。
他多半时间闭目,有时眼睛突然睁大,不看四周,像是看着远处。窗外,天色阴沉,能见度不高。
在看什么呢,空中正在形成的雨滴,街上穿梭的行人,或是那个向你缓缓飞近的影子,你的命。她知道那个影子已经出发,并将在此地将他捕捉。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养一些力气,以便最后挣扎一下。她是被指派来守护他的,清理,值守,陪伴,能帮他的有很多事情,都没什么用处。她知道他的恐惧。他不再认识周围的人,其实,除了必要的医护人员,他周围也没有什么人了。
他注意到了她。摆摆手,示意她走近些。
走近了,他的眼睛却没有看她,仍旧盯着窗外,抬手指了一下。
这种眼神她再熟悉不过,他从来不会正眼看她的,即使他眼前只剩下她。
她走过去,打开了一条缝。凉湿的空气钻进来,有股带土腥的甜味,比室内的酒精味和腐臭气好闻些。她又打开了些。她知道他正盯着自己的后背,像是有蚂蚁在爬,她向一边挪了挪。他的眼神里能生出许多昆虫和铁器,她知道,还能生出毒来。
在那段阴晦迷离的时间,她无数次地设想过再次与他相见的场景。一桌热闹空虚的酒席,一个严肃无聊的会场,或是在车站、机场这样人员密集的场所,甚至在国外某处街区。她知道他已经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偷偷办理了移民相关手续,已经将那些无法亮在明处的资产提前转移过去。在心存侥幸自我安慰之余无休无止地担惊受怕,以便在老年之后将财富像土一样扬起来,将自己慢慢掩埋。同时,在那处咸度颇高的海边,为自己购置一处无人祭扫的墓穴。有的时候,她眼前会浮现出一把刀来,短柄,锋利,出鞘无声,一刀致命。接着,心内生出恐惧,不是因为死亡骤然而降,而是自己心内竟然生着一条休眠中的毒蛇,哪怕泡在药酒里,或是制成皮具,一声呼哨,它就会醒转。而自己,就是那声呼哨的发出者,同时也是管控者。手里握着砍向自己的刀。
为什么怨恨会成为一条蛇,一把刀。她知道,但拒绝承认,那定好的婚约以及不能举办的种种借口。而在这之前,是佯似爱情那人畜无害的温馨模样。
她一直单身。她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仿佛一旦这样承认了,就承认了自己对他的爱并未放弃,或是曾经爱得足够深远有持续的破坏力。她试图将他存在的痕迹从自己的经历中抹去,抹去一片蛛网,一块窗户上的污渍。她与自己达成和解,共同努力,一并忘记那段包括自己在内的漫长时光。忘记那条蛇。
他咳嗽起来,声音沉闷混浊,发音部位不是喉咙,好像也不是气管和肺部,而是向下的更深,甚至不是来自他的身体,是从地底下某处发送而来。她快步走过去,帮他捶背,排痰。他的脑袋伏在床边,脸向下,努力挖掘自己的咳嗽,将那些堵住呼吸的尘土石块尽快倒出来。他的头发好像竖了起来,泛着细汗,耳根和脖颈处都紫红了。她用了吸痰器。同时按了呼叫铃。护士开门看了一眼。
“没事吧?”她问。
“没事。”护士转身要走。
他一口浓痰吐在地上,又接连呕吐了几口,边吐边直着脖子咒骂,声音嘶哑。
护士听到了,回过来,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
“撤你的职!”他突然发出连贯的声音,清晰,响亮。
“我没职可撤。”护士也就二十出头,脸上还有婴儿肥。
“去死!”他又咳嗽起来。
接下来,他漫无目的地咒骂,声音宏亮,听上去不像病人,反倒像是年轻人,他身体的能量好像都集中在声音之中。她知道,这是他的职业习惯,讲话,训斥,说谎。他试图从床上爬起来,失去肌力的腿脚抽搐着。
医生走了进来,表情严肃得像是贴着一层白色大理石。护士一见,垂下头去。
“怎么搞的,”他对护士说,“通知精神科会诊,有躁动症状。”
护士快步出去了。
医生转过头来,对她说:“你做得不错,希望明天还能来,病人情况不稳定,他没有人陪护,当然,这得你同意才行。”
她点了点头。
没有人,不对,应该有很多。那些在他身居高位时簇拥着的人群消失不见倒在意料之中,这些人长久以来心怀憧憬与恐惧,他们并非无情无义,只是与他的关系中并未动用情义。现在,他们恐惧并不是医院重症室的阴影,而是那蓝色与红色交替闪烁,带着金属嘶鸣的警灯。似乎与他任何一点联系都会带来不明的危险,他们急于跳出从前那张看上去结实的网。他们在跳的时候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网,只是一些虚拟的影像,夹杂着酒席、交易、女人等等暧昧不清的投影。他们在他身边出现时,像是一个个道具,烘托突出他作为主题,或者,像是一个个数字,证明他手中就应该掌握着这些数量的命运。
还应该有一些人。他的父母过世,他还有一个兄长。可惜他提早将兄长驱散在视线之外,在兄长身患重症时,以在国外考察为由拒绝探视和捐赠。他以此为荣,宣称自己铁面无私,其实不过是嫌弃他们一家老小给自己带来的贫穷烙印和伴生的麻烦。他从小多得兄长相助,就业升职之后,回家,两手空空。那时,兄长家的孩子还小,上来掏他的衣服口袋,嚷着要糖。兄长准备了一桌菜,多是素菜,酒是自己酿的,味冲,上头。喝酒时,兄长不止一次地盯着他看,他笔挺的新衣服,耀眼的新手表,停放在门口的新自行车,兄长一碗接一碗地喝着酒,直到喝醉了,也没有说什么。后来,他越发春风得意,打扮自然越来越高档,车也越坐越豪华,多少年也不回乡。兄长住在老家农村,他住在城市繁华地段,他从未发出邀请,兄长也从未到他家里来过,偶尔进城,也绕过那个地方。多年之后,有一回,他的侄子失业,找上门来,求他想想办法。他不让进门,连电话也拒绝接听,直接扣掉话筒。倒是他老婆心里过意不去,在小区外见了侄子一面,塞给他一沓钱。现在,他老婆带着儿子在国外,两人办理了离婚,当时据说是假离婚,为保全财产。最后变成了真离,真真假假,已经失去了区分的意义,婚姻这件事情好像就在一张纸上。
他犯了事,并无多大意外,他从一开始就走在这条路上,惦量着监狱与自己的距离,走得富有节奏。如果算计精准,能赶在退休之前,还没有到达,那就是赢了,活着就是一场赌。如果赌输了,只得愿赌服输。想想那些普通人用几十辈子也积累不出的财富吧,想想儿子和儿子的儿子踩在自己身体上将要开启的上层人生。这本来并不意外的事,却出了意外。有个女人将他举报了,证据应有尽有。是与他关系不一般的女人中间的一个,他与这些女人在一起的时间不一,长短取决于下一个与他相处的女人何时出现。这时他们夫妻俩已经办完离婚手续,老婆和儿子已移居国外,手上叮当作响,一串打开那座隐匿宝库的钥匙。
“本来也不想这样做的,太狠,”该女人在手机里说,语调里同时缠绕着歉意与快意、爱意与恨意,“但是,不对你狠,对自己,就太狠。”
说完就挂了,他再将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已经关机,再打,已是空号。
事情还不止这些。他老婆那边,准备再婚,她的心早已给了另一个男人,这桩情事一直滋生在暗处,生机勃勃。更有传言,儿子也是那个男人的。有了离婚证书,一切都在合法中进行。
“是有些狠,”前老婆说,语调温柔,但是不容反驳,“当年你和我结婚本就是冲着老爷子的职位,这些年,你是怎么对我的,你在外面那些事,我都知道。”
事发后,最早来带他的不是警车,而是医院的救护车。他想自行了断,未遂,临下手时,手软了,腿抖了,刀丢了。但是从此之后,有一个自己已经了断,他陷入间歇性精神紊乱,而器官也仿佛加快了衰竭。他不必再行选择,医院,监狱,自会根据他的状况进行选择,他仿佛进入了一道机器轰鸣的工业流水线。
他还在骂着,指向模糊,声音越来越低。她慢慢打扫着地上发出恶臭的秽物,像是扫着暮春的落花。她向自己幽深的心里望去,那是某条蛇多年盘踞之所,已然空了,而那把刀,还在,好钢好刃,闪烁着微蓝的光。是一把精致的水果刀,上面扎着一块削好的苹果。
杰 作
在遇到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的时候,她正匆忙开始一段有头无尾的恋情。
他写了一本书,还没想好如何结尾。初春的寒意犹自浓着,树梢上按捺不住膨胀的亮色。他在河边小树林里走走停停,嘴里念念有词。无论是解冻的冰面还是拂动的柳枝,或是在河心枯黄的芦苇丛中跳动的野鸭,他都没有看到,停留在自己故事的迷宫,神思恍惚。没有行人,这正是他选择这里的缘由,写成这本书期间,他来了有上百次,已经隐约踩出一条小路来了。她的出现是个意外,后来在两人可以无话不谈的时候,她告诉他,自己当时寻到这处僻静的地方是为了解决内急问题。当时城市公厕系统还不发达,尤其对于女士来说,经常面临窘境。她是本地一家晚报的记者,正处在不分昼夜玩命干活、貌似不求回报、实则渴望至极的工作试用期。她经常外出采访,对此类问题颇有经验,一般是出发前少喝水,到达了厂矿企业就可以利用卫生间。但是没想到这次采访竟然全部在室外,沿途连一处可以利用的地方也没找到,只能到处找树多林密之处,没想到碰到他。当时已经进入解衣宽带的程序,幸好还没有完全暴露,窘迫加紧张,她立时出了一身汗。这种窘迫是他们开始的基点。
两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互相被对方惊吓到,盯着对方看了一大会儿,然后各自转身,渐行渐远。回来之后他就写出了小说的结尾,眼前不觉闪现出了那张涨红的脸蛋,笑了一下。她再也不敢在这里逗留,回到马路上,打上车。回到家,她长舒一口气,刚才,仿佛有一段思维掉在河边,这时才飞了回来。她也想起了那张白皙木讷的脸,撇了一下嘴,恨不能朝空中那个不存在的影像啐上一口。
几天后,她接到一项采访任务,竟然又碰到了他。惊讶之余,旧恨难平,如果不是现场还有别人,她早就一走了之。采访期间,她心不在焉,低垂着眼皮,拟好的采访提纲也没用。
他笑了一下,双手捧过一杯玫瑰花茶,说,初次见面,请多包涵。她心下一惊,原来对方没认出自己来,他可真健忘,这种健忘症太有益人生了。心下轻松,她也笑了一下,随手接过他递过来的那本小说手稿塞进包里。这个健忘情节被他掩藏得很好,多少年之后也没有暴露出来,直到她忍不住抖出小树林的旧账,他微微一笑,说,是吗?这种意味深长的微笑,她懂得,于是恍然大悟,猛捶他的肩膀,骗子,你这个骗子!
这个情节非常关键,否则她不会接过那本书并且沉迷其中拍案叫绝,不会因为要在报纸上为这本书这个人做点什么而得罪了上司,最后丢了可能被赐予的饭碗。当时,她扔掉采访包,重又背起大学时代的双肩包,将束起的头发重新披散开,并找到了利用风向使之进一步飞扬的角度,昂首挺胸地走了出来,好像不是她被拒绝,而是她把那些人那座七层小楼都抛弃的样子。威武!之后,她陷入生计困难,紧咬牙关勉力支撑,对任何人也没有说过。那段注定没有尾巴的恋情自然悄然隐去,仿佛并不存在。她知道恋情的那端,有一双眼睛偶尔也会远远地盯着她看,和几乎所有寻常的男人一样,聚焦的部位无外乎丰乳肥臀。就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书的作者寄来一张表,附带着一张说明。她用了五分钟就填好。第六分钟的时候,她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员工。当时她还不知道他家就开着一家公司,她就职的这家正是他们家的合作伙伴。他家的公司规模不大,但积累的资产已经够子孙三代使用了。父亲不让他染指公司业务,只让他上学,愿意上到什么时候就上到什么时候,愿意到哪里去读就到哪里去读。他却只愿意写小说。这是父亲禁止的内容之一,列在吃喝嫖赌抽之后。自古文章憎命达,父亲懂得,明智者应当将智慧集中到财富增值上,而在一些敏感话题的区域,心知肚明,大智若愚。写文章却与之背道而驰,聪明藏不住,嘴巴又爱动,容易招惹祸端。
他在那部小说的最后写道:那时我的眼睛里注满玻璃,撞碎了迎面而来的蝴蝶。
后来,他们有一段漫长的恋爱和短暂的婚姻。结婚是他们的恋爱持续奔跑的惯性使然,举办婚礼的时候就是恋爱的终点。他们本来不愿意举办婚礼,隐隐地感觉到这是一场以解散为主题的仪式,像是对自己过往的告别。婚后,有一些鸡飞狗跳、鸡毛蒜皮的争吵,但都不是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是这段感情,自己走向了末路,仿佛是食物过了保鲜期。他们都是很负责任的人,坚持要给对方一个交代,也算是给自己一个说法,忍着干涩的口感,把那变味的食物吃下,接受五脏六腑的翻腾。终于撑不住,他们平平和和地分开了,各自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像是解开了绑在身上的绳索。真的爱过,那爱至今也是真的,只不过不再属于他们了,那是属于幸运者的彩票,它选择了别的地方。离他们也并不远,好像就在高过他们头顶,跳起来正好抓不住的位置。
感觉对方依然是朋友,偶尔问候一下,却不再相见。两人的情感经历过恋爱和失恋,还保持着友谊,从里到外都披着冰雪,晶莹剔透,只有水的固体形态,似乎远离尘世生活。这倒是他们的理想,是当时敦促他们走到一起的共性。
她现在就职于一家知名出版社,做书,各种各样的,畅销书、童书,偶尔也做做经典。经过几次进修,出版过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她已具备了业内认可的资深眼光。在此期间,她一直没有翻动那本书。分手之后,她用一张旧报纸,把它仔细地包好,放在书柜的顶层,不踩着凳子再踮起脚,根本够不到。这几年过年大扫除也没有打扫过那里,那本书上均匀地保存着他们分别之后所有的灰尘,就像经历过的所有时间和记忆的碎末,一点也没少。也许她在心里暗暗的有一个主意,连她自己也不知晓,不想再打开它了,让它成为一件沉睡的古董,安静地沉没在无边无际的海底,像一艘数百年前的沉船。那里面也许有无穷无尽的珍宝,也许只是腐烂种种,不再搅扰它,让它在海底无尽的暗处航行。
在他们甜蜜航程开始的那一段,她天天把书放在床上,随便翻开一页大声朗读,毫不吝惜五颜六色的赞美之辞,将肚里能用于夸奖的词汇,颠三倒四地说个干净,以至于后来当她推荐好书,撰写评论的时候,感觉这些话都是在重复过往。不必再打开,她几乎能背下那本书,熟到不能再熟,就像对于那个男人,似乎每一个毛孔她都清楚地知道位置和形状。忘记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已经与自己的那一段生命合体。有一段时间,她经常会涌起想忘记他这个念头,做了很多努力,无功而返。只能等来生吧,她自言自语地说。
她没有想到他的来生这么快就到来,如果有的话。她希望他变成一只什么动物,或是草木石头也行,最理想的是变成文字,经由自己的手缓缓地流出,就像是拨弄出来的琴音,就像是初春的柳枝拂过流水的表层。
她又拿出那本书来。附着一层暗黄的灰尘,和她想象的一模一样。她没有立即打开,只是静静的看着那层灰。灰尘之下,应该保留着他们俩密集的指印,温柔地交叠着。
以专业编辑的眼光,她很容易判断出这本书的价值,但是她一直没有启用这种判断。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的狂热,后来的索然无味与伴生的无聊,甚至生出蔑视和厌弃。
这是一本有些潦草的手稿,后来打印出来,复印若干,两人曾经反复向杂志社出版社投过,都是石沉大海的结局。后来当他发达之后,结交了一些出版界的朋友,印出了精装本,赠阅给朋友和自己的公司职员。还举办了一个规格颇高的研讨会,当时他有条件,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举办得更大,邀请的名人更多。那些人脸色带着酒桌上残余的红润,口吐带着荤腥气味的莲花,几乎将他捧到了天上去。她听闻之后,冷笑了一下,当时心想,自己不会对这本书再说一个字了。
他没有再写别的东西。当年他的父亲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遭遇破产,身心受到重创导致偏瘫,他接手了父亲的债务。原本这是一份庞大的家业,父亲不让他参与,说是为长子自立着想,实则是想留给自己的幼子。这也是幼子母亲的主意,长子是前妻所生。
他做起了产业,慢慢偿还了债务,后来大有盈余,走向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与他们爱情的走向几乎同步。在他产业做到最大的时候,他们离的婚。之后他慢慢地暗淡,人生轨迹竟然与父亲雷同。仿佛这条轨迹始终存在,总要选择一些代言人来承载。
实业不好做,有什么是好做的?财富的金光本来就伴生着荆棘与陷阱,那些血腥和罪恶是与生俱来的。他知道,在他的小说里也是如此描述,那个小说人物是他模拟出来的,却又真实地在自己身上演绎,他竟然提前为自己写了部自传,一语成谶。
如果当年他父亲不遭遇变故,他就不会抽身去拯救家庭,不会深陷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他的器官不会因为过度的劳累,算计与酒精轮番轰炸而崩溃。他会继续写小说,或者随便写一点什么,哪怕不写,就是到河边那条偏僻的小树林里散散步,撞见一些有趣的情节,如果。
她打开手稿,重新翻阅,如此熟悉,就像是看到那个人,还有那个自己扑面而来。这对年轻人被压在这里许久了,又饿又渴,是不是还有人内急难耐呢?她觉得自己应该笑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她将手稿一页页的烧掉,每天看几页烧几页。祭奠过程很是漫长,从冬末开始,等到就要完成的时候,花期早过。
她的目光停留在小说的最后一页,那只被撞碎的蝴蝶。这一页没有烧,这不是他写的,而是她自己,是她在那天,跳进小河那个情节里去。
她希望,他会慢慢地修改,就像当年两人开玩笑说的那样。否则,做什么呢。死去之后的时间如此漫长,无休无止。而,结尾就留在自己手上,所有的修改都会走向这里。
反复回味,冷静审视,不带感情,也不带偏见,她终于以业内顶级的眼光审了一次稿。
一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