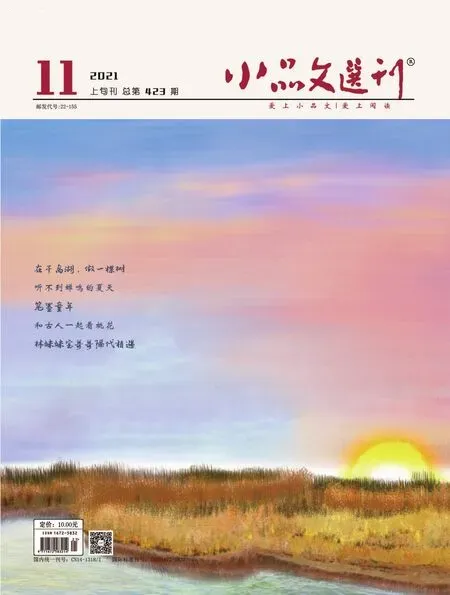栀子花,开呀开
□汤素兰

跟城里人不同,我们乡下人不需要种花。山坡上,田野边,春夏秋冬,四时八节,漫山遍野的草木都是我们种的花。
然而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曾种过一丛栀子花。
栀子花是常绿灌木。它的主干比较粗,呈灰色,若不是主干上又长出绿色细枝条,单看主干,肯定要误以为它是一段干柴。当然,你若不拨开树丛往里看,是看不到栀子花枝干的。因为栀子花的叶子很浓密。那些椭圆形的叶子,每一片差不多有三指宽,叶片厚实,两片或三四片叶子组成一轮。一根枝条上长着好几轮叶片,它们密密实实地挤在一起,将栀子花丛围得像一张绿色的大圆桌,于是,那些开在绿叶间的栀子花,就像摆在桌子上的一碗碗美食。
栀子花花期很长,从五月可以一直开到八月。但五月的栀子花开得最盛,花朵也最大。韩愈有诗“芭蕉叶大栀子肥”,这个“肥”字用得真好,当然,也只有五月的栀子花,而且是像我家院子里那样的大花栀子,才当得起这个“肥”字。
进入五月,南方雨水渐多,万物生长,蛙鸣鸟叫,天空和大地上的一切都热闹起来,栀子花也赶着趟地盛开。每天清晨,栀子花的清香会随了微风从窗户飘进屋内,把我唤醒,闻着花香,我便知道,院子里又有新的栀子花开了。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去摘栀子花,这是我每天的“早课”。然而,蜜蜂和蝴蝶总是起得比我早,等我赶到的时候,它们早已经围在这绿色的餐桌上,嗡嗡嗡地闹成一片,争先恐后地品尝那一朵朵新鲜的栀子花。
这花可不是给它们吃的!我赶紧冲过去摘那些新鲜的栀子花,生怕慢一点,它们就会把栀子花吃掉了。
那时候,我家院子里的栀子花不是用来观赏的,我把它们摘下来也不是要插在瓶子里闻花香,而是用来做菜吃。母亲把我每天摘下来的栀子花用开水焯一下,放入清水中浸泡半天,然后沥干水,加入青椒或者红椒,用大火爆炒,便是一碗菜,够全家人吃一顿。
后来我读到杜甫的诗句“栀子红椒艳复殊”,舌尖上立即有了红椒炒栀子的味道,完全没有体会到杜甫在这儿是写景,也不知道他写的“红椒”并不是我们今天吃的红辣椒,而是花椒。味觉记忆让我本能地认为,这就是一道菜,想到诗圣杜甫曾像我一样吃过红椒炒栀子,便觉得这诗特别亲切,特别接地气,有浓浓的烟火味。
那丛栀子花在院子西边,靠着院墙边的土墈。下大雨的时候,雨水常把土墈上的泥沙冲下来,积在院墙的阳沟里。每次大雨过后,爷爷总要清理阳沟,把那些冲积下来的沙土堆在栀子花丛周围,日积月累,那儿便比院子略高,土质也变得松软肥厚。栀子花长在这里,土地里的营养充足,天空中的阳光也充足,又背靠土墈,可以挡了太阳的曝晒,真是得天独厚,难怪一年四季都绿得像要滴出汁液来。
我家屋后的山坡上也有栀子花。也许是因为山坡上的土层贫瘠,这里的栀子花丛虽然多,但每丛都不大,叶片不如院子里的栀子厚实,绿得也没有那么深,带一点点黄色。院子里的栀子花是重瓣的,山坡上的栀子花是单瓣的。如果将花丛比作桌子,院子里的大栀子花丛是大圆桌,山坡上的栀子花丛就像小茶几。如果用餐具的大小来比,院子里的大栀子花每一朵都有我们平时盛饭的饭碗大,又深又结实;而山坡上的栀子花像小茶碟,六片花瓣围成一个圈,像浅浅的小小的白色碟子放在小几上,倒也十分般配。不过,它们的花朵虽小,但每一丛花儿开得多,相比院子里的大栀子花东一朵西一朵孤单单地开,山坡上的栀子花挤挤挨挨,吵吵嚷嚷,完全是一副热闹非凡的样子。
山上的栀子花会结出纺锤形的小果子。果子起先是像叶子一样的绿色,等到秋天,果子成熟了,就会变成金红色。它们小小的果壳上还有几条棱,恰似巧手扎出来的红灯笼,缀在绿叶丛中,玲珑而又喜气。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会把这些红灯笼一颗颗摘下来,晒干,卖给药店换钱。这是我的小秋收。因为摘它们,那些日子,我的手指会被染成黄色,衣服上也会有好几处黄色的斑点,怎么洗都洗不掉。大概因为这黄色,山上的栀子花又叫“黄栀子”,它含有天然色素,也是一味中药。
如今,老家的房子经过几次改造,已不复从前的模样,院子里没有了当年的栀子花。屋后的山坡,从前的山路长满杂树芒草,不能容人通过,山上林木丰茂,遮天蔽日,没有了喜光的黄栀子的生长空间,成了野生动物们的乐园。但那一朵朵洁白的栀子花,永远盛开在我的童年。虽然隔了遥远的时空,我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仿佛又嗅到了栀子花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