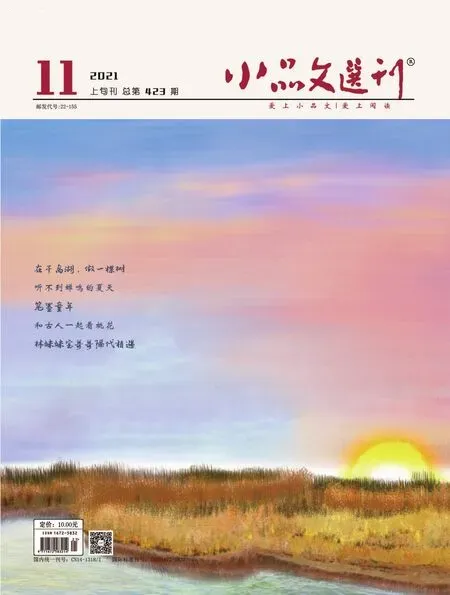干菜的滋 味
□王祥夫

那些年,人们晾晒干菜成风,秋风一起,巷子里到处都可见晾晒的萝卜干、干白菜、干豆角、干葫芦条什么的,几乎是家家如此,什么东西可以晒干储存到冬天就晾晒什么。有晾晒西瓜皮的,晒干的西瓜皮吃的时候发好,以其炖肉不赖,比冬瓜有嚼头,做什锦果脯,西瓜皮做的瓜条比冬瓜做的口感好。北京有名的“四季青”,年年冬天上市的洞子菜,是过年过节人们桌上的稀罕物。洞子菜由来已久,所谓的洞子,和现在的大棚差不多。洞子韭黄、洞子黄瓜、洞子菠菜,尤其是洞子黄瓜,在清代贵得惊人,有野史记载,一根黄瓜当时要卖到二两银子,负责给皇帝采买菜品的太监嫌贵,卖黄瓜的二话不说,拿起一根转眼吃掉,太监急了,说你不能吃啊,你再吃我就买不到了,再买剩下的那根,又长了二两银子。过去在冬季,想吃一口新鲜菜谈何容易。为了在冬季能吃到菜,人们穷尽了各种办法,一是腌渍,二就是干制。三就是买大量的大白菜和土豆放在闲房子里,闲房子不住人,冬天不用生火,可以储存这些菜,但手要勤,要不停地翻腾,把菜倒来倒去才不至于烂掉。在过去,人们住四合院,冬天储存菜不成问题。现在的四合院不是一般人能够住得起的,住楼房,到了冬天,要说储存菜,只是个遥不可及的童话。好在现在吃什么东西都已经不分季节,你想吃什么都有,只要你口袋里不缺“阿堵之物”就行。
各种的蔬菜,只要是晾制成干菜,味道就一定会比鲜的时候浓。我现在很怀念母亲在家里煮干菜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干菜泡好还要煮一煮,放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这一般都是干白菜,家里煮干菜的时候一定是冬季,窗玻璃上腾满了水汽。白菜干煮好了有几种吃法,放点儿肉当然更好,但要油大一些,可那时候哪有那么多的油?干白菜又特别吃油,吃足了油,这干白菜就会变得十分的腴美,但一定要是荤油才行,菜籽油熬干菜不行,油都会浮在上边,吃不到菜里边去,只有用大油,菜和油才会打成一片。干菜的另一种吃法是蘸大酱,煮好的干菜蘸大酱味道挺特殊。干菜做包子馅儿也挺好,但也一定要油大,做饺子馅儿比较少见,不容易包好。
我家里有一把剪子,母亲曾用这把剪子剪豆角,每年都要剪许多,剪好放在外边晾,冬天就有得干豆角吃。有时候晾好忘了吃,隔了年或者又过一年,那干豆角拿出来还那个样。干豆角、干葫芦条子、干蘑菇、金针、干苤蓝叶子,如果有,再加些油炸豆腐,统统放在一起炖,味道可以传出很远,那种味道让人感觉到平淡的日子有平淡的好。怎么炖干菜的味道就一定会让人觉得平淡呢?那味道当然是平淡朴素,炖肉,爆炒,煎鱼的味道是强烈的,是轰轰烈烈,是厨房里看不到的敲锣打鼓,而炖干菜却真是平平淡淡。炖什锦干菜,配以小米捞饭,殷实而不动声色。
去海边,见人家的墙上黑乎乎拖拖拉拉晾了不少东西,问了一声,答道:晾干菜。
走近了看,是海带,海边的人把海带叫“干菜”。
菠菜是一种一旦有了水就不停生长的蔬菜,我见过那种大棵的菠菜,比我都高,人猫在那种菠菜地里想必是干什么都不会被别人看到。把这种大菠菜连根拔下,把枝枝杈杈打了用开水拉过搭出去晾,晾干后的颜色是黑的,而那老粗的菠菜秆儿也有用,可以用来腌制。腌好后的菠菜秆儿和绍兴菜里的“臭苋子”一个意思,一吸一“咕叽”,一吸一“咕叽”,也是既酸又臭,但十分下饭。干菠菜在我们那地方一般用来吃馅子。别看干菠菜黑,用开水一焯,马上就会又碧绿起来,以其拌馅子特别好看。
中国人吃东西,从来都是“一看,二吃”。
吃饭用嘴,但从来也离不开眼,没人闭着眼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