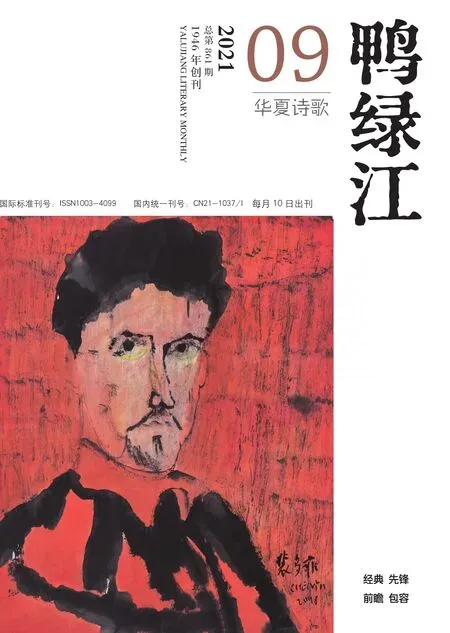于坚:一个现代主义 诗歌的逆子
李东海
于坚是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中岁数较大上学较晚的一个。1954年出生,26岁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十几岁就爱上了诗歌,1979年见到北岛创办的民间诗刊《今天》,如获至宝,成为朦胧诗派的追随者。1983年创作《尚义街六号》,1984年与诗人韩东等创办民间诗刊《他们》,开始走上一条自己独立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之路。下面我们就从于坚的四首诗中看看他的诗歌风格和诗歌本质。
他天天骑一辆旧“兰铃”/在烟囱冒烟的时候/来上班//驶过办公楼/驶过锻工车间/驶过仓库的围墙/走进那间木板搭成的小屋//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看到他 就说/罗家生来了//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谁也不问他是谁/全厂都叫他罗家生//工人常常去敲他的小屋/找他修手表 修电表/找他修收音机//文化大革命/他被赶出厂/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一条领带//他再来上班的时候/还骑那辆“兰铃”/罗家生/悄悄地结了婚/一个人也没有请/四十二岁/当了父亲//就在这一年/他死了/电炉把他的头/炸开一大条口/真可怕//埋他的那天/他老婆没有来/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他们说 他个头小/抬着不重/从前他修的表/比新的还好//烟囱冒烟了/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罗家生/没有来上班
——《罗家生》
这是于坚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对于当下这样一个弱势人物的草根命运,诗人在生活的底层发现了他,感受了他。于是罗家生成为了诗歌人物,成为于坚挖掘诗歌主题的铁矿。于坚从罗家生骑一辆旧“兰铃”自行车在烟囱冒烟的时候到厂上班入笔,写到他唯一能被工友记住的家电手表的维修技术,写到他的因工殉职和葬礼。诗歌的情绪是低调的,叙述是舒缓的,故事是平凡的。他似乎把罗家生整个地放在了一个黑白故事片的放映之中。但它给读者的心理感受却是:平淡中的凄厉,漫不经心的震动和低色调里的悲悯。小人物反映大背景。在“文革”人道主义缺失的历史中,草根人物的命运如此卑廉。但诗人没有揭露,也没有批判,诗人只是用平淡的叙述:“埋他的那天/他老婆没有来/几个工人把他抬到山上/他们说他个头小/抬着不重。”一个无足轻重的工厂工人,死后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呢?诗人没有议论,没有抒情,只用了很短的文字:“烟囱冒烟了/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罗家生/没有来上班。”
人的生命就这样平淡地开始和结束。这是大众民生真实的生活状态,也是诗歌所忽视的一个死角。于坚走上诗坛,就以“民间立场”反映民间的平民生活,这是诗歌的进步,也是诗歌人文主义的提升。
1983年,于坚写了《作品39号》,把写《罗家生》的笔调和风格彻底贯彻到了这首诗中:
大街拥挤的年代
你一个人去了新疆
到开阔地去走走也好
在人群中你其貌不扬
牛仔裤到底牢不牢
现在可以试一试
——《作品39号》
《作品39号》是于坚对平凡人物生活的又一次表达。这个其貌不扬要去新疆的朋友,在与诗人道别的时候,诗人没有形而上的人生哲学,没有经世致用的生活秘诀。只是说出了酒中之言:“其实你心里清楚/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在今天这样开放的年代,人有必要把自己装得那样“深沉、高贵”吗?一切以“某状”出现的戏子,只有自娱自乐,没有人会欣赏的。说实在的,我们天天向上地努力,不就是想活得像个人样么!
于坚诗歌的反崇高,反虚伪和反贵族倾向尤为突出。生存的现实性、平民化,是于坚诗歌的表达主题。他从生活琐事的叙述性,到诗人自身的自言自语的平民化观照,都以日常的口语和低调的陈述来完成。诗歌文本在于坚的眼中,已是一种旧街的雨巷和淋湿的雨披。诗人退出诗歌,让生活和生活者说话,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王牌和格言,于坚做得很彻底。然而他后来走得太远,已经走到了诗歌难以容忍的边缘。他在《作品39号》中最后这样结尾:
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
抱着三部中篇一瓶白酒/坐在那把四川藤椅上
演讲两个小时/仿佛全世界都在倾听
有时回头照照自己/心头一阵高兴
后来你不出声地望我一阵
夹着空酒瓶一个人回家
于坚在这里想干什么?于坚想用这种流利的口语短句,撬开诗歌语言的大门。于坚是智慧狡猾的,他在自己的诗歌中,不断营造一种与读者的亲和力:语言流畅,含义明确,人物普通,事件琐碎。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意象艰深、主题繁复的诗歌,让一些读者云里雾里,可是于坚给他们提供了可口的快餐。
于坚在《远方的朋友》中给我们展示的他所料想的当下的人际场景:
想到有一天你要来找我
不免有些担心
我怕我们一见面就心怀鬼胎
斟字酌句 想占上风
我怕我们默然不语
该说的都已说过
无论这里还是那里
都是过一样的日子
无论这里还是那里
都是看一样的小说
我怕我讲不出国家大事
面对你昏昏欲睡 忍住哈欠
我怕我听不懂你的幽默
目瞪口呆 像个木偶
我怕你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
我怕你客客气气 彬彬有礼
远方的朋友,你还来吗?你是读者,我是作者,我们应该热情洋溢地大谈文学;我们应该激情飞扬地共叙情谊。但于坚诚实地说出“我怕我们一见面就心怀鬼胎”,“我怕我讲不出国家大事/面对你昏昏欲睡忍住呵欠”。于坚是用无诗意来反诗意,用正经来反假正经。他一直在扮演局外人的身份。设想的与远方朋友相见的这一庸俗的场面,是否就是我们许多朋友相见的现实呢?于坚对于朋友的奢望不高,但他知道朋友的意义所在。所以他最后坦言:
远方的朋友
交个朋友不容易
如果你一脚踢开我的门
大喝一声:“我是某某!”
我也只好说一句:
我是于坚
——《远方的朋友》
他在蓝星诗库为他出版的《于坚的诗·后记》中这样说过:“我的主要作品是在一个普遍对诗歌冷漠的时代写作的,伴随着这部诗集的是贫穷、寂寞、嘲讽和自得其乐。”于坚是那种耐得住寂寞的大诗人。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诗人至今仍坚持写诗不多的那一个。《尚义街六号》是他1983年写的代表作,也是他自认为的得意之作,他在《棕皮手记》中谈到这首诗时这样说:“在1986年《诗刊》11月号头条发表后,中国诗坛开始了用口语写作的风气。”但是极力推崇“口语化”和“日常生活经验”写作的始作俑者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卡洛斯·威廉斯。威廉斯以此来反对艾略特的贵族化诗歌写作。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其次,要注意对阿姨生活技能的培训,包括沟通的技巧、分析问题的能力等,很多阿姨不能正确理解雇主的话语,出现不正确的解读,很多阿姨不会说话,说话的方式和方法不能有效传递信息容易以引起矛盾,导致与雇主的沟通出现问题,包括不能做到换位思考、不能从雇主的角度看问题、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些都源于在沟通和分析上的能力缺失。这是生活技能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家政服务本身。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识凡高
——《尚义街六号》
是智慧的年代
许多谈话如果录音
可以出一本名著
那是热闹的年代
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
今天你去城里问问
他们都大名鼎鼎
于坚在《棕皮手记·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中这样说:“诗人确实必须坚持地放弃那些世俗角色,仅仅作为诗人,去投入、去想象、去吐血,他才会写出真正的作品。”于坚是写出真正作品的诗人。虽然当时他把自己的画像钉在墙上,没有多少人正视,但今天的文学界,还有不认识大诗人于坚的吗?《尚义街六号》整首诗都以市民白话构造句式,在当时真的搅得诗坛沸沸扬扬。
一年十二月
您的烟斗开着罂粟花
温暖如春的家庭 不闹离婚
不管闲事 不借钱 不高声大笑
安静如鼠 比病室干净
祖先的美德 光滑如石
永远不会流血 在世纪的洪水中
花纹日益古朴
作为父亲 您带回面包和盐
黑色长桌 您居中而坐
那是属于皇帝、教授和社论的位置
——《感谢父亲》
《感谢父亲》是于坚1987年的力作。诗人们在歌颂父亲的时候,往往都是以威严、高大、出色、胸怀宽广来形容父亲。可在于坚的笔下,父亲是“作为好人爸爸您活得多么艰难/交代揭发检举告密/您干完这一切夹着皮包下班/夜里您睡不着老侧耳谛听/您悄悄起来检查儿子的日记和梦话”。在那非常的岁月,作为父亲,是那么的不易,那么的卑微和那么的和蔼可亲。作为好人的父亲,也揭发、检举、告密。干完这一切后,晚上忐忑不安地深怕儿子告密。于坚理解父亲的所做所为,深知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父亲是多么的艰难,“就这样在黑暗的年代在动乱中/您把我养大了领到了身份证/长大了真不容易爸爸/我成人了和您一模一样”。
陈光旭在《百家点评·序》说:“‘他们派’代表了诗歌语言‘口语化’追求的一种向度,构成了对经典性的以‘象征’为核心的‘朦胧诗’语言艺术规范和秩序的反叛和颠覆。”于坚是“他们派”的抗鼎之人,他在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中,作出了一定贡献,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他总是用细腻无比的语言和故事,叙述和描写生活的琐碎事件,诗歌主题的琐碎、零散,句子的泛散文化,最后使他把诗歌当作小说去写了。那么以后的小说是否可以写成诗歌呢?所以我说于坚是用口语和叙述,改变诗歌表达方式的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