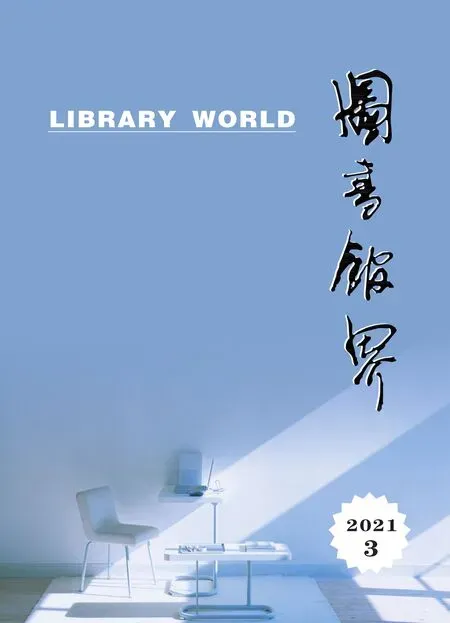《持静斋书目》及其对丁日昌洋务思想的反映
郝子靖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香港 999077)
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一作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咸丰四年(1854年)入仕,历任万安、庐陵知府,后入曾国藩幕府,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被举荐至上海参与筹办上海机器局(又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四年(1865年)任苏松太道,兼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同年10月任两淮盐运使;其后又历任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光绪六年(1880年)任会办南洋海防、节度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丁日昌还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与朱学勤、李盛铎并称“咸丰三大藏书家”。
1 丁日昌藏书概况
丁日昌藏书的来源主要有三处:一是在“庚申之劫”收购于苏州顾沅“艺海楼”;二是收购于上海郁松年“宜稼堂”;三是零星取得于江浙一带的书肆、藏书家。丁日昌的藏书楼名为“持静斋”,初名“实事求是斋”,又有“百兰山馆”“读五千卷书室”“洁园”等名。
丁日昌的藏书前后曾经过多次编目,其中较为重要的为以下四次:第一次为藏书于“百兰山馆”时由林达泉所编,编成《百兰山馆藏书目录》,已佚。第二次则是主要由莫友芝编写的《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记要》,而丁日昌及其门人也对二者进行了增补,增《持静斋续增书目》一卷于《持静斋书目》(合为五卷)。有关《持静斋书目》与《持静斋藏书记要》的区别,冯建福指出,《持静斋藏书记要》“只著录丁氏所藏宋元刻本及名抄、名校等‘传本稀见’者,实为善本目录”,而《持静斋书目》则“著录藏书三千三百多种,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持静斋藏书概貌”。这种说法可以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莫友芝给丁日昌的书信为证:
《静持斋书目》,自六月中旬考证次叙,其单部及零星之件,都有头绪,约费四十日整功。唯丛书十余种,尚未件分。其编例大致依《四库全书总目》,每类各依时代;每部下,其收入《四库提要》者,但以“《四库》著录”“《四库存目》”分注;中有宋元旧本及旧钞善本,则于分注下疏记数语以明之;其《四库》未收者,但分注刊写字;其中有未传秘本,则各系以解题。俟全目脱稿后,更于其中将有解题、有疏说者,别录出为册,使一备一精,各自为编,而此目乃完也。
第三次则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江标“以宋、元、校、钞、旧刻五类分别部居”,编为《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刊印。第四次是在1945年,由温廷敬以“宋元刊本”“明本”“钞校本”三卷编写的《持静斋善本书目》(稿本)。而本文的论述对象则是经莫友芝撰写,由丁日昌及其门人加工的《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记要》。
2 《持静斋书目》的特点
《持静斋书目》(卷一到卷四)大体按照《四库全书总目》以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其中,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十类,共四十九小类。具体如下:
经部: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集部:楚辞、别集类一(汉至五代)、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祐)、别集类四(金元)、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别集类六、总集、诗文评、词曲
与《四库全书总目》略有不同的是,《持静斋书目》将集部中的别集又按时代拆分为五个小类,与集部其他类同属一级。
《持静斋续增书目》(卷五)则按四部分类法合为一卷,其中,经部七类、史部二十二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七类。具体如下:
经部:易、诗、周礼、仪礼、春秋、五经总义、小学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情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其目的是为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除市民社会的异化,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该理论虽然存在有诸多的不足,但其中蕴含着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具有合理性。
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传记、载记、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水、外纪、职官、官职、仪制、邦计、目录、金石、史评
子部: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算学、艺术、杂技、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
集部:别集类(汉至宋)、别集类(元)、别集类(明)、别集类(国朝)、总集、诗文评、词曲
相比主要由莫友芝编写的《持静斋书目》(卷一至卷四),主要由丁日昌编写的《持静斋续增书目》(卷五)的分类方法更为细致,他将史部中的地理类拆分为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水、外纪等小类;政书类拆分为仪制类和邦计类;目录类拆分为目录类和金石类;将子部中的艺术类拆分为艺术类和杂技类。这些拆分后的小类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是“类”的下一级分类“属”,而丁日昌将其提升至“类”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注重实用性的思想。
《持静斋藏书记要》为善本目录,分为宋刊本、元刊本、明刊本、钞本四类。其中,前三者编为上卷,而钞本则编为下卷。《持静斋藏书记要》中所记载的书目质量很高,珍贵的宋元刻本、钞本较多,因此,丁日昌也有“百宋千元”之称,可见丁日昌在文献保存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其中,最为精良的有宋本《毛诗要义》、宋本《仪礼要义》、宋本《汉书》、宋本《西汉会要》,等等。
关于《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记要》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详尽记录了书籍的作者、内容、卷数、版本及流传,在《持静斋藏书记要》中还注明了是否收入《四库全书总目》;2)注明对书目的批注、题跋和校点;3)纠正前人著录书籍的一些错误;4)对书籍版本的优劣进行简要品评。《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记要》的学术价值,正如张燕婴所言:“由于丁日昌的藏书至今尚存者不少,故此二目的作用不只在了解持静斋之过去,也有现实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持静斋藏书记要》收录的多为稀见刊本、钞本与稿本,且详记版本特征,也可以借以作为判断善本与珍稀传本的重要依据。”
除了在文献学方面的学术价值,《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记要》还从侧面反映了丁日昌的洋务思想。
3 《持静斋书目》与丁日昌的洋务思想
3.1 西学为用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丁日昌认识到自强御侮的重要性,认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而与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王韬等人的接触也使他加深了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主张“师外人之长技为己之长技”。这种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洋务思想,不仅体现在他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创设新式海军等实事中,还体现在他的藏书中。
《持静斋书目》收录了一些有关西方科学技术、天文算法之类的著作。《持静斋书目》前四卷中子部的兵家类收录了汤若望(德国人)授、焦勖述的《则克录》一卷,其本名《火攻挈要》,咸丰元年刊本,是火器技术的著作;子部的天问算法类收录了《天问略》《月离》《代数学》《谈天》《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重学》《圆锥曲线说》等西洋著作;子部的杂家类收录了李善兰译著的《植物学》。《持静斋续增书目》子部的兵家类收录了《则克录》三卷(丁拱辰刊本);子部的杂技类收录了邓若函(德国人)授、王征述的《泰西奇器图说》(物理学著作);子部的杂家类收录了英国韦而司撰写的《化学鉴原》。
《持静斋书目》还收录了一些记载海外地理、历史、法律的著作。《持静斋书目》的前四卷史部的地理类收录了《职方外纪》《万国公法》等译著以及《佛国记》《西洋朝贡典录》《海国图志》等中国人编写的“外纪”。《持静斋续增书目》史部的外纪类收录了日本人赖襄撰写的《日本外史》。
除了《持静斋书目》所记载的,丁日昌还阅读了王韬和黄达权翻译的《火器略说》、容闳翻译的《地文学》、王韬编写的《法志》《俄志》《普法战争》等书,而他自己也对西学书籍的编写和翻译有所贡献,如编写了《地球图说》《枪炮图说》,招募贤才翻译西洋军火书如《炮录》和各国地理、历史书如《法人游探记》。
3.2 中学为体
丁日昌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向西方学习的仅限于科学技术,而非西方的思想与政治制度。他在《海防条议》中写道:“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于东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之正气,靖彼之戾气,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有识者所窃笑也。”丁日昌并没有倡导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而是继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固守的依然是封建伦理教化。在对待小说和戏曲上,他的想法和清廷是一致的,认为“淫书小说,最为蛊惑人心”,主张“尊崇正学”“力黜邪言”。
《持静斋书目》(含《持静斋续增数目》)并没有收录通俗小说和戏曲,其子部的小说家类中收录的作品大多为唐宋的文言小说,而明清时期撰写的作品仅有15部,像《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作品当然没有包括在内。尽管他青年时期便已熟读《红楼梦》,但他在江苏巡抚任上却严厉查禁这些作品,所禁小说、戏曲者有数百种之多。他在同治七年(1868年)发布的通饬令中写道:
“查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传》《西厢记》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分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札饬……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
丁日昌亲自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农民起义,也曾不敌太平军,因此,他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他认为《水浒传》《西厢记》之类的“淫词小说”会蛊惑人心,或教人犯上作乱,或败坏传统道德,必须严令禁止,否则会导致社会内乱。这种想法将时局动荡的原因过于简单化,也将小说、戏曲的影响过于妖魔化。他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封建王朝根基不稳的深层原因,而这也正是洋务派“中学为体”思想的局限性,即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
4 结 语
《持静斋书目》较为详细地反映了丁日昌的藏书情况,为后人学术考辨提供了依据,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丁日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随着晚清新学的兴起和书籍空前的繁多,像《持静斋书目》这样依循四部分类法已难以满足分类的要求。相比之下,康有为编写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编写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编写的《东西学书录》则摒弃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与现代的图书分类法较为接近。从中也可以看出,目录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