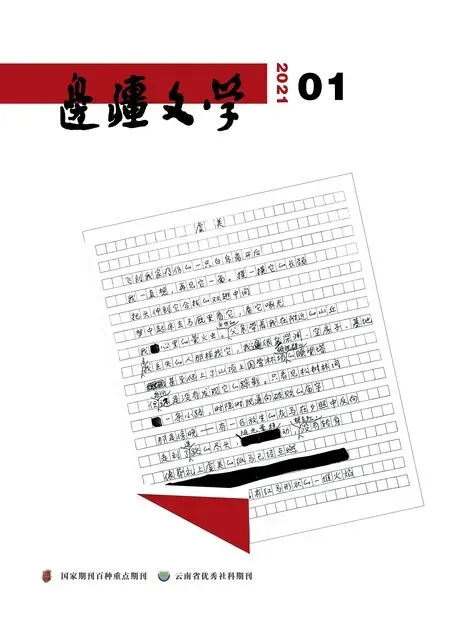行踪与真相
——论何晓坤的诗歌创作 评论
高文翔
何晓坤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起步时期属于著名的云南昭通师专文学群体,作为学校文学社社长的何晓坤,自然是其中的重要骨干。1986年毕业后,何晓坤回到故乡罗平教书,继而融入到当时的滇东文学群体中,成为当时曲靖诗坛一颗闪亮的新星。1990年3月,何晓坤创作了自己前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大鸟》,这首诗后来获得了在当时影响广泛的“1992 首届珠江源杯全国诗大赛”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至90年代的中期,这是何晓坤诗歌创作的丰收期。1996年6月,何晓坤创作了长诗《颂辞》,这是诗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此后何晓坤的人生足迹发生改变,涉足政商两翼,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2002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何晓坤的诗集《蚂蚁的行踪》,这是诗人对自己前期创作的一个展示和总结。时间进入2010年,当很多人都以为何晓坤不会再涉足诗歌创作时,何晓坤却迎来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又一个爆发期,在秋冬之际一口气创作了数十首品质上乘的诗作。在何晓坤的诗歌创作历程中,这一前一后、一断一续中间相隔15年。何晓坤的前期诗歌究竟具备哪些突出特质?诗人新近创作的这些诗作,它们所展示的究竟又是何种样的新面目?笔者试图对何晓坤的诗歌创作进行论述。
一
从收入诗集《蚂蚁的行踪》的诗作来看,何晓坤写作时间较早的诗作是写于1985年11月的《画像——祭爷爷》,及写于1986年11月的《老祖母》《忆祖母》三首诗。其中《画像》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爷爷/没有鼓声和雷声/你就把岁月之刃扎入脖颈/用血开始化妆用血染红祭坛”。《老祖母》一诗中说,“那一年发生了罕见的干旱/老祖父悄悄地枯萎了/剩下不倒的树杆/悬挂着老祖母”。虽然从这些零星的诗句中我们尚未看到事情的全貌,但我们已然确切感受到这些过往事件对刚刚涉足诗歌创作的何晓坤的影响。在诗人雷平阳谈论何晓坤诗歌创作的《无形的家居》一文中,我接触到何晓坤1986年夏天写出的另外一些诗句:“1972年是个黑色的洞/站在洞口上的我只有七岁/洞外好大的风/奶奶我站不住了呀/七十多岁的奶奶脖子上挂着木牌/她望不见我/她干枯的白发被风吹走/她以膝代步/路上铺满了破碎的碗片/闪闪发光/奶奶的血像一朵朵被风吹下的花/装点大路……”这帮助我们多少明白了诗人这些诗作中所指涉的事件的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个社会曾经刻意地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中国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曾被那个时代狠狠地踩在脚下。和所有隐起尊严惶惶苟活的人们一样,何晓坤的祖辈显然也是那个特殊时代毫不起眼的渺小的祭品。这些事件到今天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了,但祖辈曾经的遭遇,却成为诗人何晓坤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一个巨大阴影。在写于1988年12月的《颂歌》一诗中,诗人动情地写道:“亲人呐亲人/在你们匆匆的足音里/我的理智和情感都将疼痛终生”。出生于罗平富乐大山深处的何晓坤对自己的家族和亲人一直怀有绵延深广的笨拙偏执的爱,亲人的不幸是诗人灵魂深处永远的痛。这种沉重浓炽而简单执着的情感,是何晓坤诗歌精神的支点,同时也是他俗世生活的支点。 我想,这是我们理解何晓坤诗歌悲怆沉郁风格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何晓坤,其诗歌创作的一大走向是对以故乡罗平和滇东高原为地缘背景的风俗民情和自然风物的描绘与表现,总体看这与当时曲靖诗坛、云南诗坛的诗歌时尚大体一致。当时何晓坤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所关注的并非仅是那些人们通常认为的高昂提气的描述景象,和别人不一样,何晓坤明显地关注到死亡主题,并尽情地予以展现。如在写于1989年2月的《入棺调》一诗中,诗人以民间巫师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告白,全诗富有浓烈鲜明的民间色彩:
此时是吉日良辰 孤独的亡灵/大红冠子的公鸡叫出了最后的声音/黑猪的头放在案桌上/香白的米饭有三碗 大坛的酒洒在了路上/亡灵 先穿好你的衣服/崭新干净的衣服 裹紧你满是补丁的一生/然后跟着我来……/吃五谷的人 点三炷清香送你/冬牧的人 烧一张羊皮送你/寿棺是孝男用柏木做的/刀斧不入的柏木不生虫子 亡灵/你放心住进去 柏木芳香长存/柏木驱邪避神吉祥灵验/你的后代会人丁大发 富贵两全/……你进去吧 关起你的门来/买路钱已备好 丧灵冠已扎好/只要七芯灯点燃 你就会/三魂袅袅归天界 七魂悠悠赴黄泉
同期写作的另一首诗《孝歌》可看成是这首《入棺调》的姊妹篇,它同样写得异常精彩并富于神秘气氛,“死去的人 你好好走/黄泉之路多风雨 望乡台上莫回头”。通观何晓坤的诗歌创作,凡是涉及到死亡题材和主题的,都是写得比较透彻和成功的。我不好妄言何晓坤手里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神秘钥匙,但可以肯定,这同样与诗人独特的家庭身世有分割不开的复杂关联。同样是植布在高原的山川地理,同样是在人们头顶飘荡的雷电风云,在何晓坤的笔下呈现的往往是别样风貌,与我们多数人想象中的滇东高原景象殊异。如《苦谣》一诗:
停在我的鞭梢吧∕孤独的黑云 一副脊梁背负着一片天空∕你要向哪座山头挪去∕停下来 高空的巫师∕荞花的眼睫上挂满薄冰∕百草昨夜枯萎 根燃烧在泥土深处/……高空的帝王 在这样的高度俯瞰人类∕所有的灵魂都无法得到赦免∕就这样在宁静中超度一切∕无所谓悲哀或欢喜……
可以看到,哪怕是在一些颂歌式的诗篇中,何晓坤诗歌的选择视角都是独特和不可复制的。黑云是高空的巫师,是高空寂寞的帝王,荞花的 眼睫挂满薄冰,百草在一夜间枯萎……这里不仅没有浪漫的白云彩云或者其他什么,连所有的灵 魂也都无法得到赦免。如此沉重的视点,肯定不 是每个人都能够去捕获索取的。何晓坤前期诗作中写得较为成功的诗作,或多或少均具有类似 格调,如《苦荞》《英雄祭》《山祭》《水祭》《树祭》等等。如果我们非要将何晓坤的这类诗作划入滇东高原地域诗的行列,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别样的高原,是一个只属于何晓坤的高原。
二
20世纪 90年代初期是诗人何晓坤的诗歌创作明显走向成熟的时期,《大鸟》一诗的成功创作是一个明显标志。如前所述,这首写于1990年 3月的诗作当之无愧地获得了“1992 首届珠江源杯全国诗大赛”一等奖。这首诗是当时的诗人呼唤和倾慕英雄精神、向往英雄风范的写照,即便是时隔 20年之后再次阅读这首诗,它带给我的震撼依然鲜活如初:
落魄的帝王 从传说升入高空∕猝不及防身不由己∕飞行是唯一的选择∕它的背景 蓝天和云∕高远而深邃∕而大鸟 失败的侠士∕满目倦容 神情可怖∕羽毛悬在高空∕优美的行姿∕已被阳光的十指残忍地撕下∕栽入墙内的风景
这只宿命的大鸟神情疲惫却依旧要背负飞翔的使命,它无处可飞却依旧要飞,它无法履行使命却依旧肩负使命。“大鸟 在精神的蓝光下∕摇动双桨 笨拙而专注∕从森林到巢穴从天空到天空∕大鸟的羽毛远离了诺言的祭台∕洁白 而华美”。孤独的大鸟飞临人世,它忧伤而又孤傲地陷落在自身所认领的生命轨道,它是清醒 的,它矛盾而自知。大鸟“一只翅膀指向天堂∕ 另一只翅膀指向地狱∕……指向天堂的翅膀膨生着欲望∕指向地狱的翅膀苦撑着肉体”。这只孤绝蓝天的大鸟想超越世俗的自己,然而它的世俗的肉身却在下坠; 它想和世俗和解,然而它的精神的另一面却在拼命的高攀,于是大鸟就只能不停地在精神和肉体的世界中徘徊,“以华美的羽毛叩拜神灵∕以锋利的爪子踩着人间”。神灵当然是最后的归宿,而人间永远有种种说不尽道不明的苦难容不得大鸟妥协。由此,我们读出了诗人对人间苦难所怀抱的不和解的坚毅姿态。苦难是既定的,使命是自担的,“盘旋的瞬间 大鸟∕灵魂的小刀 小心翼翼地伸出肉体∕剃刮天空芜杂的胡须∕天空明净 前程似锦/大鸟驻足空中/天堂与地狱的距离均等/都只一翅之遥 大鸟横陷其中∕两只翅膀指着两个方向∕不知如何扇动”。升高抑或下坠,崇高抑或沉入世俗,精神的无限渴求和世俗的必然安排……这永远的折磨不会自行消解,它的纠缠由始至终,大鸟别无选择,它只能义无反顾地去完成这个过程:“大鸟驻足空中∕等待枪声的响彻∕那动人的时刻∕大鸟∕一只翅膀飞向天堂一只翅膀落入地狱”。使命、搏命、奋争、崇高与随波逐流、认命、安命、卑俗等等历来相对而密不可分,大鸟所陷入的这两面即是身在世俗的智者、慧者和勇者所面临的两面。大鸟不可卸载的命运担当令人肃然,《大鸟》一诗的深邃使人倍感震撼。
在何晓坤前期的诗作中,“鸟”的意象多次出现,除《大鸟》中的大鸟之外,还有《圣鸟的行姿》中的圣鸟、《哑鸟》中的哑鸟,以及林中的鸟、吉祥的鸟、黑鸟、红鸟,及同属鸟类的云雀、鸽子等等。以“大鸟”为代表的鸟类在何晓坤前的期诗作中现身,并且作者的情感投射多半是正面的积极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即“大鸟”在诗人的内心深处究竟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神秘位置?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大鸟”包括哑鸟、林中的鸟、黑鸟等在内,它们是何晓坤诗歌意识中的英雄原型。这个原型的构成极其复杂,它们在深层次上多少带有作者祖辈受劫不驯的身影,带有作者父辈经手磨难的痕迹,当然更带有作者自己自虐式写作的精神印迹,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精神深处所崇尚的英雄标杆如屈原、杜甫等圣贤豪杰的印迹。当我们在何晓坤的前期诗歌中一再地读到《哑鸟》中“哑鸟潜伏在声音的背后/它单纯的手指/游上岁月的枝条/弹出土壤的芳香/哑鸟以天使的庄严/在季节之外歌唱”,《林中的鸟》中“林中的鸟 偶尔思考的时候/先满眼迷惑不解/片刻之后 林中的鸟/便望着远远的天空/哈哈大笑”这样的诗句,我们更加明白无误地触摸到了这个隐秘的事实。
何晓坤前期的诗歌写作,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对神灵、众神、主、天苍等概念充满敬畏的陈述。如诗作《一生》:
面对神灵 抖落内心的隐秘∕我们的一生 笼罩在神的灵光之下∕我们的一生 高挂在神的额头∕……在苍天之下 在神的脚趾之下∕就要一点一点地焚烧干净
神灵何在?对于心有神灵的人来说,神灵无处不在。这个在那些彻底的无神论者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在何晓坤这里显得如此重要呢?原因就在于诗人灵念深处始终存有善恶评判的良知,诗人精神深处始终浸透着传统文化的灵汁。人类或说我们每个人需要不断焚烧的,正是那些并不洁净的欲望、隐私、爱恨等等。“在夜中祷告∕平安始于悬而未圆的清月∕主的足迹遍布苍穹”(《夜》) 。主就是上苍,就是良知的审视者,就是神。“天苍之下幸福的生灵∕深深的瞳穴填满了悲哀和正义”(《怀念大师》)。神灵也好,主也好,天苍也好,它们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心存在的判别事物的标准,就是经由期望中的人道、圣道而达至的最终的天道。俗话说“离地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究竟是心中有神好,还是彻底的无畏无惧好,中国当今60 余年的历史似乎已经作出了回答。何晓坤是心有神灵的诗人,对何晓坤个人来说,写诗就如同修行一样,是一个无论身内还是身外都需要不断清洗的过程。不管你赞同还是不赞同,这是何晓坤有别于其他诗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
何晓坤前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之作,是写于1996年6月的长诗《颂辞》,这首诗全诗长达300 行。诗人在此诗题记中写道:“最后的梦想在枝头燃烧/死亡来自语言的深处”。这个禅语般的题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自然需要通过对全诗的解读才能得出结论。然而一个颇具难度的程序首先是如何来解读这首诗。我相信对于没有足够耐心的读者来说,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挑战了,但是当我们耐心地读完这首诗、读懂这首诗,我们无疑获得了一个惊异的发现——写诗这件事是可以与神圣挂钩的,它是一个很值得人们去好好做一做的活儿。
《颂辞》究竟想说什么,说了些什么?这是一次悲怆沉郁、焦灼辗转而又大义自在的有关生存、心灵关照、迷误、闹剧、新生、再生的精神之旅,它以博大深广的笔触描绘了诗人的精神自我所历经的一个艰难的涤旧迎新的过程。犹如凤凰集香木自焚以获取新生一般,诗作展现了90年代中期诗人精神救赎的独特路径,并在最后给出结论说“让我们去寻找英雄”,寻找那个曾用巨足踩疼所有思想的神圣职责的承担者。
全诗共分为八个部分,各部分分别以“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的方式依次推进。在第一部分中,诗人一开始就通过密集突兀的意象呈现,将一场即将举行的祭祀之礼的情境展现在读者面前:
像众神相约而流的某颗泪滴/许多事物似有安排而又猝不及防/面对满山滚动的石头和预言 面对风/风中假寐的神话/就让晚祷的花儿提前开放/让草甸上的羊群接受忠贞的洗礼/晚归的狼群里环绕着一百只幼鸟的呢喃/那朵距离天空最近的黑云/在无限温暖的夜晚由黑而白/由白而红 最后熊熊燃烧在时间的键盘上/纯正的生灵已搭好了祭台 上好了祭品/庄重地跪下去 感谢先知诗歌/感谢时间和存在 不可捉摸的永恒……
猝不及防的事物不可避免地到来,石头在风中滚动,神话在风中假寐,羊群即将接受忠贞的洗礼,一百只幼鸟环绕着晚归的狼群,黑云亦然变白变红。这一切不为别的,就为着一个即将到来的庞大事件,一场牵涉到人们即将对精神、道德、责任、使命等恒久范畴予以反思的精神之旅。“沿着一条河流 沿着一条谦卑的线路∕走过去 认真阅读置于高空的每个显目的词语∕道德 责任 荣耀 使命 羞辱 法则∕香烟 废墟 伴侣 智慧和政治∕韭菜和艺术……”透过这些涵义广泛的语词,我们读出了作者所欲达至的宏大企图。显然,这样做是需要有一点艺术的勇气和胆量的。
第二部分以神话的方式描述了四组人的诞生,这四组人分别是孩子、老人、女人、一群人。孩子用圣洁的小手抹去天空的灰尘,老人用干枯的双手捧起太阳和漫山遍野的春光,女人用粗糙的大手撕去了诞生的胎衣,最后出来的一群人在看见满地花瓣的同时也看到满目飞舞的刀光。人类自身并不美好,他们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灾难,“在麦芒中奔走和死亡的人群/在麦秸中筑巢和躲藏的人群……与钢铁和玻璃无关的谈判/与爱情和欲望无关的哭泣/……你低头看地 蛇行蠕动的是寂寞的村落/舀水的人站在溪边 舀水的人没有手镯/舀水的人消失在遥远的季节/被拖长的影子 镶进灵魂的荒岗……”苦难无边,希望何在?在提供营养和口粮给我们生存的“历经劫难的麦地”。
第三部分以“怀中的女人睡了没有∕怀中的女人醒了没有 婴儿的小手∕是否抓住了时光的臂膀 婴儿的小手∕是否触到了诺言的白帆”为切入点展开。女性和婴儿无疑是母性和生命的象征,面对母亲和新生命被摧残的命运,面对被喧闹啄伤的森林、撕裂的花朵、追云的倦鸟、鱼腹中的历史,“诗人的左眼是沉默 诗人的右眼是懦弱”,“天堂的围墙外∕死了多少没有归途的来客”。使命就这样被搁下撂下,英雄的位置处于令人失望的虚空状态。
第四部分集中展现的是一座城市迷离的景象,它的建筑、人群,钢铁和轮胎、玻璃和大腿等众多纷乱的事物,以及曾经显赫一时的“一条虚设的河堤”:
去走一条虚设的河堤/圣鸟已回归天堂怀抱竖琴的智者/在两扇门之间 怀抱竖琴的智者/在水波之间 另外的笛声沿河流淌/虚设的长椅上/女人仰头望天 男人的头埋在女人的大腿之间/疲劳的城市躲进了呼吸/古老的城市躲进了呼吸/虚设的黄昏 在远离城市的山坡/熊熊燃烧
这是在宣告一座城市其实已经远离人们美好的设想和愿望,它已被“圣鸟”所抛弃,已被智者所远离。女人们母亲们悲愤地祈祷于天,而男人们则成为找不到出路和希望的迷误者。啊,我们走了半天,走了那么远的距离,原来那只是一条虚设的河堤!原来只是一场虚妄的欺骗!
第五部分继续细化那一场悲剧的典型场景,这其中出现了一个人们臆想中的“他”,即众人精神和生命曾经的引领者。这个引领者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握住你的手,并“含情脉脉”地告知人们说他“制造了许多红伞”,这个人要带领众生前往天堂,而其实“他从出生开始就着手寻找公众的墓地∕他营造过十万座忧郁的公园”。但是你果真还是上当了,在梦幻中“幸福地闭上双眼”。可当你醒来睁开眼睛,你发现“枪口在四周森然密布∕吸毒者的嘴巴和你频频亲吻∕狎昵的声音 整整响彻到下一个世纪”。于是你只好叹息“真实啊 一团郁结的谜/真实啊日趋腐蚀的剧痛”。此部分中有关引领者的历史确指我们大可忽略,因为艺术毕竟只是艺术。如果真有读者按捺不住非要较真,我们只好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告知对方——“你懂的”。
第六部分以寓言的方式展现和渲染曾经发生在“天堂”里的一场荒诞闹剧,“天堂里血流满地/天堂的血 已溢出最后的界碑/天堂的血 从凡人所不可企及的高度/倾泼下来”。在这场旷世的闹剧中,负面势力的象征“巫女”操纵了一切,天堂里血流满地。面对如此景象,先哲们唯一的选择是“泪流满面地翩翩起舞”。实际上先哲们真的做不了什么,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厄运和灾难,他们只能痛悔着、怜悯着,溺入其中无力自拔。
第七部分向我们呈现的是经历劫难之后的女性、母亲的最先觉醒,她们要孕育,要承受自己理应承受的,“女人们已打开门来交谈∕从容迎接或等待男人的足音”。“一条影子从远古飘来 女人说∕魔鬼 为何你满眼柔情似水”。涤尽旧污纳新人,一个新生的世界已然降生。“女人们走出来交谈/天空清澈见底没有一丝下雨的迹象”。
第八部分是本诗的最后一个部分,它的核心问题是“留下灵魂的住址∕让我们去寻找英雄”。可能有人会以为这首诗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应该是英雄的出现,为什么期盼中的英雄没有出现呢?答案是现实中的英雄确实没有出现,现实中出现的只是众多的庸人。那么到底谁是英雄?作者自己此时固然不是,你和我此时也不是。但是将来呢?
“英雄的巨足∕曾经踩疼所有的思想”,将来必然会有真正的英雄出现。
《颂辞》一诗构思博大,视野开阔,全诗采用整体象征的手法,将一场有关国家民族命运及个人精神救赎的长途跋涉纵横捭阖、气势恢宏地展现出来,情感复杂丰富,波澜起伏,意象新奇怪异,纷繁逼真,是诗人何晓坤前期诗作中最重要的一首诗作,在精神上、思想上、艺术上均代表了何晓坤前期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如果说《颂辞》这首长诗还存在什么缺陷,我个人的看法是全诗意象过于庞杂繁复,情感和情绪的正负呈现纠结沉滞,某种程度地导致读者阅读和理解困难。然而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曲靖诗坛也好,云南诗坛也好,都不应该忽略和忘记这首诗。
四
在诗歌创作领域辍笔十余年后,诗人何晓坤在2010年秋冬之际重新迎来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复苏期、爆发期。十余年间诗人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难能可贵的是世俗的真实生活并未将何晓坤的诗人秉性摧毁,“羽毛和诗歌∕同等洁白的事物在身外不朽”(《歌唱鸽子》),生活中的何晓坤可能扮演过这样那样的角色,但一个不可更除的角色依旧是诗人,是依然要做诗歌的圣徒。这个生命深处的情结可能并非就那么崇高,但肯定也不会卑俗到哪儿去。
何晓坤的诗歌新作中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首与蚂蚁有关的诗。还记得在作者写于1992年11月的前期诗作《蚂蚁的行踪》一诗中,我们所见到的那只“亦如遍体鳞伤的哲人∕只为守住一片青青的草地”的宿命的蚂蚁。那么,诗人新近发现的蚂蚁是些什么样的蚂蚁呢?它们是一些穷其一生终于爬上了窗台的蚂蚁,这些终于爬上窗台的蚂蚁此时“正把小脸贴在厚厚的玻璃上∕诚惶诚恐地朝里面 张望”(《爬上窗台的蚂蚁》)。显然,厚厚的玻璃挡住了蚂蚁的视线,这些诚惶诚恐的蚂蚁依旧未能将许多事物的真面目看清看透。这个必然的结局终于到来,尽管行踪并无改变,但1992 那只青春躁动的蚂蚁终于长成了2010 这群成熟的蚂蚁。
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生活中的成熟究竟意味着什么?何晓坤在诗作《你是不是可以这样陪我一起老去》里说:“我对自己已十分厌倦一个理想主义者∕坚持在现实的祭坛里种花 长出的却总是刺∕困守信念的人 注定要被信念埋葬∕这虽然残酷 却是我一生的代价换来的真理”。这段告白揭示出来的心境虽然是沉重的,但同样明确的却是并未想过要放弃信念。理想主义注定要在现实中碰壁,那么碰壁之后怎么办?从何晓坤的近期新作中,我看到诗人的选择是依旧保有对人世、对生活、对家人、妻子以及对朋友的热爱。比之于前期诗作中屡屡呈现的散发苦涩阴冷气味的诗人身影,如今的诗人面目更多闪烁着的是平静祥和,坦荡自知,是对人间诸事的谦卑敬畏,以及对苦难的感知、怜悯和仁慈。这和何晓坤前期诗作中的诗人风貌是根本不同的,它是诗人历经诸多人事的磨炼之后获得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应当承认,置身当今的中国社会,力图有所担当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何晓坤的近期诗作中呈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与生活、与环境、与社会的大面积的和解。在何晓坤的前期诗作中我们感受过诗人和诸多外在因素内在因素的对立姿态,而在近期的诗作中何晓坤不再倚势临空,他拉近了自己与原本质疑的事物的距离。今天的诗人已经学会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今天的诗人平和而不再焦灼,正如诗人在《应该找回欢乐的面孔》一诗中所呈现的那样:
应该找回欢乐的面孔 在反常的季节∕没有必要 一次次深入内心∕深入不可触摸的部分没有任何细节/不堪回首 也没有任何一条河流/可以重新流淌 或者改变方向/你总不能进任记忆的毒液 肆无忌惮地/渗入骨髓 渗入血液和脆弱的神经/一切都有定数 必须找回欢乐的面孔/找回欢乐的面孔 事实上非常简单/只需从心灵出发 看看头顶的天空/以及划过天空的小鸟 不再虐待/面部神经 不再封闭 面部表情/适时加强 面部肌肉的运动/保持张力和一定的灵敏度 并适时/裂开嘴唇 露出并不难看的牙齿
尽管多少带有一点反讽幽默的意味,但其明澈的心境、豁达的气量是显而易见的。在《灯花盛开》一诗中,诗人的这种宁静明澈、从容淡定更是透出一种巨大的佛性的宗教灵光。
“离开夜的蒲团 世界就宽敞起来/空气中有许多灰尘 但我没有看见/阳光的背后有很深的暗影 我也没哟看见/天空异常地干净甚至流浪的鸟儿/也在传递欢快的气息 今天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像我平静的内心/留住了光阴的脚步 像盛开的灯花/洗净了瞳孔也洗净被忽略的时间”这里我们必须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诗人这种新风貌的出现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如果说作者十几年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精神变化是基础,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因素是什么?阅读何晓坤的近期诗作,一个明显的事实跃然于水面——诗人对佛学禅宗的习得和浸染是一个重要原因。佛学和禅宗的奥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作为一个深具慧根的诗人,何晓坤从其中撷取了洞察世事的智悟和对待事物的欣然淡定,这无疑是对以往尖锐不妥协惯性的一种修补。“多年以后 我连尘埃也将不是∕而阳光依旧明媚 大地依旧宽阔∕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无数的我∕仍将诱惑如初 轮回依旧”(《多年以后》);“明月悬于空中∕善恶植于心里∕根在何处∕根在宿业因果中”(《涛声》)。所谓轮回、所谓善恶、所谓宿业,其实如果换成儒家的说法,不外乎就是良知良德,就是致良知,就是格物,二者的修炼几近一致。当然佛家的宿业还牵涉到三世的问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轮回问题,信不信各取所需。就何晓坤来说,对佛学禅宗的介入增强了其对佛事人事的谦卑敬畏,对人缘事缘的珍惜呵护,对自我行为的引导提升,这些作用无疑都是积极的可取的。对此,我始终怀着无限的祝福和尊敬。
何晓坤的近期新作中当然还涉及到其他诸多的内容。长诗《一个人的旅程》是诗人计划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目前已完成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共计160 行的写作,它是诗人献给自己祖父及一个不幸的时代的挽歌。类似的作品还有《七月半告先灵书》等。一如既往地展现诗人对社会人生探索的诗作,有《寻常问题》《仰望夜空》《直截了当》等。在组诗《你是不是可以这样陪我老去》中,诗人表达了对妻子相濡以沫的挚爱。在一组写罗平油菜花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比之前期诗作中的同类作品更为透彻深入的触摸和礼赞。一个日趋成熟的诗人,一批更为成熟更具穿透力的诗作,诗人何晓坤继续行走在那片长满油菜花的土地上,继续在那一块只属于他自己的充满诗意和禅意的空间尽情地舞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