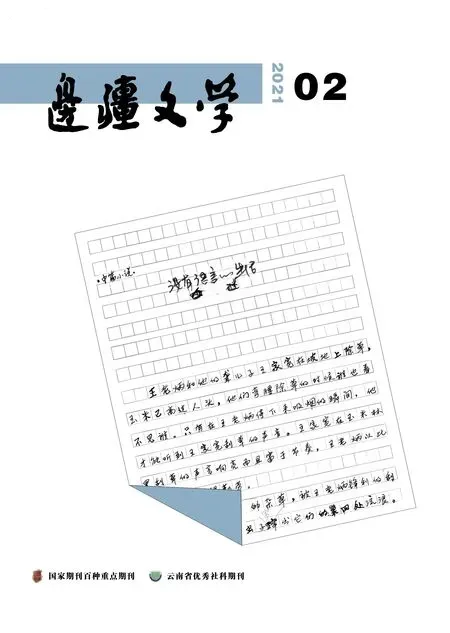云大评刊·好小说进行时
本期嘉宾:
梁豪(《人民文学》编辑,《黄牛皮卡》责编)
焦典(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黄牛皮卡》作者)
窦红宇(云南作家,《牛美丽的手脚》作者)
伍世云(云南作家,《送伴》作者)
潘灵(云南作家,《豹子》作者)
和晓梅(云南作家,《落地生花的银》作者)
李浩(作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包倬(云南作家,《驯猴记》作者)
主持人: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协会副主席)
讨论者:云南省高校教师及研究生10 余人
记录整理:何子怡、罗文斌、石蕾、李颖
时间:2020年10月23日星期五
地点:云南大学文津楼216 号
主持人宋家宏
:同学们回来了!我们进入了“后疫情”时代,疫情还在世界肆虐,但我们毕竟已经复归校园。这是我们复归校园的首期,我们又能面对面地讨论作品了,这与线上讨论是不一样的,我很高兴!九、十两个月,云南的小说迎来了发表的丰收期,全国许多刊物都出现了云南小说家的名字,很年轻的云南小说家也出现了。作为云南的“云大评刊”,这是令我们高兴的事。所以本期评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更多地关注云南作家的小说。当然,对大家读到的其他省区的好小说也不要放弃,只是相对集中于云南作家。
我们从《人民文学》开始吧,本期出现的作家焦典就是云南人,很年轻,95 后的。
看《人民文学》
桂春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
:焦典的《黄牛皮卡》(《人民文学》2020年9 期)以家乡风俗为入口,为两代甚至更久远的世代、城乡甚至更宏大的分裂的现代文明,作了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很难不让人想起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却显然更为从容地捕捉到了“生生不息”这个词所应有的律动,并以相当成熟而细腻的笔法,突破了猎奇的“异乡”写作。这无疑让人对文学有了更坚定的信心。这信心足以让我们意识到,“95 后”这一代际概念暗示的担忧,不免有某种不必要的所谓前辈的优越感;也应提起我们的反思,所谓年轻一辈的后必胜今,同样需要文化底蕴的支持。文学是世代累积的永恒劳作,有所损益的基础,恰如一座雪山,文学的一代代毕摩们,不论去往怎样的远方,总会再次投来回望的目光。田彤彤(云大2018 级硕士研究生):
作为一部短篇小说,其内容含量已经足够充实。小说中不仅出现了具有神秘感的彝族传统文化,还体现了极具现代文明意义的现实生活,这二者的关系成为现实中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毕摩作为彝族文化的守护者,在小说中被赋予了预知与全能的含义推进着叙事的进行。小说情节设置非常精巧,其中最后的雪山之旅是毕摩对自我生命预知的体现,与黄牛同行意味着渴望妻子的陪伴,而途经阿卓县的插曲则是毕摩对女儿愧疚之情的弥补。虽然这样的写法略显符号化,情节也稍显通俗,但还是可以清晰了解到文本中所蕴含的情感温度。
焦典(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小时候,在云南老家,吃得饱了就爬到屋顶吹风。天上有许多云,都低低地压着,仿佛一伸手就能拽下个云里的老神仙。正天马行空地幻想着飞呢,屋里大人又叫你帮着烤洋芋去。头在云里,脚在地上,这是我对家乡的感受,这是我想写的云南故事。不过,虽然我写的是一个边地少数民族的故事,但是我本质上想回答的,还是我所生活着的当代城市生活的问题。我想在我的文学中,找回人类勇敢、自在的品性,找回世界神秘的另一面。梁豪(《人民文学》编辑,《黄牛皮卡》责编):
这是一篇可以看语言的小说,或者说,是被语言挑动起来的小说。怎么个好法呢?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它是看着简单,其实需要下足功夫,然后,顺着已经打通的语言的腔调,正如音乐的旋律,叮咚叮咚地流,怎样都是顺势而为。像其中写夫妻、母女情深,两三句话点出,让情绪自己晕染开来,这就是雕琢和归朴的魅力。故事是歌词,好的旋律,不会把故事带歪。在这个前提下,小说基本成了,至于成了多少,这就涉及具体的分析。毕飞宇老师的评论,是一种很好的分析策略,或许还有其他路径和观点。这里再说一点,像西南彝族的毕摩,一般读者不懂,不懂但有价值,用故事告诉你它的前世今生和文化内涵,于是小说更显筋道,相当于另开一个维度。小说的维度不怕多,但须搂得住、编得圆,这跟谎话是一个道理。谎话要想扯得好,最核心的一条,我感觉是展示诚意。《黄牛皮卡》改过多版,作者让我看过一个未发表的开头。见过雪山的吉妈竹梦将皮卡开回村里,后厢是已经往生的吉妈毕摩和黄牛,秃头男孩一路大叫,如同指路,吉妈竹梦碎碎念哪学来的《指路经》,老人们一下就懂了,感叹:“我们的白云村失去了最后一位毕摩。”倒叙开门,几个细节溜出环境背景,憨然爽然悚然怆然,味道齐全,压舱石一样。这里放出来,是让有心人去思考,同样的故事化作小说时,可能形成的不同形状。好坏另讲。
赵小爽(云大2018 级硕士研究生):
云南作家窦红宇的小说《牛美丽的手脚》,发表在2020年10月的《人民文学》上。近年来,扶贫作为时事热点也是文学作品的热门选题。要在一众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务必要写出新意,讲好故事。这实属不易。本篇小说以一种戏谑的口吻,描述新涌入城市的“乡下人们”一种“无根”的状态。他们看似幼稚可笑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营造熟悉感,获得安全感。小说开篇,女主人公牛美丽即将进城,卖牛像“卖闺女”;进城后,在安置房的阳台上,小心翼翼地养猪;两个同为农村进城的妇女,全心协助牛美丽养猪。养猪,是老鹰垭口特别重要的事。养猪,为了讨媳妇;娶媳妇来,是为了让她养猪。很可爱却又很真实的逻辑,背后透露出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性。城乡转化的工程,绝不是搬进一所漂亮的新房子就能结束。当然,为了渲染氛围,人物的哀乐情绪被作者有意放大,略显失真。
李珈漫(云大2019 级硕士研究生):
窦红宇的语言描写极具地方特色,读来很亲切,但我更看重小说的乡愁意味。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山区搬进城里了,牛美丽们感觉到的却背井离乡的意味,城市对她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们对它是恐惧的。养猪其实有了象征意义,承载的是乡愁。丁雯(云大2018 级硕士研究生):
我对窦红宇这篇小说的评价有所不同,这小说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从小说的篇幅以及所达到的内涵来看,很不吻合。这么些内涵,用千多字的新闻稿也能达到。小说,要深入到新闻不能抵达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篇小说在这方面差得很远。小说里一些有意为之的技术性描写又让人感到很生硬。窦红宇(云南作家,媒体人):
2017年底,一件在我看来是大事的事情,在滇东北大地上热火朝天地发生了——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又是国家级贫困县的会泽县,要扶贫搬迁十万人。就是说,这个只有十万人口的小县城,三年内,要迎来十万从深山老林里搬进城来的农民。这些大部分因自然环境而没有办法更好生存的农民们,突然间要住在一个由政府建造的叫“新城”的地方,突然间,他们要同这十万城里人,共处一地。无疑,这次类似于“闯关东”式的小型的迁徙,肯定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历史时刻。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肯定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如何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为进城的农民们找到希望和温暖,我觉得,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就是说,史诗般的生活出现了,那么,史诗般的作品,到底在哪里?《牛美丽的手脚》,就是以这样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写成的一个中篇小说。看《收获》
马艳娥(云大2019 级硕士研究生):
伍世云的《送伴》发表于《收获》第5 期。写的是一个“炉中火命”的有命数的孩子,被动中陪伴死亡,怀着恐惧的心理送完死者最后一程,小说写得鬼气森森。让读者体味到毛骨悚然的恐惧和阴冷。阿正作为“送伴”人被送去与将死之人同睡,这是一种怎样的恐惧,和他有一样经历的还有表弟。阿正和表弟都是被无知与愚昧的习俗所侵害的无辜孩子。小说结尾阿正被迫做了“大端公”的“送伴”人,但他在目送大端公走的时候,“仿佛从什么东西里面挣脱出来了”,这样的结尾更加深化这种“荒唐”的命运无奈感。唐诗奇(文学硕士,出版社编辑):
《送伴》令人震撼。对于“送伴”这种特殊题材的书写,作者没有停留在猎奇的窥探,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把来自记忆深处的那种恐惧、疏离、纠结写得淋漓尽致。我是第一次通过小说了解到“送伴”这种习俗,随着叙事的深入,我对小说主人公的恐惧感同身受。森森然的整体氛围的营造、叙事节奏的把控、插叙的背景交代、对人物内心的深度开掘浑然一体,十分考验作者的功力。小说的最后,随着岳父的死亡,故事到达了一个高点,主人公也与自己、与恐惧、与过往达成了和解。我长舒一口气,小说戛然而止,却令人久久回味。李颖(云大2020 级硕士研究生):
这篇小说写出主人公几次“送伴”的过程,阿正的心理也在不断改变,由原先的恐惧到后来的麻木,以及文末对恐惧的解脱。作者在细致地刻画阿正心理状态的同时,也打破时间的限制,不断地转换叙事时间的视角,回忆与现实交叉,增添了叙事的丰富性。何微(云大2018 级硕士研究生):
《送伴》这个故事弥漫着一股冷硬的能量,这能量来源于作者对“死亡”的逼视和深刻思索。这同时又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小说一方面以回忆叙事交代阿正少年时期做“送伴”的噩梦过往,另一方面又以当下视角讲述成人后的阿正不断与童年创伤记忆发生博弈,从拒斥到之后逐步克服并悦纳那段过往。在小说结尾阿正终于能够直面旁人的死亡,并给予陪伴,这就使得故事为人与人之间、生者与将死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轻逸而达观的理解——“送伴”,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纯粹的陪伴。郑旭(云大2019 级硕士研究生):
这篇小说体现了作家精湛的叙事功底。开篇便以“气味”为切入点设置悬念,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故事情境之中。人物不安、惊惧的内在精神世界与弥漫全篇的颇具有民俗色彩的神秘气氛形成一股合力,爆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这篇小说也具有精神分析的特征:少年时期阿正做过“送伴”,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天然的,过早的,尤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接触到死亡,给阿正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如今,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准岳父正是当年介绍阿正去做“送伴”的大端公。在阿正送走了这位大端公后,恍惚间自己的精神创伤才得以疗治。石蕾:
《送伴》表现出了人们在死亡面前,试图以一种看似蒙昧但却能够寻得临终安慰的方式来解脱。人物心灵的转变来自对铜钱刹那间落下的感悟,“人们在离世前总想抓住和世界最后的联系”,这种联系给予他们通往未知世界的力量。文末,阿正希望自己可以帮助死者解脱,于是他也相信自己身上有“火”,可以立功德,自己仿佛也从梦魇中挣扎出来。作品带给人一种压抑恐惧的氛围,但文末主人公阿成的省悟与成全,让读者最终缓和了压抑和恐惧。桂春雷:
伍世云的《送伴》,在写作主题和笔法功力上,颇有静水深流的味道。阳气重的孩子,送逝者一段路,这迷信中萦绕的神秘色彩,有时会用以寄托亲人的追思,有时也会变成谋生伎俩的遮羞布。但它给孩子的心灵留下的精神创伤,是真实而深刻的。这不单是时代的印痕,更是时代也熨不平的边缘人生命体验中的褶皱。与其说“我”最后在大端公生命的尽头选择了和解,不如说,是“我”发现大端公也不过与我一般,是平凡的生命。“放下”,有时不是因为原谅,而是因为无奈地发现,原不原谅意义不大。孩子长大了,选择以极轻的“放下”,问了个不能承受其重的问题:“不放下又能如何呢?”这其中有伍仕云对儿童的发现,对民俗的反思,更重要的,或许是对思想史的某种消极抵抗。伍世云:(云南作家):
器皿中,我最爱的是碗,因为它日常却又那么重要。小时候,吃饭前,我总是对着空碗发呆,心想这次我是用水还是用空气把它装满,然后再倒出。而今,面对一个未动笔的小说,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空碗。那么,我该把哪段素材哪些人物放入这个碗中呢?每个故事都有它自己的气味,面对一个小说之空碗,我要做的是,找到适合故事本身的讲述方式将其填满,然后再把它倒出来。这一装一倒,故事被洗得不像它本来的面目,却更接近生活中的人物。《送伴》这个小说,我原本要倒进“悔愿”“送伴”“问期”三个词,结果有的词倒进去却没倒出来。茶壶煮汤圆,有货拿不出。这是《送伴》给我的喟叹。主持人宋家宏:
大家都集中于说《送伴》,有说不完的话,正说明好小说的魅力。这篇小说是我很长时间以来,难得读到的好小说,是入心的小说,是我所追寻的“心灵现实主义”的小说,既写人物的心灵世界,也击中读者的心灵世界。有的小说读完你真的感到无话可说,甚至想说,这样的小说写了干啥?这篇小说读的时候就让你难以平静,读完还是回味不止。看《青年作家》
谢轶群(云南艺术学院教师):
《豹子》发表于《青年作家》2020年第10 期,小说的作者潘灵是云南的著名作家。这篇小说是扶贫题材,读完一般都会称道其构思精巧,语言描写传神等,但这篇作品的意义首先不在这里。近年来写扶贫的已有很多,这些作品也并不都是在服务形势,作家们或多或少都在这个题材中追求个性和创造。《豹子》描写的扶贫,只是一个背景,内涵却是描写人心的欲望,甚至是私欲。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村干部、村民,作家都集中于他们的私欲。同类题材内容比较尖锐的也不是没有,但一般的套路是:对此惊心焦虑,发掘、解释现象成因,然后思索和“指明道路”。潘灵却以流利的写实风格,直面人心,直面现实。李田力(云大2019 级硕士研究生):
正如潘灵自己所说的那样,作品中的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头“豹”,这头豹在欲望的驱使下不断在死亡的边缘试探。“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终于,李小东在美好前程幻想的驱使下、黄二狗在老婆孩子的幻想的驱使下,无情地剥夺了在天价野生菌吸引下冒险上山采菌的桂花的生命。同样,小说中李小东的女朋友莎莎为了傍上一个小公务员、莎莎父亲为了能让两个年轻人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他们内心深处那头欲望的“豹”也在不断地咆哮并驱动着他们也一同铤而走险。最终,子弹在颤抖的双手下一颗颗地射向了一头头骚动不安的“豹子”。李珈漫:
《豹子》这篇小说颇具新写实小说的意味,展现了世俗生活中小人物的生存欲望。主人公李小东为了一己之私,明知山有豹偏向豹山行,在他唆使黄二狗上山打豹的过程中,也将莎莎、廖老幺等人牵涉入欲望之网中。最后小说戏剧性的结局,出人意料,“枪响之后没有赢家”。潘灵(云南作家,《豹子》作者):
我写小说,就迷恋这个“小”字。小说这种文本,自甘其“小”,想想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我们这崇尚“大”的国度,有种文本喜欢往小处说,多好!我对“大”有恐惧感,“大”总是轻易地覆盖掉“小”。我选择做一个小说家,就是要把被“大”遮蔽或覆盖的“小”重新凸显或呈现出来。我痴迷那些小人物,关注那些小事件,甚至那些小心愿和小欲望。正是“小”,组成了我们的小小人生。人人心中都住着一头豹子!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心中真的住进了一头欲望的豹子,我们就用理智的猎枪,给它致命一击。然后,把痛苦和悲伤留给自己,而不是祸害他人。看《十月》
陈林(文学博士,昆明学院教师):
李骏虎的《木兰无长兄》发表在《十月》2020年第5 期,这部作品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木兰辞》塑造的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是一位铁血柔情、情深义重的巾帼英雄,她在与家国的紧密关联中从“文小姐”成长为“武将军”,而李俊虎笔下的主人公则从健康活泼、性格开朗的“木兰”变成一位抑郁症患者。如果说《木兰辞》写出了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那么《木兰无长兄》则写的是钢铁是怎么被毁弃的。抑郁症是一种现代病,因此,“木兰”的身心俱废具有普遍意义。作者重点书写家庭、教育对木兰精神成长的戕害、不幸,木兰的生命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已凋零。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作者有他的关切和思考,而在艺术表现上可谓别具匠心。标题《木兰无长兄》直接取自《木兰辞》中的句子,由是,古今两位女孩及其世界形成了深度的互文关系,而“无长兄”正是“木兰”这代“90 后”独生子女的写照。在写法上,作者通过精选几个“横截面”描述“木兰”的成长史,并在不同的“横截面”之间建立紧密的内在关联,层层推进,文深旨远。我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李骏虎赓续了鲁迅的小说写作传统。李田力:
这部作品的前后基调是清晰对立的,以木兰的父母离婚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的木兰基调积极、明亮,后半部分则晦暗、阴沉。当我见到那黑色的物体,以为是黑狗复活,实为木兰时,给读者心灵重重一击。黑狗在小说中成为一个意象,它的意蕴不亚于小说中的人物木兰。何微:
这篇小说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关注到了青年抑郁症患者。通过讲述一颗稚嫩美丽的心灵在成长过程中被家庭的种种变故所摧毁,小说突显出批判意味,对摧毁木兰的一切发出了诘问。此外,小说运用平淡日常的笔调,将父母的琐碎交谈如闲笔一般穿插文中,以及“我”和“父母”如同旁观者的存在,都从不同层面强化了故事的悲情氛围。旁观视角的“隔”,正隐喻着人心的疏离和淡漠,旁观者并不知道抑郁如何降临在女孩身上,坠跌何时开始,只能大致拼凑出一个可能的轨迹。当“我”以及读者看到抑郁的木兰时,悲剧早已被不可挽回地发生了。“孩子,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勇士”,是不忍的叹惋,也包含着旁观者的自责与省思。李珈漫: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花木兰,是勇敢而著称的巾帼英雄,这篇小说中的小女娃是因为“太淘了”才被邻居冠名为“花木兰”。而她终于被毁,源于家庭的破裂,父母的自私、无责任心,令人感慨。李颖:
这部作品从女性主义动物伦理批评的观点来看,女性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互惠互助的伦理关系,她们同处于男性的压迫与暴力之下,她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作者打破了原有的动物与人和谐的关系书写模式,用外界力量的暴力联系狗和人类的命运,深化了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李骏虎用锐利的眼光审视女孩的命运,大黑狗也是作者审视命运的体现。从动物到个人再到普遍心理问题,古名今用,古今印衬,反思当今社会上普遍的心理疾病。赵小爽:
这篇小说初看似乎不起眼,甚至没有细细读的欲望。研讨会后因为师兄的力荐,再联系师妹提到的“黑狗”意象细细品读,发现这篇小说还是值得一说的。尤其是抑郁症这个话题。但本文的叙事似乎与高立意并不匹配。一方面,“木兰”这个经典化的人物名号,一旦使用,读者难免会有心理期待,然而本文并没有在古今互文性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为突显抑郁症主题,“木兰是黑狗的化身”这种处理也比较尴尬。加上故事是借“我”与父母的言谈呈现,节奏过慢,也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罗文斌(云大2020 级硕士研究生):
和晓梅《落地生花的银》(《十月》2020 第5 期)记忆与现实无缝交替,双轨平行的并置书写,打破线性叙述的时间流。加上二者的反复交替,外公藏匿的往事被嫁接到现实,放置在相同的时间段里,形成共时化的叙事结构,大大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小说在情节和叙事技巧上取得成功,对于人物的内在矛盾冲突的书写,仍存有一定的缺憾,不管是在外公纠结是否搭救欧明阳时的犹豫,还是质问欧明阳为何枪杀好友灰爷时的不解和悲痛,和晓梅对外公内心的矛盾冲突,都缺少一定的完整与细腻展现。何子怡(云大2019 级硕士研究生):
和晓梅似乎喜欢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但是往往不正面描写战争。从这篇小说中,我感受到和晓梅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悲悯情怀。她是从个体的角度,而不是从阶级、党派的立场写人物的命运。写出战争本身的残酷,在战争的环境下个体仍然人性未泯。丁雯(云大2018 级硕士研究生):
和晓梅《落地生花的银》沿着外公的记忆将故事拽回了1936年的滇西北,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人物情绪处理得当,小说中外公见到青年的态度几番变化,从诧异、讽刺、厌恶到同情,突出了外公对国军的排斥和对生命的珍惜。作者亦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处:丧失希望的生活要如何自处?战争留下的创伤到底需要多久才能愈合?在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愈发剧烈的人性冲突,值得深思。马艳娥:
和晓梅的《落地生花的银》是一部有“纳西气氛”的小说,这里的“纳西气氛”,主要是指纳西族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纳西族居住地复杂的生活条件使纳西族人民形成了其特有的纯朴、勤劳、坚韧的民族底色,那留在一座石塔下,“留着给有需要的人”的一袋粮食,还有欧明阳不愿卷入国共两军相互残杀而选择逃跑,都体现了纳西人民的民族意识,也是他们独特的纳西气氛——忠义之气。田彤彤:
在小说中,作者将云南放置在具体里的历史背景下,使情节体现出历史厚重感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云南的别样风貌。同时,外公与欧明阳,他们的关系是一种脱离政治与历史背景后,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展现,是一种人性的温度。另外,和晓梅特别注重对于耳朵与听觉的描写,这在之前《连长的耳朵》中也有提到。或许在她看来,肉眼所见的世界仍然单一,听觉才是她心目中感知世界的最佳方式。谢轶群:
和晓梅的小说,故事极有戏剧性,但从不叙述得酣畅,她惯于把原本曲折跌宕、引人入胜的情节用细节特写、心理陈述、插叙阻隔、旁观议论等切割得支离破碎,给阅读带来难度也带来探究的蕴涵。读完如上风格的《落地生花的银》,我很想用媒体语言这样宣传:“一位年近九旬的富商,一生严守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岁月深处一次血雨腥风中的邂逅,一张生死以之的照片和家书,一笔下落不明的财富,多年后因一次车祸而在风烛老人的记忆里层层唤起。乱世中的嘱托,竟如此出人意料又如此震撼人心。神秘消失于大地的那笔财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生根开花的深沉情怀?作品展现生命的真,探讨世间的奇,魂系人类的理。”传奇性、历史感、宿命意味和现实人文关怀在《落地生花的银》里熔铸,沉雄,苍茫,而又庄严。李浩(作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得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轻松迅速的、比问题来得更快的回答这种喧嚣之声中,它显然更难得被听到了。”我不是第一次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但在无数次的引用之后再次地引用并用它来言说和晓梅的《落地生花的银》却是恰当的,在阅读的过程中这句话就数次自然、自动地浮现出来,甚至有些“按捺不住”。我记住这句话是因为它说得太好了,小说如果不能提供那种精神复杂性、告知我们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那它就丧失了本质性的意义,就会简化或沦落为普通消费品;我引用这句话是因为和晓梅的《落地生花的银》提供着复杂性,拥有着多重回绕并设有延宕开去的歧义。和晓梅(云南作家,《落地生花的银》作者):
和所有讲故事的人一样,如果你问我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我会狡黠地保持沉默,然后告诉你: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一个“存在”。写它就是为了记住那些极有可能在岁月流逝里被忽略和遗忘的真实。有段时间我专注于写儿童文学,两相比较,我觉得童话来自童年时光的幽暗隧道,小说则来自成年人的无从抉择。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每一种选择都将走向不同的方向,迎来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当人物在分叉口踟蹰不前的时候,小说家需要代替他们思考,然后做出抉择。毕晓蕾(云大2019 级硕士研究生):
葛亮《飞发》刊于《十月》2020年第5 期。作品以港式“孔雀”、沪式“温莎”,两大理发界传奇在香港都市中的沉浮为背景,叙写了一门手艺、两代人的不同命运。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变”的是匠人由上流社会走向市井街巷的境遇,“不变”的是匠人对技艺的坚守。作品最后以一个传奇为另一个传奇送终,为“匠艺”在城市发展浪潮中的辉煌与落寞送上了一首挽歌。谢轶群:
葛亮的这篇小说是一个多维交织、沧桑浑茫的佳作,于理发这样的小事情写出了一部香港社会(也牵连内地)五十年代以来的平民史,作品中普通港人在时代潮流里的浮沉悲欢令人感叹。小说写得非常沉着,全篇用的是不经意的口气,有一种曾经沧海的平淡,因而细品沉厚有力。作品中平常市井烟火气里风雷隐隐,历史的浪涛和人性的波澜交叠,体现出作者不小的格局。《飞发》体现了一种作家气质和学者内涵的结合,我喜欢这样的小说。《对河》(同期《十月》)的作者是42 岁的马笑泉。一篇散文化的小说,描述从幼年到中专生活的时光,比较稀薄的故事淹没在静态描写和心理叙述里。全文流溢浓郁的怀旧气息。“对河”意味着距离,是在经济大发展时代消逝的旧梦,简单,纯朴,在回忆过滤中显出美好。娓娓道来、节奏舒缓的口吻适合怀旧。中年是适合写怀旧文章的年纪,年轻了没有沉淀易显矫情,年老了如果感情冰结、感性衰萎,会写得文学味不足。
看《长江文艺》
丁雯:
包倬也是云南优秀的小说家,他的《驯猴记》发表在《长江文艺》第10 期,被《小说选刊》2020年第11 期选了。小说以孙小圣和方小农从蛇园失踪为线索,“我”和王立春寻其踪迹,最终完整挖掘出了方小农一家三代“驯猴”的悲剧故事。三代人与猴都存在着紧张的关系,最后,孙小圣已无法回归自然,人和猴的相互一跪,人猴皆有无奈、歉疚,才更显“驯猴”的残忍,人类在驯化动物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被驯化呢?小说让将我的思绪引向更深远之境,人与人之间又何尝不如此?刘敏(文学硕士,武汉传媒学院教师):
在作家包倬扎实严密的叙述下,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了生活朴素的质感。祖孙三代与猴子之间不同的悲情羁绊,伴随着隐去了的时代话语符号,传达出作家试图再现历史现实的文学理想。驯猴者一出场就是已被生活打压的抬不起头的形象,他把对生命的温情转移到猴子身上,驯猴成为他人生仅存的英雄梦想。但当驯猴者想让猴子离开培养它奴性的地方,重返自然时,这只听话的猴子却失控了。个体的生存尊严与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相互碰撞,究竟是谁在拯救谁?谁才是真正的弱者?小说如设问般的结局,引我们走向对故事更深层次的思考。
毕晓蕾:
作品以一种紧张且混沌的状态开场,方小农带着一只猴子逃离动物园,方家三代与猴子的故事、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逐渐清晰。方家三代与猴子的故事,实际上是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的缩影。方小农在人类征服自然万物的过程中,做了一次“叛徒”,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主题也在他与猴子的“生死与共”中逐渐清晰。包倬(云南作家,《驯猴记》作者):
谢谢“云大评刊”,从2013年开始一直关注我的写作。像我这种野生写作者,面对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很紧张。特别是“云大评刊”,我是看过你们对某些作品“全面开火”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真诚的批评态度,让人尊敬。《驯猴记》是我去年写的“三记”的一篇,另外两篇是《掩耳记》和《走壁记》,它们应该是会2021年刊发出来。这三个小说,写的都是阿尼卡的小人物,各有侧重,但相互关联。《驯猴记》写的是人和猴子,其实写的是人或猴子。我想写出一种无力的宿命感,以此观照我们的现实生活。
主持人宋家宏:
本期讨论就到这里吧,请各位回去进一步整理自己的发言。这一期好小说多,有些较好的作品我们无法顾及了,是个遗憾。感谢各位用心阅读当前作家的作品,感谢本期嘉宾以文字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本期推荐:
1、伍世云《送伴》,原载《收获》2020年第5 期。
2、焦典《黄牛皮卡》,原载《人民文学》2020年第9 期。
3、李骏虎《木兰无长兄》,原载《十月》2020年第5 期。
4、潘灵《豹子》,原载《青年文学》2020年第10 期。
5、包倬《驯猴记》,原载《长江文艺》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