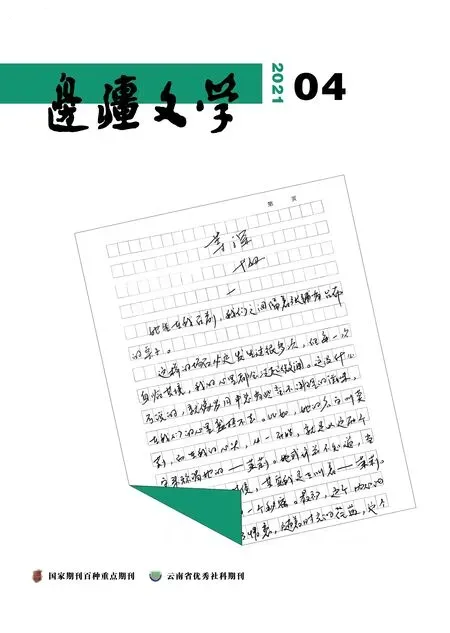荒墟上的生命
何刚
空心菜、豆腐菜、韭菜,哎呀,还有黄瓜、辣椒、茄子……
一种、两种、三种……哦,这几小块地还种了18 种菜呀!
我站在三楼办公室从窗户看出去,见一群女生站在后边菜地里叽叽喳喳,评说着几块菜地。这群学生入学时间不长,对老师还没有太深的怨恨。知道是老师种的菜地,她们兴致盎然。吃零食的时候,玩耍的时候,她们都愿意到这里来。
办公楼在学校最下边,挨着围墙。校园坐落在一块缓坡地上,办公楼后边是最低洼的地方。退后5年,这里倾倒建筑垃圾,碎石、断砖、砂灰。原本和菜地不沾边。
学校地处坝区,最初的建设者(第一批教师),他们的妻子在农村,还深深地接着“三农”地气。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小院里种果树,搭葡萄架,在几幢楼房后边,临着院墙开辟菜地。上世纪,这样的行为还深受鼓励,时过境迁,当下更多的却招致最起码是不以为然或是鄙夷——瞧,这老师,几块小菜钱也要省!
两年前,一位到学校来指导的省城教研员,见到菜地很惊奇,简单询问后问我说,老师种菜会不会给学生不好的影响?我说哪会,这些学生都来自乡村。他摇头不置可否。
学校门口有一块空地,长满野草。几年前,县上一位挂点领导建议开展勤工俭学,还一次次过问,空地便被分到各班种菜。一年后,因为难于开展和领导调离以及学业负担沉重诸多原因,地块被老师瓜分。种菜风气再次兴起。
找一手小白菜,摘一个瓜、一把辣椒,送给同事和朋友,也是一种情趣;买一点肉,菜地里找菜,几个人凑一起,煮一顿饭,喝一台酒,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去。事后想起,也有内心的一丝温暖和怀念。
下一场雨,施一次肥,两三天不见,你会惊喜地发现,蔬菜鲜绿地拔节长高。一个女教师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菜,哎呀,那些烦也就瞬间不见。
这样,一个女教师就打起了这块荒墟的主意。她说的时候,我们都只一笑,想着她也就一说而已。岂料,一个假期后她宣布说自己也有菜地了。我们跑去看,果然,她捡出石头砖块,开辟出差不多半幢楼大小的面积,种了几样蔬菜,地边上还栽活了一株臭菜(树),购置了锄头镰刀水桶钩担,还有一个水泵,可以把隔着一个果园的消防池里的水抽来。
今年,我原先种的菜地学校规划为绿化区,正月里早早种植的瓜菜一下子无地移栽。我跑到办公楼后边去看,剩下的荒墟堆满碎砖块,且覆满枯败的飞机草和各种藤蔓,望着就让人心生畏惧。开辟菜地的女同事已经调离,我就试探着向现在的地主开口,意外地他分给我两小块。
我把三月瓜和辣椒移过来。
小小的两块菜地,两三挑水就浇过来。
换衣服,穿雨鞋,折腾一身劳动的行头只挑两三挑水,哪方面讲都有不尽之兴。锄头和砖石碰撞火星之后,除去野草藤蔓,捡去乱石,最先被我开发的是狭窄的一溜地块,长五六米,宽半米,种了一排红豆一排瓜;一个周末闲着无事,突发奇想并付之于行动,除去乱草扒平之后,我从旧菜地里挑来十多挑土铺出一块菜地,且立马播种:空心菜、豆腐菜和麻叶青。一个星期后出苗,嫩绿的菜苗弱不禁风的样子,逗人怜爱。继续挑土,这样又开出一块,撒茴香、芫荽和菠菜。连续一个月里,每个周末劳动两个小时的最后成果是乱石窝里我种出一片黄豆。又栽了一排瓜。栽瓜的时候,我挥舞锄头,乱草碎石,火星四溅之间,一条小小的麻蛇被拦腰斩断,我把它挑到地边上的水泥地上。这里少有人来,蛇尸就一日日曝晒,成为干尸,惨不忍睹。
地块一侧是一小段未填平的沟壑,覆盖枯枝乱草。某天我经过的时候,听见草丛里窣窣响动,抬眼望去却吓了一跳,一条锄把粗的麻蛇扭着身子正往草丛里钻。关于这条蛇,不止一次地听老教师们说起。都说是在校园里见过最大的一条蛇。过去,食堂在旁边的时候见过,办公楼做女生宿舍的时候见过,也在路上见过。还说,曾经有人要捉它,蛇仓皇遁入墙角石头缝里,被人揪住尾巴,却无论怎么拽都没有拽出来,一松手它溜之大吉。
五月份的时候,所种之菜按部就班,该开花的开花,该结果的结果。清晨,挑七八挑水,在学生起床前我浇好菜水,周末从容,劳动时间可以安排在早上或者傍晚。周末浇水之外开挖薅锄,忙得一身透汗,结束后洗洗澡,感觉一身轻松,心情惬意,这时候就可以做很多事,喝茶、阅读、写作,也可以上网和朋友聊天。
当然,更多的是在课间,在办公室匮乏之时,就一次次地走进菜地,享受女教师说的放松心情。一天一个样的蔬菜,有收获劳动成果的内心喜悦,也有关于生命的内心顿悟。
庄稼也是生命。
是生命就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几个菜友不时交流,说瓜秧太嫩,只能施薄肥;说害虫太多,水白菜不喷药种不出来;说种子没留好,太早开花……
我们是教师,责任是育人。种庄稼和育人,都有一个过程,都在经历中成长。几年前,我让一个有自杀念头的女生天天去看菜,一个月后她笑容灿烂说,那念头成为过去,请老师放心。我在前边说过,现在的学生对老师充满厌恨。学习的压力还在其次,你想想,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少年,他能有多大的人生目标。对这些乡村少年而言,最为严重的是亲情缺失。现在农村学校,从小学就寄宿,只能在周末回家,问题还在于,很多留守儿童即使回家也见不到父母。幼小的心灵过早地承受孤单,变得无比脆弱。我现在教的一群男生,说得上学习认真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是逃避劳动(值日扫地),躲早操课间操,更为严重的是不交作业。学习怠惰让所有老师伤透脑筋。好不容易联系到家长,竟然大多数都不在家,还有家长给子女说情,老师,我家孩子脑袋笨,你多担待,他不闯祸就可以了。老师可以批评学生,但不可以批评家长(事实上,价值观错位原因,或者说现在农村随着收入的增加,少数家长口大气粗,一不小心老师自找尴尬)。当然,如果你要给家长上理论课,说人的大脑都分九个区,聪明程度完全一样……更显书呆子气。
班上有一个女生,入学成绩很好,人也灵气清秀,我指定她担任副班长,但很快我就发觉她缺乏热情。学习不热情,做事不热情。体育课她跑回教室躲避,让她参加拔河或者迎面接力,她都十分不情愿。新年时候,让她参加舞蹈排练,她告诉文艺委员说,她宁死也不参加。有一次她来请假,脸红扑扑的像是发烧,让她到卫生院看病,她说要回家。我联系不上家长,她说奶奶(父母在福建务工)下地劳动去了。发烧,如果没有人陪护,老师不放心,我反复说,也给她找了药,她十分不情愿地离开了。下午她又来了,我看她脸色恢复正常,说不要请假了,却说不通;我批评说,有病要到医院,回家干什么,医院又不开在你家里。她就一直站在我办公室里,一副我不准假就不离开的样子。我无奈之下联系了为学校服务的车子,还请了一位女教师送她回家。女老师回来时说,这个学生急切地回家,好像就是回去讨她奶奶骂。老人一见就唠唠叨叨骂,骂她不认真读书,骂她麻烦老师,她却没有一点气恼的样子,拽着奶奶,很亲切,脸上漾着笑。
酒醉送不回家的人,内心深处那个自己怕的人在吓唬着他;打闹一天,吃免费营养餐(早点),又吃两餐寄宿制生活补助(每月120 元),然后不读书不学习的男生,回家讨奶奶骂的女生……他们内心深处隐藏一只魔兽,用亲情喂养,养饱了沉沉睡去,饥饿之时就让孩子们肆意妄为。当然,也没有人能够预知,这群孩子将来又会怎样的在社会中表现。
三月里撒水白菜,很费事。春回大地,气温升高,一方面要一天两头水,还滋生很多害虫。三四天出苗,长出两个叶子,看着已经覆盖了地皮,一个不小心,那些看不见的虫子一两天就可以把嫩叶啃光,白费功夫。学校门口那片等待施工的地块却不然,几场春雨后,一块块地里,那些冬天散落的种子自己草一样蔓出来,长得一片葱绿,还竟然没有一个虫眼。真是应了那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古话。开工前夕,我原先种的几块菜地里,也拔了十几斤真正无公害纯绿色的小白菜,分送给朋友。
自然的造化,自有它的奥妙。也正因为这样多姿,大自然也就充满魅力,充满迷人的斑斓色彩。
5月里天气酷暑,也是蔬菜繁茂生长的时期。办公楼一楼楼梯间开了一道小门,因不使用而关锁,门外边迎着我的菜地有两级台阶,劳动间隙可以坐着小憩。楼房是东西向,山风吹拂,带来丝丝凉意,下午三四点钟,从闷热的办公室逃出来,这里是一个极好去处。此时,带一本书坐在阴凉里阅读是很相宜的。每个下午,我几乎都可以在那里耗去一两节课时间,能读十几二十几页书。
一个下午,我和往常一样阅读一篇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我读得思绪凌乱。其时,我抬头环视,突然发现右侧那块阴凉的水泥地上团着好像是见过的那条蛇。距离我十多米。我凝视着它。正中的蛇头不时翘起,像是观察和瞭望。十多分钟后,它扭着身子,慢吞吞钻入草丛。另外一次我不经意的闯入,令蛇惊恐不安,它倏一下,似乎是快速地扭动着滚到草丛立即不见影踪。从此内心就不止一次地牵挂了这条蛇。走过或者坐下的时候,都想象着它的出现,但想象的情景一次也没有发生。怎么地就不见了踪影,假如它再次出现,我在心里说,我一定退后5米,不打扰它。
菜地下边是院墙,院墙外是一排高大的桉树。早晨到地里去,地头间会有跳跃的麻雀,人走过去才扑哧哧的惊飞;也不时见到敏捷地蹿跃在树枝或者院墙上的松鼠。一个黄昏里,高大的桉树上甚至还停歇了两支乌鸦,耷拉着黑黝黝的翅膀,脑袋低垂,像熟睡。土地生长蔬菜,但也一样生长虫子。下透了雨,黄蚂蚁如泉般从小小的洞穴里涌出,漫天飞舞;蛐蛐在草间慌张跳跃,伸缩着身子前进的拃拃虫,慢吞吞爬行的蜗牛,在菜叶间结了茧的菜青虫,挂在枝叶间或者跨越地界结了网的鬼脸蜘蛛,忙忙碌碌的蚂蚁,背着一盏灯爬行的萤火虫……
去年,不经意间,我种出了一个超大萝卜,高40 多公分,胸径20 几公分,很多同事前往观看,一个工龄37年的同事说,没有见过这样大的萝卜;今年,听说我又在石头窝里种菜,也不断有人去看。一对退休老夫妻感慨说,哎呀,真的是只有懒人没有懒地,石头窝里也能种庄稼。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我种菜之外,还爬山找菌,也不时和朋友们聚会聊天喝酒。种了菜,写了文章,找了菌,小得意之时,就在微信朋友圈里晒。
有人就问我,你哪来这么大的精神?
我说闲出来的。但仔细想,又似乎难有一个答案。
石刻经,沙地书,水上字,事物都逃不出久远或瞬间这样的时光宿命。都说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和草木比,人生很长,和自然比,一世又算得了什么,连一眨眼的功夫都算不上。
一个夜晚,我在办公室静坐,竟然接二连三地有3 只马蜂闯入,飞蛾扑火一般在灯管上扇着翅膀嗡嗡嗡撞击和爬行,直到力竭掉落地上,我用苍蝇拍把它们送到室外。我就想,这小东西向往光明,朝亮光飞翔或许就是它生命的方式。
围墙外是农田,蛙鸣和蛐蛐欢唱是一种原生态;那些发着强光的校园路灯,只是多少而已,一年四季都有扑火的飞蛾和昆虫,在夜晚或者清晨死亡,像前赴后继的勇士,这也是一种原生态。飞翔、扑火、死亡,虫子们,不,应该是所有生命都有自己开始和结束的方式。
哦,这正如我经管着的这片荒墟,也正如我在荒墟上开辟的菜地,在生命的时光里,有华丽的欢唱,也有悲伤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