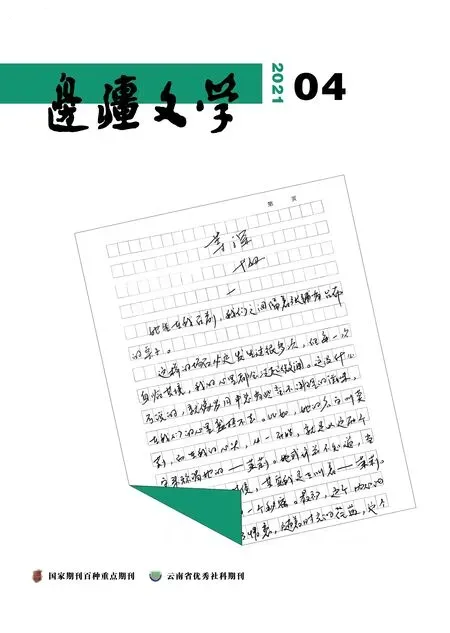雨天书 短篇小说
田兴家(苗族)
我一醒来就下着雨,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但我还是起床开了门,兴许晓默就在今天到达。院子里的泥土完全湿透,一脚绝对踩出一个深脚印。糖梨树下有几条蝼蛄挖的通道,我想象着那玩意如何肥嫩。一条通道的尽头,微凸起的泥土动了动,一只半大的蝼蛄冒出头。那只黑色母鸡从树上飞下来,啄住蝼蛄又飞回树上,一群小鸡叽叽喳喳地抢着吃。
昨晚上我梦到一群飞翔的蝼蛄,它们气势汹汹地攻击我的房子。梦中的我惊慌失措。就在我打算要出逃时,村主任提着网袋跑过来,那模样跟他年幼时一样。村主任吹着口哨,右手在空中画着曲线,蝼蛄沿着曲线飞进左手的网袋里。最后他突然瞪我一眼,用那种开会讲话的语气说:“油炸透后,用来下酒,绝对美味。”我吞了吞口水,他骄傲地笑着走了。
假如晓默今天傍晚到达,雨肯定已经停了一会,那我就把这个梦讲给她听。晓默听完后应该要唱一首歌,然后我们会相拥着哭泣很久。想到这些我鼻子发酸,抬眼看向糖梨树,那群小鸡依旧叽叽喳喳。黑色母鸡从茂盛的叶子里探出头来看我,怪叫两声后缩回头,小鸡全部安静下来。我瞬间有点生气。
肚子里一阵搅动。我想我的肚子里有两条金鱼,它们时不时就甩动尾巴,把我搅得难受。我怀疑是那天在河沟喝水所导致的。那是一条神奇的河沟,年幼时我目睹过一群长翅膀的金鱼从水里飞向天空,它们兴高采烈地叫着,有两条追逐着绕圈子,似乎是故意绕给我们看的。当时阿丑满脸鼻涕,提着网袋站在我旁边,待金鱼飞远后,他说:“有一天我要学会本领。”我感到很吃惊,问他学什么本领,他说:“指挥这些会飞的生物。”我回家把阿丑的话告诉父亲,父亲说:“他是个有正能量的孩子。”果然,多年以后,阿丑就当上了村主任。
有人喊我一声,我看到西村的阿婆翻到石墙上,对我做了个鬼脸,然后跳下墙来。别看这个阿婆已经年老,走路颤巍巍的,她可是翻墙的能手。阿婆年轻时曾开过一个“翻墙班”,招三个强壮的小男孩当作学生(包括我在内),整天讲解翻墙心得以及翻墙技巧。听了阿婆的课后,其他两个小男孩都翻墙摔死了,唯有胆小不敢尝试的我还活到今天。此刻阿婆像是在淤泥里,一脚深一脚浅地向我走来。
“我是来跟你谈判的。”阿婆说着接过我递过去的板凳,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下去,似乎感觉很累。屋檐的雨水不紧不慢地掉在阿婆脚边,我这才发现她已全身湿透,正冒着若有若无的白气。我知道阿婆正在心里发功。“我总怀疑,我养的那条毒蛇半夜溜出来,被你的黑母鸡吃掉了。”阿婆又说道。
听说阿婆二十岁时,丈夫去世,她每天去坟前哭一回。有一天,一条筷子般的毒蛇从坟里钻出来,阿婆认为是他丈夫变的,于是就带回家养,每天给它讲一个故事。一年又一年,毒蛇长大了,有大腿那么粗,阿婆每天晚上都搂着毒蛇睡觉,有传言说她还和毒蛇做那种事情,半夜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可一个下雨的清晨,醒来的阿婆发现毒蛇不见了,找遍整个村庄都不见。阿婆断定毒蛇是趁她半夜睡着时悄悄溜走的,因为那天晚上睡觉时她没有搂紧毒蛇。
“你打算怎么办吧?”阿婆盯着我,咳嗽两声,继续说:“这几天你一直躲着我,所以我只能亲自来到家里找你。”
“你的毒蛇肯定长翅膀飞走了。”我没好气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村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那你为什么老是躲着我?”
“我不想看到你哭泣的样子。”我蹲下身来,换一种语气说:“阿婆,你要试着理解我,别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
“我这么老了,还能哭什么,我只不过想让你把那只黑母鸡赔给我。”
提到这我就来气。那只黑色母鸡原本是在地上生活的,我总是捡它下的蛋吃,它就飞到树上去生活了。这个村似乎什么生物都可以飞,唯独我们人类不可以。我曾向村主任抱怨,我说:“阿丑,我也想要飞,你指挥我一下吧。”村主任笑眯眯地说:“不要急,等我忙完工作了,带你去美国安装一对翅膀。”我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自从他当上村主任,就当面一套背地一套,这让我极其不适应,要不是一直在等待晓默,我早就离开这个村了。这些阿婆是不理解的,我也无法向她解释。
“你看看这些雨,一点停歇的意思都没有,似乎要下到世界末日。”我转移话题。
“可怜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阿婆说:“你呀,简直跟你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世界末日估计就要到了,我总觉得这段时间的夜晚比较长,那些蝼蛄趁我不注意就钻进我的左耳,吱吱地吵个不停。”
“你妈失踪后不久,你爸总在半夜提着镰刀来敲我的门,想残害我养的那条毒蛇,我只能装睡着,用呼噜声把他吓走。”
“你真的无法想象,那些蝼蛄吵累了,就会断成两半,头部从我的右耳爬出来,尾部留在我左耳里腐烂,这些迹象都在表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最后几个字,我故意加重语气说,我想吓吓阿婆。
“其实你妈没有跟那个卖米粉的小商贩走,她是失踪的。一个人失踪就是突然不见了,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世界末日一到,我们就会无法动弹,永远生活在黑暗中,连话都不能说,但我们的思维是清晰的,我们可以虚构一个人,然后想象他的一生。”
“你以为你爸真的是因为上山寻找野蜂蜜摔死的?不,你错了。你爸故意用遍体鳞伤的尸体迷惑我们,其实他变成了一只野蜂。有一年我带我的毒蛇去山里,看到一只野蜂在采花蜜,它的脸跟你爸一模一样。”
一只蝼蛄又从通道里冒出头来,黑色母鸡忽地飞到地上啄住,自己吞掉了。它看了我和阿婆一眼,又飞回树上。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整个天空阴沉沉的。我听到村主任在他家房顶上故意咳嗽,仿佛村里要发生什么大事。我突然感到心烦意乱,那两条金鱼又搅动了一阵。
“阿婆,你从院子里出去吧,铁门没有锁。”停了片刻,我又说:“我不想看到你在墙上对我做鬼脸。”
“好吧,可怜呀,我们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了。”
阿婆站起身来,抖动一下身体,掉了一摊水,她颤颤巍巍走出院子。伸手拉开铁门时,一道闪电劈过来,阿婆的头发瞬间变成一堆熊熊烈火,但她没有任何反应,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远。她的背影越来越小,头上的火越燃越旺。
这令我想到了张三,他说我曾经教过他的初中语文。他第一次来看我时确实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什么时候有过学生,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估计是上辈子的事吧,人们都说我是死而复生的人。有时候我真想爆粗口骂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没有逻辑了,那些醒着的人其实是在昏昏欲睡。我把我的观点告诉村里的人,他们吹芦笙跳着舞来侮辱我,那奇怪的舞姿像是在梦中一样。唯有张三把我的观点记录在笔记本上。
“一个人的背影才是他最真实的内心写照,因为面部表情可以伪装,而背影不可以伪装。”这句话是张三说的。我再看阿婆的背影,已经不见了,只看到一堆火在空中晃动着。张三曾经带几个年轻人来到我家里,为我拍了很多张背影照。张三说要挑一张最好的打印出来给我挂在墙上,但是一直没有实现承诺,我也懒得问他,因为那几个年轻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让我感到害怕。
我似乎又看到一群光头,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一齐打我、踢我、骂我。“你这模样也能当老师?”“你怎么能对一个女同事下狠手?”“你还算个男人吗?”他们的声音乱成一片。有人把我拉起来,用力将我砸在地上,我感觉背上有一根骨头断了,马上一只脚猛踩在我双腿间,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醒过来,我像狗那样趴着,那些穿同样衣服的光头排队在我屁股后撞击。
我们可以假设这只是一个编造的故事,晓默,你不要过于替我难过。你侄儿已经长大,你哥和你嫂离婚了,你哥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没有精力管教你侄儿,于是你侄儿学会了抽烟,那天我在路上碰见他,他还把烟头朝我扔过来。你爸去年过世了,他临终前说要去找你,你妈哭了一天一夜,声音都哑了,从那以后就变成了哑巴。晓默,我不会再和你讨论孤独,我早就战胜孤独了。这让那些石头不高兴,但它们拿我没办法,最多也只能在背地说风凉话。
又有人喊我一声,我回过神来,又是西村的阿婆。她又翻到了石墙上,对我做着鬼脸。我知道今晚又要失眠了,一天中只要看到阿婆的两次鬼脸,晚上就会害怕得睡不着觉。我狠狠地瞪着她,她头上的那堆火依旧燃着,隔着老远热气不断向我袭来。那只黑色母鸡飞过去,欲扑灭阿婆头上的火,阿婆迅速头一歪,用手指比作枪对准母鸡,母鸡立即吐血倒地身亡。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阿婆的动作竟如此敏捷。那群小鸡叽叽喳喳的,它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让我感到很舒服。”阿婆笑着说。她晃动着头,摸了摸头上的火,像是摸头发一样,那表情有些得意。
“真是晦气的一天。”我不高兴地说道,歪过脸去。我觉得不解气,随即又补充道:“那些蝼蛄怎么不钻进她的耳朵里,让她受耳鸣的困扰而死。”
阿婆一定能听出我是在骂她,在这一点上她是很聪明的。我偷偷斜着眼睛看阿婆,她在石墙上调整一下坐姿,并没有生气的迹象。我这才注意到,阿婆身体的范围内没有下雨,也许是她头上那堆火的缘故。她身体以外的地方仍在淅淅沥沥的,那只黑色母鸡的血已经被冲干净。
“我想想还是回来一趟。回来是想找你合作。”阿婆抬起右手做了一下手势,继续说:“你想想吧,在这个小村里,只有我们可以相依为命了。”
相依为命?我差点就笑出声来,我才不会上阿婆的当。其实只有晓默可以和我相依为命,但我不忍心告诉阿婆,我怕她头上的火会突然熄灭,然后她去向村主任告状,那我是负不起责任的。自从阿婆的毒蛇失踪后,我知道村主任在想方设法寻找我的缺点,想在会议上公布出来,让村民们一齐放声大笑三分钟,把我置于死地。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你不知道吗?战争就要开始了。”见我没回应,阿婆又说道:“他们都在隐瞒你,但我想还是对你说实话吧。村里前两天已经组织了一支军队,那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蠢蠢欲动,就等着村主任下令了。”
阿婆的话让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她说的这些是否属实。我调整一下情绪保持镇定,装作无所谓地说:“打仗能有什么用,也阻止不了世界末日的到来。”
“你不要故作清高,到时候战争一开始,你还得来找我。”阿婆清了一下嗓子,继续说:“别忘了当年你爸是怎样求着我教你翻墙的,只可惜你烂泥扶不上墙。算了,我说这些旧事做什么。我只想告诉你,除了翻墙,我还有很多本领没露出来。”
“谁去找谁,还说不定。战争真要发生,大家都自身难保,特别是像你这种年纪的。”我蔑视一般地说道,我想我不能在阿婆的面前表现得太懦弱。
“那就等着瞧吧。”阿婆嘴角笑了笑,接着说:“我的猜测肯定没错,你现在已经感到害怕了,可怜呀。”阿婆说着往墙外跳去。
石墙有两个成年人那么高,原计划砌成一个正方形,可只砌了三条边,是父亲未完成的梦想,但我无力帮他完成了。我看不到阿婆的背影,只看到那堆高高燃起的火,火越来越远。我觉得阿婆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也许她是某个世界的人虚构出来的。那个世界的末日到了,某个人便躺在黑暗中虚构出阿婆这样一个人物。从阿婆的身上可以看出,虚构她的这个人一定有些怪异。
我再向远处望去,估计阿婆已经到家了。我想我得去找村支书,问他是否听说了村里建立军队的事情。我找了一把伞撑开,过去捡起死去的黑色母鸡,我打算送给村支书。据我所知,村支书卧病在床已有半年,村里的一切工作都由村主任主持。村主任那种敢用“阿丑”作为名字的人,有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提着黑色母鸡的尸体走出院子,估计那群小鸡通过树叶的缝隙看到了,它们齐声大哭起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懒得理会,快步往村支书家走去。肚子里的那两条金鱼又开始搅动,这一次搅得很厉害,也许它们已经饿了,我从前天下午起就没有吃任何东西,因为我不想看到小凤那肥胖的身体。
一进村支书家院子,难闻的药味立即扑鼻而来,他家那条躺在屋檐下的狗突然睁开眼睛,摇着尾巴朝我跑过来,想咬我手中的黑色母鸡尸体。我踢了狗一脚,它惨叫一声又回屋檐下躺下了。村支书的妻子正在屋里捣药,村支书在卧室里痛苦地呻吟着,他的儿子和儿媳在楼上吵架,但听不清吵些什么。
“你来得正好,他这几天一直叨唠,说想见你一面,估计是有重要事情要和你商量。”村支书的妻子说。
我心里一惊,莫非是村里建立军队的事情,难道村支书已经听说了?看来这些大事村主任都没有跟他商量,要不他不会说想见我一面。村主任真是个心比天高的人呀。我替村支书感到愤愤不平,赶紧往卧室走去。
“我知道你会过来的。”村支书停止呻吟,试着坐起来,看着很费力。我摆摆手止住了他,让他躺着说就行。
“没什么礼物,就把这只黑母鸡送给你吧。”我把黑色母鸡的尸体放在村支书的枕头边。
村支书努力歪着眼睛看了一眼,长叹一口气,嗫嚅着什么。楼上传来砸东西的声音,好像是砸了一个花瓶。村支书痛苦地呻吟几声,然后对我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后生,只是你读的书太多了,那些书籍让你忧郁,所以你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村支书又呻吟了几声,继续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学习知识的。”停了片刻,他又说:“你现在正一步步走入毁灭之中,不知道你自己领会到了没有。”
这几句没头没尾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难道村支书想见我只是为了跟我说这几句话?这让我一时还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想跟他谈谈村里建立军队的事,但思虑一番决定等他先开口,因为我怕我先开口了会伤他的心。
“我一直都打算要帮助你,但我现在无能为力了。”村支书说,他的表情似乎有些难过。“这样吧,给你一个机会,你把这只鸡拿到龙凤餐馆,叫小凤炖了给我送过来。”听村支书的声音,我知道他一时是死不了的,且有可能会好转起来,重新掌权。
我拿起黑色母鸡的尸体走出卧室。村支书的妻子不见了,地上放着捣好一半的药,我注意听楼上,什么动静也没有。但我没对这一切进行想象,匆匆跨出了大门,屋檐下卧着的狗连眼睛都没睁一下。
途中我摔了一跤,肚子里的两条金鱼终于安静下来,我想它们一定是饿昏了。一只蝼蛄在地上爬行着,它那慢吞吞的模样似在挑衅我手中死去的黑色母鸡。我替母鸡感到愤怒,便把蝼蛄捡起来,看它那肥嫩的肚子和崭新的翅膀,然后丢进嘴里吃掉了。
到达龙凤餐馆时,小凤正坐在门口剪脚指甲,看到我提着黑色母鸡的尸体,她笑眯眯地站起来说:“今天自己带材料来了?”小凤笑起来跟村主任很像,她是村主任的侄女。小凤的丈夫叫阿龙,是个开大货车的。餐馆用他们夫妻俩的名字命名,特色菜就是龙凤汤,经常有人开车过来尝。
我把黑色母鸡的尸体朝小凤扔过去,她那肥胖的身体一偏,伸手抓住鸡脚。我把伞放在饮水机处,大声说:“先给我煮一碗面,再把这只鸡炖了。”
“是给别人炖的吧?”小凤问。
“是的。”我怕她不认真对待,于是欺骗她:“给村主任炖的,炖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咦,还挺会来事的,不错不错。”接着她又说:“村委一天只给我两顿饭的钱,所以你一天只能在我这里吃两顿饭。现在还没到中午,你确定要吃?”
我说:“确定。”
看着小凤斤斤计较的样子,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想问问她,昨天我一天都没吃饭,她是不是应该把两顿饭的钱给我,但我想想觉得算了。小凤把黑色母鸡的尸体放进盆里,打开煤气灶忙碌起来。为了对她的斤斤计较表示抗议,我一口气喝了两杯水。
面条很快就上桌了,我剥两瓣蒜放进去,搅拌一下吃起来。小凤倒热水烫鸡、拔毛、破肚,有条不紊地忙着,我看到她把内脏收起来了。龙凤餐馆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这里面炖的鸡都没有内脏。听说小凤要把内脏留给阿龙吃,好让开货车的他起得像鸡一样早。
小凤正把鸡剁成块,一辆疾驰的小车一个急刹,停在餐馆门口,下来两个男人。小凤放下刀,把他们迎进门。他们点了一道龙凤汤,说是开路路过,特意停下来尝的。小凤笑眯眯地说:“先坐着等一会,我家的龙凤汤是现炖的,比较鲜。”接着她指墙上的电话号码,建议那两个男人存下,以后来之前可以打电话预定。那两个男人存下电话号码后,四处看了看,到靠窗那桌坐下,轻声地谈起了什么事,不时放声大笑。
小凤把剁好的鸡肉放进高压锅里炖,我看到她留下了三分之一。我知道她留着为那两个男人炖龙凤汤,我起身想要过去质问,但无意间注意到那两个男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还打着领带),我一阵惧怕,又坐了下来。我仔细听他们谈话,其中一个说:“这回战争真的要开始了。”另一个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他们都沉默下来。
小凤从冰箱里拿出一截蛇肉,有大腿那么粗,她砍下一小点,把剩下的放回去。我惊讶得半张嘴巴,那一定是阿婆养的那条毒蛇,原来被龙凤餐馆一点一点地端上餐桌了。我再次起身又坐下,那两个穿同样衣服的男人直盯着我。
“这是你们村的那个疯子吧?”一个男人轻声问小凤。
“有时候疯,有时候好。”小凤把留下的鸡肉和切好的蛇肉放进另一个高压锅里。
“听说以前是老师,后来犯事坐牢,就变疯了。”那个男人好像显得很兴奋。
小凤嘘了一声,用眼神示意他,他就没再往下说了。我抬起碗,把剩下的汤全部喝掉。那两个男人不再关注我,继续谈起事情,比刚才压低了声音,我听出似乎还是关于战争的。我怕他们谈着谈着又盯着我看,便蒙住耳朵躲到桌子底下。
过了二十来分钟,有人踢我一脚,我松开蒙耳朵的双手,听到小凤说:“鸡肉炖好了,你快点送去。”我站起身来,那两个男人突然大笑,其中一个说:“像这样的人,在战争中肯定要死。”我向他们看去,但他们没有看我。
我的伞不见了,怎么也找不着。我怀疑是我躲在桌子底下时,被那两个男人悄悄拿走的,但我不敢问他们。我只能冒着雨,提着小凤打包好的鸡肉,往村支书家走去。
路上我看到晓默的侄儿,他和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迎面驶来。到我旁边时,他们一齐朝我吐口水,幸好我反应快,及时躲开了。雨似乎比刚才还大,我全身很快就湿透了。我突然想:这样的雨天,没有母鸡了,那群小鸡怎么活呢?我似乎看到它们哭泣的画面,它们哭得死去活来的,我心里不由得一阵发紧。
走到村支书家院子,看到他家大门紧锁,我这才注意到先前那难闻的药味没有了。我感到莫名其妙,走过去敲门,一点回应都没有,我喊了几声,还是一点回应都没有。那条狗突然愤怒地爬起来,朝我狂吠几声,跳起来想要咬我。情急之下我把鸡肉朝它扔过去,它三下五除二把包装咬碎,大口地吃着鸡肉,还对我笑了笑。
我心里乱糟糟的。我想大哭一场,但晓默还没有来,没有人会拥抱我。肚子里的两条金鱼搅动几下,我想我只能回家。我特意绕从村委会大楼走,我要看看那帮人在准备什么行动。我从窗户看到会议室,村主任正在对一群小伙子训话,那群小伙子穿着同样的衣服,晓默的侄儿也在里面。我一阵惊恐,赶紧走开了。
村主任的儿子在路坎下的地里抓蝼蛄,他把抓到的蝼蛄穿成一串,那串蝼蛄动着脚挣扎着,不时还扇动翅膀。村主任的这个儿子十三四岁就辍学了,整天在村里游手好闲的。我想向他打听有关战争和军队的事情,便笑着打招呼道:“抓去给你爹下酒吗?”他说:“是抓给你爹下酒。”说完他大笑起来。我觉得没趣,继续往家走去。
我湿淋淋地回到院子里,那群小鸡突然从树叶里飞出来,有二十只左右,显然是刚学着飞,有些晃来晃去的。我意识到了什么,用手指比作枪,朝小鸡射击,但一点用处都没有。它们朝我扑过来,我扒开一只,另一只又补上,不停地啄我的脸。我蒙着脸蹲在地上,它们又啄我后脑勺和已掉光头发的头顶。我惊叫着说:“你们的母亲逝世,只是一个意外,并不是我干的……”但小鸡们根本不听解释,我感觉我的头顶已经冒血了。我只得站起来冲出院子,还好那群小鸡没跟上来,又飞回了树叶中。
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得选择去阿婆家。阿婆正在屋里立筷子,她头上的那堆火好像没有先前旺了。阿婆手一松,三根筷子就立在了半碗清水中,接着她微闭眼睛念念有词。我在一边耐心地等待,我想阿婆应该是在向死去多年的丈夫询问毒蛇的下落吧。有那么一秒钟,我冲动得张开嘴,想告诉阿婆她的毒蛇死在龙凤餐馆里,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过了一会,筷子往一边倒去,阿婆赶紧伸手扶住。阿婆拿起筷子,舀半瓢剩饭放进碗中,摇了摇碗,最终把“水饭”倒出门外。然后她似笑非笑地对我说:“看,我说的没错吧,你会来找我的。”
我说:“我能有什么办法?你把我的黑色母鸡打死,那群小鸡找我报仇,我现在连家都回不了。”
“可怜呀,要是你早的时候把那只黑母鸡赔给我就好了。”阿婆把碗和筷子洗净,放回碗柜里,摇了摇头上的火,接着说:“说说吧,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想请你过去把那群小鸡也了结了。”
“可以,但你得告诉我一个秘密。”
我说:“好的,我正好有秘密要告诉你。”
我和阿婆很快回到我家。阿婆所站之处没下雨,我就站在她旁边,却淋着雨。我朝着糖梨树挑衅地叫一声,那群小鸡又飞出来了。阿婆用手指比作枪,对准飞过来的小鸡,一只接一只地射击。很快那二十来只小鸡全掉在地上,村支书家的狗不知从哪冒出来,看到那么多死去的小鸡,哈哈大笑地冲过去吃。
“你要告诉我的秘密是什么?”阿婆笑了笑,把耳朵凑过来。
我在内心里纠结一番,还是打算把毒蛇的下落告诉阿婆,我说:“你养的那条毒蛇在龙凤餐馆里,现在还剩这么一截。”我用手比画了一下。
阿婆突然一跺脚,面部扭曲成一团,想不到她愤怒的表情这么吓人。她头上的那堆火瞬间熄灭,但头发完好无损,只是所站之处又下雨了。阿婆做了一次深呼吸,转身走出院子。我在铁门处看,她是朝着龙凤餐馆走去的。
在转角处,那群穿同样衣服的小伙子四处搜寻着什么,雨依旧淅沥地下着,但他们毫不在意。两辆小车一前一后往村口驶去,我认出前面一辆是村支书家的,后面一辆是刚才在龙凤餐馆吃饭的。小伙子们大叫一声,朝着小车追去,晓默的侄儿冲在最前头。村主任披着雨衣,提着什么东西,不慌不忙地向我走来。
待村主任走近后,我发现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大信封。他把信封递给我,和蔼地说:“这是你的学生寄给你的,前两天就到了,你一直不过去拿。”我接过信封,看到上面有“张三”两个字,心里一阵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是一幅照片——我的背影照。我想,等晓默到了,我们就一起把照片贴在墙上。
村主任已经转身走了,我朝他喊道:“战争就要开始了吗?”
他头也不回地说:“是呀,你最好不要出门。”
照片已经淋了雨,我赶紧回到屋里,把照片锁进箱子。我脱掉湿透的衣服裤子,在床上躺下来。雨好像更大了,哗哗地打在窗外。肚子里的两条金鱼搅动了几下,我捂着肚子翻身侧着。村支书家的狗估计已经把小鸡吃完,它来到我床边,我懒得理会它。它猛地抖动身体,甩下一摊水,朝我笑了笑,转身出去了。
晓默,下雨天合适谈论什么,世界末日,还是感冒?可惜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感冒过没有。那就谈论即将发生的战争吧,等到黑夜来临人们就会穿上苗族服装吹着芦笙跳起舞,在战争中等待死亡或者重生。晓默,你侄儿也加入了村里的军队,他那神气的模样也许会让人羡慕。如果他在半夜三更战死沙场,你一定要托梦给你母亲,让她不要再哭泣。
晓默假如我躲在窗前远眺看到一个矮个子姑娘从田里回来手举一片荷叶那个姑娘一定就是你晓默你跟路上遇到的人打招呼天色渐渐变暗有很多话还没说出口战争就要开始晓默你快一点吧我在为你感到心急如焚屋檐越来越低我们像是回到遥远的童年暗黄的电灯下简单的晚餐一如往常可是战争就要开始枪声突然响起你丢开荷叶朝我跑来惊慌失措的样子瞬间让我流下眼泪……
我似乎听到什么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声音越来越真切,不一会就变得密密麻麻的了。我爬起来向窗外看去,一群壮大的蝼蛄队伍飞过来,很快就到达了院子。眨眼之间,已经有蝼蛄从那扇破窗飞进来,我赶紧下床跑出卧室。屋里的大门没关,蝼蛄已经飞进屋里,一齐朝我扑来。我想跑出门外,但蝼蛄越来越多,形成一道门把门框堵住,我根本挤不出去。
我大声地叫喊着求助,但我的声音卡在声带里传不出来,连我自己都听不到。我想到了村主任,他会不会提着网袋跑过来呢?蝼蛄已经沾满我的全身,我想扒开眼前的蝼蛄,可连手都抬不起来。我知道还有很多蝼蛄继续朝我扑来,我的整个身体越来越重,最后失去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