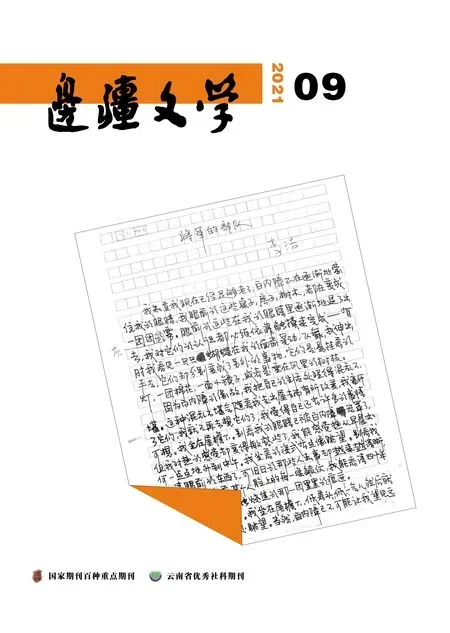怀羊记
李光彪
漂泊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唯有几个散落在城市缝隙中的老乡,如走进海市蜃楼森林里为数不多的几只羊,隔三岔五,总会找羊似地你找我,我找你,互相邀约,轮流坐庄,聚在一起喝茶打牌,叙旧聊天,畅饮几杯。
老乡们经常约会相聚的地方,叫“乡巴佬羊汤锅”。那是一个餐馆的名字,是一位老乡进城打拼多年后开的,天天经营来自家乡的黑山羊肉和山茅野菜。每次去“乡巴佬羊汤锅”这个“根据地”。老乡见老乡,浓浓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全都浓缩在故乡浓浓的羊膻味里。
1
故乡的山如千层肚,一望无际连向天边。白云缭绕的山间,草木郁郁葱葱,每一座山头都是天然的牧场。祖祖辈辈饲养的家畜,要数黑山羊最多,多的人家几十只,甚至上百只,少的人家十几只,是黑山羊生长的摇篮。
在故乡,任何一个孩子呱呱坠地,总有人问,是生了个“满山跑”,还是“锅边转”?一打听便心知肚明,“满山跑”是男孩,长大是个放羊掌门立户的。“锅边转”则是女孩,长大以后是嫁出门给人做饭的。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男孩就像羊一样,比女孩重要,不仅可以放羊,还可以多读几年书,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在我家,母亲却是把羊当猪牛饲养。每天黄昏,放牧归家的羊,常被母亲叫我配合她,隔在门外,一只一只扒着头,数着进圈。有时,羊群乱了,数不清,又要把羊赶出来反复数,总担心哪一只羊丢失在山上。
不论哪只羊生病受了伤,母亲总会想方设法给它们喂草药、包扎。尤其是哺乳的母羊,母亲还要牵出圈,拿来菜叶、苞谷、黄豆隔槽喂养,生怕母羊奶水不足。直到小羊羔一天天长大断奶,才平等对待。
过上十天半月,母亲总要把羊圈楼上那匹好几米长用树凿成的羊槽拿下来,撒上盐,让羊“噗嗤噗嗤”舔吃。羊群“咩——咩——咩”嘶叫着,顺着羊槽排成两列纵队,争吃打闹,一派欢天喜地。
母亲给羊喂盐,有时是在野外放牧溪水潺潺的山箐边,拿出一块随身带的盐块,在那几块大石头上摩来擦去,一边摩擦,一边呼唤羊,羊就会听到指令似地争先恐后跑来舔吃石头上的盐。此刻,母亲手里的盐块成了遥控器,羊跟着母亲从这个石头跳到那个石头,仿佛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把母亲围成了圆心。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放牧归家的时辰已到,是母亲召唤羊群回头,准备赶羊回家,清点羊群的特有方法。
有时,羊多绕眼,疏忽大意,就会丢失,直到回家进圈清点时才发现,就要重蹈覆辙去找羊。可找羊并不是容易的事,我曾经跟着母亲去找过两次羊。
有一年夏天,我们一群娃娃去放羊,我家一只怀孕临产的母羊不知在哪座山掉队了,直到放牧归家进圈清点羊时才被母亲发现。稀里哗啦吃过晚饭,母亲一边责怪我,一边领着我沿着赶牛羊的路准备连夜上山去找羊。
迎着锅底黑的夜色,母亲在前我在后,还有我家那条看家护院的大黄狗。母亲一边走一边呼唤羊,我也忽松忽紧弹奏着喉管,张大嘴巴“咩—咩—咩”似像非像学羊叫,上山不久,远远地就听到了羊的叫声。这时我才发现,羊通人性,我们在找羊,羊也在找我们。我和母亲顺着羊叫的声音,继续往前找,很快就找到了那只刚生下小羊羔不久的母羊。喜出望外的我抱着热乎乎的小羊羔,就像抱着自己的小弟弟跟着母亲蹦蹦跳跳回到家,全家人高兴至极,就连邻居也像看孩子出生似地跑来看热闹。
还有一次,我们一群娃娃把羊赶上山,贪玩的我们只顾跑到大老远的公路上追汽车和拖拉机,既没有人“扎羊头”,也没有人“收羊尾”,羊群就成了无将指挥的部队,散兵游勇满山遍野乱跑。直到黄昏赶着羊群回家进圈清点时,才被母亲发现,羊丢失了三只。
家里的每一只羊,母亲都分别给他们命名,羊的档案就装在母亲心中的U 盘里。火眼金睛的母亲一眼就看出丢失的是大羯羊、馋母羊和她的孩子。
故乡的每一座山都装在母亲的心中,每一条山路都连着母亲的百度。母亲反复盘问我放羊的地点和线路后,就带着家人和我,还有那条看家护院的大黄狗,打着手电筒,连夜翻山越岭去找羊。可是,不管我们怎样呼唤,羊没有半点回应,夜来的山野只有碧波荡漾的松涛在号啕大哭,还有一些怪声怪气的夜鸟在山谷里撕心裂肺地鸣叫。母亲却拉开嗓子唱起了放羊调:
正月放羊正月正,离开爹娘动了身,
羊儿赶在前面走,儿子抓棍后头跟。
二月放羊是新春,山上嫩草往上升,
羊儿不吃东山草,赶在河边吃树条。
三月放羊三月三,女儿放羊绣牡丹,
牡丹绣在荷包上,看花容易绣花难。
四月放羊四月八,儿女放羊带剥麻,
不知不觉天黑了,儿女剥麻一大把。
五月放羊是端阳,糯米粽子蘸白糖,
人家端阳多热闹,儿女放羊在山上。
六月放羊三伏天,热得儿女汗布干,
羊儿热得不吃草,儿女热得心发慌。
七月放羊七月七,牛郎织女配夫妻,
女家丈夫出远门,男人在家多纳闷。
八月放羊是中秋,高山放水低山流,
高山放水归大海,儿女放羊不回头。
九月放羊菊花黄,菊花做酒满堂香,
人家做酒有人喝,我家做酒无人尝。
十月放羊小阳春,百样小草齐枯根,
羊儿不吃枯叶草,儿女拿棍赶不了。
冬月放羊冬月冬,遇到寒天刮大风,
冻得羊儿不吃草,儿女小脸冻红了。
腊月放羊腊月八,家家户户把羊杀。
杀了羊儿好过年,儿女匆匆赶回家。
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是在为我们撑腰打气壮胆,不要怕那些豺狼虎豹,我们手里不仅有刀斧棍棒,还有猎枪。
那一夜,虽然全家人出动,但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找到羊。闯祸的我躺在床上睡了个鸡眨眼,却梦见我家的三只羊是被贼偷的,已经赶进了汤锅房,变成了狗街集镇上香喷喷的羊汤锅,香喷喷的粉蒸羊肉,香喷喷的下酒菜。
还没等天亮,东方发白小星稀时,母亲就把我从梦中摇醒,催促我起床,一起去山背后的村庄找羊。
花枝招展打扮一新的母亲,就像传说中的咪依噜,仿佛不是要去找羊,而是要去做客。母亲领着我,出了这个村,又进那个村,挨村挨户,见人就甜嘴甜舌打听羊的下落。果然不出母亲的意料,误把庄稼当作草吃做了一夜俘虏的羊终于在白石崖村找到了。可是,虽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父老乡亲,但按照乡村的生存法则,牛羊残害了庄稼,都必须按质论价赔偿。愧疚的我就像不会说话的羊,只好默默“低头认罪”,把头插进裤裆里,听母亲反复向田地的主人道歉,双方磋商达成赔偿粮食的斤头,才把丢失的羊还给我家。
回家的路上,我像家里那条看家护院的大黄狗,屁颠屁颠跟在母亲后面,又高兴,又气馁。高兴的是三只羊失而复得,气馁的是要赔偿人家三十斤粮食,已是我一个月读书住校的口粮。母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叫我猜谜语:三十六只羊,赶进汤锅房,杀单不杀双,七天要杀完,一天杀几只?可是,木头木脑的我横算竖算,怎么也答不上来。母亲却不告诉我答案,只是丢下一句话:这么简单的算术都不懂,再不好好读书,就回家来放羊算了。
母亲的话仿佛是在用羊鞭狠狠地抽打了我一顿。吃了败仗的我耷拉着脑袋,跟在母亲和羊的后面,也成了羊的俘虏。
2
故乡山高坡陡,村庄依坡就势躺在山上,田如裤带系在山腰,地如膏药,东一块,西一块贴在山梁。抬脚出门,不爬坡,就下坎,很多农活都是背的多,挑的少。因而家家都把宰杀后的羊皮晾干,请皮匠缝制成羊皮褂,多的人家大大小小几乎每人一件,少的人家也有三四件,用来干农活时穿。既可以减轻背、挑、扛、抬时货物与身体的摩擦,又可以缓解疼痛,保护衣物。
故乡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小饲养员。到了寒冬季节,草木枯零,每天放学回家,我常被母亲安排去蚕豆田里,麦地埂边,找那些嫩生生的小草回家喂吃奶的乳羊。
但是,有极少数“䯐肋巴”的乳羊,由于亲生母羊是头胎生育,奶水少,不够吃,别出心裁的母亲就会叫我配合她,以苞谷黄豆为诱饵,连喝带哄牵出另一只奶水充足的母羊,准备给“䯐肋巴”乳羊“讨奶吃”。正在低头吃苞谷黄豆的母羊扭过头吻吻正在拼命吃奶的“骇肋巴”乳羊,明白不是自己的孩子,又跳又叫,表示不满,强烈反抗,最终拗不过母亲和我,一次又一次被软禁。有奶便是娘的“骇肋巴”乳羊通过“讨奶吃”,一只只得以顺利成长。
在我的眼里,最残忍的要数骟公羊那一幕。当幼小的公羊断奶不久,母亲就会选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请来村里的劁猪匠,把一只只年幼无知的小公羊拖出圈,按倒在地,让劁猪匠握弄着亮汪汪的刀,割去睾丸。每次目睹那无法反抗,声嘶裂肺,痛苦呻吟被骟的小公羊和劁猪匠拎着那些还流着鲜血,像洋芋蛋的“胜利果实”扬长而去时,我的心也仿佛挨了一刀,总担心那些被骟小公羊的命运。可是,在母亲十天半月的精心服侍下,一只只小骟羊还是有惊无险,又肥又壮渐渐长大了。
慢慢地我才明白,羊群要发展壮大,除选留一两只健壮的种公羊外,其他的公羊都将经历这场苦难,被割去睾丸,成为羯羊。原因很简单,只有大羯羊才能卖得好价钱,家里才会“发羊财”,我才有足够的钱交学杂费,买书纸笔墨,顺利多读书识字。
那时,常听母亲说:“工人爱件大棉衣,农民爱件大羊皮”。的确,在那个物质匮缺的年代,一件羊皮褂至少要两三张羊皮才能做成,跟一件棉衣的价值差不了多少。可要缝制一件羊皮褂,并不比添置一套新衣服简单。从一只小羊生下地,要饲养两三年,历经一场又一场疫病,才能长成大羊,确实不易。所以,母亲常把那些病死的小羊皮剥下,钉在木墩头上,让我当作今天的沙发坐。而且,母亲哪怕是家里再穷,卖羊也不卖皮,宁可少卖点钱,也要折成价,把羊皮从买主手中赎回来,晾干后,有计划地请皮匠缝制成七大八小的羊皮褂,让全家人个个都有羊皮褂穿。
新缝制的羊皮褂白生生的,毛朝里,皮朝外,穿在身上,里面保暖,外面防脏。可一遇水淋,就会“翻硝”,脆烂。为了延长羊皮褂的使用寿命,母亲总会把榨油剩下的油枯,炼油后的油垢,抹在羊皮褂上,用手反复揉抹,放在高高的柴码上,让阳光曝晒。尤其是每年杀年猪时,盼望着把猪尿泡当球玩的我,常被母亲使唤,安排我把猪尿泡上那些丁丁点点撕不干净的“花油”,连同猪尿泡一起反反复复在羊皮褂上搓揉,直到猪尿泡揉得半干,油被羊皮吸净,母亲才让我往猪尿泡里吹足气,扎紧线,自由自在当球玩。也有时一不小心,猪尿泡被狗叼走,追不回来,不仅让我没有球玩,而且还会遭到母亲的责骂,让羊皮褂错过了一次搽油的机会,令我既无奈,又失望。
经常把羊皮褂当作衣服穿的母亲,旧的穿着干农活,新的当衣服外套穿。就连做客,也经常穿着那件心爱的大羊皮褂。并在人家面前炫耀“是大羯羊皮做的”,让村里很多人眼气。并且隔壁邻居虽然有借农具、家具的习惯,可母亲却舍不得把她那件崭新的羊皮褂借给别人穿。总是说:“我是个害冷痨,穿在身上就脱不下来呢!如果不嫌弃,这件拿去穿,这件拿去穿……”说着就拎出一件旧羊皮褂打发邻居。有时去猫街、狗街卖菜、卖猪鸡,母亲也穿着她那件心爱的大羊皮褂。路上走累了,脱下来坐着歇气,到集市上脱下羊皮褂垫在屁股下就地坐着,就摆开了货摊。买卖完毕,站起身,抖抖灰,羊皮褂又穿在了母亲身上。
有一年秋天,放暑假回家的我跟着母亲去放羊,出门时,还天晴地绿的,没带雨具。谁知,羊赶上山放了不久,排山倒海般的黑云就像被狗撵羊群,密集涌来,“唰啦啦”下起了“太阳雨”。急中生智的母亲,把我拉到就近一棵密匝匝的罗汉松树下,把羊皮褂翻过来,毛朝外,让我像只小鸡躲在母亲的身后,仿佛装扮成要耍龙舞狮的样子,顶着羊皮褂避雨。一场大雨过后,我和母亲的衣服几乎都没有被雨淋湿,干生生的。让我又可以在雨后的山间,尽兴地吆喝着羊,采摘着野果,拾着蘑菇。就在日头偏西时,我和母亲收拢羊群,准备赶着羊下山时,在一块“二荒地”里见到了一片“白哗哗”的“火把鸡枞”,母亲只好把身上的羊皮褂脱下,才把全部鸡枞兜回了家。
伴随着母亲饲养的羊换了一群又一群,羊皮褂也换了一件又一件。“荣升”奶奶的母亲,经常把羊皮褂铺在地上,让大哥、二哥的孩子在上面学坐、学挪、学爬,摇摇晃晃站立起来“打登登”学走路。有时,母亲不仅要领几个吃奶娃娃,而且还要忙煮饭、做家务,别出心裁的母亲,就在舂米的石杵臼里,或是石缸里垫上羊皮褂,让孩子们坐的坐、站的站,在里面玩耍,既稳当,又安全。直到手头的活计忙完,母亲才把孩子们从石杵臼、石缸里抱出来。据母亲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是用这种方法领大的。
如今的家乡,仍有人饲养着黑山羊,而羊皮褂几乎全由那些麻蛇皮口袋改制而成,穿起来既轻便又漂亮,还可以像衣服一样随便洗。羊皮褂已经成了稀奇旧物,进了农耕博物馆,只有那段羞涩岁月打摞在故乡人身上的补丁,令我至今难忘。
3
羊肉是故乡难得的美食。
那时,一年半载也吃不上几顿肉,但我们村每年到了端午节、火把节、中秋节、彝族年、春节这几大节日,生产队那几个当头的人,总会召集大家宰杀两三只羊。羊肉有蒸的,有煮的,一碗一勺,多多少少,一人一份,分给全村人。不论穷的富的,过年过节家家都能吃上肉,滋润滋润生锈的肠胃。
每当得知村里杀羊的消息,我们一群孩子就像村里那些嗅觉灵敏的狗,马马虎虎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敷衍了事做完大人安排的拾粪、找猪草之类的活计,就会早早地跑到生产队杀羊煮肉的地方看热闹。杀羊,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看一场不花钱的大戏。被杀的羊一般是羯羊,或者是不会生育的蒙母羊,看上去油光水滑,满身堆肉。只见几条汉子七手八脚把羊按倒在石阶边沿上,杀手握着一把亮汪汪的尖刀,从羊的耳朵根部猛刺杀下去,鲜红的血顺着刀尖哗啦啦流淌,羊声嘶力竭挣扎,一直到死都睁着眼睛不闭。好奇的我们一边麻利地帮大人打下手,拉羊脚、剥羊皮、翻羊肠肚、烧羊头蹄,一边多脚多手不停地往那几口簸箕大的铁锅下添柴凑火,个个都争先恐后,拿出最积极的表现,讨好操刀掌勺的大人,盼望早点分到肉、吃到肉。
柴火在熊熊燃烧,锅里的肉在不停地打滚,馋猫见肉般的我们如饥似渴熬到下午,“总管火”就会打发我们一个还带有点筋筋肉的骨头,让我们先尝一口,啃得津津有味。当我们把那些啃过的骨头扔出手时,看到的是一群狗互相撕咬“汪汪汪”争抢骨头的拳王争霸赛。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是导演者,如看了一部很成功、很过瘾的电影战斗片。
柴不停地在我们手里添加,火在笑呵呵地燃烧,临近黄昏,到了分肉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我们跑回家拿着锅碗盆,一边跑,一边喊“分肉喽——分肉喽!”
前来分肉的大多数是娃娃,各家各户各式各样的锅碗盆依次排队摆开,等待分肉的时光总是那样漫长,迫不及待我们就叮叮当当敲响锅碗盆,催促“总管火”分肉。当“总管火”把肉一份一份分到自家锅碗盆里时,我们嘴里的口水不知往肚子里咽了多少次。各自端着肉回家,一下子,羊肉的味道弥漫开来,整个村庄都是香喷喷的羊肉味道。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那种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羊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又香又暖心。那是我们可以放开肚皮美餐一顿的肉,几乎要到下一次节日轮回才会消化。那种柴火味的羊肉,多少年过去了,至今仍埋藏在我顽固的蛋白酶里,成了味觉里挥之不去的乡愁。
4
在故乡,很多人家杀羊时,不仅煮“羊汤锅”,还剁“羊肝生”,做“粉蒸羊肉”。“羊汤锅”如杂锅菜,容易做,而“羊肝生”就有技巧,要把羊的心、肝、肺、肠、肚煮熟后剁成肉沫,再把杀羊时留下的血用花椒面、辣椒面浸泡,与青笋丝混合拌匀后方可上桌,吃起来又凉、又香、又脆,是一道可口的下酒凉菜。“粉蒸羊肉”也是故乡人的“发明创造”,剔除头脚、内脏下水煮汤肉,其他羊肉宰成小块,连骨头带肉爆炒后,撒上早已准备好的粉蒸面(米、花椒、茴香籽、八角、草果,同锅炒后混合磨成面)拌匀,趁热装进甑子底垫有一层厚厚鲜嫩茴香的木甑,加火猛蒸。出甑的羊肉如猪肉粉蒸排骨,香喷喷地诱人。
“羊汤锅”总是与故乡节日相伴。尤其是猫街集镇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二月初九”“三月十二”,天台街的“正月十六”,牟定县城的“三月会”,永仁的赛装节等等之类的民族传统节日,“羊汤锅”就会星罗棋布,“遍地开花”,节日里到处都弥漫着浓浓的羊膻味。故乡的羊汤锅不仅集市上的乡街子卖,山头上的山街子也卖。如化佛山立秋节令之日“赶秋街”,柜子山“六月六”,都有不少人搭起临时棚子,支起大锅,就地取柴,蒸一甑米饭,煮一锅“羊汤锅”,就地撒上青幽幽的松毛,再加一壶自家酿制的小灶酒,就开张经营,招揽山客了。
从小放过羊,穿过羊皮褂,拾过羊粪,吃过不少羊肉的我,进城三十年,骨子里浓浓的羊膻味总是让岁月无法漂洗干净。有时思念故乡,想吃羊肉,自己去菜市场买上两三斤回家,模仿记忆中故乡人煮“羊汤锅”,做“粉蒸羊肉”,却始终没有故乡的那个味。
客居滇中楚雄鹿城,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彝族“火把节”,除了那些别出心裁的商贸活动外,还有颇具特色的“羊汤锅”一条街。一个个招人惹眼的“羊汤锅”招牌,一间间新搭的货棚下,吃“羊汤锅”的人络绎不绝。我和朋友总会互相邀约,去凑个热闹,甩(吃)上几碗,喝上几盅,解解馋,过上一把“羊汤锅”瘾。
在楚雄,大多数人吃羊肉,都喜欢跑去彝人古镇。那里卖羊肉的摊点很多,白天以卖“羊汤锅”为主,晚上卖烤羊肉。楚雄人卖羊肉就图个货真价实,一只刚宰杀好的羊,掏空肚杂,赤裸裸挂在烧烤摊旁,挂在羊肉餐馆门口,实实在在告诉你,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要吃哪块,割下哪块,一边加工,一边烧烤,一边吃,卖的就是眼见为实的新鲜。不少外地来的游客,看着就眼馋嘴馋,一屁股坐过去,又是羊肉又是酒,喝着喝着,酒也多,话也多,深更半夜都还坐在羊肉摊上,聊不完的天南海北。
而我们常去的“乡巴佬羊汤锅”就像羊肉串一样,把漂泊在外的老乡们的血脉串连在一起。“故乡”这个词,在我们的心里,已是“羊汤锅”里熬煮不化的骨头,总是那么余味绵长,那么耐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