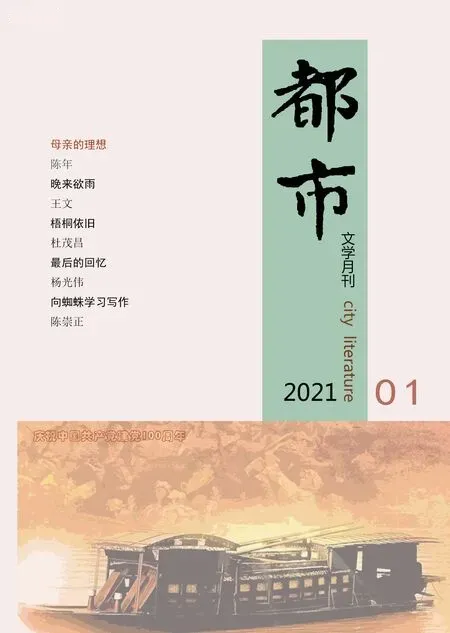母亲的理想
陈年
看韩国电影《寄生虫》,当看到没有工作的基宇一家在半地下室里为比萨店折包装纸盒时,李劼不由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她凌晨坐在小板凳上包小馄饨的样子:左手拈起一张馄饨皮,右手拿一块舌形的小木板往面皮子上抹一点肉馅,手心里一团一攥,四方的面皮就变成一朵含苞欲放的花。
母亲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凭着她的聪明和勤劳让全家人过上幸福的好日子。从二十七岁到四十七岁,这个朴素的愿望伴随着她走过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李劼是在香港回归那年的二月出生的,听母亲说那一年春节时,每个单位都发了串串灯,大街上的建筑物上、树上也挂满了一闪一闪的彩灯,说是家家挂灯户户披红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然而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十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街头所有的彩灯彩旗都撤了下来。这是国家重大事件留给普通老百姓的记忆。
这一年二月,他们的小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没有钱装修,他自己弄点涂料刷了刷房,又到五金店买了一张白铁皮,自己动手包了包门皮,上面用铜钉镶出一个金灿灿的“福”字图案。大门是一个家的脸面,所以花在上面的钱和心思就多些。母亲对门很满意,那时还没有高端的防盗门,矿区人流行用白铁皮包门,一扇银光闪闪的门暗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三月份的时候他们抱着刚刚满月的李劼欢天喜地地搬到了新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分房子搬新家更值得纪念。
福祸相伴,住进新房子的第二年,二十七岁的母亲离开了她工作十年的单位。她下岗了,从此成了一名无业人员。母亲不甘心沦落为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而且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她成为全职太太。当初为了买房,刚刚结婚一年的他们和亲朋好友借了大量的外债,谁家也没有闲钱搁着,各家有各家的困难,为了信誉,他们必须尽快把钱还给人家。母亲心急如焚,天天出去找工作,可煤矿上根本没有多少工作岗位适合女工。
为了重新找到工作,她厚着脸皮求一位队长,想得到一份农场的工作。农场是为了安置下岗工人新成立的一个单位,主要工作是开荒种地,养猪,养兔,养鸡。工作条件并不好,每个月只能拿百分之七十工资。但是失业的女工们已经有点饥不择食,只要有工作可干她们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当然把工作当作救命稻草的人家都是穷工人。
队长是父亲的熟人,以前两家关系还不错,不同的是队长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他写得一手好表扬稿,矿上的广播站天天念他的稿子。凭借稿子,队长脱离生产一线进入机关,再进入领导层。煤矿地界小,队长也算是领导人物。
母亲被安排在蔬菜大棚工作,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刚开始满脑子都是浪漫的画面,外面天寒地冻白雪茫茫,大棚里面绿油油的菜蔬生机勃勃地生长着。红色的西红柿、紫色的茄子、绿色的小青菜……恬静安然的农耕田园生活是她一直向往的。
母亲工作没多久就离开了农场,好像是刚刚领到了一个月的工资。母亲用那笔钱给她买了一个巨大的布娃娃。娃娃的腰间有一个小机关是声控喇叭,隔空拍一拍手,娃娃会叫爸爸,再拍一下,叫妈妈。布娃娃一直陪伴着她长大,直到李劼的个子一点点超过它。她七岁时终于可以轻松地抱着布娃娃出门找别的小朋友玩耍了。不过这时布娃娃已经被蹂躏得面目全非,顽劣的她把娃娃的眼睫毛拔光了,卷曲的黄头发也被修剪得七长八短,还用油笔在脸上画了许多蓝色的圆圈。藏在里面的喇叭早坏掉被扣出来丢了。一种习惯吧,过年时母亲把娃娃肚子里的人造棉掏出来,外壳洗干净挂在阳台上,冷不丁看去,晃晃荡荡就像挂着一张人皮。有一回她也学着母亲的样子给它洗澡,把娃娃开膛破肚。母亲回来怎么缝也缝不好,她不得不丢掉了这个亲密伙伴。
这么详细地讲述一个布娃娃,是因为布娃娃和母亲的工作有间接的关系,买布娃娃的钱是母亲最后一次领工资。她那么珍惜布娃娃,也是对体制的一种怀念。离开农场后母亲再也没有进入任何一家单位,她和国有煤矿完全没有关系了。布娃娃让母亲丢掉重回国企的幻想,破釜沉舟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李劼曾读过母亲当年的一篇小说,小说不长,只有几千字。母亲曾经是一位文学青年,她还组织过文学社团,据说文学社最鼎盛时有三百多名社员。这些文学社员遍布矿区各行各业,有机关干部、有老师、有煤矿工人、有售票员、有农民轮换工、有小商小贩,这些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而走到一起。他们中最出色的一位还被推荐到鲁迅文学院上学。母亲也算有点文学天赋,她的作品在省里的刊物发表过,那是唯一一次,后来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没有再把文字变成铅字。
小说的题目叫《礼物》,漫天的大雪,温暖潮湿的大棚,绿油油的菜蔬,在铺垫好浪漫的环境后一个穿着红大衣的女人出现了。因为寒冷,她的苹果肌被风雪染成可爱的樱色。她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了表示感谢,她准备给队长送一件礼物——一个精心挑选的剃须刀。外来货,是从香港那边夹带过来的。女人的哥哥在广州工作,她托哥哥买的。这件礼物本来是准备送她丈夫的,现在被拿来送给另外一个关系自己命运的男人。物尽所用,既然是礼物就应该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这个男人可以帮她找到工作。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工作是一件天大的事。的确,送男领导刮胡刀有些暧昧的意思,但她也许就是需要利用这一层的暧昧。
女人带着礼物去找队长,公事私事都有,公事是黄瓜秧该转棚了,私事是她想转到另一个蔬菜大棚,小青菜的管理要轻松些,黄瓜棚的劳动强度太大了。
队长笑眯眯地听完女人的要求,伸出的一只手先是无声无息地放在女人的肩上,很快就试探着向下移动,并像蛇一样慢慢滑入女人的领口,他的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搂着她的腰,他的身体从她身后一点点靠过来,近得让她能感到一种可怕的坚硬。忽然,队长把她的肩膀掰过来,并把舌头伸进她嘴里强吻了她。女人完全被吓傻了,身体的姿势极端别扭,却又感觉无法动弹,完全僵在那里,像一截木头。她一点也不懂得配合,队长可能有些扫兴,接下来并没有对她实施进一步的侵犯,就把她放走了。据她对这个好色男人的了解,他并不缺女人,他的手下有近百名女工,为了得到一份轻闲点的工作,很多女工争着往他怀里扑,有时甚至还会明里暗里争风吃醋,这一点让他变得更加倨傲,甚至开始挑挑拣拣起来。女人明知他有这个嗜好,却依然选择一个人去送剃须刀。因为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安全的,不是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女人从办公室出来后,一路在哭,她当时不是不能反抗,而是不愿意反抗,她逆来顺受还是希望留住那份工作,最起码能拿到那个月的工资。她想用最小的牺牲保住工作,一份稳定的收入对她的家庭太重要了。
回到家里女人一次次的刷牙,她遭到了羞辱侵害,却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女人知道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一辈子也不能,如果说了那会毁了一个女人的名誉。没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自己的妻子遭受其他男人的侵害。
女人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件礼物送出去,那么她的工作自然保不住了。
现在,母亲还有一天刷四五次牙的习惯,有时候正看着一部电视剧,她站起来就去刷牙。父亲说,你妈有洁癖,和你当医生的姥姥有关。医生们大都有洁癖。一天洗无数次手,还用小刷子仔细地刷指甲缝。
读母亲的小说,让李劼长时间沉浸在悲哀中。为母亲生活的那个年代。“下岗”这个词对于95 后的李劼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了解母亲下岗的原因,她特意在网上搜索了1998 年时世界、中国究竟发生什么大事,怎么一下子会有那么多的失业者。
1998 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危机的起源发生在泰国,当时泰国经济疲软,外汇储备不多,还欠着大量的外债。泰国的这个特殊情况被金融大鳄索罗斯盯上,他先是借一大笔泰铢,把泰铢换成美元,当泰铢贬值后再买回泰铢给人还回去。泰铢最后贬值了60%,泰国的股市也狂跌70%,泰国老百姓蜂拥到银行挤兑,先后挤垮了56 家银行。泰国的很多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因此失业。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的经济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老国企,大都背负沉重包袱,这场风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中国统计年鉴》的记载中,当年原有国有企业职工1.1 亿人,集体企业职工4000 万人,1998 年经历下岗潮后,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则为5200 万,集体工减为1000 多万,这减少的7000 多万人大部分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以一家三口计算,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群超过2.1 亿,间接影响的人数就更多。而母亲就是这7000 多万人中的一员。
现在从经济发展的大局来看当年的下岗政策,也是一个时代艰难的抉择,国家和小家一样,日子困难时,只能让他们自谋出路。与其困在工厂里,不如让他们出去各显其能自己找饭吃去。后来在这批下岗工人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煤老板、企业家、地产大亨,但更多的还是一些普通人。他们其实连农民工都不如,农民还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城里撑不下去,回家种地,最起码吃饭没有问题。下岗工人却什么也没有,他们只能握着一双空拳打天下。
70 后的母亲没怎么读过书,她读完初中便不上学了。这也注定了她没有多少上升的空间和资本。没有大学文凭,也就没有通往上层社会的敲门砖。李劼曾问过母亲,怎么连个高中都不读?是不是学习特烂?一天也混不下去?
她承认有点不怀好意,谁让母亲一天到晚总是逼她学习。记忆里母亲对她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学习去。一个天天让别人学习的人,自己却只有初中文化,是不是有些讽刺。果然母亲的脸一下红到耳朵根,她支支吾吾地说,他们矿上的孩子那时都不上高中,全国大趋势,经历过十年“文革”,国家急缺人才,大中专院校便从初中招生,成绩好的学生都考中专。考上中专就有了工作,还读什么高中,简直是浪费。对于普通的工人家庭,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最好的结局。
和母亲比起来父亲似乎好一些,读了一年职高,可并没拿到高中毕业证。两个初中毕业生相当于半文盲吧,两个人又没有什么深厚的家庭背景,这种家庭的结合可想他们要面对的困难有多大。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对他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道魔咒。
丢了农场的工作让母亲很受打击。忧心忡忡的她决心自救,她失业前是一位水质化验员,学的是细菌检验,四处碰壁后,母亲买来了一堆培育蘑菇的书,在家里学着种蘑菇。没有实验室,她在厕所的一角用塑料布搭起一个小棚子,自己用废纸箱做了接种箱,在箱子上装了一块玻璃,开了两个可以伸进手的圆洞。配置了工作用的酒精灯、试管接种针等等。有一回她刚用酒精给两手消过毒,点酒精灯时着火了。幸好李劼父亲在家,要不差点引起火灾。经过多次失败她从日常食用的平菇中成功地提取培育出食用菌种,雪白的菌丝长满培养试管,毛茸茸的像一团棉花。有了菌种就成功了一半,接着她又培养繁殖出第二代菌种。母亲野心勃勃要建一个蘑菇场,成为一名农场主。这时附近村里的一个亲戚正好有一个蔬菜大棚转让,母亲便通过关系承包了下来,对这份新工作她充满信心。
种蘑菇首先要解决生产原料问题,棉籽皮产量高是最好的原料,可是北方种棉花的地方很少,长途运输的成本太高不合算。还有一种用锯末,但要杨树、柳树的,杨树、柳树木质软,不宜做家具,原料也少。剩下的就是玉米芯,出菇率不高,但原料容易找到。母亲回乡下大量收购玉米芯,玉米芯收上来还要用钢磨磨成花生米大小的颗粒,这样才能利于菌种的生长。李劼父亲有工作要上班,人手不够,母亲便招了一个女工,是乡下的亲戚,叫李劼母亲表姐。女人嘴甜,为了表示亲近,把“表”字除掉了,喊母亲姐,喊父亲姐夫。母亲呢,摇身一变成了老板,虽然手下只有一个工人。
好看的姨为了逗李劼开心,特意从乡下带了两只小兔子,兔子养在菇场,李劼有空就去喂兔子。兔子爱吃“奶奶草”,一种开黄花,根茎有白色奶汁的草。小兔子的嘴巴一刻不停地蠕动,每天吃很多很多的“奶奶草”。父亲总是开玩笑说,要吃红烧兔子肉,李劼哭着不让他吃小兔兔,这时姨便跑过来哄她。
玉米芯按比例加入糠皮、白糖、石灰,经巴氏发酵灭菌后接入菌种制成一个个小枕头样的菌包,成千上万个菌包叠摞起来,像电影里摆在阵地的沙包。母亲就是指挥打仗的那个将军。菌包摆在通风不见光的大棚里面慢慢生长,有时则长出黄色绿色的杂菌,这些受了污染的菌包要及时挑出来,要不整个菇场就完蛋了。菌房里还要定时消毒,用稀释过的敌敌畏喷洒。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当袋子里长满白色的菌丝时,就要出蘑菇了。出菇时期温度、湿度的把控是关键,李劼父亲夜里便睡在菇房,隔几个小时起来给蘑菇喷水。姨不舍得在外面花钱租房,也住菇房。为此母亲还给她加了一点工资,并许诺蘑菇大量上市以后,再加一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种出第一批蘑菇时,母亲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她眼里那些蘑菇就是一张张长在菌袋上的钞票。一批菌包管理好的话能出菇三到四茬,她觉得挖到了聚宝盆,钱会源源不断长出来。李劼隐约还能记着蘑菇场的一些事,一朵朵白花盛开在培养袋上,母亲把白花摘下来放在塑料筐子里。很奇怪李劼记忆里一直是白花,而不是蘑菇。
母亲和父亲打架,她的鼻子流血了,地上有一个绿盆子,母亲洗脸,里面的水是红色的。这些场景一直留在李劼记忆里,有一回说起当年种蘑菇的事,母亲惊讶李劼那么早就记事了。
父亲对母亲动手后,漂亮的姨带着兔子离开了李劼家。父亲恼羞成怒也不来菇场帮忙。李劼父母和矿区其他家庭的父母一样,时不时会吵架,控制不好情绪就会动手。除了菇场那一次,后来还有很多次,当然父亲手下还是有分寸的,并没有把母亲打得鼻青脸肿见不了人。说起来他们都是要脸面的人。穷人的脸皮更薄,扯不得。一扯就坏了。
姨走后,所有的活只能母亲一个人干。接下来,母亲病了,咳嗽、胸闷、低烧,开始以为是感冒,吃了很多感冒胶囊,VC银翘片,都不管事。父亲还算有良心,回来照顾菇场,不久他也病了,和母亲一样的症状。后来到了省里的大医院检查才知道他们得的是孢子过敏症,也就是说,看不见的蘑菇孢子进入了他们的肺。身体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停止了这个发家致富的好梦。
母亲又一次失业,“工作”成为她心里的一道隐疾。
母亲曾有过一段在北京短暂的打工经历,她当年文学社的朋友邀请她去做书,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把别人的作品复制粘贴成一部面目全非的新作品。母亲失望而归。
网上流行过一个段子,说是失败的老鸟生了一个叫作希望的蛋在窝里。那个蛋就是李劼。她成为母亲冲出去的一发子弹。母亲把她的理想完全寄托在女儿的身上。母亲对李劼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两岁时就能识得几百个字,五岁时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全班年纪最小,个子最矮,别人轻轻推一把她都能摔个跟头。母亲特别在意她的考试成绩。她没有为别的事打过李劼,但考不好一定没有好果子吃。李劼成为一个内心忧郁的孩子。
李劼上学后,母亲腾出手准备大干一番。她这回吸取以前的经验,没有投入太多的本钱。她用一千块钱做活动经费,开了一家自行车配件店。店面很小,只有三个平方米。这一排小房子,原来是人们放柴炭的地方,因为临街,有人动心思在墙肚子上安了门窗,开成了门面房。一家这样做,后面的邻居都学着开了店铺。这种小店极其简陋,连一个柜台都放不下,父亲在墙上钉了几层隔板,上面放着各种配件。家里的小书架也出自父亲的手,满满当当地摆着各种书,他们特别舍得给李劼买书。而她却对另一个架上的东西感兴趣。李劼下学后去店里玩,便认识了闸把、闸线、辐丝、脚蹬、单支、双支、前叉、内胎外胎等等。她记性好,说一次价钱就记住了。但母亲从来不让李劼充当小售货员。
店里没有暖气,冬天时要自己生火炉,母亲的手背都是裂开的血口子。公共厕所在五百米外,为了少上厕所,她从来都不敢喝水。那个自行车配件店开了三年。生意一直不好,为了招揽顾客,他们在店外摆了两只打气筒,免费使用。有的人用完,不好意思会丢几个钢镚,有的会笑一笑,拍拍口袋说一声没零钱。大多数人都是停下来打气,打完跨上车子就走了。如果有人让母亲帮着给自行车打气,她也不会拒绝,弯着腰撅着屁股,两手用力一下一下抽拉着气筒。她想的是和气生财,也许某一天人家就会来店里买一根内胎。
李劼读三年级时,母亲忽然关掉了配件店。关掉的原因是她读高年级了,怕同学们知道了他们是修自行车的,而瞧不起她。
配件店关闭后,母亲很快又开了一家话吧。从电信局申请了四个电话号码,屋子里安了隔板,一个小格子间里放一部电话,长途3 毛,短途1 毛。还有电话卡,有20 块的,有30 块的,比直接打电话便宜一些。话吧开了不久手机开始流行,来话吧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少。
五年级时,很多家长把孩子往城里的学校转。母亲开始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在哪儿上学都一样。有一回她到学校为李劼开家长会,老师给家长们念了两篇作文,并说那是班里最好的作文。但这几篇作文她都在作文书上读过。她每个月都要进城为李劼买一些课外读物,顺便在地摊上给自己买几本盗版小说。盗版书便宜,十块钱三本。
那次家长会后,母亲决定给她转学。要想进城里上学,必须本人有房子,还是学区房,这是母亲第一次听说学区房。他们手里没钱买房,母亲听从别人的建议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花钱托关系把李劼一个人的户口迁到姑姑家的户口上,姑姑的房子在城里是学区房,且还是重点初中。时间不等人,迁户口的工夫,学校有了新政策,光个人有城里的学区户口还不行,还要直系亲属关系,也就是说必须是自己父母的户口也在城里的学区。母亲一听就凉了,折腾了半天,李劼还是不能在城里上学。
为了能让李劼进城,母亲也是豁出去了,她和父亲一合计,决定在城里买房,买不了大的买小的,买不了楼房买平房,只要是学区房就行。父亲骑一辆破自行车在城里转悠,还真让他问到了一套,老旧小区,顶楼,面积也不大,只有50 多平方米。要价12 万。母亲去看了房,除了价钱别的都满意。房主一分钱不降,母亲咬咬牙还是决定买了。他们开始挨家挨户地借钱。这几年他们虽然没闲着,但真没挣着钱。把正在经营的话吧盘出去又借了九万多,才买下了城里的房子。那些借钱人的名字母亲记在一个小本子,天天愁得睡不着。不久母亲病了,输液吃药折腾了一个多月,后来还是父亲了解她,他把记账的小本子藏了起来,母亲的病奇迹般地好起来。
好事多磨,当时房主说要半年后才给腾房,他们的新房还没装修好。父亲一口答应。半年后孩子正好升六年级并不耽误上学。中间又有点插曲,半年的时间,房子涨价了,见钱起意,房东便不想卖给他们了。兔子急了也咬人,母亲发挥了矿区人粗犷豪放的优点,把房东的祖宗八代臭骂一顿。而父亲摩拳擦掌准备揍得他满地找牙。一文一武,两个人合作得不错,房东终于搬走了。
经过战斗,房子虽然被夺了回来,却误了开学时间,李劼半路插班进去,不得不又花了一笔钱。安顿下女儿的学校,母亲和父亲权衡再三开了一家早点店,卖小馄饨。他们手里没有多少钱,馄饨店投入少,只要交一笔房租就行了。小区里住户自己改建的门面房还不算太贵。他们到二手市场买了几张桌子,再买了两口锅一摞碗,几包一次性筷子就开张了。墙外面挂一块小牌子——馄饨馆。
母亲的小馄饨一直是家里招牌饭,有亲戚来了,母亲便包一顿馄饨吃,好吃还省钱。母亲的手艺是和奶奶学的,也算是家传。虾皮、冬菜、紫菜、香菜、葱末、熟芝麻、蛋皮丝放在碗底,用滚烫的鸡骨头汤一冲,激出调料的香味,再把煮好的馄饨倒进碗里去,上桌前洒一点白胡椒粉,点几滴香油。馄饨鲜就鲜在那一碗汤里嘛。
人生地不熟,城里人是瞧不起外来户的,这种歧视也没有恶意,有点像你无意中侵入了人家的领地,天天在眼前晃来晃去,主人当然没有好脸色。刚开始馄饨卖得不好,他们家顿顿都是吃剩馄饨,煮着蒸着煎着拌着,东西好吃也架不住天天吃,吃得她和父亲看到馄饨就躲,宁愿吃白水煮挂面。母亲一个人吃,一边吃一边还琢磨到底哪儿不对。她一次一次调配汤料、馅料,但还是没有人光顾。后来,她灵机一动,把卖剩下的馄饨免费送给周围的邻居品尝。吃人的嘴软,城里人也一样,天天吃免费馄饨也不好意思,小店里客人慢慢多起来。那些热心的吃客还会张着油汪汪的大嘴不断提意见给母亲,母亲根据他们的要求改变汤的配方。
母亲开始买了肉自己手工剁馅,后来楼下的邻居有意见,不得不买了绞肉机,母亲总说味道上差一点。纯手工打的肉馅更香。馄饨皮薄,母亲从不偷懒,总是要一碗一碗地单煮,这样的煮出来的皮子劲道有弹性。开水大火,馄饨刚进锅时像一朵朵的白莲花在水里徐徐盛开,最多煮一分钟就要出锅,多煮几秒,皮子已经煮老,馄饨也不能保持原来花朵的样子。母亲讲究入嘴的东西既要好吃还要好看。
小本买卖,雇不起服务员,小店只有母亲一个人忙活,包馄饨,煮馄饨,端饭,洗碗,收拾桌子,收钱,忙得像一只陀螺。为了不影响李劼的学习,他们家的馄饨只卖一早上,上午十点收摊后母亲还能给下学回家的李劼做中午饭。
馄饨都是现包现煮,母亲没有帮手,便天天凌晨四点起来先包一部分馄饨出来。李劼有时起来上厕所看到厨房的小窗亮着,推门进去,灯光下的母亲和案板上的小馄饨一样散发着一圈柔软的光。那一只只馄饨,如一群鸟,扑闪着翅膀,准备冲向天空。包一个馄饨不到5 秒,母亲每天大概要包一千多个,重复一千多次动作。她把时间卡得刚刚好,包到规定的数目时,天光大亮,出摊的时间也到了。
小学毕业李劼数学、英语考了100,语文96,母亲高兴得比卖了100 碗馄饨都开心。
人缘好,买卖才好。母亲的脸上常年挂着一脸的笑,大姐、大哥、小妹,叔叔、婶婶、爷爷、奶奶不离嘴。一天到晚总是笑,她脸上皱纹却越来越多。李劼看不得母亲的笑,那是一种没有底线的笑,对谁都笑,哪怕是顾客带着的一只狗呢,母亲也要问候一下。有一回她捞了一只馄饨讨好狗,被狗的主人一顿训,人家的狗很名贵,是吃狗粮的,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母亲讪讪地不知该怎么办,馄饨已经吞进狗肚子,不可能掏出来。她给狗主人不停地道歉,以后再听话可爱的小狗,她也不敢喂人家了。
他们家的小馄饨后来成为小区的招牌,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就为吃一碗馄饨。也有人劝母亲把店面开大一点,她都以没有人手忙不过来拒绝了。李劼知道母亲手里没钱,扩大店面就得招工投资,而她挣的钱,都被她拿来交了学费、书费、补课费,尤其是一对一的家教费。说白了,馄饨是小买卖,这个手艺只能养家糊口,不能发家致富。
李劼读高三那年,他们一家已经进城七年,也算是在城里站住了脚跟。她在市一中上学,但成绩并不好,一模考试六门课的总分数是452。母亲黑着脸说,这个分数只能考一所普通的二本学校。这肯定是班主任老师告诉她的,这所学校一直保持着考完试开家长会的传统,也就是给家长一个交代,你的孩子这段时间学得咋样,用三位数总结一下。天地良心,其实她已经很努力地学习了,一天差不多有十多个小时泡在学校里,屁股都快长痔疮了。可是成绩就是涨不起来。她也下了点功夫,比方晚上十二点以后睡,可是第二天早上瞌睡得厉害,又把熬夜的那几个小时补回去了。回忆起那段时光,李劼觉得在人才济济的一中上学时是她最受打击的三年,这让她严重地怀疑自己的智商。
可想而知,她第一年高考落榜了。那一年因为道路拆迁改造,母亲的馄饨小店没了。母亲一个人关着门在阳台上哭。她的哭声低低的,似乎是怕他们听到。
母亲再一次失业。
母亲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没有了店面,她又弄了一辆二手三轮车,在小区门口的空地卖小馄饨。她早早起来骑着三轮车,把做饭的家什拉出来,把桌子凳子摆好,把巨大的遮阳伞撑起来。做露天生意最怕的是老天不照顾,刚刚还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一会儿就下起雨刮起风。她不得不把摆好的小吃摊收起来。
因为做的是熟人的买卖,没有房租,她卖得便比别人便宜些。当年一碗馄饨1元,后来涨到5 元,5 元以后,无论成本怎么涨,再也没有涨过价。母亲说,再涨,那些老主顾就不来了。
李劼补习一年,考上了重点大学。母亲看到贸大的录取通知书时,笑成了一朵花。贸大的旁边是鲁迅文学院,两所学校之间仅仅隔了一条文学路。鲁院是文学的圣殿,传说在那里读书的作家们养着一只可以谈文学的艺术猫,夜里猫和作家们一起畅游在文学的大海上。母亲虽然不写小说了,但她和一些写小说的朋友还联系着。那位从鲁院毕业后的朋友,在北京发展得不错,还成了知名作家。母亲讲这些时眼睛里有一种光,那光大概也可以叫作文学吧。
凭李劼的成绩,她本可以读中山或南开的新闻系的,可是因为母亲一再暗示想去鲁院文学院看看,她在最后几分钟里,把第一志愿改成了贸大。主要是李劼那一刻心软了,她低头时看到母亲的白头发,像一朵白菊花盛开在头顶。
没想到母亲这么快就老了。她读高中时母亲好像还没有白头发,四年下来,竟白了大半,平时全靠染发剂遮着。
这些年她把和母亲对着干当作快乐,凡是母亲认为对的,李劼必定唱反调。一想到马上就要逃出母亲的手心远走高飞了,在人生的大事上权且听她一回,全当可怜她那颗慈母心。李劼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她知道从往年的成绩看,她考贸大根本没有戏。可是那年风云突变,炙手可热的贸大录取分数降了5 分,就这5 分把李劼这只小妖收了进去。
去贸大报到完,母亲急急地把她和父亲带到了鲁迅文学院。她结结巴巴地对门卫说了三次那位文学朋友的名字,一再强调他当年在鲁院读过书。而门卫根本不关心这些,只是潦草地登记了一下他们的身份证就放他们进去了。原来只要拿着身份证,鲁迅文学院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参观的。母亲分明有些失望,讪讪地收起证件,带着他们步入这个文学的圣殿。
母亲像一个朝拜的圣徒,一边走一边辨认着院子里的那些塑像分别是哪位著名作家,还如数家珍地讲着他们写过什么作品,有过什么经历。父亲插嘴说:“小劼,晚上吃烤鸭吧。北京的烤鸭出名。”母亲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母亲在鲁院也没有遇到那只传说中可以谈文学的猫。
在去烤鸭店的路上,母亲小声对李劼说,你是我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