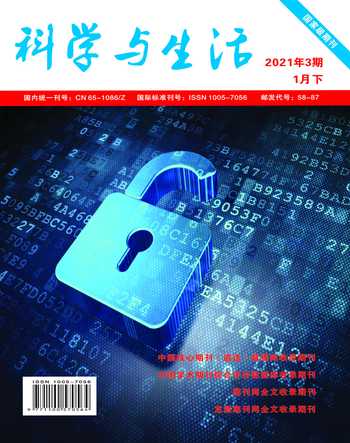享受成长,静待成功
张梓萌
成长于成功,如“红屋”之于莫里斯;如“存在主义”之于萨特的现代哲学奠基;如吉卜力工作室之于宫崎峻的柏林金熊奖。
成功于成长,如“诺贝尔文学奖”之于莫言;如圣彼得大教堂之于米开朗琪罗;如阿根廷国家图书馆之于马尔克斯。
成长与成功好像这样一种关系:微妙的我中有你与你中有我。成长是线,成功是点。成长是包裹着成功宇宙的“果壳”,成功是书写成长之路的红纸。
他们从未分离,所以那一众两者兼而有之的佼佼者在这二者的统一中窥探、摸索、体验;获得他们的超脱、胜利与满足。这以后他们会说:“我要把我获得的成功归结于一路以来的成长;我要为我持续不断的成长感谢那一路上获得的成功。”他们当然可以这么说。
成长是黑暗而模糊的暗室,所以常要伴一盏名叫成功的灯。
因为成长其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与变数,所以你不能确保一路都是一帆风顺,随之而产生的怀疑在所难免。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功都没有降临,那么你会逐渐丧失方向感,茫然无措。在此情此境只有成功袭来,才能提振士气,突然惊觉。那种感觉仿佛是破茧成蝶,一个人的上上下下好像充满了新生般的力与激情。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试。”若此剑一出即天下闻名那便自然大大的益于这位剑客的成长了。就好像一部《千与千寻》一夜之间便催成一位日本动画界的巨擘---宫崎峻。
而相对的成长来说,成功更像娇美异常的鲜花。但这美丽的花却也要成长作为容纳其中的花园。成长使成功变得更美。
芥川龙之介在他的老师夏目漱石写完那篇有名的《我是猫》之后说到:“先生以后不仅能赚更多的钱请我们吃火锅,写得也越发好了。”除了芥川的雅趣,一个人的成长也的确带来了实在的“好处”,这也是成长对于成功的意义。
成长与成功就是这样,存在在和谐自然的统一当中。可是是否有太多的人把成长与成功割裂开来了呢?
盲目的追求成长,或盲目的追求成功。当然,那些也只是他们眼中而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当这一点印证在可爱的孩子身上,显得尤为不忍与可惜。
当父母还没有想明白成长与成功的关系时,可爱的孩子就已经提前成为了他们手中的“牌”。怎么出这一张“牌”,就得根据各自父母的口味了。有一味追求“纯天然”而自由放养的,他们认为成长是首要,而成功不应在考虑之列。但凡有妨碍“纯天然”品性的生成的成功,那么宁可弃之不要。他们迷信“成长”的魔力和主观能动性,从此衍生出来的观点有许多种,例如“读书无用论”、“送孩子读美国高中”等等。
对于他们难加苛责,因为他们所说的“成长自然”确是天性。然而我只知道,坚持自然的猴子至今生活在树上。
更多的则是奉成功为神明,弃成长于不顾。“无论死活”也要在孩子身上实现理想的那一类。如果说前者还稍可理解,那么这一类就有违常理了。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前有虎妈,后有鹰爸。他们挥动着强有力的大手给孩子指引方向。完全顾不上成长之于成功,亦或成功之于成长,他们要的是胜利。这种扭曲心理的蔓延甚嚣尘上。
一双双大手捏造出来的,我担心是袒露着脚后跟的阿克琉斯。
这并不是极端假设,这是真实的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象。因为成长与成功的无知导致的这一结果,再次印证了一个有些可悲的事实:鲜活的创造力正在流失。不管是“海外”还是“大手”。
不禁有人要问:“这一切到底因何而起?”那我只能是默然,因为我知道那背后肯定又是大到虚的宽泛的指责。而如果对“所有人”共同的错误进行批判,那么连指责的效力也没有了。我们唯一能做得只有好自己的判断。
我们享受成长,我们又期待成功。纵然我们不能如维特根斯坦,轻易地在维也纳的市中心建一幢“维特根斯坦的房子”;或者像司各特在苏格兰造一座“阿伯茨福德庄园”;又或者像帕拉迪奥完成流芳千古的“圆顶别墅”。不仅从中享受了成长的乐趣还在身后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我们自己认定的成长与成功。成功必使成长,同样成长也必使成功。
这两者应该永远的相伴着,让这种相伴变成一种固定和诗意。由此我记起,木心在其诗集《温莎公园的爱情故事》里的几句诗,意思大概这样:
“黑松林静静的陪着黑色的墓碑,他们在夕阳下,寂静又荒凉。”
或许有些生涩,但成长与成功的关系不也正是如此吗。
指导老师:徐兵强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高三(1)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