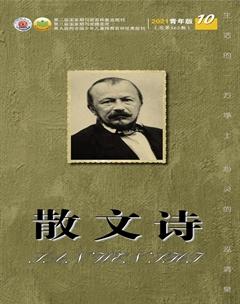爱神者即是渎神者
2021-11-03 03:51
散文诗(青年版) 2021年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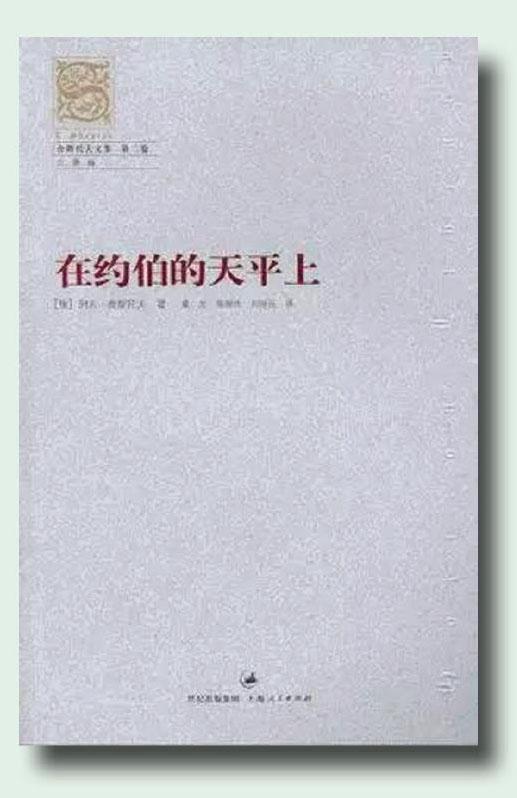
因于伽利略的前车之鉴,尽管笛卡尔主张以自我为唯一可信的前提来驱除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神秘,但他并没有说出“上帝是骗子”“人类将成为上帝”这样的话;他只是审慎却不乏决绝地说:我思,故我在。两百年后,笛卡尔想说却未明说的话经由黑格尔之口说出。当作为唯理论代言人的黑格尔主张一种“统一的、共同的、作为他自己的实质和本质的精神”时,他深知笛卡尔才是那个统一的共同精神的真正表达者。
在此之前,笛卡尔的学生斯宾诺莎先于黑格尔两百年落实了这一精神并将其遥遥传给了黑格爾(列夫·舍斯托夫直言:全部黑格尔整个地来自斯宾诺莎)。凭借对神性之必然性的信仰,斯宾诺莎将必由之路引向“实体”和数学;他像考察线、面、体积一样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甚至考察神和心灵——尽管他完成这一切之后依然劝导人们要全心全意地爱上帝。
就行动而言,斯宾诺莎才是真正的“近代哲学之父”,他因而也是那个真正的渎神者——舍斯托夫感叹道:“最爱上帝的人,结果却成了杀死上帝的凶手。”这便是斯宾诺莎的历史命运。无论如何,“明晰和清楚”以杀死上帝为代价而被实现了;一种确实性业已被赢获,对统一前提的逃脱行动业已完成,个别事物注定会纷纷出世。但同时,作为擅自主张的出逃者,人将不得不独自面对死亡的永恒惩罚。
猜你喜欢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21年10期)2021-10-20
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21年3期)2021-05-08
语数外学习·高中版中旬(2021年11期)2021-02-14
文萃报·周二版(2020年37期)2020-10-20
杂文选刊(2020年9期)2020-09-12
课堂内外(高中版)(2018年11期)2018-12-26
初中生世界·八年级(2017年4期)2017-05-03
初中生世界·七年级(2017年4期)2017-05-03
学生天地·小学低年级版(2014年12期)2015-01-17
中学生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8期)2008-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