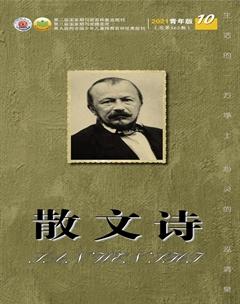都市物语
彭进
饥饿艺术
她们说到饥饿。
满脸的骄傲。
这是她们值得珍藏的标签。
这是她们赖以炫耀的资本。
她们说到瘦,说到腰如束素,身轻如燕。嘴角不自觉扬起微笑,自信挂在胸前、脸上。如同自己就是七步成诗的才子曹植笔下的洛神,就是帝王掌中翩然而舞的仙子……
她们的小腿已瘦如干柴,却保持着优美的曲线、修长的形状。
她们的脸上,覆盖着一层一层的滋养。
那些手脚长满老茧的人,若是知晓底细,一定会惊愕、诧异,大惊小怪:“哎哟,那么漂亮的脸蛋,原来贴上了一层层,大额的钞票……”
已经没有人,羞于喊饿;
也没有人,为消瘦而羞怯。
那些肥头大耳的人啊,恨不得,将体内的油脂剥离出来,当成可怕的罪证,偷偷掩埋掉。
当她们看到饥饿,看到易子而食的片段,或许,同样是一脸的不解,如一个不谙世事的皇帝那般:“何不食肉糜?”
当真实的感觉,失去了阵地,饥饿,就成了一种艺术。设计,创造,展示,招摇,竞相攀比。饥饿艺术家,不仅仅活在卡夫卡笔下,活在昨日,更活在今朝,活在我们亦真亦幻、以假乱真的世间……
外科医生
也许,曾经梦想当一名侠客。
持一柄利剑,风餐露宿,行走天涯。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笑傲江湖,血染黄昏……
只要足够锋利,足够迅速,当利刃刺破肌肤的刹那,不会有疼痛,不会有鲜血,也不会有恐惧与失落,而仅仅有,黄鹂歌唱春天、春风轻拂嫩柳的天籁之音。
最终,还是拿起了一把锋利的刀,站在无影灯下,以飞快的速度,将一个人的肌肤,划开。
柳叶刀,足够锋利;
熟稔的动作,足够迅捷。
可是,血,还是涌了出来。
那个曾想当侠客的人啊,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将那为非作歹、作威作福的凶手处之以刀,缉拿归案,然后,归位、缝线、清洗……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那个沉睡着的人啊,当他在残余的疼痛中醒来,只知道发生在体内的故事,却不知晓,那把侠客的锋利的刀啊,在他的体内走过的路途、遗留的痕迹。
瑞雪辞
年初的大雪落在医院。
笼罩着新生、衰老、伤痛、寂静。
那个满面欣慰的年轻人啊——雪,落在他的脸上,钻进了他的脖颈。
他的笑,瞬间将这上天的赏赐融化。他感谢这场年初的雪,与他的同伴,同时降临。
仿佛上苍,给他努力的奖赏与暗示。
可是,那个丢掉了左腿的人啊,目光呆滞,满面风霜,六神无主,喃喃自语。
这冷的雪、寒的风,不只是在窗外肆虐,更像是一条条凛冽的鞭子,抽打他脚手架上的过往与艰辛。他在想,雪化了,河开了,那栋正在快速生长的大楼,再也不会出现他已佝偻、残缺的身影……
雪花,正在有条不紊地下。
一场场宁静,悄悄发生。
无影灯下,柳叶刀所向披靡,它是一个时代的英雄。
利刃划向病变的器官,如同切割掉那些我们不愿丢掉的陈年回忆。
大雪落在医院,落在新生与死亡交织的场所。
动脉是事件,静脉是细节。
呼吸。心跳。血压。脉搏。
年初的大雪落在医院,落进我们重新精神抖擞的人生。
天地大白,呈现最纯洁的吉祥。
隐藏在我体内的石头
我常常羞愧于我的怯懦。
我惧怕黑暗,惧怕蛮横无理的暴虐,惧怕空穴来风的诽谤。我甚至惧怕那空气中横冲直撞的飞鸟,惧怕一只长着斑斓花纹的不知名的爬虫……
我常常羞愧于我的怯懦。我胆小如鼠,从不敢惹是生非,心灰意懒之时,甚至想找一个山洞,将自己密封起来,以远离尘世的喧嚣与风暴。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种软体动物,体内缺乏铁、钙、骨骼,甚至一个能支撑自己独立行走的硬塊。
可是,有一天,一种前所未有的疼痛惊醒了我,折磨着我。一位年老的医生告诉我,那是我体内的石头,正在通过身体的管道,在游走,在彷徨……
我诧异不已,大惊失色。原来,我的体内竟然还有如此坚硬的物件?原来,我那所有的软弱、怯懦、胆小怕事,仅仅是一种误判、一种猜想。仿佛,我早已举起一块硕大的石头,仰天长啸,怒目圆睁,梁山好汉一般,敢于面对一切的挑衅、争端、格斗,敢于以一己之力,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甚至于摧毁一座山、一座城……
隐藏在我体内的石头啊!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它是我曾经以为缺失的灵魂。
它,融化于我的血脉,重塑了我的脊梁。
它,用坚硬划伤了我,用剧痛唤醒了我,让我知晓,我的体内,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能量,似乎陡然之间,给了我一副铠甲,给了我一副铁石心肠!
疼痛,常常让我们丧失尊严,丢掉自我,又屡屡给我们以激情、热血,以及迎难而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