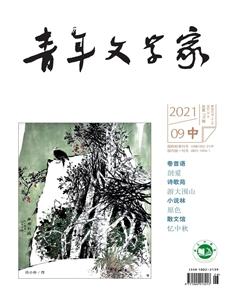试析萧红作品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原因
谭地嫚
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坛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女作家。她身为女性,书写女性,一直以独特的视角深刻体察着她那个时代的女性悲剧。三十一年如昙花一现的生命,坎坷踉跄、颠沛流离,但留给我们的却是一曲曲力透纸背的女性生命悲歌,其中蕴含的悲剧力量穿透时空、历久弥新,既有助于我们了解1949年以前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也为当代女性生命立场的审视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一、萧红作品中女性悲剧命运的体现
(一)社会悲剧
女性受到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她们的命运有一种无处突围的悲哀。如《生死场》中的福发婶说她怕男人,觉得男人和石头一般硬。成业和金枝结婚后,便开始殴打金枝,骂她是“败家鬼”。王婆自杀后,她的丈夫赵三怕她拖别人一起死,便用刀一般扎实的扁担切在她的腰间。月英生病后,不但没有得到丈夫的照顾,甚至还被其用砖块围起来,和变相的活埋没有区别!这些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变得空洞虚妄、毫无价值。
在《呼兰河传》中,蕭红道出了旧社会众多女性的心声,“指腹为亲,好处不太多,坏处是很多的”。女性的一生从在娘胎里就已被打上封建思想的烙印,此后,也一直被其阴影笼罩着。小团圆媳妇是一个童养媳,她天性活泼,不懂规矩,是婆婆打骂的对象。她生病了,周围人不去请医生,把她推向了痛苦无以复加的“深渊”。她“太大方了”,“一点儿也不知道羞”,便被婆家“好心”结束了生命。萧红以“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的个人体悟,借小团圆媳妇诉说着她身为女性的悲哀与无奈。
(二)生育悲剧
生育作为女性的权利,可以说是身为女性的独特幸福来源,但在《生死场》中却截然相反。萧红给我们呈现的女性生育过程是粗糙凌乱的,她们始终被动接受着不堪重负的生育刑罚。五姑姑的姐姐生产时疼得在地上打滚,但无人理会。当她难产时,婆家首先做的是为她预备葬衣。甚至还有许多像李二婶子一样因难产而死的女性,她们的死亡无人关注、无人在乎。在那个时代里,女性“个体生命的泯灭与消失,无声无息,现世众生的生存依然那样繁华和热闹”。女性因无法承受生育苦难而去世的模样就像动物的死亡一般廉价,不过这仿佛是她们的宿命。
萧红常常拿动物的生产同女性的生育作对比,把后者的悲剧命运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窗外墙根下猪在生小猪时,麻面婆也在叫喊着生产;当狗在房后草堆上生产时,房内的五姑姑像鱼一样赤身裸体地产下她的孩子。《生死场》中的王阿嫂早产时,“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萧红已经把女性的生育降到了最低标准,但可怕的是,这般生育场景还一直上演在“生死场”上,日复一日,没有终止。
(三)性格悲剧
如果说封建社会、男权社会的压迫和生育的苦难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外部原因,那么,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女性自己的妥协。她们对自身的处境采取不抵抗的态度,甚至处于一个不自知的状态。《小城三月》中的翠姨被安排与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定了亲,哪怕她早已将芳心许给“我”的堂哥,也不会去主动争取爱情;《生死场》中的麻面婆对丈夫二月半的辱骂习以为常,她永远只会默默舔舐着伤口;福发婶被男人霸占后,就匆忙嫁到婆家,忍气吞声。从这些人身上看不出任何身为女性的鲜活、坚忍,有的只是惊人的“自律性”和被奴役性格。
这些女性不但不反抗,不去思考导致自身遭遇的深刻原因,还对她们的下一代进行精神施暴,使其延续了这种悲剧命运。《过夜》中小金铃子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一方面,她是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牺牲者,但她并没有企图反抗,反而不自觉地担当起了施暴者的角色。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她向13岁的小金铃子砸雪块。她把小金铃子看作长大了就可以当妓女来为自己赚钱的工具。她被别人“吃”,又“吃”自己的下一代。她被残害,又通过残害下一代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不安。可以说母性意义的丧失是女性在精神世界对自我价值的深度消解。
二、萧红作品中女性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
(一)对情感的求而不得
孤独寂寞几乎充斥了萧红的整个童年时光。其亲生母亲是多病之身,还要承担生育的任务,便再难顾及其他事情。生母病逝后,父亲续弦,萧红又遭到继母的冷嘲热讽。祖母对她也是疏远和嫌弃。在她18岁时,唯一疼爱她的祖父也去世了。周围的亲人带给萧红的无一不是难以言说的巨大苦痛。这也成为萧红的生命底色,并贯穿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
1910年,萧红怀有未婚夫汪恩甲的骨肉,汪以回家取钱为由,一去无回。后来她于患难之中结识了萧军,但随即两人性格产生冲突,加之萧军出轨,这段感情便无疾而终。1938年,她又与端木蕻良结为夫妻,但在婚后却发现端木十分胆小虚伪。萧红始终走在寻求爱情慰藉的路上,但爱情带给她的悲苦却愈演愈烈。求而不得是她的悲哀。
(二)对健康的求而不得
萧红早年怀孕时被汪恩甲弃于旅馆,严重缺乏营养,就此落下病根,本就十分虚弱的身体,在承受了两次生育之痛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心灵上的巨大折磨。“萧红在产前心情是很好的,不但细心地做了自己的衣服,还给小孩子做了衣服,踏实沉醉在做妈妈的幸福中。”但她囿于生存窘境,无奈将孩子送给了别人,心中何等痛苦与无奈!此外头痛、胃痛、经痛等多种疾病都长期光顾着萧红。可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三)对女性地位的求而不得
萧红自出生时起就因其是女儿身而受到诸多排挤,不受家人待见。她为反抗家里人给她安排的婚事,于18岁时毅然离家出走。后来在与萧军相互扶持的六年日子里,她的才华逐渐超过了萧军,这让大男子主义的萧军难以接受。她不是一个对丈夫百依百顺、言听计从的大家闺秀,而是身上早已存在着女性主义光辉的民国才女。但萧红生活的那个时代甚至不允许女性有如此才情和敢于反抗的勇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萧红的精神家园注定会是永久的失落与荒凉。
三、萧红作品中女性悲剧命运的现代意义
萧红常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但她从未停止过和命运的博弈。所以她在作品中也同样呼唤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勇于反抗的女性形象。《生死场》中的王婆便是如此。她一生经历了三段婚姻,无论什么时候,她从未觉得自己身为女性,就理应顺从与忍让。面对第一段婚姻中丈夫的家暴,她选择改嫁,面对第二任丈夫的离世,她又再嫁赵三。她正面反抗着“好女不嫁二夫”的思想,始终追求着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幸福。王婆身上体现的是不同于金枝、翠姨的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反抗之美。又如《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在她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前,人们都赞美她有福相,是个“兴家立业的好手”。但在她自作主张嫁给了冯歪嘴子后,人们便一转从前的态度,开始讽刺、诋毁她。她无畏别人的闲言碎语,和冯歪嘴子过着自己认为的幸福生活,还生有一子。我们从中能够窥见王大姑娘的反抗之美,哪怕这种反抗只是沉默,但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代里已经显得难能可贵了。
萧红在为我们描绘彼时东北中国乡村的那幅女性受难图时,不仅写其不幸,还超越这些不幸,寻求其根源,为此她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之美的女性形象。这一类女性与中国现代文坛其他几位女性作家所描绘的女性不同。如丁玲所写的莎菲、梦珂,都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冰心常写的是有着如丝叹息的母爱、童心、大自然。而萧红笔下的女性甚至没有赖以生存的方舟,她们独自忍受着贫穷、饥饿,将人活得不像人的痛苦诉说得淋漓尽致。从这种对比中,我们更容易管窥萧红笔下这类女性的现代意义。她们背负了历史、社会给予的多重苦难,一直哀号呻吟着,最后又从中奋起。通过阅读萧红的作品,我们了解到女性要想真正获得解放,从根本上来说,则是自身要正确认识在社会、家庭中应处的地位,应充当的角色,并为此努力实现人格的独立平等和思想的脱胎换骨。
本文通过萧红自身的经历来体察她对女性的理解,通过她的作品来思考她对女性悲剧命运的阐释。她将心中经年累月的苦之旋律投射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有着长久生命力的悲歌。这首歌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希望今天的女性同胞们能够挣脱牢笼,摒弃依附心理,在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让“萧红式”的女性悲剧永远不再上演。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