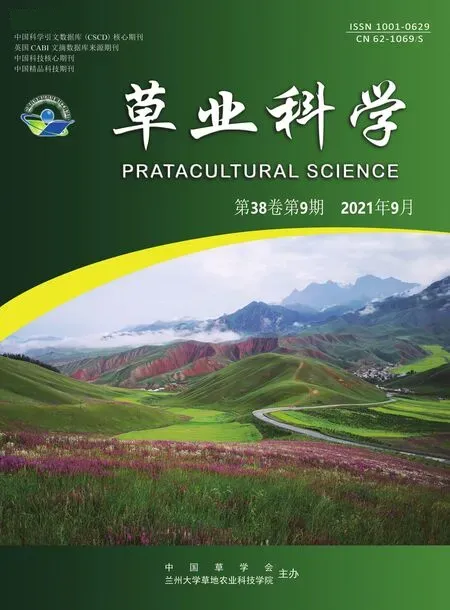黄土高原草地植被的嬗变
夏 悦,王国会,沈禹颖,马景永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20)
草原是人类重要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草原具有保持水土、稳增碳汇、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保障畜牧业生产和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等诸多功能[1]。我国是草地资源大国,约41.7%的区域属于草地[1]。维护草原生态系统健康不仅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需求,也是新时代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必然选择。近年来,草原与生态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与广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草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因此,加强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治理,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黄土高原是我国重要的草原分布区,也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典型生态脆弱区。其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仅记载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还反映了史前至今中华大地亿万年生态环境的演变轨迹[2],是研究中国自然环境变化与干旱半干旱区人地矛盾及植被变迁的典型区域。从水草丰美、林木广布的丰饶之地变为鸟无栖处、树矮草稀的荒山秃岭,经过多年治理又重新焕发盎然绿意,黄土高原经历了不同草地植被的演变。了解黄土高原草地植被的演变历程对于该区域植被的恢复重建及水土保持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1.1 黄土高原概况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中部偏北部,黄河中上游地区,地跨陕、甘、宁、晋、豫、青和内蒙古等多省,总面积约为6.24 × 107hm2。黄土高原属于我国第二级阶梯,整体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变化较大,在300~2 500 m[2](图1)。区域内地形地貌复杂,沟壑纵横,在长期的风力堆积与流水侵蚀的旋回中形成了以为塬、梁和峁等为基本单元的地貌格局[3]。黄土高原地处中纬度季风带,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季节分布不均且年际变化大,多年平均降水量为200~800 mm,并受地形和季风环流影响呈现自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2]。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4]。
1.2 黄土高原草地植被现状
黄土高原处于中国东部湿润区向西部干旱区的过渡地段,受气候、地形及地势的影响,区域内形成了一定的水热梯度。植被区系成分过渡性特征明显[5],植被景观自东南向西北呈现为落叶阔叶林–森林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的地带性分布格局[6]。目前,除耕地外,黄土高原的土地覆盖类型中草地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37.51%[7](图1),其草地广泛分布于内蒙古沙地和沙漠区、陕西中部和北部丘陵沟壑区,宁夏中南部和甘肃的大部分区域,发育的草地植被类型主要包括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以及灌丛草原。这些草原植物群落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以旱生植被为主,结构简单,草层低矮稀疏,叶片较小,群落生产力较低[2];但不同类型草原的分布区域和主要物种有所差异(表1)。

表1 黄土高原草原类型与分布情况[5,8-16]Table 1 The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grassland on the Loess Plateau

图1 黄土高原土地覆盖类型图Figure 1 A map of the Loess Plateau show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cover
2 黄土高原草地的演变
目前,学界对黄土高原历史植被的研究主要通过孢粉、同位素、植物硅体、土壤成分分析以及对历史遗迹和文献考证等方法来进行[17-22]。由于黄土高原分布范围广,区域内地貌复杂,实证探究的区域不同,光热和水分等自然条件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发育的植被类型也有所差别。而且,不同的研究方法,受技术和误差的影响使得研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研究结合前人的研究,以时间为尺度,以气候及人类活动为重要线索,通过文献查阅、史料探究等方法系统阐述了黄土高原草地植被的嬗变历程,以期为黄土高原的生态恢复与重建提供一定的科学指导。
2.1 黄土高原形成至更新世时期(距今250 万年至距今约1.2 万年)
黄土高原形成于250 万年前[23],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变化是影响黄土高原草地植被演替的主要因素。受地球轨道要素周期性变化的影响,250 万年以来黄土高原气候呈现出明显的干湿交替的现象[24]。进入第四纪以后,气候逐渐由暖湿变为冷干[25],黄土高原植物孢粉从松属花粉占绝对优势变为蒿属、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含量明显增加[26]。更新世期间,气候表现出温和半干旱–寒温半湿润–温和半干旱的变化过程,草地植被也随之经历了森林草原、草原和荒漠草原的多次转化。根据泥河湾盆地和渭河盆地孢粉分析结果发现,更新世草本植物是黄土高原植被的主体[26-27]。在更新世暖期,黄土高原主要是温带针阔叶疏林和草原景观。到晚更新世,黄土高原蒿属和藜科等旱生草本植被分布变广,草原向干草原转化,草地植被类型有疏林草原、草原、干草原和荒漠草原等[26]。
2.2 全新世早期–全新世中期(距今约1.2 万年至公元前2029年)
全新世早期,受全球气温回暖的影响[28],黄土高原植被类型开始向疏林草原转变。有关学者通过对甘肃会宁和西峰地区的孢粉组合分析发现,该时期乔木花粉开始增多,其浓度与草本花粉浓度基本持平[29],这表明在这一时期黄土高原主要发育草原和疏林草原[17-18]。到全新世中期,气候变得更加温暖湿润,原有的草原和疏林草原向湿润型转变,关中、晋南和豫西北地区开始发育了亚热带落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30],陕北高原北部也形成了由松、榆及小乔木组成的森林草原景观[31]。唐领余等[32]通过研究甘肃定西、秦安等地全新世黄土沉积剖面的孢粉记录证明,在全新世早期至全新世中期,黄土高原古植被曾经历了荒漠草原–森林草原(或疏林草原) –针叶林或温带森林–森林草原的演变过程。
2.3 夏朝–战国时期(公元前2029 至公元前221年)
全新世晚期(距今约4 000年),全球经历了一次大的降温,气候开始变冷变干[28]。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土高原的垦殖活动随着农耕文明的繁荣日益显示出其破坏性。自此开始,黄土高原的植被演变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加。
夏朝至战国时期,由于人类生产力低下,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垦程度较低,黄土高原绝大部分地区仍保持着较好的疏林草原景观,植被发育以疏林草原为主。《诗经》、《山海经》等史料及文献记载表明,六盘山以东、吕梁山以西、渭河以北、长城以南的黄土高原分布着面积广大的草地和灌丛。在离石–延安–庆阳这一植被分界线上,南部植被类型以疏林灌丛草原为主,其中栎属、桑属为主的落叶阔叶乔木占比较大;北部植被类型为半旱生和旱生草原,草地和灌木占有重要的地位[33-34]。此外,在对董志塬和及苏家湾等地黄土剖面的孢粉分析中也发现,此阶段草本花粉和乔木花粉浓度较高,孢粉组合中松属增多,蒿属、禾本科、菊科略有下降,进一步证明这一时期黄土高原的主要植被类型为疏林草原[32]。
2.4 秦–西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5年)
秦至西汉时期,气候较为温和湿润,农耕业兴起[35]。秦国势力向渭河上游和泾河流域扩展,重农政策的推行加速了黄土高原农耕区向西北的拓展。秦统一六国后,又向西北地区大量移民屯垦,兴建咸阳宫、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等大型工程。人口涌入和修筑长城等工事使得黄土高原地区耕地紧张,兵民大规模屯田开荒,天然植被有所减少。直至秦末汉初,沿秦长城经东胜东、榆林北、靖边北到环县一线以北为草原景观,此线以南为疏林灌丛草原景 观[30, 34]。
西汉年间,统治者吸取秦苛政速亡的教训,奉行轻徭薄赋、让利于民的统治理念以修养生息。仁政之下人口激增,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以缓解土地压力。国内安平富庶,但边疆却战祸连连,游牧民族侵扰不断。为巩固边防,汉文帝接受晁错建议,开始大规模“徙民实边”。之后,历代统治者基本延续这一政策。汉武帝时期,曾使“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6-37]。大量移民、驻兵涌入黄土高原,西汉末年,该区域人口负载已过千万[38]。此外,汉代建国之初便开始兴修水利,民间耕作技术不断改进,农业开发力度较之前大大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及农耕的发展,黄土高原军屯与民垦的规模不断扩大,草地面积萎缩,特别是南部的关中、洛阳盆地和天水盆地,垦草为田之风盛行。然而,太原–龙门–宝鸡这一农牧界线以北除河谷平原外的大部分地区,草地植被仍保持自然状态[39]。
2.5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5年至公元581年)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转为寒凉[35]。从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到东晋安帝义熙五年的200年时间内,出现寒灾的次数多达46 次,北方农牧业生产严重受限[37,40]。因此,游牧民族南下建立政权,战祸频仍的民族混战由此开启。由于混战导致区域政权不稳,百姓户籍限制不强,流动相对自由,黄土高原农业人口大量迁出,落户于更宜居宜产的南方地区。据《续汉书·郡国志》、《晋书》所记录,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 黄土高原总人口还有507.6 万人,至西晋,全区人口仅余208 万人[38]。游牧民族逐渐占据山西河曲、偏关、保德、陕北、陇东马莲河流域等地,畜牧经济成为此时黄土高原主要的经济形式,农牧界线回退到吕梁山–渭北–陇东一线[41]。人口压力的下降及以游牧为主的畜牧经济的发展使得黄土高原秦汉大规模开发破坏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相当一部农田渐渐转变为次生草原和灌丛植被,草原面积扩大,部分黄土丘陵区呈现“杂树交荫”、“层松饰岩、列柏绮望”的繁盛景观[34],生态环境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35,42]。
2.6 隋唐时期(公元581年至907年)
隋唐时期是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历史阶段[42]。暖湿期带来的是又一次的文化繁荣和人口增长,农耕业继秦汉以后达到新的高峰并不断向黄土高原西部和北部边缘推进[41]。隋末战乱也使得丰州一带大量百姓向南迁徙至陇东庆州、宁州等地[43],原有的草地、林地多被开垦为农田。加之唐都城百万人口的垦殖、柴薪、建材等需求,关中西部的岐山、陇山、山西北部的离石、岚县大量林草植被进一步被破坏,农牧界限向北推至阴山一线[37]。
唐末,暖湿期结束,气候趋于干旱[33]。朔方县从“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灵秀之地逐渐变为“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黄沙肆虐处,“清流”也变为“渍沙急流”的“无定河”。毛乌素沙地向南侵袭,榆林靖边一带“广长几千里,皆流沙”[44]。以上史料记载反映出,唐后期黄土高原土地沙化问题已不容乐观,自然植被破坏严重,部分地区草原开始向荒漠草原和荒漠转变。
2.7 宋元时期(公元960年至1368年)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翻耕工具得以改进,印刷业、冶矿业欣欣向荣,大兴土木的社会风气蔓延民间,这些都导致人类对黄土高原的破坏再次升级,林草资源耗损严重。北宋中期,宋夏矛盾升级,宋政府在西北边线修筑了近500 个城、关、堡、砦,大量砍伐周边林木[45]。而且,为了“究地利,增广人兵”,还规定凡川原、河谷、漫坡地带,禁止放牧,牧业发展乏力。为谋兵饷边粮,几十万驻军在西北屯田垦荒,范围之广几乎到达“无地不耕”的地步[46-47]。一些不宜耕种的草原、荒漠草原也被垦为农田,黄土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受重创[41],草地不断退化。加之宋代火攻是对阵西夏的重要手段,作为战场的黄土高原中西部(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山西西北部等地)大火频频,草原焚毁“甚众”,“不可胜计”[47]。人类活动干扰的加剧和气候的趋于干旱化,最终导致宋朝黄土高原植被出现明显变化,一方面草原带向南沿绥德、庆阳、平凉一线延伸;另一方面某些耐旱植物的分布更广,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白草(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等旱生植物的生长区域增加[33]。此时,黄土高原不仅平坦的塬、峁、梁的顶部与河谷地被尽数开垦利用,缓坡和陡坡也遍布耕地。许多河谷平原以及黄土塬区已没有天然森林,呈现草原景观,且北部土地荒漠化也继续南侵。
金元时期,游牧民族实力不断壮大,侵占中原。黄土高原地区夷狄聚集,胡化倾向严重,元朝统治者虽在陇东平凉等地屯田,但农田不如前代面积广大,关中地区仍是“人稀地广,蒿莱满野”[48],灌草等植被较之前有所增加[43]。
2.8 明清时期(公元1 368 至1911年)
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的破坏达到了顶峰。明代初期,为御夷狄,黄土高原北部修筑长城和堡寨,长城沿线兵民大量樵采垦殖。同时,统治者还制定鼓励垦荒种粮的农业政策,山西北部宁武、偏关、雁门等地的山地近乎全垦,屯田“错落在万山之中,岗阜相连”,“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47]。至明中叶,“小冰期”到来,植被恢复能力减弱。加之烧荒不禁,开垦不止,黄土高原本就脆弱的生态更加失衡。据《明神宗实录》及正德《大同府》记载,烧荒几乎成为明长城守军的一项军事政策,长城外侧数百里范围要做到“务将野草林木焚烧尽绝”,这使得黄土高原草地植被生境遭受重创[49],草原退化严重,大片地表裸露[50]。长城沿线荒漠化加剧,地方县志记载了不少城镇因流沙湮没而废弃的实例[51]。
到清代,该地区焚林焚草、毁田开荒现象变得更加普遍,农耕区发展至长城以北[52]。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明显下降。在这样恶劣的生境下天然植被难以恢复和更新,不断向高山和陡坡萎缩[53]。在汾河流域的县志中常见“土地多烧瘠”、“地瘠贫”此类描述,《重修延绥镇志》也记录“镇(榆林) 之山荡然黄沙而已,连冈迭阜而不生草木”[36]。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的滥垦、滥牧、战乱使黄土高原自然森林和草地植被几乎破坏殆尽,长城以南的草原基本消失[52],草原荒漠化程度加深。
2.9 民国以来(1912年至今)
近代中国饱受战火之苦,大量人口内迁西北。为满足迁入人口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不得不在黄土高原进行大规模的垦殖活动。建国后,人口快速增加,导致农业欠收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这一时期,奉行“以粮为纲”农业政策,强调牧区粮食自给,黄土高原纯牧户近乎消失[54]。以农退牧,过度的开垦造成黄土高原植被退化惊人,植被生境极度恶劣。据统计,1960–1962年陕甘晋三省开荒约百万公顷[55],草地植被不断退化,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为保黄河安澜,遏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国家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工作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实践。其中,在20 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植树造林、梯田和淤地坝建设工程[56]。但受理论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尚未形成系统的治理模式与方案,在植被建设中重乔木而轻灌草、树种草种结构单一等问题造成了造林保存率低,大面积人工林草地在建植5~10年后陆续退化、死亡或成为“小老头树”,生态治理成效并不显著[12],从根本上未能扭转黄土高原草地植被持续退化的趋势。20 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约30年,山西吕梁山北部山麓至分水岭处茂密的乔木和灌木区就已成退化成裸露的山地[57],陕西延安宜牧草地也从186.7 万hm2减少到120 万hm2[12]。
20 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生态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黄土高原生态建设进入了集中规模治理阶段,植被逐渐得到恢复,草地退化现象也得到显著改善。在1981年11月举行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治理与预防并重,除害与兴利结合;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并重,乔灌草结合,草灌先行;坡沟兼治,因地制宜;以小流域为单元,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综合治理,集中治理,连续治理”的生态环境建设理念[58]。基于此理念,国家在黄土高原继续落实70年代末期规划布局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之后又实施了小流域治理工程、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退耕还林(草)工程、坡耕地整治工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保护性耕作试验示范项目、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试点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和可持续发展项目[59-61],不但对当地恶劣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改造,还推行了适合黄土高原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合理模式,政策激励与科技支撑并举,有效地扭转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趋势,推动了区域植被的恢复与重建。尤其是在1999年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后,黄土高原草地植被的改善进入了快车道。相关研究表明,1982–1998年黄土高原草地覆盖度年均增速仅为0.32%,到1999–2014年就已经达到1.76%[62]。截至2018年,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面积已达3.33 × 107hm2(包含荒山禁牧),植被覆盖度已由原来的31.6% 提高到65.2%,有力地推进了生态环境的向好发展[63-64]。
3 黄土高原草地植被嬗变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黄土高原草地植被演化历程的探究,可以发现,自然条件是造就黄土高原脆弱生态环境的基础,不合理人类活动的干扰及其累积效应是造成黄土高原近几千年来林草植被退化,生态环境几经崩溃的主要动因。黄土高原作为我国主要的农牧交错区,历史上属于民族混战之地,其农耕业和畜牧业的范围随朝代更迭和民族势力变迁呈现交替消涨的局面。在黄土高原,草地生态系统适宜发展的农业类型为畜牧业,以游牧为主养畜方式实际上有利于草地植被的恢复。但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因与生产环境不匹配而逐步破坏黄土高原稳定的生态基础,致使该地种植业效率低下,长期处于“广种薄收”、“越垦越荒,越荒越垦”的恶性循环[55]。
揆诸历史,黄土高原林草植被的退化与其农耕业的发展历程基本吻合,偶有几次灌草植被得到适度恢复都是在区域人口减少、游牧经济占据主导的背景下出现(表2)。自新石器晚期一直到汉初,这里的农业发达程度一直高于黄河下游平原和南方各区,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人口聚居地,人口负载较高,但区域内严狁、鬼戎、土方、羌、薰育等游牧部族较多[65],农耕人口优势并不明显。且由于耕作技术及劳动工具的限制,对黄土高原的开发力度还比较小,黄土高原原有的林草植被发育良好。秦至西汉时期黄土高原人口增加近3 倍,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应用有力促进农耕业发展迎来第一个高峰,耕作区向阴山、贺兰山推进。之后动乱频繁,受旱作雨养农业的生态限制,黄土高原在我国农业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华北平原,区域人口大量流出。到东汉时期,黄土高原大约只有300 万人[38]。魏晋之际,游牧民族南下占据黄土高原大部分区域,畜牧业进而农耕退带来草地面积的增加,草地植被有所恢复。隋唐盛世,统治者农业上兴修水利,政策上推行均田制等重农政策,农耕业再次繁荣,耕作区沿渭河向西到达天水、陇西、直至湟水谷地,连地势较高的黄土台塬也被开垦利用。唐以后,气候变化和战乱影响,黄土高原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直至宋朝,该地区人口恢复到1 000 万左右,华夷军事力量在此对峙,农业技术发展,黄土高原屯田垦荒的范围和程度均急剧增加。后来,元统治中原,大肆屠杀汉人的政策致使农耕业人口大量减少,农区锐减,黄土高原灌草植被有所增加。明清时期黄土高原人口持续增加,农耕业发展迎来大繁荣,对黄土高原的开发利用达到顶峰,河川谷底的平地基本已经被开垦并向坡地、山地延伸,长城以南疏林灌丛连片消失,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彻底沦为农田[39]。

表2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人口变化与草地变迁[38]Table 2 Changes in the human population and grassland on the Loess Plateau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这样不合理的开发一直持续到20 世纪中后期,黄土高原区频繁的自然灾害使政府逐渐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水土保持工作由此大规模展开。但由于缺少植被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在植被选择、布局、造林种草技术等方面并不成熟,建设成效甚微,并没有扭转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12]。20 世纪80年代,国家从预防破坏和强化治理两端协同发力,采取工程措施、耕作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先后在黄土高原布局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成效显著。70 多年间,
黄土高原生态治理模式从“单一工程措施为主”向“工程措施、耕作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发展,工作侧重点也从“坡面治理–沟坡联合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林还草与治沟造地”的转变[62],在这个过程中人为因素对黄土高原植被环境的影响开始变为正向。黄土高原不再是濯濯童山、草木萧疏的荒凉景象。目前,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已接近该地区水资源植被承载力的阈值,区域生态治理和修复进入新的阶段,仍需继续探索新的治理思路和措施[66]。
4 结语
世易时移,山河换颜,250 万年间黄土高原的植被生境几经巨变,但草地始终是其最主要的植被类型。在较早的地质时期,黄土高原植被演替的主要驱动力是自然条件的改变,气候、地形地貌、水文等变化对草地植被类型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在更新世,黄土高原草地植被随气候变迁经历了森林草原、草原、荒漠草原的多次嬗替,晚期草原向干草原转化。随着气候的回暖,在全新世早期至中期的几千年,黄土高原草地植被大致经历了荒漠草原–森林草原(或疏林草原) –针叶林或温带森林–森林草原演化过程。到全新世晚期,黄土高原草地植被的退化主要是自然环境背景下人类活动的作用。人口负载的增加、农耕业的纵深发展,超载放牧、过度樵采、烧荒、战乱等不断侵蚀黄土高原脆弱的生态基础,使得植被的自然恢复能力大大减弱。黄土高原原有的森林草原向草原、荒漠草原甚至荒漠演变,草原带南移,草地退化严重,不少地区地表裸露,俨然荒山秃岭。直至20 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因地制宜的开展,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才被遏制,破坏严重的草地植被逐渐得以重建与恢复。
以古鉴今,结合黄土高原草地植被的嬗变史及该区域多年的生态治理实践,可以得出对未来黄土高原生态建设的几点启示:一要坚持防治结合、系统治理的工作原则,在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各组分的基础上综合实施工程措施、耕作措施和生物措施,遏制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态势;二要以地质、历史时期的植被情况为参考,基于现有气候条件和区域水文条件科学设计区域内建植植被的种类和密度[66],构建起结构稳定、功能持续高效的植被体系,充分考虑草在区域植被重建与恢复中的重要性;三要调动群众参与黄土高原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以政策和法律为保障,为黄土高原生态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保驾护航;四要合理规划农牧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草地农业,构建新型的农林草牧耦合系统[67],以实现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