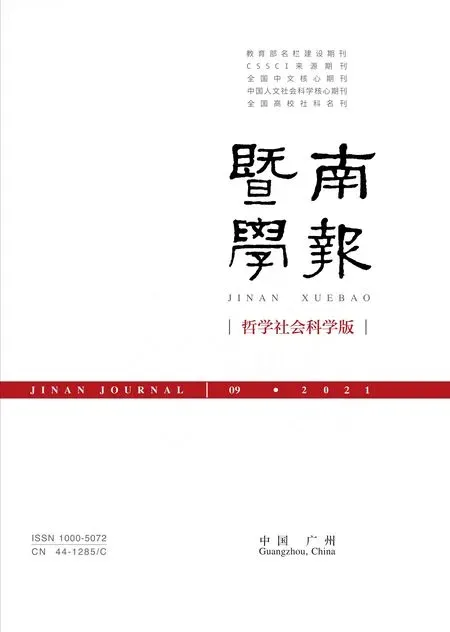制度知识在魏晋的断裂与延续
黄 桢
由秦开创的王朝体制经两汉四百余年的拓展逐步走向发达。职官、礼仪、刑罚、赋役、军事等各方面制度随之不断蓄积,趋于严密。本文所谓“制度知识”,既指向制度的具体承载物,比如律令和仪注,也包括皇帝、官僚等政治参与者对制度的理解与记忆。在这两个层面里,后者乃主体,也是此项知识创造与传承的根本所系。
作为日常行政、国家建设的典据,制度知识实为体制运行的基石。对其重要性,汉人已有明确的认知。一个标志性的例证,是“熟习故事”被视作官吏必备的素质,擅长此道者往往受到朝廷上下的推重。《后汉书·黄香传》云:“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党锢列传》云:“(刘)祐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谢承《后汉书》云:“(龚遂)弥纶旧章,深识典故,每入奏事,朝廷所问,应对甚捷。桓帝嘉其才,台阁有疑事,百僚议不决,遂常拟古典,引故事,处当平决,口笔俱著,转左丞。”黄、刘、龚诸人均凭借制度知识的造诣而获得位望的攀升。另一方面,制度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东汉中期学者开始呼吁撰述当代制度,以扩大制度知识的传播范围,达到“人无愚智,入朝不惑”的效果。作为汉末学术的热门领域,“制度之学”在桓帝朝以降的数十年间催生了一批围绕官制礼仪的专门著作,如胡广《汉官解诂》、蔡邕《独断》、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应劭《汉官仪》等。制度知识的体系因而日渐庞大精深。
自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事开始,群雄相争,兵革不息,王朝秩序彻底崩坏。曹魏及继起的西晋政权没有带来局面的长期稳定,随着宗室内斗、五胡南下,烽烟再度弥漫。在这“天下乱离”的形势中,制度知识饱受冲击。尽管学界对魏晋时期政治体制发展的滞塞现象多有述及,但其成因往往只是以“局势动荡”一笔带过,还缺乏细致的探讨。制度知识的存续状况是引导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线索。本文将重点考察制度知识中围绕官制、礼制的部分在汉末以降的解体过程,进而关注这一困境下曹魏、东晋等新兴政权的挣扎和调适。依赖士人家学,制度知识的传承并未完全中断,其不绝如缕的一面也会在后文论述。
一、制度知识的散乱及影响
《晋书·礼志》云:“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宋书·礼志》云:“汉末剥乱,旧章乖弛。”《南齐书·礼志》谓:“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史书对“旧章殄灭”的反复陈说,足以表明汉魏之际制度知识传承失序的严重程度。
京城是王朝体制下一切资源的中心,荡覆京畿的“董卓之乱”揭开了制度知识散亡的序幕。初平元年(190),董卓挟献帝出走长安,临行之际对洛阳城大肆破坏。司马彪《续汉书》云:“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图书典籍受害尤深,史称“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只剩下七十余车随帝西迁。两年后,长安朝廷再次动乱,这批图籍也“一时燔荡”。由它们承载的官制、礼制知识自然难以幸免。建安初年志在协助汉廷重建官制礼仪的应劭,对制度知识遭遇的这场浩劫有直接的陈述:“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遣,开辟以来,莫或兹酷。”
文献湮灭造成制度知识散亡的具体情形,可以通过以下二例来了解。崔豹《古今注》载:“《日重光》、《月重轮》,群臣为汉明帝作也。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晖》,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后二章亡。”据引文,东汉光武帝时期群臣创作并献给太子的歌诗,成为东宫礼乐的一部分。不过,其中《星重晖》、《海重润》两章在汉末动乱中亡佚,后人已无法沿用。朝贺、祭祀等重要礼制场合演奏的雅乐也因乐章不存而濒临失传。《晋书·乐志》云:“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直到曹操平定荆州,找到曾经的雅乐郎杜夔,令其“考会古乐”,轩悬钟磬之制才逐渐重建。
各种实物在战乱中的毁损也造成了制度知识的佚失。挚虞是西晋礼制建设的主持者之一,他在回顾舆服变迁时提到:“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我们知道,玉佩向来是君臣服制的重要元素,刘向有言:“古者天子至于士,王后至于命妇,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东汉明帝对佩玉之法进行了革新,“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不过正如挚虞所说,皇帝百官的玉佩后因时局动荡而灭失殆尽,由于无从获知形制详情,这项制度一度废停。幸赖王粲对汉家旧佩有所记忆,该仪制才勉强恢复。又,《宋书·礼志》“指南车”条云:“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引文显示,张衡的创造使东汉皇帝得以在车驾中加入指南车,但伴随实物的消逝,相关知识未能传入曹魏朝廷,以致制度的真实性遭到怀疑。另外,《晋书·杜预传》载:“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可见,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欹器一直作为礼器放置在皇帝御坐之侧,但因原物遗失,形状不明,此制度只得在汉魏之际中断。
随着汉献帝迁都许昌以及曹操统一华北,军阀混战的局面逐渐平息。接下来我们关注制度知识散亡背景下的制度兴复。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一些精于制度之学的官僚。首先可以举出的就是上文已提及的应劭。在献帝刚抵达许昌的建安元年(196),应劭便献上《汉仪》,其上表提到:
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
从篇目可知,《汉仪》涵盖律令、诏书、故事等多方面内容。该书当由应劭鸠集劫后残留的各种典制章程而成。“未足”乃谦辞,应氏对《汉仪》的定位正是“纲纪国体,宣洽时雍”,他渴望着这部著作能作为重建制度的参照。《后汉书·应劭传》载:“(建安)二年(197),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可见应劭在建安二年之后继续编撰以汇聚制度知识为主旨的书籍。在“旧章堙没”窘况中,这部《汉官礼仪故事》的上呈可谓切合时宜,献帝朝廷“朝廷制度”、“百官典式”的恢复均从中受益。对于应劭为制度延续所作贡献,史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司马彪《续汉书》云:“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
王粲与卫觊是另外两位在汉魏间葺理制度知识的代表性人物。前者与撰写《独断》以及东汉国史之《礼乐志》、《郊祀志》、《车服志》、《朝会志》的制度学大家蔡邕具有学术继承关系。这从《三国志·王粲传》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据张华《博物志》“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之语,蔡邕藏书确实尽赠王粲,其中当不乏官制礼仪方面的资料。前文所举“玉佩”的例子已显露王粲在制度知识上的积淀。建安十八年(213),魏国建,王粲被拜为侍中,“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他在恢复封爵制度、宫廷雅乐方面的贡献已由学者揭示。卫觊曾在献帝朝廷担任尚书,主持制度的整顿。王沈《魏书》云:“初,汉朝迁移,台阁旧事散乱。自都许之后,渐有纲纪,觊以古义多所正定。”魏国建立后,卫觊也被拜为魏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三国志·卫觊传》记其曾撰有《魏官仪》一书,应是重建官制过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史家在回顾汉魏间制度变迁时都会提及王、卫的事迹,如《宋书·礼志》云“魏初则王粲、卫觊典定众仪”,《南齐书·礼志》称“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可见二人在复兴制度上的确取得了成绩。
承乱而起的蜀汉、孙吴政权,也在恢复官制礼仪的道路上努力尝试。刘备治下,数位学者因明习故事、通晓朝仪而获得职任。比如孟光,本传称其“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刘备定益州后即“拜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许慈也是由于擅长礼仪之学而备受礼遇。孙吴方面,《南齐书·礼志》云“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所谓“拾遗汉事”,就是收集有关汉代制度的资料与信息,为当前官制礼仪建设提供参照,“汉官六种”之一的《汉仪》一书即其遗事。《隋书·经籍志》另记有韦昭的《官仪职训》一卷。韦氏也是孙吴的史臣,撰写该书的用意可能与丁孚“拾遗汉事”一样,均在于制度知识的整理。
经曹魏一朝的修复与积累,官制礼仪在西晋迎来全新的局面,尤其是禅代之际“荀顗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裴秀议官制”,堪称盛况。关于承平时期的制度知识,既有研究多有涉及,此处不赘。很快,晋末新一轮的动乱又阻断了制度知识的发展,接下来转入对两晋之际相关情况的考察。
四世纪初的十余年间,在匈奴铁蹄的蹂躏下,洛阳、长安相继陷落,晋室在北方已无立足之地。驻扎在建康的司马睿拾获继统的机遇。新政权在纷乱的局势中仓促成立,既远离过去的政治中心,其基底又不过是司马睿领导下的将军府(后为丞相府),种种因素决定了东晋王朝的政治发育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官制礼仪在东晋前期尤其残破。比如,职官架构较渡江前大幅萎缩。九卿中的卫尉、大鸿胪遭省并,光禄勋、大司农、少府、太仆或置或省,隶属太常的博士、国子助教也大量减员。作为行政中枢的尚书省同样遭受减损,江左初期废止了西晋三十五曹中的十曹,此后又削除了二千石、主客等曹。再来看国家祭祀的例子。“江左初,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也”。明堂亦未建立,相关礼仪付之阙如。东汉明帝确立的五郊迎气之礼,为魏晋所遵循,但“江左以来,未遑修建”。舆服之制更是颓败不堪,“自晋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据《晋书·舆服志》,过江以后,装饰冕旒的白玉珠已无法备齐,故侍中顾和奏:“旧礼,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难得,不能备,可用白璇珠。”汉晋临轩大会,都有“充庭之制”,“陈乘舆车辇旌鼓于殿庭”,以展示王朝文物之盛,即张衡《东京赋》所谓“龙辂充庭,云旗拂霓”。不过此制“晋江左废绝”。《晋书·舆服志》记有“中朝大驾卤簿”,可窥见西晋皇帝车驾之盛。而东晋一朝因缺少五时车、司南车、金钲车、豹尾车等属车,始终“大驾未立”,皇帝郊祀只能乘拼凑而成的法驾。皇太子主持释奠,因无高车,也不得不以普通的安车出行。
东晋官制礼仪的窘况,与“中兴草创,百度从简”有关,而制度知识的散亡亦为重要诱因。这一点可以通过皇帝车制进行说明。《晋书·舆服志》云:“其辇,过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谢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坚于淮上,获京都旧辇,形制无差,大小如一,时人服其精记。”辇为魏晋皇帝“小出”所乘。因既无实物,又无记载流传至江左,孝武帝太元年间以前竟无法兴造。指南车的情况与此类似,《宋书·礼志》载:“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刘裕于晋末从后秦手中夺得实物,才使建康朝廷获取了关于指南车的知识。朝廷礼仪方面也能举出例证。《晋书·华恒传》曰:
及帝加元服,又将纳后。寇难之后,典籍靡遗,婚冠之礼,无所依据。恒推寻旧典,撰定礼仪,并郊庙辟雍朝廷轨则,事并施用。
咸康初年,成帝到了加元服、纳皇后的年纪,却由于承载着礼制信息的典籍亡失,一时无法开展。华恒匆忙间搜集孑遗,撰定礼仪,才缓解了尴尬。上引文还透露出,婚、冠之外,郊庙、辟雍的行礼方法以及行政运作的一些规则在渡江初期亦不明晰。另外,《南齐书·百官志》云:“晋世王导为司徒,右长史干宝撰立官府职仪已具。”从佚文可知,干宝《司徒仪》以讲解司徒府中各属官的职掌为主要内容,是司徒府行政运作的指导。以史学见长的干宝推寻旧典、撰立此书的缘起,应是中朝的相关职仪没能顺利南传。《晋书·刁协传》“朝廷草创,宪章未立,朝臣无习旧仪者”之语,明确展现了制度知识在东晋初期的普遍缺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官僚、学者凭借制度知识上的特长,活跃于政治前台,受到统治者的优遇。与刘隗并为元帝宠臣的刁协,当初得以迈入权力中枢的一项要因,就在于熟识旧仪。刁协本传称:“协久在中朝,谙练旧事,凡所制度,皆禀于协焉,深为当时所称许。”在渡江前,刁协做过太常博士,亦曾在成都王颖、赵王伦、长沙王■、东嬴公腾府中任事,转任多职加上注重积累,故能“谙练旧事”。这一才能对于“新荒以来,旧典未备”的建康朝廷弥足珍贵。贺偱也是一例。贺氏世传礼学,对王朝仪制多有了解。贺偱在元帝登基后被拜为太常,主要职任就在于兴复礼制。《晋中兴书》载:“贺循,字彦先。拜太常,每存问议先朝旧事,以此比校循所奏,绝不符同,朝野咸叹循之渊学也。”《晋书·贺偱传》云:“时尚书仆射刁协与循异议,循答义深备,辞多不载,竟从循议焉。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两条材料显示了贺偱因其制度之学为朝野所推仰。另外,荀崧、华恒在东晋前期位遇优厚,也与自身久仕中朝、谙识朝仪有关。当然,上述诸人取得的成果比较有限,制度在东晋前期并未摆脱惨淡之相。穆帝朝以降,随着政治环境走向稳定以及对北方传来的制度实物、制度文献的接收,官制礼仪才进入复兴的时代。
二、制度知识的家内传承
上文通过梳理实物、文献在魏晋乱世中的亡毁,细绘了制度知识所面临的断绝危机。凭借部分谙熟制度的官员的努力,官制礼仪得以在动荡之后逐渐修复。制度知识的人际传播孔道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士人家学的支撑。
家庭教育对学术文化在汉晋间的绵延贡献尤大。陈寅恪指出,汉末以降官学体系瓦解,知识生产及流动的方式彻底改变,学术中心移于家族,“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学界对经学、史学、文学乃至谱学、医学、书法等学科在家族内的传承已多有研究,但尚未充分注意官制朝仪从魏晋开始也成为家学的重要成分。下面将以案例的形式对此加以揭示。
(一)颍川荀氏
魏晋盛门颍川荀氏的家族文化中就带有礼仪朝章之学的基因。
从现存史料来看,荀攸是最早同制度之学建立连接的荀氏人物。《隋书·经籍志》云:“梁有荀攸《魏官仪》一卷。”荀攸卒于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生前任魏国尚书令。那么所谓的“魏官仪”,是指曹操魏国的官制仪式。上一节提到,魏国初建,曹操以侍中王粲、卫觊典定制度。从《魏官仪》的署名来看,作为尚书令的荀攸亦曾参与,且总统其事。至于卫觊本传提到的那部《魏官仪》,大概是曹丕、曹睿时期卫觊据魏国官仪进行增损的结果。荀攸后人留下的材料不多,其家庭文化方面的情况已无从得知。
荀勖一支从西晋开始在制度之学上崭露头角。荀勖在咸宁年间向武帝提交了著名的“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之议。在这篇上疏中,他首先罗列了西汉、东汉、曹魏各朝在并官省职方面的作为,继而分析官制运行的原理,由此提出了九卿划属尚书、御史台归入三公府等计划。《南齐书·百官志》卷首序言是对历代官制文献的回顾,两晋的部分提到了荀勖的上疏:“山涛以意辩人,不□□□。荀勖欲去事烦,唯论并省。定制成文,本之《晋令》,后代承业,案为前准。”从引文看,荀勖的上疏影响颇大,其中的一些观点被朝廷法令采纳,并为后代所承袭。另可作为参考的是,荀勖亦深谙法律。《晋书·刑法志》载,文帝为晋王,“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觊、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晋书·荀勖传》又云,武帝受禅后,命荀勖“与贾充共定律令”。律令也属于朝廷典章,明晓职官制度的荀勖自然易于兼通。
擅长官制礼仪之学的荀勖子孙对永嘉丧乱后南北方的制度建设都发挥了推动作用。荀勖孙荀绰永嘉末在王浚府内任职,晋愍帝建兴二年(314)石勒平幽州,绰被带回襄国、任为参军。因谙熟华夏制度,荀绰颇受石赵政权信重。《隋书·经籍志》史部职官篇记载的“《百官表注》十六卷”就是荀绰指导石赵官制建设时撰成的文字资料。南迁江左的荀勖子荀组、组子奕等对东晋的礼制兴复有所贡献。《晋书·礼志》载,太兴二年(319)元帝命臣下讨论郊祀,刁协等认为应夺回洛阳后再执行该礼,荀组则举出汉献帝于许都立郊祀的故事,认为“自宜于此修奉”。该提议获得了王导、庾亮等人的支持,东晋的南郊祭天仪式由此建立。另外,由于中原板荡,室家离析,官民在凶礼的开展上遭遇不少难题,荀组也参与了解决方案的议定。《晋书·荀奕传》云,成帝朝百官通议元会时皇帝是否应致敬司徒王导,荀奕指出须区别大会、小会,元旦大会不应致敬。他的见解被采纳为元会仪则。《晋书·礼志》又有荀奕讨论读秋令之仪的记载。
荀彧后人也在家学中注入了官制礼仪的内容。彧子荀顗是西晋新礼的开创者。魏末咸熙元年(264),司马昭“奏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晋书·礼志》言之稍详:“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这部新礼在礼制史上意义重大,学者视其为官修礼典的开端。本传称荀顗“明《三礼》”,反映了应用性知识背后存在更深层次的学术涵养,经学为其关于朝廷礼式的构思提供了有力支撑。“族曾祖顗见而奇之”的荀崧又成为了东晋初期礼制重建的主持人之一。其本传云:“元帝践阼,征拜尚书仆射,使崧与(刁)协共定中兴礼仪。”《晋书·礼志》则谓“晋始则有荀顗、郑冲裁成国典,江左则有荀崧、刁协损益朝仪”。《通典》记有荀崧参与一些具体仪节的讨论。另外,荀崧本传收录了太兴初年荀崧请增置博士的上疏。该文梳理了魏晋时期博士等职设立、选用的情况,同时为当前博士员额如何配置提供了建议,由是可见荀崧对官制亦相当精熟。
顺带指出,上面提到的“议官制”的河东裴秀,其家族文化中亦有制度之学的一席之地。除了官制的改定,司马昭在咸熙元年建立的五等爵制也出自裴秀的策划。《晋书·裴秀传》称:“秀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另外,裴秀注意到尚书三十六曹有分工不明的情况,试图通过“诸卿任职”来捋顺行政运作。尽管这项方案未能提交,但足以反映裴氏在官制方面的深入思考。裴秀子裴頠参与了西晋时期明堂礼等仪制的讨论。裴秀孙裴宪的制度知识在石赵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石勒称赵王后,他与王波撰朝仪,“于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石勒因此大悦,尊裴宪为司徒。
(二)北地傅氏
魏末名臣傅嘏,精于官僚制度。明帝景初年间,刘劭撰《都官考课》,试图改革百官黜陟之法。尚担任司空掾的傅嘏作论反驳。这篇文字切入的角度是考课法的先例以及建安以来的官制进展,由此可以看出傅嘏在制度变迁的问题上已有不少积累。傅嘏此后历任尚书郎、黄门侍郎、河南尹、尚书等职,一直对朝廷的官制建设十分在意。《三国志·傅嘏传》云:
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难,未能革易。
傅嘏认为,从秦汉到当下的设官分职一直存在“不应时务”等缺点,需要全面改定官制,才能“至于治”。不过,这一建立在对制度弊端深入反思之上的改革计划,因魏末政局不稳,未能付诸实践。
傅嘏在朝廷制度上的考究态度,融入了家庭文化,子、孙中都出现了以制度之学见长的人物。傅嘏子傅祗在怀帝即位后任尚书左仆射,本传称“祗明达国体,朝廷制度多所经综”。傅祗在这方面的学识成为了朝廷维持制度运转的重要凭借。进入石勒政权的傅祗子傅畅,因“谙识朝仪”而为石勒所倚重,“恒居机密”。他撰写的九卷《晋公卿礼秩故事》是围绕西晋职仪的学术专著,是书不仅为后赵政权的相关建设提供了指导,在东晋中后期传至建康后,又充当了晋宋之际制度与制度书写发展的助力。
傅玄—傅咸是北地傅氏另一显要房支,其家学同样强调官制礼仪的掌握。《晋书·傅玄传》比较完整地收录了傅玄的两篇上疏。第一篇作于晋武帝即位不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散官制度的调整。第二篇的背景为水旱灾害频发,在傅玄提出的五点建议中,有一条是改革河堤谒者之职的方案。这些材料透露出傅玄对制度问题的长期关注。最能展现傅氏官制礼仪之学的是《傅子》一书。《傅玄传》云:“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这部列于《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的著作,含有大量关于职官、仪制的研究。比如《宋书·礼志》引用过傅玄书中对辇车、幅巾的考证:
1.《傅玄子》曰:“夏曰余车,殷曰胡奴,周曰辎车。”

《北堂书钞·设官部》保留了不少傅玄关于官制史的论述,略举数条:
1.《傅子》云:“尚书者,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
2.《傅子》云:“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
3.《傅子》云:“魏明帝以管宁为太中大夫,赐朝服一具、衣一袭、被一领、安稳犊车一乘。”
另外,《续汉书》刘昭注以及《晋书》、《隋书》、《初学记》等著作也曾借助《傅子》来讲解制度沿革。
傅咸继承了其父傅玄的制度学问。咸宁五年(279),傅咸倡议并官省职,上疏中他多次对比古今官制,可以看出傅咸的相关学养。惠帝朝他与御史中丞解结的一场争论更能显示其对朝仪旧典的熟稔。针对官场浮竞之风,时任司隶校尉的傅咸奏免吏部尚书王戎。此举引来解结的弹劾:“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傅咸遂上书辩解,文中不只援用《晋令》,也提到武帝朝荀恺奏石苞的先例,还梳理了自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二职设置以来的分工。因典据充分,“条理灼然”,“朝廷无以易之”。《晋书·礼志》又载:“(挚)虞讨论新礼讫,以元康元年(291)上之。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虞之《决疑注》,是其遗事也。”元康元年以降,挚虞与傅咸曾共同主导礼制建设,这说明傅咸在朝廷仪礼方面亦有造诣。《礼志》另收有傅咸关于读秋令、立社稷以及百官丧制的议论。
永嘉之后傅氏南迁,制度之学相传不绝。代表人物是傅咸曾孙傅瑗。傅瑗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后期担任尚书祠部郎,该职的拜除当与其通晓王朝礼制有关。《通典》记载了他与徐邈关于移庙、告庙仪节的讨论。《隋书·经籍志》有傅瑗所撰“《晋新定仪注》四十卷”。所谓“新定仪注”,是东晋政府在经历了前期的“朝廷草创,宪章未立”后重新整理仪制的产物。《晋新定仪注》署名傅瑗,说明他是这项事业的主持者。《宋书·傅亮传》称“父瑗,以学业知名”,由上述考释可知,此处的“学业”包括官制礼仪之学。
(三)“王氏青箱学”
东晋以降崛起的制度学世家以琅邪王氏中王彪之一支最为显要。《宋书·王准之传》载: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官制礼仪是引文中王彪之所练悉的“朝仪”、“旧事”的重要方面。王氏“家世相传”的“青箱学”大概就是官制礼仪之学。
“青箱学”的开创者王彪之为王导从弟王彬之子。晋哀帝兴宁年间,主政者桓温“陈便宜七事”,建议大规模并官省职,王彪之据此上呈修改意见。这篇“省官并职议”是王彪之官制思考的集中体现。他在文中分析了行政运作的基本原理,重点针对六卿、宿卫官以及侍中等内官提出并省计划,并且论述了“令大官随才位所帖而领之”的“帖领”方案。王彪之的不少见解,尤其是“帖领”的办法,被东晋南朝统治者采纳、继承。王彪之对朝廷仪制的谙练则在桓温废海西公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是时温将废海西公,百僚震慄,温亦色动,莫知所为。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夺,乃谓温曰:“公阿衡皇家,便当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传》。礼度仪制,定于须臾,曾无惧容。温叹曰:“作元凯不当如是邪!”时废立之仪既绝于旷代,朝臣莫有识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当阶,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
因“废立”久未施行,百官已无人能识旧仪。而王彪之援引《汉书·霍光传》等文献,须臾之间撰定仪制,遂凭借朝仪之学为朝廷所服。另外,王彪之积极参与穆帝、孝武帝朝的各类礼议,根据严可均的整理,王彪之曾上呈关于元会仪的“日食废朝会议”,关于冠礼的“帝加元服议”,关于婚礼的“婚礼不贺议”、“婚不举乐议”、“上书论皇太子纳妃用玉璧虎皮”、“上书论皇后拜讫上礼”等,以及关于丧礼的“奔丧议”、“太后为亲属举哀议”、“丧不数闰启”等。
前引《王准之传》云,王彪之将自己收集的“朝仪”、“旧事”缄于青箱,传予子孙。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自然能不断培养精于官制礼仪的学者。王彪之孙王讷之于晋末任尚书左丞,《晋书·礼志》记载了安帝元兴三年(404)他关于“郊祀不得三公行事”的议论,其观点获朝廷支持。王彪之曾孙辈的王准之、王逡之、王珪之三人并为制度之学的翘楚。王准之“明《礼》”,亦通晓历代故事,本传对其学养有直接的赞誉:“准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本传又称:“撰仪注,朝廷至今遵用之。”《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篇记有数种不著撰人的刘宋仪注,比如“《宋仪注》十卷”、“《宋仪注》二十卷”等,这里面应含有王准之的贡献。《王准之传》中永初二年(421)所上“奏请三年之丧用郑义”的议论,又体现了他在凶礼方面的知识积累。王逡之在宋齐之际为萧道成齐国的礼制建设倾注了心力,《南齐书》本传云:“升明末,右仆射王俭重儒术,逡之以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参定齐国仪礼。”《南齐书·舆服志》载,升明三年(479)宋顺帝锡齐王大辂、戎辂各一,逡之议以为大辂即《周礼》五辂中的木辂。这是逡之“参定齐国仪礼”具体事例。《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下有王逡之撰《礼仪制度》十三卷,该书很可能就是逡之所定齐国仪礼。王珪之则在宋齐之际被敕撰写了《齐职仪》。在这部五十卷的官制大著里,王珪之详究历代设官分职,将品级、职掌、黜陟、冠服等多种制度元素汇聚一处。作为中国史上首部官修政典,《齐职仪》为南朝以降的制度书写设立了新的标杆,可谓意义重大。
三、小 结
以上搜集材料,对魏晋乱世中的制度知识进行了概观。两次全国性的动荡打断了制度知识的有序传承。它们的散乱与亡失,造成后续的制度恢复步履维艰,秦汉式政治体制的延续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刚从动荡中崛起的新政权,就已对制度知识在政治发展上的价值有所体认,其标志就是多位官僚因精于制度之学而为人君所重。
制度知识依靠士族家学而延续不绝的一面也被揭示。这段时期注重制度知识传习的家庭,多为势族高门,其成员往往在朝中占据显位。这种现象的形成,源自制度之学与家族地位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官制礼仪是政治运行的必备元素,汉晋间世事的动荡和政权建设的需求,造成这一领域的知识变得稀有而珍贵。正如上引刘义康对王准之的赞叹“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明故事、晓朝仪的人物往往因此获得统治者的重用。另一方面,官场经验是习得制度知识的重要途径。高门子弟既有承自父祖的“青箱”,又自幼浸润在官场文化当中,他们对官制礼仪的理解和把握自然非寒素所能企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让世传官制礼仪的家族得以维持较高地位,这门学问也在一代一代的积淀中走向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