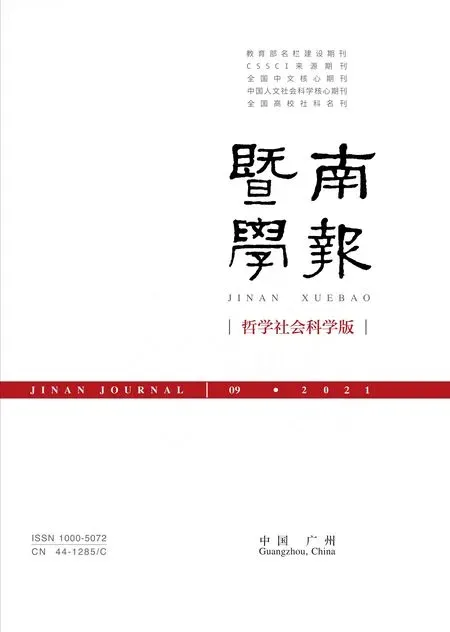杨维桢撰《张氏通波阡表》不同文本的差异及其成因探析
——兼论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贡献
杨晓春
元代松江,活跃着众多的地方家族,是元代松江地方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些地方家族社会特征多样,有的积极出仕,有的隐居地方,有的专注艺文创作,有的热衷地方活动。其中祥泽张氏家族,则属于隐居型家族的代表。有关张氏家族,我们所能了解的主要史料首推杨维桢撰的《张氏通波阡表》。此文载于杨维桢的文集,还载于方志,而且还有幸保留了杨维桢的墨迹,从历史文献的保存来讲,可谓幸运。杨维桢是元末的大文学家,号为东南文宗,声名卓著,不免增加了此文的知名度;此外杨维桢书风独到,还是备受关注的一位书法家,因为这一层原因,更增加了《张氏通波阡表》的知名度。然而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不小,特别是有关张氏家族的世系的差异尤其大,对于试图利用此文的研究者造成了困扰。
近来孙小力先生广泛收集杨维桢的著述,并加以校勘和笺注,汇总为《杨维祯全集校笺》,为研究者利用相关文献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嘉惠学林。其中当然也收入了《张氏通波阡表》一文。《杨维祯全集校笺》以《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为底本,还根据他本等进行校勘,或改正底本,或注明异文,但是并未能说明不同差异造成的原因。甚至因为并不讨论不同文本形成的原因,导致利用某一版本来更正底本文字的时候,实际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改动,从而改变了底本文字的特征。而此种校勘的方法,用于像《张氏通波阡表》这种比较特殊的对象身上,并不能说是上选。
本文试图全面比较《张氏通波阡表》几种文本的差异,并着重说明导致不同文本的差异的内在原因。
一、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的三种文本
传世文献中,此文或题作《张氏通波阡表》,载于《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铁崖漫稿》,或题作《通波阡表》,载于正德《松江府志》。存世的杨维桢墨迹,亦题作《张氏通波阡表》,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有多种影印本。但是正如孙小力先生已经在《杨维祯全集校笺》中指出的,墨迹本曾经拼接,并非完本,缺失了一百六十多字。这一情况,墨迹本本身也有比较明显的迹象,拼接之处的界格并不衔接,而且拼接处上下各盖了一个章。《杨维祯全集校笺》还以《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为底本,校以墨迹本、《铁崖漫稿》本、正德《松江府志》本和王逢《张氏通波阡表辞》。综合起来,可知《张氏通波阡表》现存主要有三种文本,以下将其文字分别转录。
(一)《张氏通波阡表》墨迹(保留了复文符号=和厶字,原文所书“句”、“叶”字用括号括出)
张氏出青阳,历汉、魏、晋、唐,为显官甲族者,代不乏绝。入宋为三叶衣冠者曰士逊,称橫浦居士者曰九成,无尽居士曰商英。==渡江拜相,子孙遂居杭之菜市。有八世祖厶游淞,爱干将山之樱桃坞为隐地,因结庐居之。六世祖厶又自樱坞迁山昜之祥泽汇,与其子号千一居士者,开丘凿井以养其亲。居士自奉至俭,事继母孝谨,不一日衰。遇冬雪,扫隙地,撒粟以食冻禽,翔集者以千数。居士往来,慈乌或有翼而随者。尝为里豪邹氏者拓土田若干顷,后……以其咈喏为曲直,人负不平,不之邑而之公,乡称张片言。仓丁有给米曰养廉,吏缘为奸(句),格(句),公率众走愬南垣,复给如初。众率口钱罗拜公,=力却勿受。众委钱而去,公弗侵毫毛,以之周贫饿,余力创乡之义井、义舟,建大石梁者三。寿七十有一终。娶同里孙氏,生三子。长义;次德,出赘陆氏;次瑞。=之子曰麒。=尝从余游,每恨先裔成谱未修,三祖之石未立,惧丧乱之余,弥远弥失。招致余过其家,上其祖冢,曰通波之原,拜而有请为三祖阡表。余以其积善之庆,流及五世至麒,而其业益修,门益大,张氏子孙,食其报者未艾也。于是属比其事,书之于石,而又系之以辞曰:
张氏得姓,出自青阳。勋之显者,曰韩之良。柱下相君,弥寿有苍。八世贵盛,莫过于汤。茂先仕晋,博洽是长。商英扈驾,子姓在杭。寔为鼻祖,由杭徙淞(叶)。五世戴德,地汇其祥。仁孝授受,柢固原长。五世既昌,八世莫京(叶)。刻辞阡表,用昭后庆(叶)。
至正乙巳春,李黼榜第二甲进士、奉训大夫、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乩杨维桢撰并书。
(二)《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卷二《张氏通波阡表》(《铁崖漫稿》略同)
张氏出青阳,历汉、魏、晋、唐,为显官甲族者,代不乏绝。入宋为三叶衣冠者曰士逊,称橫浦居士者曰九成,无尽居士曰商英。商英渡江拜相,子孙遂居杭之菜氏。有八世祖某游淞,爱干将山之楼桃坞为隐地,因结庐居之。六世祖某又自楼坞迁山阳之祥泽汇,与子号千一居士者,开丘凿井以养其亲。居士自奉至俭,事继母孝谨,不一日衰。遇冬雪,扫隙地,撒粟以食冻禽,翔集者以千数。居士往来,慈乌或有翼而随者。尝为里豪邹氏者拓土田若干顷,后嗣贪侈无度,倍益田,入佃者不能庚,号泣其门相什伯。公捐己有代庚,绝邹氏交。嗣荡业后来谒公,公抚之如子,不令失其归。年九十有三终。娶华亭陆氏,生男某。筑草堂号隐庵,博涉史籍,尤精梵典,攻星历、阴阳、风水之术。攻苦茹淡如父风。与儒释唱和,有诗偈若干首传于乡。寿八十有五终。娶夏氏,生男曰英,字卿。其为人广颡大耳,美髭髯,其声如钟。自幼机警,通史传学,尤长于律书。中慈而外刚,见善若嗜欲,恶则视如仇。然乡闾以其咈喏为曲直,人负不平,不之邑而之公,乡称张片言。仓丁有给米曰养廉,吏掾为奸(句),格(句),公率众诉南垣,复给如初。众率口钱罗拜,公力却勿受。众委钱而去,公弗侵毫发,以周贫饿,余力创乡之义井、义舟,建大石梁者三。寿七十有一终。娶同里孙氏,生三子。长义;次德,出赘陆氏;次瑞。瑞之子曰麟。麟尝从余游,每恨先裔谱未修,三祖之石未立,惧乘乱世之余,弥远弥失。招致予过其家,上其冢,过通波之原,而有请为三祖表阡。余以其积善之庆,流及五世至麟,而其业益修,门益大,张氏子孙,食其报者未艾也。于是属比其事,书之于君,而又系之以辞曰:
张氏得姓(出自青阳,勋之显者),曰韩之良。柱下相君,弥寿有苍。八世贵盛,莫过于汤。茂先仕晋,博洽是能。商英扈驾,子孙在杭。实为鼻祖,由杭涉淞(叶)。五世戴德,地汇其祥。仁孝授受,衹固源长。五世既昌,八世莫京(叶)。刻辞表阡,用昭后庆(叶)。
(三)正德《松江府志》卷十七《冢墓》引《通波阡表》
张氏出青阳,历汉、魏、晋、唐,为显官甲族者,代不乏人。宋为三叶衣冠者曰士逊,称橫浦居士曰九成,无尽居士曰商英。商英拜相,后子孙渡江,遂居杭之菜市。有八世祖某游松,爱干山之樱珠湾为隐地,因结庐居之。六世祖某号八七居士者,又自樱湾迁凤凰山阳之祥泽汇,与其子通号千一居士者,开丘凿井以养其亲。居士自奉至俭,事继母孝谨,不一日衰。遇冬雪,扫隙地,撒粟以食冻禽。居士往来,慈乌或有翼而随者。年九十有三终。娶华亭陆氏,生男显。筑草堂号隐庵,博涉书籍,尤精梵典,及星历、阴阳、风水之术。攻苦食淡如父风。与儒释唱和,有诗偈若干首传于乡。寿八十四终。娶夏氏,生男俊,字晋卿。其为人广颡大耳,美髭髯,其声如钟。自幼机警,通史传学,尤长于法律。中慈而外刚,见善若嗜欲,恶则视如仇。然乡闾以其咈诺为曲直,人负不平,不之邑而之公,乡称张片言。性好施,赈贫周急,凿义井,创义舟,建大石梁者三。寿七十终。娶同里孙氏,生三子,长恺,次悌,次珤。恺之子,曰龙,曰凤。悌之子,曰兴,曰旺。珤之子,曰麒;女曰妙龄,适卢祥。龙之子,曰宗仁、宗礼;女曰淑清。凤之子,曰宗义;女曰淑宁。兴之子,曰英。麒之子,曰彬,曰恒。麒尝从余游,每恨先裔成谱未修,三祖之石未立,大恩丧乱之余,弥远弥失。招致予过其家,上其祖冢,曰通波之原,拜而有请为三祖阡表。予以其积善之庆,流及五世至麒,而其业益修,门益大,张氏子孙,食其报者未艾也。于是属比其事,书之于石,而又系之以辞曰:
张氏得姓,出自青阳。勋之显者,曰韩之良。柱下相君,弥寿有苍。八世贵盛,莫过乎汤。茂先仕晋,博洽是长。商英子姓,扈驾在杭。实为鼻祖,由杭徙松(叶)。五世载德,地汇其祥。仁孝授受,本固源长。五世既昌,八世莫京(叶)。刻辞阡表,用昭后庆(叶)。
奉训大夫、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维祯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危素书,前江西等处中书省左丞周伯琦篆额。
二、《张氏通波阡表》三种文本之间的异同
第一,从具体内容之间的异同,可以判断墨迹本和《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本(以下称文集本)十分接近,而这两种文本与正德《松江府志》本(以下称府志本)则有非常大的差异。
文集本与墨迹本的文字基本相同,并且墨迹本用于断句的小字“句”和“叶”在文集本中也得以完整保留,可以判断文集本来源于墨迹本。因此,三种文本可以区分为两个系统:墨迹—文集本系统和府志本系统。
第二,文集本与墨迹本还存在着一些局部的差异,主要的文字差异均可以判断为文集本的错误。
文集编纂时,根据作者的手稿收集基本资料,是一种常规手段。当然收入《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时,此文墨迹还是完整的。至于形式方面文字内容的一个明显的差异,即墨迹本最后撰文时间和撰者的题署并不见于文集本,同样也是符合文集编纂时的一般做法的,因为文集中的文章作者是明确的,都归属于某人名下,于是通常不需要再保留此类文字。至于墨迹本的复文符号和“厶”字多见于手迹,改为原字和“某”字,以及“昜”改为“阳”等等,也符合一般的整理中的文字处理原则。此外,墨迹本“公率众走愬南垣”文集本作“诉”,墨迹本“公弗侵毫毛”文集本作“发”,“惧丧乱之余”作“惧乘乱世”,墨迹本“上其祖冢”文集本无“祖”字,墨迹本“拜而有请为三祖阡表”文集本无“拜”字,墨迹本“刻辞阡表”文集本作“表阡”,则并不影响文意。
而存在着文意上以及内容上不同的文字差异,主要是以下几处:(1)墨迹本“子孙遂居杭之菜市”,文集本作“菜氏”;(2)墨迹本“爱干将山之樱桃坞为隐地”,文集本作“楼桃坞”;(3)墨迹本“六世祖厶又自樱坞迁山昜之祥泽汇”,文集本作“楼坞”;(4)墨迹本“吏缘为奸”,文集本作“掾”;(5)墨迹本“=(瑞)之子曰麒”,文集本作“麟”;(6)墨迹本“流及五世至麒”,文集本作“麟”;(7)墨迹本“书之于石”,文集本作“君”;(8)墨迹本“出自青阳。勋之显者”,文集本作双行小字;(9)墨迹本“博洽是长”,文集本作“能”;(10)墨迹本“由杭徙淞”,文集本作“涉”;(11)墨迹本“柢固原长”,文集本作“衹”。
以上11处文字上的差异,绝大多数都是字形相近的差异,十分符合根据一种文本转录文字时因为不够仔细或者因为底本文字不易识别带来的讹误。又主要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有名词如地名、人名的差异,包括(1)(2)(3)(5)(6)共五处,其中(2)(3)实际上是同一种地名的差异,(5)(6)实际上是同一种人名的差异,很多时候没有其他的参证资料难以判断孰是孰非;一类是普通词汇的差异,包括(4)(7)(9)(10)(11)共五处,根据文意等往往可以判断正误。先看后者。显然(7)(10)(11)三处从文意上都可以判断是文集本的错误,(4)则文集本似乎也可以解释,当然仍以墨迹本为佳,而(9)则通过押韵的考虑也可以判断是文集本的不当。再看前者。一共三个专有名词的不同,最容易判断的是“张麒”还是“张麟”的人名问题。此人是杨维桢的熟人,也是他邀请杨维桢撰写这篇文章的,杨维桢当然不可能出错。仅此,已能说明墨迹本准确性很大。而此人的名字还出现在杨维桢为张氏撰写的《三味轩记》和曹睿为张氏撰写的《(积善堂)记》中,均作“张麒”。《(积善堂)记》也记到了松江的小地名,作“樱珠湾”。还可以用府志本来比较,可以发现“菜市”、“樱桃坞”、“张麒”作“菜市”、“樱珠湾”、“张麒”,则可以肯定几处专有名词的不同是文集本的错误。此外的(8)是形式处理问题,文集本作为双行小字,或许是作为注文处理,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刊刻时漏了文字临时改成双行小字救急处理的缘故,但是有时也容易给人造成误解。
总之,我们可以判断文集本与墨迹本具体文字有所差异的地方,都是文集本转录文字时不够仔细造成的新错误。这种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集本确实来自于墨迹本。
第三,关张氏家族的世系,墨迹—文集本和府志本两个系统差异非常大。
作为一篇记录张氏家族墓地的文章,张氏家族的世系问题是其中必然涉及的一个主要的,同时也是关键的方面,然而两个文本系统在这方面的差异却非常大。
墨迹—文集本系统所载迁祥泽以后世系可以图示如下:

府志本系统所载迁祥泽以后世系可以图示如下:

两相比较,不但家族成员的多寡差别很大,家族成员的世系和名字也颇有不同。而其中一致的方面,主要是张麒及其五世祖号千一居士这两个关键人物的亲属关系是一致的,并且名(号)是一致的。
这种现象显然不能用某种文献传播过程中的变化来解释,但一定是与文献本身形成过程中的某种特殊的原因有所关联。
有关张麒的家世资料,主要有杨维桢撰《张氏通波阡表》和王逢撰《张氏通波阡表辞(有序)》,两篇文章的撰写出于同样的原因。因此,两个文本系统的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所载世系的是非问题,还可以通过与王逢撰《张氏通波阡表辞》的比较,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明。查王逢撰《张氏通波阡表辞》所载世系与府志本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异,其中还讲到:“征前进士会稽杨公维祯为《阡表》,复征逢撰《家庙辞》,勒之碑阴,可谓知所本也。”可见杨维桢和王逢的两篇文章是刻在一块碑上的,杨维桢的文章为碑阳,王逢的文章为碑阴,竖立在张麒家族墓地之上,显然应该得到了张麒家族的肯定,不应该出现有关世系方面的可靠性的问题。
此外,曹睿撰《(积善堂)记》记张麒父亲名为珤,又称其六世祖为八七翁,都可以和府志本《通波阡表》对应。
如此看来,不免令人对墨迹—文集本的记载的可靠性产生非常大的怀疑。
第四,还有一些具体行文的方面,墨迹—文集本和府志本两个系统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以下举其中有关史实的几个方面略加说明(前面已经叙述的世系部分则不再涉及)。
(1)墨迹—文集本记张商英渡江,府志本记张商英子孙渡江。铭词中也略有不同,各与前文相对应,前者作“商英扈驾,子孙在杭”,后者作“商英子姓,扈驾在杭”。王逢撰《张氏通波阡表辞》称“张氏宋丞相商英裔也,高宗南渡,子孙遂居杭之菜市”,与府志本一致。张商英是北宋时期的知名人物,《宋史》有传,记其大观四年知杭州,但是不久便又出任京官,乃至拜相,而其卒在宣和三年。当然不能出现张商英在两宋之际扈驾南渡杭州之事。因此,如府志本那样写作张商英子孙渡江是可取的。
(2)墨迹—文集本较府志本多出千一居士的一段事迹:“尝为里豪邹氏者拓土田若干顷,后嗣贪侈无度,倍益田,入佃者不能庚,号泣其门相什伯,公捐己有代庚,绝邹氏交。嗣荡业后来谒公,公抚之如子,不令失其归。”这一段文字的保留还是删除,说不上对错,删除或许是考虑到作为同乡的邹氏的感受的缘故吧。
(3)墨迹—文集本记千一居士之子“寿八十有五终”,府志本记千一居士之子张显“寿八十四终”。
(4)墨迹—文集本记千一居士之孙张英(乡称张片言)“寿七十有一终”,府志本记千一居士之孙张俊(乡称张片言)“寿七十终”。以上两点是同样的情况,涉及两个人物的寿命有一年的差异,似乎两人之间还有关联。当然,表面上很难判断各自的对错。
三、《张氏通波阡表》主要文本差异成因分析
以上的文本比较,已经充分显示了《张氏通波阡表》墨迹—文集本系统和府志本系统的巨大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
府志本显示了撰文、书丹、篆额者的署名:“奉训大夫、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维祯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危素书,前江西等处中书省左丞周伯琦篆额”,则这一文本应该来自石刻,实则是一种石刻本,或者说是一种间接的石刻本(石刻本身和拓片,可谓直接的石刻本)。前文已经述及《张氏通波阡表》确实是刻碑的。石刻本作为一篇刻在碑石之上,立在一个家族墓地,涉及一个家族历史的文章,应该是经过这个家族最后认可确定的本子。墨迹本则不然,显示的是撰文者写成一篇文章之后的状态。通常,作为一篇碑刻文字,从文章的撰写到刊刻于碑石,往往要经过三个主要的阶段。首先是撰文,撰成之后由撰文者提供文章手稿给需要刻碑的人。而涉及私人以及家族的文章,往往是由事主向撰文者提供基础资料,以便撰文者参考。其次是书丹,往往由擅长书法的人将已经撰成的文稿书写一遍,多数情况下像阡表这一类的文字都是用楷书;而碑额部分,则往往用篆文。再次是刻碑,由刻工将书法墨迹摹写到碑石之上,再行刊刻。唐宋以来,一般用双勾法影写书法墨迹于薄纸之上,再用朱砂在薄纸的背面涂满双勾线条之内的部分,然后将薄纸的背面贴压在碑石之上,使得碑石表面留下朱砂的字迹,再予刊刻。《张氏通波阡表》墨迹本最后题署:“至正乙巳春,李黼榜第二甲进士、奉训大夫、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乩杨维桢撰并书”,正是撰文阶段的产物;而正德《松江府志》所录《通波阡表》的署名涉及书丹、篆额者,则是其中第二个阶段的工作的产物。
还可以注意的是,墨迹本署“至正乙巳春”,这是撰文的时间,而府志本中这个时间不见了。因为撰文的时间和刻石的时间往往不一致,所以撰文时所署的时间在刻石时往往就删除了。当然,通常还会专门题署一行立石的时间。不清楚是原碑并无立石的时间还是正德《松江府志》在抄录碑刻文字的时候把立石的时间略去了。
总之,墨迹本和府志本即石刻本,反映的是一篇石刻文字在文本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留下的不同的痕迹。一般情况下,石刻文字在形成的不同阶段,其文字差异不会太大,但是存在较大的差异的情况其实也并不少见。《张氏通波阡表》则属于差异较大的例子,差异形成的原因,估计和杨维桢在初撰时并未掌握张麒家族准确的世系,于是又增加信息重新撰写,形成定稿,最终刻石有关。有关邹氏的一段文字,很可能是最初由张麒提供给杨维桢,后来张麒觉得有一些不妥,又建议删除了。现存墨迹只是杨维桢的初稿,并非杨维桢最后的定稿,不料保留至今,于是和最后根据定稿刻碑的石刻本构成了较大的差异。而墨迹本初稿得以保存,也便进入了杨维桢的文集;在转录过程中,又造成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从《张氏通波阡表》形成的实际情况看,府志本即石刻本在相关的记事方面,特别是有关家族世系方面是可靠的,而作为初稿的墨迹本则是不太可靠的。
四、兼论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贡献
上文的讨论,已经显示正德《松江府志》所保存的《张氏通波阡表》文本在史实方面的可靠,而这种可靠性正是来自于石刻本的优势——往往是最终改定的本子,并且经过当事人的确认。这个问题,也涉及正德《松江府志》这一类方志文献在保存石刻文献方面的突出作用,在中国古代金石学史上还有其一席之地,附此简略说明。
通常认为,中国金石学发展到宋代,达到了一个成熟期,也是一个高峰期,此后的元、明时期则是相对的衰微期,而至清代、民国,则又是一个高峰期。这种总体的认识,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介于宋、清两个高峰期之间的元、明时期,在金石学史上仍有其独有的特征和贡献。比如元代出现的《金石例》和《河朔访古记》二书,前者专言金石体例(虽然以金石文例为主),是现存金石类例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影响深远,后者则结合实地考察来讨论金石文物,独树一帜,两书可谓元代金石学史上之“双璧”,有其开创之功。又比如地方志中包括“金石”一目,在清代、民国时期蔚然成风,保存了大量的金石资料,其数量甚至要超过专门的金石著作(其中有关石刻的旧金石著作的情况,大略可以参考《石刻题跋索引》而获得总体的印象),有着很高的资料价值,而元、明时期特别是明代的地方志中便已经较多地出现记录金石资料的做法。这同样也是金石学史上需要注意的方面。正德《松江府志》正是明代方志用心收集石刻资料的典型例子。
同一种文章,在石刻中通常还会具备撰文、书丹、篆额者的署名,很多时候还会具备刻石者的署名和立石者的题名以及刻石或者立石的时间,因此往往比文集等传世文献要多出一些信息。其中书丹、篆额、刻石、立石者的题署都是和石刻的刊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反过来,我们一般也就可以通过书丹、篆额、刻石、立石者等信息推测相关文本的来源是石刻本身。粗略地统计,正德《松江府志》具备如上一些信息的文章,多达115篇,上起六朝,下迄方志编纂前不久的明成化年间,其中又尤其以元代的石刻文字居于绝大多数。据此可以推测,在正德《松江府志》编纂的时候,曾系统地收集松江一地保存的石刻资料。而元代,正是松江地方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频繁,并且正德年间相去元代只有一百多年,很多元代碑石仍然存在,足以通过查访获得,于是大量的元代碑刻文字得以收录其中,构成最主要的部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观察正德《松江府志》的时候,发现元代史料非常集中的原因所在。当然,正德《松江府志》不仅仅通过碑石收集了元代史料,还通过公文、诗文集、笔记等其他途径收集了相当可观的元代史料。其中多数是其他文献中未能保存的,综合起来,正德《松江府志》也成为元代松江研究最为重要的史料集。
最后,关于正德《松江府志》通过石刻来广泛收集地方文献并且能够比较完整地抄录石刻文字的卓越之举,还有必要补充说明一点,这种优良的做法在松江地方志的编纂中并未得到继承。崇祯《松江府志》的篇幅要比正德志多出很多,虽然也载录了很多来自石刻的文章(估计来自正德志),但是一些反映文献来源为石刻的关键信息如撰文、书丹、篆额、立石者的署名,几乎都删除了。同样拿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来说,末尾的题署“奉训大夫、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维祯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危素书,前江西等处中书省左丞周伯琦篆额”就完全删去了。这当然是有意识的举措,可见当时的方志编纂者对此的认识。从石刻文献的保存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两相比较,也便更加可以看出正德《松江府志》独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