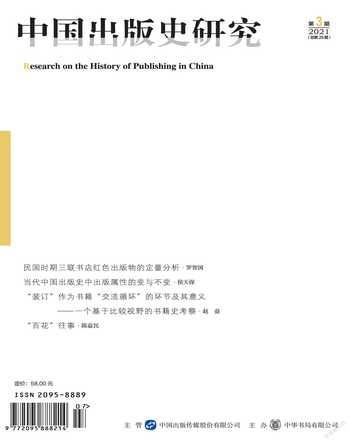民国时期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物的定量分析




【摘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与《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民国时期总书目》《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比较,可知三联书店曾大量出版传播马列主义著作和宣传共产革命的红色读物,该店是延安与国统区之间的传播媒介。这些红色出版物屡屡列名国民政府的禁书目录。三联版红色读物约占三联出版物的16.1%,三联版马列主义著作约占民国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16.2%,三联版禁书占民国时期禁书的16%左右。三联版马列著作、红色读物、违禁图书呈相互交叉的复杂关系,这反映出三联书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国 三联书店 马列著作 红色读物 定量分析
民国时期出版界有“五大书局”之说,即按照出书数量和营业额的多寡,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五家最著。三联书店包括前身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其副牌、化名书店。生活书店成立最早,时间是1932年7月1日。生活书店正式成立之前的《生活周刊》时期曾零星出书。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笼统称为三联书店。并不在其内。就出书数量而言,商务印书馆1903—1949年共出书15137种,平均每年出版约329种;中华书局1912—1949年共出书5908种,平均每年出版约160种。三联书店1932—1949年共出书2149种(另有8种为生活书店成立之前出版),平均每年出版约126种。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出书之和占到民国出书总数的17%罗智国:《近代中国书业的非凡时代(1905—1937)》,黄山书社2018年版,第98页。,可谓民国出版界的“并峙双峰”。三联书店自然不能与其鼎足而立,但有其他书局不可替代之价值,即出版过大量传播马列主义学说和宣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出版物。本文试图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曹鹤龙、李雪映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下简称《三联书店图书总目》)为主要文本进行分析,将该书目与《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民国时期总书目》《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进行比较,以寻求《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和红色出版物的特殊性,探索三联版红色读物与国民党查禁书刊之间的关系。
一
就《三联书店图书总目》本身而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三联书店共出书2157种,另出刊杂志74种。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在1948年10月才正式合并,生活书店从1932年至1949年出书约1200种。新知书店1935—1948年出書400余种。读书出版社未见可靠的统计数字,《中国出版百科全书》认为出书200多种许力以主编:《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书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588页。。但新知书店以汉口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书甚多,出书总数应该比读书出版社要多一些。
必须承认《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很不完善,2157种只能视为暂时的数据,因为根据同为三联书店自编的志书,尚有其他不同说法。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事记(1932—195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事记(1932—1951)》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各年出版书籍的数量,经整理做成表1:
由表1得出三联书店1932—1949年共出书2016种,这比2157种少141种。数字统计很难做到复式簿记般精确无误,依据《三联书店图书总目》,笔者将三联书店1949年以前的出版情况重新统计,做成表2:
再用一例说明统计之难以精确。同为三联书店自编的志书,《生活书店史稿》1939年出书数,竟出现三个不同的数字:200余种、240种、123种《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2、106、141页。。如果说2157种和2016种相差并不悬殊的话,1939年出版数字相差一半就有些离奇了。此处把1939年出书数单独拎出来,一方面因为三联书店出书达到高峰期,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其他书局都因横遭战火摧残而业务凋落,生活书店的业务却能蒸蒸日上,这是很不寻常的现象。1939年是生活书店由盛转衰的拐点,其前因后果将另文展开分析拙文《全面抗战前期生活书店的兴衰起伏探析》,未刊稿。。
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出版了多少种马列原著译作呢?需要对马列原著译作稍做界定,从最狭义的角度说,是指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文集、言论集,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据《三联书店图书总目》进行统计,马列原著译作约有86种。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全国解放前,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有530余种之多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那么,三联版马列著作约占全部马列著作的16.2%。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出版机构,这是国统区任何一家书局做不到的革命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出版了多少种红色出版物呢?根据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樊希安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就出了200种,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樊希安:《从红色出版中心到学术文化出版重镇——党领导下的三联书店革命出版历史回顾》,《中国出版》2011年第13期。。这意味着三联版红色读物占据全部红色读物的半壁江山。这个说法是否夸大呢?
这里也需要对红色出版物或红色读物进行界定,前述马列原著译作为其中之一大类,此外尚包括三大类:外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等的译作,毛周刘朱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中国作家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问题进行描述或阐释的著作。后两者亦可泛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根据《三联书店图书总目》统计,红色出版物有418种,剔除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和印次,尚有348种(详细目录已另做表格)。延安时期出版的红色读物总数约为271种《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中),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766页。,这意味着三联版红色读物的数量超过同时期延安出版的所有红色读物的数量。樊希安说的三联版红色读物200种的数字不但没有夸大,反而大大低估了。
三联版红色读物348种仍显保守,实际数量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本文进行不完全统计,并未一一考察书籍具体内容。有些著作如《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上海新文艺书店1930年版。此书正是《青春之歌》里林道静走向革命的启蒙读物。该书被禁参见王煦华、朱一冰合辑:《1927—1949年禁书(刊)史料汇编》(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看似普通,内容却宣扬马克思主义,但本文并未将此类著作囊括在内。若以348种为准,仍占新中国成立前三联版图书总数2157种的16.1%左右,说明三联版红色读物的比例高、数量大,三联书店具有极其鲜明的红色革命基因。
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作为出版业的龙头,经历了公私合营,最终在曲折发展的岁月里毅然生存下来。三联书店却历经关停并转,1951年并入人民出版社,作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1954年4月,三联书店获中央批准创建编辑室,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六个编辑组。1949—1965年、1973—1974年、1978—1985年这些年份里有冠名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所以在《三联书店图书总目》里能查到这些年份里出的书籍。1982年,人民出版社经上级批准,在内部重新成立三联书店编辑部。鉴于香港三联书店一直负责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在对外开放的大形势下,三联书店有必要恢复独立建制,以发挥其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胡绳等六人为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给文化部党组和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编委会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77页。。1986年元旦,三联书店挂牌成立,逐渐发展成专业的学术出版机构。
商務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编印各自的图书总目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以商务印书馆1981年5月同时刊印《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为最早。
中华书局在编印图书总目时间上略晚于商务印书馆,1987年编印《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但中华书局编印图书总目的种类最多,1993年出版《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91)》,2002年出版《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92—2001)》,2012年出版《中华书局百年总书目(1912—2012)》,正式出版的总目计有四部之多。
三联书店1995年推出图书总目,跟商务印书馆一样出版过两部,1995年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2008年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2007)》。顺便说明,开明书店迄今未曾公开出版图书总目笔者收集到一种小32开黄色封面的《开明书店图书目录(1926—1952)》,有86页,无编者、出版时间、地点等信息,属于非公开出版物。。跟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将1949年以前的总目单独成书不同,三联总目是合订本。不过在编纂体例上,三联总目将1949年10月之前单独成编,这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联书店图书总目》有着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图书总目做一比较,便能看清其意义与价值。首先,将三联总目与商务总目具体内容进行比较,我们只有选取同一作者、同一内容的书籍,方能确定不同书局不同版本的优劣。两家出书极少有重合者,所幸我们找到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商务印书馆的目录内容是:约翰·克里斯多夫(世界文学名著:长篇小说)Romain Rolland:Jean Christophe……傅雷译四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0页。三联书店的目录内容是:730约翰·克里斯多夫(1—4册)
(法)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上海骆驼书店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出版,4册,第1册1945年12月初版,第2册1946年12月再版,第3、4册1946年1月初版,1947年2月3版,1948年4版,连续页码2350页,32开。曹鹤龙、李雪映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0页。三联目录的优势可谓一目了然。第一,三联书店给每种图书编号,《约翰·克里斯多夫》编号为730,新中国成立以前图书编号至2157,出版总数一清二楚。这是生活书店的传统,即从1938年10月起,生活书店将全部出版物逐一编号,印刷成册分寄给各分支店使用,目的是方便各店添配书籍北京印刷学院、韬奋纪念馆编:《〈店务通讯〉排印本》(上),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第二,商务版虽然有原作者和书名的法文,但没有原作者的中文译名;三联版没有外文名,但有原作者译名。第三,商务版没有出版时间,这会对使用者造成不便。三联版不仅有初版时间,而且有再版时间;不仅有各分册的不同初版时间,而且有各分册的不同再版时间。第四,出版机构似乎不用单独标出,但三联书店的副牌书店和化名书店很多,所以“骆驼书店”这一化名书店值得交代。第五,三联版描述书籍具体形态,如“2350页,32开”,这传承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术传统,意在达到“见目如见书”的效果。
其次,将三联总目与中华总目进行比较,须选取同一作者、同一内容的书籍,我们找到郭沫若译《战争与和平》,中华书局的目录内容是:战争与和平(全三册)\[俄\]托尔斯泰著郭沫若译
1939年8月出版32开
长篇小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2页。三联书店的目录内容是:749战争与和平(1—4册)
(俄)Л.托尔斯泰著,郭沫若、高地译,上海骆驼书店1947年1月初版,1948年8月3版,4册(36+440,478,478,416+14)页,32开,有图。长篇小说。书前有郭沫若写的序,高地的译校附言、英国毛德的《论战争与和平》。书后附人名索引。高地根据原文本并参照两种英译本译出,因前半部参考了郭沫若的译本,并经郭沫若校读,故联名刊行。初版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1年12月至1942年11月出版。两下对比,可见三联目录的内容更为详细。需要说明的是,骆驼书店是生活书店战后在上海建立的第三线书店,按照周恩来指示的一、二、三线的原则创办:第一线在政治上冲锋陷阵,随时准备牺牲的;第二线偏重于理论著作和与现实政治接触较少的历史读物和社科基础读物;第三线以出版中外文艺读物、知识性读物和工具书为主《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3—234页。。三联书店出版西方文学经典名著译本,绝大部分译自苏联作品,这使三联文学出版物有着鲜明的苏俄色彩。
《三联书店图书总目》的另一个优点,在于附录有“书目索引”和“著者索引”。索引方便查找,或者更平实地说,当人们并不想完整地了解全书,但希望印证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时,就可以利用索引,按需所取从中间读起。此外,三联书店特地创制出“边码”,译者把原书的页码标在相应的地方,照样印在书上,这就是“边码”,由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发明沈昌文:《八十溯往》,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有了边码,原著索引可以照搬到汉译本中,既减少了编辑查对页码的繁重工作,又方便了读者查核原文内容。
这里将三联总目与商务、中华总目相对比,以证明三联总目的详尽可靠。三联书店出版过348种红色读物,通过目录进行粗略的统计,商务印书馆出版红色读物约为27种,中华书局可能一种都没有。从商务印书馆走出来的知名人士,如陈云、胡愈之、茅盾、郑振铎、周建人、叶圣陶等,在1932年前大都脱离了商务印书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再者商务主持人既不明确支持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不宣扬被国民政府禁抑的共产主义。在商务工作过九年的茅盾1934年曾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被查禁的书才三两本。”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为了业务上的平稳发展,商务尽量不去触犯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其出版的马列主义读物或红色出版物是少之又少的。可见三联书店在民国书业中具有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鲜明的红色特征。
三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三联版图书在整个民国书业中处于何种地位?
《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应为《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组成部分,两者在不同时期依据不同材料编纂而成。《民国时期总书目》收錄1911年至1949年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不含线装书)12万种,分为社会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律、政治(上下)、经济(上下)、军事、文化科学艺术、教育体育、中小学教材、语言文字、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上下)、外国文学、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下)、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综合性图书17种共21册,各分册中每一图书都有编号,每册后面附录索引,按书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三联书店出书2157种,占民国时期出书总数的2%弱。
查阅《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卷》,其中马列主义类收录64种,5种出自三联书店5种书目即0008《什么是马克思主义》,0020《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0023《马克思主义百年纪念》,0026《什么是列宁主义》,0036《列宁主义问题》。。查阅《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类收录233种,42种出自三联书店42种书目即0223《费尔巴哈论》,0226《反杜林论》,0232《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0233《伊里奇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0236《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0237《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0239《辩证法唯物论》(新华书店晋察冀书店1941年版,三联书店翻印过),0253《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0264《哲学选辑》,0269《新哲学研究纲要》,0272《平凡的真理》,0277《哲学译文集》,0292《辩证法唯物论》,0295《新哲学概论》,0311《大众哲学》,0312《哲学讲话》(实际与0311同),0319《哲学研究提纲》,0321《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0322《社会科学底哲学基础》,0323《新哲学大纲》,0324《哲学》,0325《辩证法唯物论》,0333《辩证法唯物论入门》,0334《思想方法论初步》,0336《辩证认识论》,0340《唯物法唯物论回答》,0346《新哲学教程》,0347《自然哲学概论》,0348《哲学初级研习提纲》,0349《哲学研习提纲》(实际与0348同),0368《科学的哲学》,0373《辩证法的逻辑》,0375《社会科学论文选集》,0378《思想方法论》,0393《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0422《社会哲学概论》,0423《科学的历史观》,0424《唯物史观讲话》(实际与0423同),0426《科学历史观教程》,0428《历史唯物论》,0433《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0439《历史唯物论浅说》。。
《民国时期总书目》这两卷中收录的马列主义著作总和约为297种,其中三联版47种,三联版马列主义著作约占民国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15.8%。巧合的是,前面统计过三联版红色读物约占三联版图书的16.1%,这两个百分比非常接近。不过这仅仅是巧合而已,因为三联版马列著作约86种,远超《民国时期总书目》的47种。这说明《民国时期总书目》并不完备。该书目编后记说“此目所收约占民国时期出书总数的90%”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综合性图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编后记,第1页。按:国家图书馆编纂新版《民国时期图书总目》,截至2021年夏已经出版五卷,计划出版十八卷。从已出版的五卷来看,收录图书数量比《民国时期总书目》增加34%。,似乎过于乐观,《民国时期总书目》主要根据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馆藏图书编制而成,那时《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尚未面世,因此《民国时期总书目》这套大型目录难免会有遗珠之憾。
我们不该对《民国时期总书目》求全责备,因为《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能够补充三联书目之不足,就检索所及,0314《方法论与思想方法论》和0338《唯物辩证法》两种为三联总目所遗漏。同理,《三联书店图书总目》不可能将所出图书一网打尽,其不完备之处亦可通过其他资料来弥补。《生活书店史稿》中有《三民主义读本》《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孙哲生先生演讲集》,以及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论文艺问题》《论新阶段》《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9—110、113、313页。等,这些书都为三联总目所遗漏。
《民国时期总书目》不仅遗漏部分图书,而且存在书名改头换面而内容完全相同的重复收录的情况。上述47种著作中,0348马特著《哲学初级研习提纲》和0349马特著《哲学研习提纲》,前者为三联书店1949年6月初版,后者为三联书店1949年7月再版。虽然书名改变,实则是同一本书。同样,0423《科学的历史观》为永田广志著、阮均石译,新知书店1937年8月出版,0424《唯物史观讲话》即为上书改名重版。47种中至少有2次以上重复,这个比例不能算低。
《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同样存在非三联版图书而予以收录的情况。三联总目1276收录《西行漫记》“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上海复社1948年9月再版,光华书店发行,381页,32开,光华丛刊之八”曹鹤龙、李雪映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1页。。光华书店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东北解放区开办的化名书店,但胡愈之主持的复社不是,既然版权页标注复社出版,就不该列入三联总目。此外,三联总目收录“立信会计丛书”和“立信商业丛书”共55种,由生活书店与潘序伦合作创办的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潘序伦担任社长,生活书店派诸祖荣担任经理,合作时间从1941年6月至抗战胜利。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可视为生活书店的副牌书店,仅限于两家合作时间段之内。因此三联总目中的编号为1436、1440、1441、1464、1465、1466、1468—1476、1488这16种应该排除在外。
限于条件,我们不能将《三联书店图书总目》所有条目都置入《民国时期总书目》一一对勘。这里仅将《三联书店图书总目》与《民国时期总书目》稍做比勘,已能看出无论是综合书目还是单一书目,都可能有遗漏,或多录重录,无法像算术一样做到毫厘不差。各家书目相互补充,相互映照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通过其他材料的佐证,为书目查漏补缺,着力做“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工作。这大概是对待书目的正确态度。
三联总目收录不全,民国总目同样不完备,在没有更确切的分析样本之前,我们只能就地取材拿来进行量化分析。三联书目在民国总目中占比不到2%,却出版过约16.2%的马列著作,这是国统区任何一家书局都未曾做到的出版壮举。
四
国统区的三联书店与边区、解放区的党内出版机构相比又如何?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边区和解放区出版过多少种书籍,是极其庞大的统计任务,目前较全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印的《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141页利用该书目进行量化统计,值得参考。。由于其极高的书目重复率,本文不将其作为量化分析的样本。如果缩小时空范围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总共出版多少种书籍?
据周文熙编制的《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中),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767页。此外,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4页认为延安自1936年至1947年先后出版了400多种书籍。两个数字相近。,延安出版图书为331种,另有补遗31种,其中红色读物经统计大约271种,其他为医学、农业技术读物等。如果这个数字可靠的话,那就意味着三联书店出版红色书籍数量超过延安出版的红色书籍数量,不过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里只将两种书目相对照,我们会有什么发现呢?
鉴于《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与《三联书店图书总目》有不少书籍相同,能够推断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概存在两条传播路线:一条是由上海传播到延安,另外一条正好相反——从延安传播到国统区。从上海到延安的传播,从两份目录里能找到吴黎平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柯柏年等翻译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张仲实翻译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伯虎翻译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等。最具代表性的是《资本论》全译本,1938年在上海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共印三千套,其中两千套从上海运到广州,谁知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这批巨著沉入海底丧失殆尽;读书出版社重新从上海发货,运到广州湾,然后辗转运到桂林。读书出版社桂林分店打包装箱,交给八路军办事处经重庆运到延安。
之所以提出上海到延安的传播路线,是因为吴黎平(吴亮平)引起我的注意。首先,他是生活书店的台柱作家、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他翻译的《反杜林论》是流傳甚广的马列经典译本,生活书店还出版过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等其他译作。其次,他在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陕北时担任毛泽东的翻译,在延安主持过中宣部编译局的工作。毛泽东1942年9月15日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凯丰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吴译《反杜林论》1937年10月由生活书店出版,1940年8月由延安抗战书店出版。此译本最早于1930年11月15日由上海江南书店初版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9页。,说明吴黎平在去延安之前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吴黎平,像三联作家群中的张仲实、艾思奇、柳湜、柯柏年等也都是如此。张仲实在1936—1938年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生活书店之前出书比较分散,张仲实担任总编辑后,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系列丛书。哲学社会科学读物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他担任总编辑以后开始注重起来的。吴黎平等人把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带到了延安,他们是马列原著的播火者。虽然延安已有张闻天、博古、陈昌浩、凯丰、张如心、陈伯达等从苏联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同样能写能译,但他们党政要务在身,并非专业翻译家,因此从上海来的这批马克思主义翻译家起到了更重要的传播作用。
抗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从延安到国统区有条传播路线,如艾思奇1937年抵达延安后,不断给读书出版社写信,要社里注意着重出版哪些书籍;有时还在延安组稿,托人带到武汉、重庆,请读书出版社出版。遇到有从延安到国统区来工作的作家,他都介绍给读书出版社,争取让他们为该社写书范用编:《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33页。。延安至国统区的传播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的传播,另一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延安的马列原著译作有《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王学文等译《政治经济学论丛》、杨作材译《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凯丰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经由生活书店等传播到国统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著作、陈昌浩《近代世界革命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从延安向国统区传播。
1940年初读书出版社各分支店的门市部销售过《新民主主义论》。抗战时期三家书店曾出版毛泽东著作,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论联合政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91页。此外,三家书店在国统区出版过的毛泽东著作另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文艺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三种。。吴黎平等翻译家奔赴延安,把马列主义翻译事业带到了边区,这很容易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位于国统区的三家书店,怎样拿到从延安来的这些马列主义著作的稿件?从三联版志书中能找到以下三处线索:
1938年初,原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励生(徐可倬)从延安带到西安一册新版《论持久战》,交给西安分店经理张锡荣。张经理阅读后立即向总店汇报,认为应以最快的方法使这本书在国统区大量出版发行,使读者能很快读到这本指导当时抗战的重要著作。他亲自交办印刷厂照原样排印,印好后即发往国统区各大城市,广大读者争先购阅《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9页。。该书的开本、排版、封面以及未切齐的毛边形式,完全和延安解放社的初版本一模一样,使人觉察不出是西安翻印本。印完之后随即毁版不留痕迹。该书遭到国民政府的查禁,原因大概是广州、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合作的关系不像之前几个月那么密切。1938年10月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遭到搜查,张经理被关押。经过邹韬奋、徐伯昕的积极营救,10天后法院判决该店因“售卖禁书”处罚棉背心100件,折合法币300元,张锡荣被保释出狱。张锡荣调任重庆总管理处,另由周名寰任西安分店经理。不到半年,1939年4月西安分店又被查封,周名寰被捕,虽经多方营救却未成功,周名寰病死狱中,成为三联书店因公殉职的烈士,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次惨痛记忆。
1940年王益在上海孤岛领导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他在总店和上海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双重领导下工作。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张继恩常到书店,把《新民主主义论》原稿带给王益,这篇长文曾发表于延安《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标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知书店在印单行本时,觉得书名太长,于是擅自做主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在今天看来是违反出版纪律的。没想到后来《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正使用这个言简意赅的书名《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编辑委员会编:《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7页。。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延安向外源源不断地传播开来。
1945年抗战胜利,读书出版社回到上海重新创业,出版的首部著作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范用编:《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这套书由博古主持,编译1936—1941年苏联《哲学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的哲学论文,最初由延安解放社1941—1943年分四册出版,本为配合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而编写,第一册《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宇宙观》,第二册《马克思主义底辩证法》,第三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论》,第四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这套书直接从延安带出来纸型,由万国钧从重庆运至上海。通过这三例可推断从延安到国统区存在着一条清晰的传播路线。
我们把1932—1949年三联版红色出版物进行分年统计(另有出版时间不明者6种,总共348种),做成表3:
通过表3,我们发现三联版红色读物有两个出版高峰期:一个是1938—1939年,另一个是1948—1949年。由于《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没有出版时间,所以暂时不能相互印证。但仍可大胆推测,第一个高峰期出现的外部原因是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武汉,国共两党合作的联络地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均设在武汉,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三家书店能夠接受从延安方面递送过来的稿件;内在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抵达延安,能够埋头从事专业的翻译工作。这个高峰期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向主要是从国统区到边区。第二个高峰期出现的原因是:生活书店最初并非党的外围出版机构,在“皖南事变”里被国民党扼杀后,与共产党关系日益密切,党组织先后派遣张友渔和胡绳来做生活书店总编辑,逐渐发展成为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一样的党的外围出版社。到解放战争时期,三家书店跟随解放军的行程,每解放一座城市,就同期在这座城市开设书店,有组织、有系统地大批量出版红色读物。第二个高峰期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向是从延安等解放区向全国范围内辐射。
通过以上两条传播路线,先后形成两次出版高峰,身处国统区的三联书店与位于边区、解放区的党内出版机构就这样有机联系在一起。三联书店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红色革命文化,成为与国民党反动文化政策相斗争的战斗力量。
五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三联书店出版这么多红色读物,自然会引起当局的关注。国民党政权怎样查禁书籍报刊,三联书店怎样规避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是需要另文讨论的问题。这里仅检索统计三联版348种红色读物中,到底哪些列入政府的禁书目录?换个说法,国民政府前前后后查禁过哪些三联版图书?
国民政府总共编印过多少禁书目录,是不易查清楚的问题。笔者所能搜集到的史料,主要有以下三种:(1)王煦华、朱一冰合辑《1927—1949年禁书(刊)史料汇编》《民国十八、十九、二十年度中央查禁各种反动书籍杂志名册》,王煦华、朱一冰合辑:《1927—1949年禁书(刊)史料汇编》(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88页;《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王煦华、朱一冰合辑:《1927—1949年禁书(刊)史料汇编》(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254页。,(2)张静庐编《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一九三六)》,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254页;《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种书刊目录(一九四一)》,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238页。,(3)张克明辑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1927.8—1937.6)》张克明辑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1927.8—1937.6)》,《出版史料》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91—156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1938.3—1945.8)》张克明辑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一),《出版史料》第四辑,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47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二),《出版史料》第五辑,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68—93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三),《出版史料》第六辑,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158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四),《出版史料》第七辑(1987年第1期),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23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五),《出版史料》第八辑(1987年第2期),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28页。、《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1946.2—1949.9)》张克明辑录:《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1946.2—1949.9)》,《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这三种目录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王煦华、朱一冰合辑的禁书目录和张静庐编的禁书目录多有重合,不过前者为手抄本,后者为排印版张静庐所收录的《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一九三六)》,即为王煦华、朱一冰辑录的《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由此可窥见张静庐作为中国出版史的开创者,编纂这套史料的重要性。;二是王煦华、朱一冰合辑的禁书目录并无出版机构,难以认定是否为三联版图书;三是书籍、报刊、传单并列,张克明辑录禁书目录里有很多用三角符号标出的原档案标明为传单的印刷品,李默整理的《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书刊补遗》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76页。多为红色报刊;四是同一种禁书目录里所列书籍有重复,所以统计总数可能比实际情况略多;五是目录在时间上不连贯,部分时间段残缺不全。张克明辑录的目录在1937年5月至1938年2月之间出现空白,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的目录资料空缺。后者可能是因为在新书业的呼吁请愿之下,自1945年10月1日起,国民党政府废止《战时新闻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禁书数量确有大幅度下降。
第一种禁书目录是王煦华、朱一冰抄录的《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和张静庐整理的《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一九三六)》。将两份目录相比对,可知国民党1929—1934年的禁书目录中有如下14种书籍,之后三联书店也出版过:1929—1931年:《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左翼小儿病》《唯物论辩证法入门》《国家与革命》《辩证法唯物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
1932年:《费尔巴哈论》《论反对派》。
1933年:《反杜林论》。
1934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论列宁》《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查禁缘由有如下几种:宣传共产主义,宣传苏俄革命,宣传马克思唯物论,宣传阶级斗争,共党刊物等。王煦华、朱一冰合辑:《1927—1949年禁书(刊)史料汇编》(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221、234—238、242—245、248—254页。以上14种禁书见于王、张两份目录,但二者皆无出版机构。这些书名在三联总目里都能查到,但并非1929—1934年出版。这批书里最早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是1937年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和1937年张仲实翻译的《费尔巴哈论》。生活书店最早的禁书是1933年12月萧参(即瞿秋白)译《高尔基代表作》和邹韬奋《韬奋漫笔》,1934年生活书店的禁书有四种,全部为文学作品张克明辑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1927.8—1937.6)》,《出版史料》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1934年生活书店禁书共四种:茅盾《残冬》、丰子恺等《劳者自歌》、郁达夫等《迟暮》、萧参译《高尔基创作选集》。。这14种禁书能够确定并非三联出版物,为何还要一一寻拣出来?原因是这些书虽被政府查禁,但三联书店照出不误,国民党的查禁政策似乎并没有起到惩戒作用。为什么呢?原来“党政对于禁书向来不在事前通告,我们根本上不知何书是在禁售之列,必须等到有宪兵或特务在门市搜去几本书才知道这些书是禁书”北京印刷学院、韬奋纪念馆编:《〈店务通讯〉排印本》(中),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54页。。这就造成了屡禁屡出、屡出屡禁、前出后禁、前禁后出的情况,所以会重复查禁同一种书。如1933年10月生活书店初版《高尔基代表作》,同年12月即以“宣扬普罗文艺”为名被查禁。1934年查禁书目里《高尔基创作选集》,备注有“即《高尔基代表作》”张克明辑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编目(1927.8—1937.6)》,《出版史料》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42页。,所以是重复被禁。
第二种禁书目录是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41年7月印发的《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种书刊目录(一九四一)》这份目录还收录于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59頁。可惜编者把“日期”一栏尽行删除。,收录于张静庐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从1938年1月至1941年6月共查禁961种,经过核对三联版有157种,占比约为16.3%。前述三联版马列主义著作约占民国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16.2%,两个数字颇为相近。
就生活书店而言,抗战全面爆发前书店开辟汉口、广州、香港三个分店,1938—1939年在全国建立20个分店,27个支店,5个办事处,3个临时营业处,9个流动供应所,曾创造了书业奇迹。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55个分支店被迫关停49个,只剩6个分店。1941年2月8日至21日,半个月内生活书店6个分店有5个被查封,只剩下重庆分店。生活书店之所以遭受重创,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出版的书籍数量分别为219种和157种,出版的红色读物分别为55种和48种,出版的红色读物数量达到了高峰,被国民党查禁的书报数量同样达到了高峰——虽然查禁的时间要略微滞后一些。
邹韬奋1940年3月30日在《全民抗战》周刊上发表公开信说:“本店出书共达910余种,其中有关思想问题者仅40种,为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为应禁者26种,在此26种中尚有10种为已由内政部审查通过得有执照者。足见本店在出版方面即偶有被认为有错误之处,亦甚微细,且早已接受纠正。本店出版的杂志,都已经过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0页。此文名为《为生活书店辟谣,敬告海内外读者及朋友们书》,内中提及的禁书26种,大概是某种宣传策略,事实绝不会如此之少。据张静庐整理的禁书目录《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种书刊目录(一九四一)》,三联版禁书有157种,其中生活书店有86种。由此进一步推断:1937—1939年是生活书店的飞速发展时期,1940—1941年初“皖南事变”是生活书店遭遇重创时期。“皖南事变”次月,邹韬奋辞去国民参政员,秘密出走香港,以示对国民党摧残文化事业的抗议。
第三种禁书目录为张克明辑录,在三种目录里最为完备。此书目像第二种张静庐《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种书刊目录(一九四一)》一样包括“书刊名称”“著译者”“出版者”“查禁理由”“日期”“查禁机关”,不过多出“送审者”一栏,在三种书目里最为详尽,最适合进行量化分析。
这份禁书目录按时间顺序,从1927年8月到1949年9月,基本按月排序。其中三联版禁书1933年2种,1934年4种,1935年3种,1936年8种,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共7种,1937年至4月有25种。全面抗战时期(1938年3月至1945年8月)的禁书总数和三联版禁书总数,可整理成表4:
根据表4,共查禁书籍1914种,其中三联版295种,占比15.4%。前述三联版马列主义著作约占民国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15.8%;据《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种书刊目录(一九四一)》,三联版出版物有157种,约占16.3%。笔者以为这三个异常接近的数字绝非偶然,由此大胆推断,民国时期三联版马列主义著作和三联版禁书都占总数的16%左右。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作为书业翘楚,两家出书之和占到民国总数的17%,我们可以断定,三联书店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红色出版物方面超越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整个国统区的民国书业中处于领军地位。
将张静庐编《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种书刊目录(一九四一)》和张克明辑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1938.3—1945.8)》进行比对,前者收录961种禁书,后者同一时间段(从1938年1月至1941年6月)收录1041种禁书,多出80种。这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张克明充分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的身份,既依据国民政府中央审查委员会档案,又依据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档案,所以资料来源比前者单纯依靠国民政府的文件要全一些;二是两份目录查禁机关都有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者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委会政治部,查禁单位多一些,禁书数字随之升高。
经过一一比对两份禁书目录在1938年1月至1941年6月的查禁情况,张静庐的禁书书目几乎全部再现于张克明的禁书书目中,且三联版书刊只有12种未见于张静庐的禁书书目,分别是《八路军的战略和战术》《大众政治学问答》《三民主义读本》《三民主义概论》《中国现代革命史》《民众画报》《列宁主义初步》《宇宙风》《抗战中的政治问题》《社会月刊》《红区时论特辑》《时事文萃》。这12种同样未能收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之中,由此可补充三联总目之不足。
以上两份禁书目录中,《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种书刊目录(一九四一)》没有一种是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1938.3—1945.8)》中商务版有8种,中华版有2种,三联版有295种。三联出版物的红色品格由此卓然可观。
按月统计张克明辑录的禁书书目,禁书最多为1941年3月的89种,三联版书籍被禁最多为1939年1月、1939年10月和1941年4月,均为15种。这组数字说明生活书店所面临的严峻局面。“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书店施行毁灭性打击。事变后的第二个月,半个月之内生活书店仅存的六个店面中成都、桂林、贵阳、昆明、曲江五个分店被查封,书刊财产被没收《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0页。。读书出版社五家店面中四个分店被封:1941年2月8日成都分社被封,2月20日昆明分社被封,2月22日贵阳分社被封,全体社员被捕;3月2日桂林分社被迫停业范用编:《战斗在白区:读书出版社(1934—194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只剩下重庆一处,新知书店总处在桂林的门市部被迫停业。数字与历史事实能够相互对应起来。
当然,并非所有数字都能得到历史的解释。在表4里,1941年查禁图书数量最多,为437种,但三联版禁书所占比例并非最大,仅51种占11.7%。占比最大的是1939年的297%,可见国民政府对付三联书店最严厉、对三联损害最大的年份是1939年而非1941年。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统计结果。
六
最后稍做总结。民国时期的三联书店出版物具有独特的红色品格。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作为民国出版界的龙头企业,对推进新文化起到重要作用。相形之下,三联书店作为小型书局,出版的红色读物之多在国统区书业中堪称中流砥柱。
三联版红色出版物包括马列主义原著译作、外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译作、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中国作家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问题进行描述或阐释的著作等。三联书店不仅出版马恩列斯原著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出版毛泽东著作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三联出版物并非全为马列主义著作,亦非全为红色读物,还包括“世界文学名著译丛”等文学读物。三联书店的出版人既有生意人的精明,又有革命家的头脑。三联书店在推动革命事业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一家有信仰的书局的文化品格。
三联书店的革命出版事业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根据张静庐和张克明两份较全的禁书目录,三联版禁书数量的占比分别约为16.3%和15.4%。三联版马列著作约占民国时期马列著作的16.2%,三联版红色出版物约占三联出版物的16.1%,这几个数字都巧合地接近于16%。或许这里面蕴含着我们未曾发现的深层历史。
数字的巧合并不意味着几份书目的重合,经过比对书目发现,三联版马列著作并未全被国民党查禁,如《资本论》从未列入上述几种禁书目录之中。禁书目录中又涵盖大量非红色出版物。追溯原因,大概抗战初期“审查标准,尚称宽泛,一般的抗战读物可以通过,惟对马列主义及中共要人作品则均在严格查禁之列”北京印刷学院、韬奋纪念馆编:《〈店务通讯〉排印本》(上),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页。,国民党查禁对象除了马列原著译作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外,还有抗战救亡读物、国际问题读本、文艺作品以及通俗连环画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抗战的继续和‘摩擦’的未见稍减,查禁书报问题也随之加厉了。范围扩大到关于陕北,关于八路军,关于游击战,以至关于社会科学,新哲学,关于苏联的书报”北京印刷学院、韬奋纪念館编:《〈店务通讯〉排印本》(中),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页。。国民党实践中无法查禁所有马列著作,只能查禁其他“有碍观瞻”的红色出版物,可谓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为三联书店反反复复展开反查禁、反围剿、反封锁、反压迫的革命出版事业创造条件。
三联书店中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自创办伊始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但生活书店最初只是一家政治“左”倾的小型书局,总编辑张仲实奔赴延安后使生活书店与延安产生直接联系,由此形成了国统区与边区的双向文化交流。“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逐渐向党组织靠拢,遵照周恩来指示,书店按照三线原则进行秘密斗争。到解放战争后期,在香港中共文委领导下,三店合并联手统战,三联书店达到了历史上的出版高峰,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精神食粮,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基础。
三联书店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加入文化统一战线,与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机关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成功组织了国统区的文化抗战,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到解放区传播文化星火,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羅智国,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d” Publications by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Luo ZhiguoAbstract:A check of the Overall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32-1994) against the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7-1949), the Overall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the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12-1949), the Overall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1912-1949), and the Condensed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in the Yanan Period (1937-1948) informs us of the fact that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had published a large amount of “red” books on spreading the MarxistLeninist works and promoting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that the company acted as a medium fo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Yanan and the areas of China controlled by the Kuomintang (KMT). These red publications were repeatedly put onto the list of prohibited books by the KMT government. Red publications by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ccounted for 16.1 percent of its total publications, the MarxistLeninist works published by the company took up a share of approximately 16.2 percent in such works off the pres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and about 16 percent of the books prohibited in this era were published by the company. The MarxistLeninist works, red publications, and prohibited books published by t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featured intertwine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which shows that the compan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preading Marxism in China.
Keywords:Republic of China,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MarxistLeninist works, red publications, quantitativ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