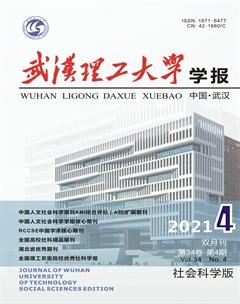新时代美德教育的困境与重建
摘 要: 新时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存在多重困境,为此必须重构美德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实践路径,从根本上优化改进美德教育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和教学方式。这需要逻辑上解决美德教育“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核心问题。美德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需要寻找新的价值引领、目标定位与使命担当,必须将真正触及灵魂深处的道德实践引入日常生活之中,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做出不负新时代的选择。
关键词: 美德伦理; 美德教育; 道德重建
中图分类号: G410; B8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4.018
美德是一个人在道德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表现为一种相对固定的、习惯性的行为倾向和行动模式。美德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内容,其目的就是要培养每个公民的积极的、优秀的、向善的道德品格。大学生的美德教育对于塑造和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关涉到我们培养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公民和接班人的问题。然而,当代高校的大学生美德教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存在多重困境,比如理想教育与现实社会的分离、美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错位、道德灌输方式与学生主体性的矛盾、世俗生活与崇高美德之间的张力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建构美德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实践路径,从根本上优化改进美德教育的基本目标、主要内容和教学方式,着眼于全面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优秀道德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基础。
一、 美德教育是什么?
美德教育何以可能?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美德教育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的哲学家。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率先发起了关于美德本质的争论。他认为从前的哲学家都只是解决自然界的哲学问题,没有思考关于人的问题。通过与不同的人展开激烈的争辩,苏格拉底提出了关于美德的非常重要的论断:“美德即知识”、“美德可教”、“无人自愿作恶”等重要哲学观点[1]。美德不仅在客观上存在,而且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拥有了美德就等于拥有了知识,一个真正有美德的人都不会去作恶,那些作恶的人都不是自愿的,而是缺少美德的知识。苏格拉底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些人根本就不认同他关于“美德即知识”的观点,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美德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
那么,美德究竟是什么?美德的英文是virtue,它在古希腊哲学中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最初含义是指事物所拥有的功能或用处,例如耳朵的功能/美德是听,眼睛的功能/美德是看,笔的功能/美德是写字,书的功能/美德是供人阅读,也就是说一物有一物的功能,一物有一物的美德。如果事物的功能就是美德,那么人的美德是什么?事物的功能是它对人的好处、用处,人是否也存在这种类似的功能呢?很显然,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别的事物的功能,而是以其自身为目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美德是一种心灵功能的完满实现,这种功能能够使人具备卓越的品质,做任何事情都能在过度与不及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例如勇敢就是鲁莽和怯懦之间的中道,节制就是放荡和不敏感之间的中道,友谊是谄媚和愠怒之间的中道。按照儒家的观点,具有美德的人就是道德上的谦谦君子,相反,具有恶德的人就是道德上的无耻小人。在现代伦理学中,美德已经不再是一种功能性的概念了,而是一种内涵具体的伦理概念,专指人在实践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秀道德品质和人格特征。
回到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争论,一个人的道德美德如何能够成为知识,这是哲学史上争论不已的话题。美德如果是知识,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知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借助于知识论的哲学分析。按照柏拉图的知识论观点,人类的知识可以基本上分为两大类:经验知识和形而上学的知识。前者是通过感官经验所获得的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例如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医学知识,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农业知识;后者是通过理性思辨所获得关于非经验世界的知识,例如哲学家对真、善、美的思索,对于存在、本体、价值的探讨。很显然,柏拉图的这种二分法基于他对世界的理解,他把世界分为看得见的经验世界和看不见的超验世界[2]。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完全拒斥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不可检验的,因此应该统统从知识的地盘中清理出去。将知识的范围限定在经验知识,并以科学实验的方式来进行证实,这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论谋划。无可否认,知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认知表达,而不是客观世界本身。据此,美德属于客观的事物,它是人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某种存在品质,而不是关于这种品质的知识,所以,很明显美德不是知识,关于美德的认知表达和理论描述才是知识。
如果美德不是知识,那么是否意味着“美德即知识”这提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它实际上在促使我们思考:关于美德我们能够拥有何种知识?这种知识是否可以传授?美德教育是否只是一种纯知识教育?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回归到对道德本质的理解。现代伦理学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难题,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问题:即如何从事实性的陈述(“是”)中推導出应然性的道德判断(“应该”),它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现代人所深陷其中的事实与价值的分裂(the dichotomy of fact and value)。这种分裂意味着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世界与作为主观存在的价值世界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客观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番模样,而主观世界所呈现的则是另外一副模样。作为道德性的“应然”,与作为事实性的“实然”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这是现代伦理学所面临的一种知识论困境,在事实性的自然科学面前,伦理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身份地位[3]。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道德价值、道德判断只不过是人类心理、情感和意志的表达,无法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经验知识,因而都是“非科学”的内容,应该同形而上学一样从科学的地盘上清理出去。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各个学科专业加剧分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彼此独立,曾经的“一致性让位于分裂”[4]。
美德很显然是一种道德价值,能够在道德上对社会产生某种利益与好处,属于德性的范畴。这样,美德教育就属于价值观教育,它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种知识型教育,这种教育的重点不在于传递关于美德的知识,而在于如何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美德教育,特别是它在个体层面所要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实都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美德。很多思想政治工作者、德育工作者没有真正弄明白德育的本质,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困惑和误解。他们要么是将它等同于一般的知识型教育来进行灌输,要么是将它当作传统的道德教化来进行说教,失去了它本来的生动内涵与实践价值。这些未经反省的做法,都没有抓住美德教育的真正本质与内核。
二、 美德教育为什么?
美德教育为了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二个逻辑问题。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不同类型的教育其育人的功能有很大的区别。作为教育,我们强调的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一个优秀的人才需要多方面的培养,而不只是某一个方面。很显然,美德教育是道德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一个人的健全人格,帮助学生建立卓越的道德品质,这与培养智力的知识型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道德品质的培养对个人发展来说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要排在智力、体育和美育之前的主要原因。美德教育重在教化人心,促人向善;美育重在美化心灵,使人爱美。然而,美德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处于一个相对边缘、被遮蔽的状态,它的真实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用哲学家的话说是一种“虚假存在状态”[5]。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真正搞清楚美德教育的本质和目标,更多的是从规范伦理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思考问题;更多地强调了要求学生“做好事”(do good things),而不是重在要求学生“做好人”(be a good man)。
从美德伦理的角度来分析,“做好人”与“做好事”的德育模式存在根本的区别。首先,“做好人”重在培养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做好事”重在建立人对于外在道德规范的纪律约束意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一样,都是为了维护现代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着重在于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行动,不关注行动者内在的动机与价值追求,这属于明显的外在论、后果论。它要求我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遵守已经制定的“条条框框”和制度规矩,例如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不准随地吐痰、遵守红绿灯交通规则等。片面地强调行动的后果约束、行为约束和规矩意识,这往往忽略了人的内在气质、品格与美德[6]。美德伦理要求人们发自内心地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而不是被外在的规则牵着鼻子走。当一个人自觉地追求美德生活,他实际上就是在追求一种合乎自然的生活秩序,具有较高的“合目的性”。例如,一个节制的人就是有美德的,他并非是在父母和他人的强迫下过这种生活,而是一种自我立法、自我约束,发自内心地认为有节制的生活本身就是好的、值得欲求的。一个人完全可以过一个花天酒地、浪荡公子的生活,但当他一旦决定了要节制,就意味着“美德意识”的觉醒。
其次,“做好事”在道德上体现为一种可公度的规范性要求,而“做好人”则是一种不可公度的美德要求。“好事”之为“好”,必然有其好的标准。规范伦理学正是要提供这样一条关于“好”的标准,例如,功利主义者认为那些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事情就是好事情,利己主义者认为那些能够促进自我利益的事情就是好事情,利他主义者认为那些能够促进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事情才是好事情。这些好事情的标准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规范,而社会制定出来的规则是普遍化的、可公度的,所有人都应当一视同仁,在其所约束的范围内不允许有例外,例如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红绿灯、系安全带的规则。相反,美德要求人们去“做好人”,如谨守良心、荣誉感、爱国、团结等,这些都是无法公度的心灵内在品质,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外在行为标准。美德的行为标准高于一般性的道德底线标准,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就是一个道德上及格的人,但还不能算是有美德的人;只有当他乐于助人时,才能说是具有友善的美德。一个人心地善良,在人们的眼中是一个好人,但也可能由于某种意外或差错,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没有“做好事”,但仍然称得上是一个“好人”。
最后,做好事着重于对人的道德行为的理性计算,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制定出来的道德规则,而做好人则着重于对人的道德品格、情感、心理和意志的培养和认同,看它是否符合人们从良心上肯定、赞美的人格形象。做一个好人当然要体现在行为上,没有做好事的具体行动无法证明一个人是好人;但它又不仅仅体现为行为,还包括行动者的主观内心状态,对道德行动的认知、情感与意志,以及对他人与社会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做了哪些好事,做了几年好事,这些是直观上可以计算的,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常常采用这些可量化的方式来评价学生,并作为道德奖章的主要判断依据。如果纯粹追求做好事所获得的奖励,那么它就会演变成追名逐利的行为,类似于功利主义的利益计算,看看从这件好事中能够得到哪些回报与好处,例如想获得三好学生、道德楷模、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在康德看来,为了外在的利益而去做好事,不能算是有道德的人,因为它是受到利益欲望的驱使才去做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愿行为,真正的道德行为应该是建立自由意志的基础上,由行動者来自我立法、自由完成的。考虑社会环境、舆论媒体的压力,计算个人利益的得失,屈从于外在的规则标准,而不是听从内在良心的呼唤,这种行为只能算是受道德原则支配的欲望而已,而不是内在自我完善的独立追求[7]。
做好事与做好人的区别实际上来自于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对道德本质理解的根本差异。一般来说,规范伦理学以道德行动为中心,致力于制定出普遍化的道德原则或规则;而美德伦理学以行动者为中心,致力于探究怎样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怎样过一个幸福的生活[8]。前者强调的是做事,即那些符合普遍道德规则的事;后者强调的是做人,即要做一个道德上优秀的、卓越的、圆满的人。因此,美德教育是一种“树人”、“育人”、“成人”的教育,要让一个人身上的那种“成人之美”激发出来、锻造出来,让人性中善良的、美好的道德品质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因素,致力于成为一个“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9]。
当然,我们在强调做好事与做好人之间的差别的同时,不应该忽略二者之间的联系。一个抽象的“好人”是难以理解的,他必须通过某种行为、语言、情感来表达自己,来向人们展示一个好人的形象。内在的高尚品质离不开外在的行为表现,通过道德行为来证明美德的力量而不是脆弱。一个有美德的人,其言行是一致的,他会经常用美德的要求来反省自身的行为;而一个言行不一致,甚至伪善的人,他的行为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却因其缺少美德品质而减损了其自身的价值。
三、 美德教育如何做?
美德教育如何做?它在当代如何复兴?这是美德教育的第三个逻辑问题。不少学者指出,当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存在很多问题,面临着很多困境,特别是传统美德教育普遍处于衰落的状态下[10]。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美德教育正是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要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反思与重建。
首先,新时代的美德教育必须进行价值转换。新时代的美德教育必须着眼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如何进行价值转换,这是新时代面临的一個重要道德课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中的很多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已经证明不再适用,或者被抛弃了,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契约关系,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工作与生活,寻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必须在现代社会中进行价值重塑,注入新的思想内容,转换成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践场景,并为当代人所理解的美德价值,才能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那种生搬硬套传统,发起狂热的“读经”“诵经”运动,将经典止于言谈,却不付诸实际行动,这种方式或许能够提高学生的国学修养,却只能“轰动一时”,却不能持存一世。当人们只是将它作为一种诵读的内容,而无内心的敬畏之心、仁爱之情时,它只不过就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与符号而已。美德教育不是要回归故纸堆,而是要投身于新时代的伟大事业建设之中。
其次,新时代的美德教育必须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青少年的成长与其环境息息相关,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健全的道德人格。特别是那些处于成长期、叛逆期的青少年,他们的价值观还未定型,很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很难有国家、集体、家庭等宏大概念,更多的是个性、自我、情感、游戏等生活化概念,个体化的自由生活占据了中心位置,他们喜欢从个人爱好、情感态度来考虑自身行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去干,很少考虑行为对自身和他人的影响,甚至根本不考虑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当代大学生中有些“游戏一族”“怪诞一族”在游戏中虚度青春、消耗生命,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任何道德品质、美德人格、心灵精神的意识,缺少生命本应具有的理想信念,属于精神上的“缺钙”[11]。因此,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风气和学术氛围,让他们在积极向上的教育环境中茁壮成长,就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新时代的美德教育必须以育人为主。美德教育的重点是“育”而不是“教”,它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型教育,不是要学生记住哪些知识点,理解哪些重点概念,而是要让学生真正认识到道德的作用与价值,认识到做好人是值得的,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令人赞赏的。很多德育工作者在这方面常常犯错,要么是采取知识型教育的灌输方式,要么是采用政治课的价值灌输方式,完全丧失了道德教育的生动性、活泼性与魅力性。美德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教化,它需要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环境育人模式,更需要雷锋、白求恩那样的榜样和模范人物的激励和引领作用,而不是在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内讲解有限的道德知识。美德虽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道德要求,但它一定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一定要让大学生明白美德自身的内在价值,明白选择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是值得的、是可欲的,是构成善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让他们自觉地追求和培养个人的优良品德。无论是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的孔子、孟子,都承认美德内在价值的独立性。柏拉图说,一个正义的人无论是遭遇贫困、疾病还是不幸,最终都将证明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外在的不幸只会增添他人性的光辉[12]。孔子也由衷地赞叹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
最后,新时代的美德教育重在培养美德情感。美德教育不是知识教育,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也就是要培养每个公民的心中的道德感和道德力量,使得人们能够自觉自愿地按照美德的要求来行动。道德感包括内在的良心、诚实、正义感,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符合美德要求的事情,更容易找到美德的方向,获得道德正能量和价值感。情感教育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缺席的遮蔽状态,伦理学研究与教学的主流模式是探究道德原则、规范及其应用,考察道德判断、道德推理和道德论证,这些抽象的道德理论毕竟离鲜活的道德实践还有一定的距离。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着道德冷漠、道德滑坡、道德堕落的现象,很多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之后演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同情之心、关怀之心、敬爱之心,以至于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道德空气变得如同雾霾一般肮脏,令人窒息。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在教育中过度地强调了知识理性,而忽略了情感、意志的培养,没有把握美德思维的深刻性,美德情感的强度和美德意志的坚定性和持久性[13]。真正的美德教育是知、情、意的统一,是对道德美德的有限知识,对美德情感的涵育培养,对美德意志的执着追求。
总之,美德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选择成为有美德的人意味着它将参与人的生存论建构,意味着它将在各个方面重塑我们的道德人格和内在心灵。一个真正有美德的人将无惧于外在环境的压力与名利的引诱,将始终以美德作为人生的第一价值追求。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需要寻找新的价值引领、目标定位与使命担当,需要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做出不负新时代的选择,它在根本上需要直指人的心灵与灵魂,让每个青年学子发自内心地产生对美德的价值感、意义感与崇敬感。美德教育不是枯燥无味的道德说教,也不是机械呆板的理论灌输,更不是什么迷惑人心的心灵鸡汤。真正的美德教育应当触及人的灵魂深处,在一个道德破碎、道德虚无的世界中抚慰人的内在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撕碎那些道德实践中的种种“虚假存在”,重建更具有本体论、生存论意义的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参考文献]
[1]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42.
[2] 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2.
[3] 万俊人.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2008(5):225-235.
[4] 茱莉·A.罗宾.现代大学形成:知识变革与道德的边缘化[M].尚九玉,译.贵阳:贵州出版社,2004:2.
[5] 张鲁宁,杨海燕.美德教育“真实缺失”与“假性存在”的成因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07(7-8):89-94.
[6] 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Ethics[M].Trans.Louis Infield,Indianapolis 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30:71.
[7] Rawls,J.A Theory of Justice[M].Ma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192.
[8] Rosalind Hursthouse.On Virtue Eth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5.
[9] 夏明月.美德倫理的规范性来源[J].哲学动态,2014(3):70-75.
[10]万俊人.美德伦理如何复兴?[J].求是学刊,2017(1):44-49.
[11]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5.
[12]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61.
[13]詹世友,汤清岚.美德的内在结构及其塑造途径[J].道德与文明,200(3):15-20.
(责任编辑 文 格)
Dilemma in Virtue Education of the New Era and Its Reconstruction
LI Hong-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Hunan,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ultiple difficulties in the moral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virtue education,and to optimize the basic objectives,main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virtue education.This needs to logically solve the three core problems of virtue education: “what”,“why” and “how”.Virtue is a way of human existence.The moral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needs to find new value guidance,target orientation and mission.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moral practice deeply into the daily life and make the right choice on the road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virtue ethics; virtue education; moral re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21-03-12
作者简介:李红文(1982-),男,湖北麻城人,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6325);2021年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项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稀缺卫生资源分配的伦理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