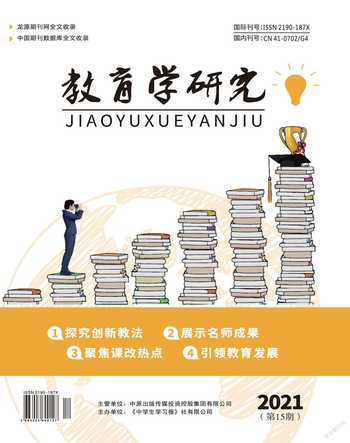建筑与装饰的“藕断丝连”
尚书
摘要: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蓬勃发展,“装饰”一词似乎成为了建筑设计界十分敏感的词汇,净化、剥离甚至坚决反对装饰成为了现代主义设计师鲜明的旗帜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反思这个被迅速均质化的城市,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装饰似乎又被人们重新审视。本文旨在从装饰的角度出发,探讨20世纪建筑设计发展与装饰之间的关系,同时站在当代的视角,剖析装饰的“对与错”。
关键词:装饰,现代主义,建筑设计
一、设计师们与装饰的“纠缠”
从装饰的角度看20世纪的建筑发展,并不是单纯从形式出发或者片面地看待装饰,而是由浅及深去回望那个时代的建筑设计思想发展脉络,去理解设计与装饰的关系,去剖析装饰的存在价值以及它自身的“对与错”。
“我跟你讲,将来有一天,关在由宫廷墙纸设计师舒尔策或凡·德·维尔德教授布置的牢房里会被视为加刑。”[1]79
1.1、 觉醒:“无用附加性”装饰的剥离
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之后,工业产品上浮夸甚至带有强制附加性的装饰,以及机械化生产带来的设计水准、产品质量、审美层次低下等种种问题诱发了以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为首的工艺美术运动。作为工艺美术运动主要实践人物的莫里斯,从建筑设计、家具设计、平面设计等多领域进行探索,将装饰从华而不实的“无用附加性”中解放出来,朝着实用、美观、大众的方向发展。至此,现代设计开始萌芽,而设计师与装饰之间的“纠缠”也拉开了帷幕。
1.2、 尝试:净化装饰的开始
新艺术运动作为前者的发展,以法国为起点迅速席卷了欧洲大陸,并且逐步分化出维也纳“分离派”、德国“青年风格”、英国“格拉斯哥学派”等不同派别。早期的新艺术运动将自然曲线发挥到了极致,设计师们开始不断探索新材料与新技术带来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例如赫克托·吉马德细致入微的巴黎自然风格地铁口系列设计;维克多·霍塔的优美自然的铁艺栏杆造型。但法国、比利时等国的新艺术运动仍旧具有一定的矫饰倾向。维也纳“分离派”与德国“青年风格”作为新艺术运动的分支,从表现形式上与新艺术运动却有很大差别。他们将目光转到直线与几何,如同“分离派”的名称一样,号称要与学院派决裂。水平与垂直线条构成了建筑的外表,装饰作为点缀功能附着于建筑物上。英国“格拉斯哥学派”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查尔斯·麦金托什为首的“格拉斯哥四人小组”提倡简单的线条与几何构成,并且将黑白灰作为建筑的主体色调,而装饰的附加作用似乎已经微乎其微。
维也纳“分离派”、德国“青年风格”与英国“格拉斯哥学派”从建筑的外观上扫除法国、比利时等国新艺术运动带来的矫饰倾向,颇具影响力,并且成为欧洲建筑设计探索中净化装饰的重要一环。
1.3、 上升:对装饰“罪恶”的声讨
1908年,阿道夫·卢斯发表《装饰与罪恶》,声讨装饰的种种“罪行”,并迅速引起极大的反响。卢斯对于装饰的极端反对态度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现代设计师的支持。“监狱里百分之八十的犯人都有刺青。监狱外那些有刺青的人,不是潜在的罪犯就是堕落的贵族。如果一个有刺青的人死的时候还是自由之身,那么他在未来得及实施谋杀前就死去了”。20世纪初,欧洲各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大工业生产方式叩开经济的闸门,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掩盖了手工艺的落寞。“做装饰的工人得工作二十个小时以获得一个现代工人工作八小时的收入。……今天一半的工作都贡献给了装饰制作。”[1]69-70
卢斯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对装饰进行批判,他认为装饰浪费人力、物力与材料,是对国民经济以及生产资料的无端消耗。关于卢斯观点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会在下文中讨论,在此我们只需看到卢斯为去除装饰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4、延伸:大西洋彼岸的“功能之花”
19世纪末,大火灾过后重建的芝加哥成为了高层建筑的故乡。路易斯·沙利文提出“形式追随功能”。这一创造性的主张阐明了功能的主导地位与装饰的从属地位,从而摆正了建筑功能与装饰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沙利文的建筑外部十分简洁,装饰非常有限但相当精致,他避免那个时期美国盛行的历史折衷主义风格,他的装饰母体采取自然风格纹样,舍弃历史装饰符号。
沙利文最大的贡献是奠定了高层建筑的结构与形式基础,他采用钢结构承力来取代传统的墙承力,为未来摩天大楼的发展指引了方向。王受之先生在《世界现代建筑史》一书中谈到:“沙利文一方面承认了古典的、历史的重要性,但却从进化论的理论角度反对简单的抄袭和模仿,主张在传统继承上的发展和变化,为新时代设计新建筑。正因如此,他才会在现代建筑史上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2]
1.5、剔除:狂飙突进的现代主义
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包豪斯的建立,现代主义建筑以及现代设计思想开始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正统的现代主义思想以实用功能和经济性作为建筑设计的出发点,在传统建筑材料昂贵和施工周期冗长的情况下,面向工业化大生产,系统性地引进工业技术和标准化设计,并且力图预制化,同时注重建筑形式的真实性,主张与历史风格决裂,提倡简洁,反对装饰,倡导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风格。密斯的“少就是多”,柯布西耶的“新建筑五点”,现代主义建筑已然将装饰完全剔除。巴塞罗那德国馆、萨伏伊别墅等一系列现代建筑的里程碑显示出来的简单纯粹的功能,极其理性的态度都表明现代主义设计师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二战结束后,经济得以恢复,科技得以进步,加之格罗皮乌斯、密斯等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移居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开始以突进似的速度向全世界扩展。战前的现代主义到战后发展成为“国际主义风格”,并且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自此,“几何框架”与“玻璃盒子”迅速占领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而装饰似乎也彻底被人们所抛弃。
1.6、反思:人情味去了哪里
1972年7月15日,美国圣路易的低收入住宅群“普鲁蒂-艾戈”被拆毁,这一时刻被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称之为“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死亡,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安藤忠雄先生在《安藤忠雄论建筑》一书中谈到:“20世纪,伴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国际主义建筑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建筑舞台,运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的钢铁、玻璃、混凝土材料开发出了经济合理甚至达到良好物理性能的标准化建筑……无视建筑物所在地的特殊性,使方盒子建筑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蔓延,使人们的生活空间千篇一律、单调乏味……?”[3]
20世纪40-70年代,世界各地被“方盒子”迅速均质化,在纽约看到的一栋建筑,它同样可以出现在北京,出现在東京,出现在柏林或者是任何适合城市发展的地方。民族性的、地域性的风格特征淹没在了钢铁与玻璃之下。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这个被同质化的城市,曾经的人情味去了哪里?随之出现了一些建筑家试图来改变这种现状,设计界特别是建筑设计,的确需要一场革新来打破国际主义风格的垄断,而后现代主义也就在这样的呼声中登上建筑历史的舞台。
后现代主义设计师罗伯特·文丘里提出“少就是厌烦”的观点,以此来挑战密斯的“少就是多”。文丘里主张通过历史建筑符号来丰富建筑形式,并借鉴了美国好莱坞等诸多通俗文化,他强调建筑应该走戏谑、轻松的装饰路线,其代表作“文丘里母亲之宅”中的山花开口部分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共同抵制世界的迅速均质化,人们开始关注建筑的民族性、地域性、人情性,而作为实现这些特性的形式手段之一就是装饰。国际主义风格逐渐式微,建筑设计也在多元并存的趋势下不断发展。
二、从当代视角再论装饰的“对与错”
其实卢斯反对的是无用附加的、毫无实际功能意义的装饰,但是其对于装饰的极端态度也一直饱受争议。卢斯观点的进步性在于他看到过度甚至是矫揉造作的装饰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并且为现代主义的到来打下了理论基础,其局限性在于直接否认装饰的一切存在价值,这种过于绝对的观点甚至把装饰归为“罪恶”,站在当代的角度来看,这种极端的态度显然对装饰有失公允。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而装饰恰好是实现这一期望的手段之一。事物的发展是螺旋上升的。看似装饰是在历经了一个世纪之后又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但是这次回归同曾经相比显然是具有质的飞跃的。曾经的建筑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或为了宗教、政治而装饰,总是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久而久之,就是为了装饰而装饰。而在经历了国际主义风格之后,人们对于装饰的认知有了极大的改变。
如后现代主义建筑通过历史符号的戏谑性来构成建筑的形式,历史符号往往可以唤起人们很多追思与情怀,而戏谑的历史符号又不至陷入传统装饰的桎梏中,进而使建筑具有人情味的同时使装饰获得良好的平衡性。
三、装饰的“中庸之道”
现代主义盛于理性,同样也衰于理性。物极必反,现代主义的极端理性最终导致世界的均质化,建筑变得单调乏味,没有人情味。反推过来,当年装饰走向衰落起因也是过度的矫饰。如果装饰能在复杂与空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那么装饰势必可以发挥其最大的优势,为设计的丰富多彩添上绚丽的一笔。
当今社会存在很多这样的现象,某些设计师在设计私人住宅的内部空间时,常打着“现代简约”的名号使用一种“极端极简”的风格,空间单调到不知所措的地步。这种空间极其纯粹,如果作为艺术空间或者展示空间而言还是很有几分韵味,但是作为私人住宅显然不合适。
装饰一旦失去控制走向繁杂冗余,势必会造成视觉污染,浪费生产资料,消耗物力财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尚未形成一个对于设计有成熟认知的社会语境。甚至一些从事艺术设计的人员对设计、装饰并无深刻的理解,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低下,同时,为了这种低级审美趣味,大量急功近利的设计被制造出来,进一步对大众的审美形成错误的导向。[4]
装饰的存在一定是要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服务于人的,除此之外的装饰都会显得复杂且啰嗦,这就是装饰的“中庸之道”。
斯蒂芬·R·凯勒特在《生命的栖居—设计并理解人与自然的联系》一书中,关于“积极环境影响设计理论”中谈到了“象征自然体验设计”。凯勒特认为人的本性是亲近于自然的,因此在设计中融入自然元素的装饰对于人的身心健康是大有益处的。他认为装饰不能完全没有关联或是一模一样的重复,一定是有一定规律和韵律来表现,极为精致且不规则,连贯且有组织,并且能够吸引人去感受他们的整体美。凯勒特对于装饰的态度是他以自然形态对于人的心理及健康所带来的益处为出发点,这种装饰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他阐明了装饰因何而生,又该以何种方式去呈现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装饰的存在一定是有意义的,它是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设计以人为本,装饰也是同理。无用附加性的、不伦不类的装饰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真正的装饰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要么使人观赏起来心情更加愉悦,要么可以成为产品的附加值。如果一件物品去除装饰反而更加引人注目,那装饰将毫无意义。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各异,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追求美的脚步永远不会停下,平衡装饰与美的关系对于设计师来说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奥地利)阿道夫·卢斯.装饰与罪恶:尽管如此1900-1930[M].熊庠楠,等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2] 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02-106.
[3] (日)安藤忠雄.安藤忠雄论建筑[M].白林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20-21.
[4] (美)斯蒂芬·R·凯勒特.生命的栖居—设计并理解人与自然的联系[M].朱强,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5] 徐辉.对《装饰即罪恶》的再解读[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4(03):1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