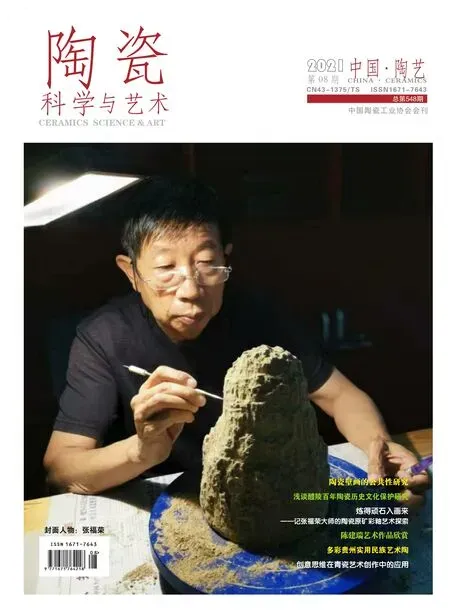浅谈“合樽壶”创作理念与人文情怀
刘孟芳
一、引言
当宜兴人发现第一块可以磨成粉制作紫砂壶的石头开始,就注定了紫砂的不平凡。正可谓是“千锤万击出深山”。将黄龙山中的石矿开采出来,经过匠人们精湛的锻炼手法,将生硬的石头变成温软的泥巴。从宋朝开始,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紫砂壶艺经久不衰。众多艺术门类在时间长河中湮没绝迹,如同大浪淘沙一般,经过一代代紫砂匠人们的千淘万漉,才成就了当今的紫砂。紫砂壶,从第一把“供春”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勤劳的紫砂匠人的不断摸索实践中,将紫砂创作推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高度。因为紫砂泥料的可塑性,挖掘出了紫砂无限的创作空间。
二、“合樽壶”的创作理念
在剖析紫砂壶的深层次内涵时,就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书法、茶艺、金石等等。紫砂器物从宋朝时开始,仅仅是作为一种盛水的器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加上每个时代的匠人手法的变更,也结合了每个时代的审美情趣,紫砂壶的文化层次逐渐被抬高。从拙朴的泥巴登堂入室,可以与雍容华丽的瓷器不相伯仲,成为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艺术的一朵奇葩。在此期间,从苏东坡的“东坡提梁”、“曼生十八式”到近代壶艺泰斗顾景大师与吴湖帆等人合作的景舟石瓢,再到当代的“亚明四方”、“曲壶”,都是文人墨客参与其中,与紫砂匠人探讨,对紫砂壶的造型设计、文化内涵重新定义。紫砂壶在宋朝发端,盛行在明清。明清时期百家争鸣,这个时间段的经典器型数不胜数:“吴经提梁”、“大亨掇只”、“德钟”、“鱼化龙”、“寿珍掇球”等等,到民国时期,更加繁荣。建国后,我国的文化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人所制的这把“合樽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设计出来的。樽,本指古代盛酒美器,有“合樽促坐”一词,意思就是与志同道合之友人,执壶对饮,其乐融融之意。“合樽壶”作品属于光素器范畴,身形改良于传统器型匏尊,流把、盖钮优雅隽秀,与传统的匏尊相比,添加了新的韵味。两相结合,顾取名“合樽”,饮酒可,饮茶亦可,皆是人生之乐趣。尤其是与友人执壶共饮,推杯换盏之间,笑谈人生。
三、“合樽壶”的人文情怀
将喝茶的紫砂壶与饮酒的樽相结合,既有区分点又有相同点。区分点很多,如:在材质方面、功能方面。但相同点都是与志同道合之友人共饮,正所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君子交,如入芳兰之室,就如李太白所写的一样: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一种君子之交的洒脱。“合樽壶”壶将中国传统的茶文化与酒文化在紫砂的载体上展现,一方面展现了饮茶的情怀,或有苏轼的“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的淡淡哀思,或有陆游的“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的时光易老的伤怀,更有张可久的“春水煎茶”的悠闲淡雅;另一方面,展现了饮酒的情怀,或有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豁达,或有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不羁,更有范仲淹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暗倾诉。茶与酒,两种不一样的液体,被历代文人雅士、走夫贩卒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定义。“合樽壶”是将茶的文雅静气与酒的醇香烈气相结合,既有理性,又有烟火。人生百态,如茶之甘苦,齿留香,亦如酒之入喉,性烈,慰心宽。
四、结语
紫砂壶这门传统的艺术,在数千年的传承中如陈年佳酿,愈发旺盛。历代紫砂匠人呕心沥血,在紫砂艺术这片浩瀚的海洋中纵横驰骋,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了当下成熟的紫砂壶器型、制壶技巧、泥料选择、窑温把控等等规则。我们继承先辈们流传下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更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新,开拓进取,将紫砂艺术发扬光大,努力推到更高的文化层次。“合樽壶”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是对传统器型的改良,加入本人对紫砂器物的理解,融入当下的审美情趣,力求用极简的线条勾勒出紫砂壶的韵律。经过本人反复尝试,最终成型,呈现世人,分享紫砂魅力。